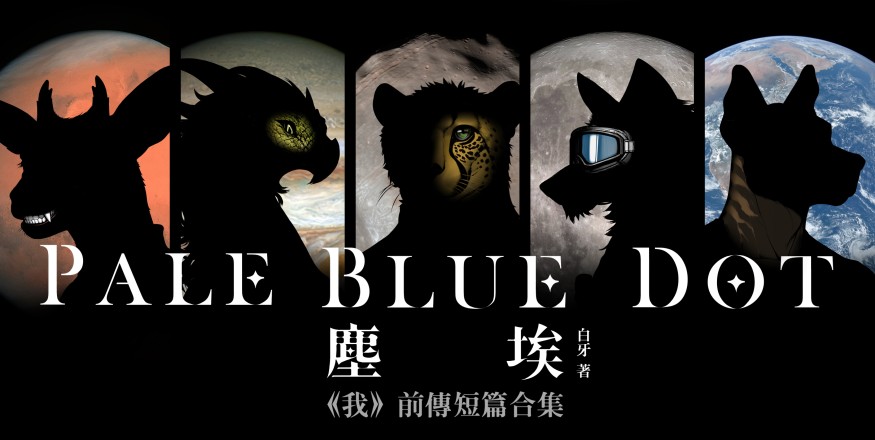硫酸鹽燃燒廠高聳入天際的巨大煙囪,一如以往排放著濃厚蠕動的煙霧。紅色示警燈在其頂端閃爍,和天空中稀疏的星星一同映照在透明穹頂上形成幾個亮點。
聽說蓋亞化完成以後,帷幕穹頂將會降下,我們能在紅色星球的地表以肉眼直接眺望夜空。當然,那個時候就不會是紅色星球了,再說,我也不可能活那麼久。
數年的辯論,最後經過公投,壓倒性決議進行不可逆的蓋亞化工程,永久把戰神星改變成眾人眼中期望的樣子。好吧,至少是大多數人眼中期望的樣子。
「抱歉!」突然的聲響將我自思緒中抽離,一匹高大的駝鹿進到電梯時,巨碩鹿角和其他幾匹紅鹿的撞在一起,發出喀喀的碰撞聲。在他慌忙轉身致歉時,又引發了更多碰撞,我能感覺到自我角上吹過的風壓。
沉默的無聲責難在整個空間漫延著,窘迫駝鹿的耳朵末梢都變成醬紅色了,而事情更在電梯發出過重警告時達到致死程度的尷尬。他只能再次道歉,然後退出電梯。
「大型種族要有自覺,不要影響到別人啊!」
「就是說啊,挑人這麼多的時候來擠電梯,是在想什麼呢。」
「真是的,愈來愈多不懂禮貌的人了。」
細碎的耳語在封閉空間迴盪,產生各自的漣漪。我揉了揉剛剛被身前那頭紅鹿比著誇張強調手勢時推去撞上扶手的額角,將視線轉回穹頂之外的巨大煙囪。
沒有那層高分子聚合物阻隔的天空,星星看起來會有什麼不同呢?
50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ZfeOoEtsb
這個區域的人潮稀疏一些,行走步調也慵懶的多,但仍然是那種一沒跟上節奏就會被其他人踩死的程度。
好像為了代替壞掉不知道多少年的路燈,色彩濃郁的霓虹招牌不時閃爍著,讓整個區域的廉價感增添了一些俗氣。
酒吧、舞廳,旅館。所有稍微有一點規模的城市,都會有這種地方──世界的暗面──讓負擔得起價碼的顧客顯露最真實樣貌、宣洩所有不被表面社會承認的需求。
打扮鮮豔又前衛的愛情零售業者們倚靠在滿是塗鴉的牆上,對所有經過的行人發出隱晦又明確的邀請。按照某種涉及太多暴力的協議,主要大街路口分別站著不同種族的凶神惡煞,穿著樣式相似的黑色皮夾克,兜售著絕對不可疑的貨品──從快樂、悲傷或麻木,到因為急難流當的家傳寶物──買到賺到,童叟無欺。至於連霓虹燈光都照不進的小巷裡頭,各種液體──可能是紅的、白的,或是黃的──濺上斑駁的牆面,覆蓋住先前留下的黏膩污漬。
我的目的地相對單純很多,這色彩繽紛的街景嚴格來說也不是我的世界,我們只是共享著相似的棲位罷了。不過,這不就是同鄉的定義嗎?
走著走著,我注意到了某種不和諧的跡象──行徑的人群小心翼翼繞開一小段距離,好像刻意閃避什麼那樣──是一頭黇鹿,腹面朝下的趴在大街上,雙眼沒有完全闔起,顯然也沒有焦點,而且舌頭都從嘴巴裡跑出來了。周圍的行人好像被某種看不見的立場阻隔般,維持著夠遠但又不失禮的距離從旁通過。
有趣的是,在這最深層慾望被放大無數倍的墮落天堂,卻依然可以清楚看見世俗慣性在我們靈魂上刻劃的痕跡。
據說草食動物都是這樣的,不喜歡成為突出的那個,因為會更容易被注意到。上個月才有匹紅鹿就這樣倒在中央車站大廳,都發臭了才被管理單位清理掉。
我掙扎幾秒鐘,嘆了口氣,拿出我的個人終端,通知醫療單位。但我知道很多時候,公共緊急服務都不願意進到這裡來──「咎由自取」,我想他們是如此替自己辯護的。
我又回頭瞥了倒在地上的黇鹿一眼,思索著自己是不是應該要多做些什麼。在我能得出任何結論之前,後方湧至的人潮將我向前推去,黇鹿便這麼消失在我的視線範圍之外。
我再次嘆了口氣,甩了甩頭,承認自己無法替那匹黇鹿做任何事情,就不要假仁假義自尋煩惱了。畢竟,我也不想再讓自己惹上麻煩──字面上的,一屁股麻煩。
ns3.15.26.7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