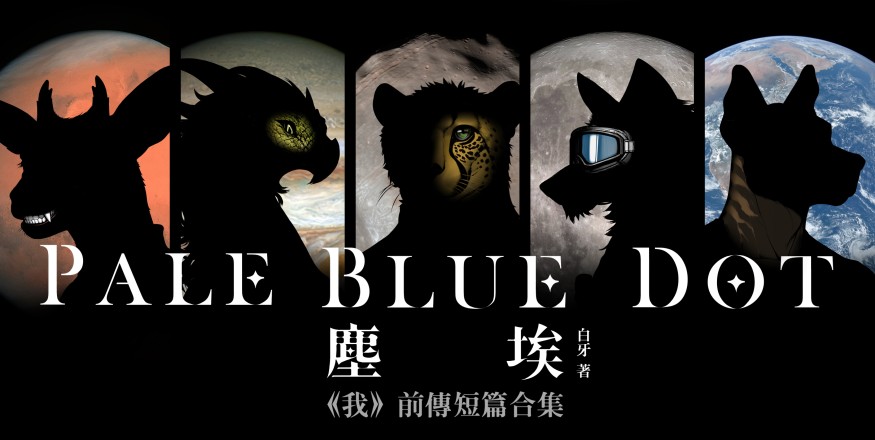長廊兩邊,歷代皇帝正用十分哀怨的眼神看著我,而黃白色的照明熠熠閃爍。我真搞不懂,為什麼要讓吃電力的光源模仿搖曳不定的火炬。
「公爵大人。」禁衛軍小隊長向我鞠躬,低垂目光看向地上,他的手下模仿隊長的動作,迴避我的視線。「這個時間,不知道大人有何貴幹?」他們在害怕。嘗試靠著紀律深植腦中的命令,對抗乞求著雙腿立刻開始狂奔的本能。
「來做我早就該做的事情。」我把手上的空酒瓶隨意丟下,讓碎玻璃噴濺得滿地都是。接著對著他們豎起右手食指,下達清楚的最後通牒。「滾。」
「我……我的職責不允許。」他的瞳孔放大到都快要炸開了,尾巴也夾到兩腿之間,但卻沒有移動。
「敬佩你的忠心耿耿,所以我會假設你是因為腿軟了或是耳朵不好,才敢繼續擋我的路。」我緩緩的說道,展開意識,將他手上的長矛從尖端開始往下捲起,直到長柄武器在刺耳的金屬扭曲擠壓聲中變成一顆拇指大小的球體。「我不會再說一次。」幾片玻璃碎塊飄起,緩緩的繞行著小隊長的頸部,以尖端抵著皮膚,切斷了幾根白色的毛髮。
隊長身後的衛隊成員們向彼此交換著不確定的目光,但沒有人離開半步。我很肯定隊長快要哭出來了,光榮殉職和被超自然力量捏成一坨肉泥之間是有些許差別的。
「為了……帝國。」他用顫抖的聲音完成了句子,淡藍色的雙眼中是必死的決心。
我嘆了口,放下手,碎玻璃和金屬球落回地面,發出清脆的碰撞聲。我最討厭固執又愚蠢的大灰狼了。再說了,斯諾支派的大灰狼都長一個樣嗎──純白的毛皮配上藍眼──那讓我更加煩躁了。
我將這群蠢狼砸上牆壁,控制在只會失去意識的力道。
我跨過昏厥的軀體,用意識扯開王座廳大門,隨意扔在一旁。
「晉見皇帝陛下。」我大步的走向王座,拿出我所有的諷刺儲備說道。
白狼有些慵懶的坐在王座上,右手肘倚靠著華麗的扶手,將下巴放在手背上。他緩緩的抬起眉毛,用湛藍的雙眼打量著我。
「免禮。」他隨意的說道,好像我們正在聊午餐要吃什麼。
「你以為我會接受這個命令嗎,在開什麼玩笑?」怕他有限的智商無法立刻了解我在說什麼,我拿出了我的終端在那蠢狼面前晃了兩下。
「拒絕來自皇帝的直接命令,這已經是叛國了,公爵路瑟。」他換了隻手來撐住另一邊下巴。「你是不想要德意志公爵的位置了嗎?有很多人搶著要呢。」
「我的確不是很喜歡公爵王座,服役期間的舊傷總是讓我久坐會全身痠痛──我需要椅背更高一點的。」他平板的語氣戳中了我的笑點,讓我打趣著回應道。「比如說,你屁股下的那張就不錯。」
我展開意識領域,打算將那自以為是的蠢狼拽下王座,好好按在地上磨擦,但卻撞上了一道堅固無比的屏蔽。
「我可是有給你台階下喔。」雖然是用臉下就是了,但我覺得這已經滿足人道守則頂標。
我維持著相同的速度向王座走去,沒有慢下腳步。
「妄尊自大的白癡。」白狼站了起身,惡狠狠的說道。「你媽還在吃奶的時候,我的異能技藝就已經爐火純青了。」
伴隨著強大的衝擊波,大理石地板以皇帝為圓心碎裂,輻射出不規則的龜裂紋路朝我漫了過來。我鼓起意識,接下衝擊,讓裂紋停留在我身前幾公尺的地方。
「我還以為,現在是我負責講粗話呢。」我擴大領域,包圍住皇帝的意識圈,擠壓了回去。白狼踉蹌了一下,但還是站著。
他朝我瞪了過來,湛藍的雙眼變得通紅,其中的憤怒好像讓那目光要噴出火焰來一樣。
只是,我看過嚴厲許多的。相比之下,這就像……什麼都不是。
我又向前踏了一步,繼續對他施壓。突然,我周圍的地板炸開,噴濺出的碎石和衝擊被我的防禦圈擋下。
「別出心裁呢,皇帝陛下。」我將煙塵和小碎石揮開至一旁。「只是你大概需要分貝高很多的火力才能擺脫我。」我本來以為這不過是讓我分心的障眼法,白狼打算逃跑了,但接著發現周遭地板都被染上暗紅──是血,繞著我一圈,將我包圍在中央的紅色血液,沿著白色大理石裂紋暈開。
「看來那雜種沒把你訓練得更精明一點。」強大的壓力自四面八方襲來,意識圈遭到壓縮讓我輸出大減,像被在腹部揍了一拳那樣的跌坐在地上。「次殘品終究只是次殘品,當然只能教出次殘品。」
我鼓起全力抵抗著,沒有餘裕站起來,地上的血液,離我最近的邊緣部分開始沸騰,冒出許多泡泡並滋滋作響。
「那個沒用的雜種,連最基本的義務都沒辦法盡到。」皇帝怒吼著,雙眼綻放紅光,口沫橫飛。「帝國只要求一個繼承他力量的後裔而已,一個!」他比著激動的手勢強調,大小不一的碎石因為我們領域的相互碰撞而緩緩飄離地面,在空中轉動。
白狼一揚手,一陣劃破空氣的聲響隨之傳來。還好我早有準備,數個金屬塊撞在我的意識領域邊界,被擠壓成扁平的形狀。
「結果呢,生了個跛腿的無能小雜種?」皇帝全身的毛髮都豎起來,體型看來變大了兩倍。「我都已經很寬容,不計較他的『異常』了,連這麼一點基本要求都辦不到嗎?」白狼咬牙切齒的說道,語氣好像吃到什麼髒東西一樣。
「你最好把剛剛那些話收回去。」我緩緩的起身站好說道。以為有成功控制住怒氣了,但是語氣比我以為的還要冰冷很多。「我不會允許任何人汙辱里希特,或是他的獨子。」我緊握雙拳,感受著意識中能流的波動和脈搏共鳴著,腳下的石板開始碎裂成細小粉末。
「雜種狗要替雜種出頭嗎?」白狼放聲大笑。「我真是沒有聽過更好笑的笑話了。」他作勢擦掉眼角的眼淚,擺出誇張的表情。
「哈哈。」我乾笑了兩聲,鼓起全力,集中在屏障上的一個點上放出猛擊,敲碎了皇帝的領域邊界,讓他腳步一歪,發出驚愕和吃痛的悶哼。當我發出的攻擊撞上白狼的防禦圈時,他直接向後飛了出去,摔上純白的大理石壁。
一道裂谷自我腳下延伸至被按在牆上動彈不得的白狼下方,將王座廳切成兩半,建築本體還因為剛剛的衝擊微微搖晃著。而皇帝發出低聲的呻吟,微微抽動肢體掙扎著。
「我保證,會很快。」腳下的碎石發出喀喀的聲響,我走向狼狽的皇帝。「如果你堅持把場面弄得更難看的話,就會拖很久了。」我繼續對白狼的防禦圈全方位的施壓,感受到蜘蛛網般的裂紋滿布其上。
他奮力抬起頭來,用鮮紅的雙眼對我投來睥睨的神情。就我快要折斷白狼身體的情況下,真的是很不簡單。他死死咬住牙齒低吼著,想要開口但顯然辦不到。
「如果你堅持的話。」我聳了聳肩,不介意多花點時間把他拆成更細緻一些的碎片。
「路瑟,住手!」我回過頭,看見灰黑色的哈士奇滿頭大汗的衝了過來,靈活的跳過各種原本是建築一部分的大形碎塊。
「杭特。」我微微向西伯利亞公爵點頭致意,但沒有鬆開對白狼的箝制,持續穩定的施加壓力。皇帝終於因為劇痛叫出聲音了。
「快停下!」他來到我身邊,抓住我的右臂懇求道。「你再不停手,我就必須向議會要求緊急仲裁了。」
理解了杭特話語中的意思以後,過大的衝擊讓我放開對意識領域的維持,白狼摔到地上又呻吟了幾聲,而我則無法控制的轉向杭特,對上他的目光。
「你是認真的嗎?」我強迫自己保持鎮定,專注在哈士奇的棕色大眼睛上有一點點幫助。的確,以血液壓縮我的意識圈,還有隨身攜帶精金作為武器使用──我剛剛太氣憤了,沒有把這些線索連結起來。
「皮克西爾波克陛下是議會成員。」杭特的雙手攪在一起,豆大的汗珠自濕透的毛髮末端滴到滿布裂痕的大理石地板上。「受到規則保護。」他來回看了我和皇帝幾眼,最後好像下了什麼決定一樣深深吸了口氣接著說下去。「而且我猜你不會想要親手殺死里希特的兄長。」
「理性的屁眼見證,在逗我吧?」無法控制的,我發出惡毒的咒罵。我還以為只是同支派的大灰狼都長得很像而已,里希特真的和這傢伙有血緣關係?
「不要把我和那雜種相提並論。」白狼啐道。「他是格雷支派生下來的雜種,不是純血的斯諾,只不過運氣好,繼承到我父親的一襲白毛和藍眼而已。」
「所以……皇帝的……不,帝國的命令和方針,議會一直……知情?」我不想理會那頭蠢狼,奮力的從齒縫中擠出這些字句,嘗試不要吼出來。
「拜託!」白狼靠著牆撐住上半身坐起,一邊大笑一邊喘不過氣似的咳了幾聲。「你是不是沒有搞懂,什麼叫做影子政府啊?」
「最新的命令是議會發出的?」我繼續強迫自己忽略皮克西爾波克,向杭特問道,希望他能給出否定的答案,但哈士奇棕色眼睛中的愧疚和焦慮說明了一切。
「那雜種到底教了你什麼,才能讓你無知到這種程度?」白狼繼續發出難聽的笑聲,真希望他笑到岔氣然後當場升天。
「這是關鍵的時刻,路瑟……」杭特喃喃的說道。「是終幕結算的濫觴,是一切事件的開頭。月球的觸發情節早就被決定好了,議會權衡了所有利弊得失,最後安排的劇本。」他又用了懇求的語氣,直視的我的雙眼說道。「即使你不贊成,但拜託不要進行違反規則的干預。」
「你們的陰謀詭計通通都可以見鬼去。」我轉頭就走,離開王座廳。我很清楚,如果自己再多待一秒鐘,一定會繼續完成剛剛被打斷的事情──把宮殿給拆了,讓那頭噁心的白狼好好安眠在瓦礫堆下,不要跑出來汙染空氣。
我也一點點都不在乎該怎麼收拾這一團混亂,反正皮克西爾波克也是議會成員的話,影子政府會自己想辦法的。
守衛隊的成員都還沒有清醒,我再次跨過他們,打算循最短路徑離開皇宮。又看了一眼長廊中,掛滿著描繪歷代皇帝能有多愚蠢的畫作,我審慎考慮了幾秒鐘要不要直接把牆挖出一個洞,再把飛艇給叫來。
「幹嘛?」我在身後感受到了杭特的波形,沒好氣的問道。
「這個嘛……」哈士奇有些尷尬的抓了抓頭。「議會通知我,你字面上的要把皇宮屋頂給掀了以後,直接請家族工程師開啟蟲洞讓我過來的……」他歪了下頭,擺出頗具殺傷力的微笑。「能讓我搭個便車回去嗎?」
我嘆了口氣,抓了抓耳朵,點點頭,比了比其中一條走廊向他示意。
「你要回莫斯科嗎?」我在停機坪找到了飛艇,啟動駕駛艙門讓我和杭特進去,然後開始設定航線。
「我想順道去看看亞歷山大。」哈士奇帶著微笑說道。「直接去柏林吧。」
「說到這個,」想到那匹小哈士奇我就更心煩了。「你什麼時候要把你兒子給接走?」我啟動人工智慧駕駛,確認航線,飛艇開始準備飛行程序。
「欸,你答應要訓練他的呢。」杭特滿臉事不關己那樣的笑著說道,讓我愈來愈確定,比起訓練莫斯科侯爵的異能,他更希望那個惹禍精離自己愈遠愈好。
「是里希特答應的。」我不太開心的指出事實。
「而你繼承了里希特的所有契約。」杭特指出了另一個事實。
精明的混蛋。
如果這匹哈士奇不要老是裝蠢,我大概就不會那麼常需要克制想好好揍他一頓的衝動了。
人工智慧操縱飛艇起飛,開始以超過一般人能夠負荷的強度開始加速和翻轉。我展開意識領域把杭特一起包覆進來,抵銷掉重力造成的慣性影響。
「喔……謝了。」哈士奇說道,我擺了擺手表示沒什麼。我記得杭特是艾普西隆級的異能者,應該能夠從我意識圈的脈動察覺我在做什麼。
飛艇來到平流層,我轉頭從觀景窗向外看去,看著一望無際的廣闊蒼藍色天空。
「杭特……」過了一段時間,我還是決定打破沉默,說出困擾我已久的問題。「里希特是當代最強大的異能者,對吧?」
「在你出現之前,肯定是的。」哈士奇轉向我說道,我能從觀景窗上的倒影看見他鼓勵的溫暖笑容。
「我很確定,他還是比我強大。」我淡淡的說道,回憶著一些被里希特像是布娃娃那樣摔來摔去的場景。「你也有看見他的屍體對吧?」杭特的表情變得陰暗了一些,但他點了點頭。「所以……那些傷口,完全不像是幽影造成的,而且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夠真的傷得了他呢?」我沒辦法直接說出內心空洞中所深埋的那個恐懼,我也沒辦法確定我究竟期待能夠得到……平靜、救贖,或者只是一個確切的答案?我只有滿滿的疑問。
「不,不是你做的,或是你害的。」杭特說道,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
「如果不是我的話,為什麼里希特要封鎖我的記憶?」疑問像是黑夜至深之刻,萬籟俱寂之時,自我胸口內部無法停歇的尖銳抓搔感,張牙舞爪的摧毀所有殘餘的理智和安全的假象。「為什麼……我的記憶中會有那麼多的空缺?有那麼多,都是和他相處時光的空缺?」
「我想里希特一定是有很好的理由才那麼做的。而且不要忘了,他不可能在沒有得到你的同意下封鎖你的記憶。」杭特再次給了我一個堅定的笑容說道。
但是如果我只是樂於逃避事實的懦夫呢?你的信心是從哪裡來的?又或者,真正的問題是,杭特這麼說的原因是對我有信心嗎,還是基於知道──或是不知道──真相?
「你分發時選擇的信條是什麼?」我們各自沉默了好一陣子以後,我又拋出了新的問題。
「結果可以正當化動機。」杭特有些抽離的說道。
「看不出來你是功利主義者。」這個答案讓我有點訝異,轉過頭去對他抬起了一邊眉毛回應。「所以你會為了……」我想了想該怎麼說。「……更遠大的利益,說謊騙……不,引導我往正確的方向前進嗎?」
「不,我不會。」他微微歪了下頭,帶著一抹淡淡的微笑說道。
「你現在正對我說謊嗎?」我問道。
「不,並沒有。」他依然帶著那淡淡的微笑重複道。
「你知道我想要的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在說謊吧。」我回過頭,確認了一下儀表板的資訊說道。
理論上我強大到足以讀取杭特自我領域表層的波動,里希特用自己示範給我看過一次,但警告我這是萬不得已的非常手段。違反個體意願窺視對方的心靈,是非常邪惡的事情──里希特強調道──人被詛咒為自由,但這詛咒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根本。
「我知道你可以,」他也將頭轉回去,靠上椅背說道。「但我知道你不會。」
對哈士奇的宣稱我哼了一聲回應,不打算再深究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信條和相對應的暗語只是作為最後投票的權重,還有上交記憶資格的鑰匙而已,並不是真的是某種必須要嚴格恪守的規則。」杭特像是在自言自語般的說道。「或許也有當作分發時宣示陣營、確立盟友和敵人的作用,但也就這樣了。」他摸了摸胸口,我能從上衣的輪廓看出那是某種圖樣的掛墜。「分發的目的,是讓有足夠野心去形塑世界的議會年輕成員,踏上旅途,在世界各處中親身經歷、身體力行理想和抱負,最後得出屬於自己的解答的過程。」一抹淡淡的笑容出現在哈士奇的臉上。「如果不會改變,才有點奇怪呢。」
我輕輕嗯了一聲回應,想像著當時里希特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和想法踏上旅程的。
「所以啊,」杭特繼續說道,閉上雙眼,放鬆全身靠上坐椅。「不要因為里希特將他的暗語交給了你,你就覺得自己就必須要按照存在主義者的信條行動。」
「我不是存在主義者嗎?」我誠心發問,偷偷瞥了眼哈士奇在觀景窗上的倒影。
沒想到杭特的反應是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但仍然閉著雙眼,調整一下坐姿,可能想要找個舒服的姿勢。
「看來在剩下來的旅程中,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下哲學。」他的嘴角上揚,可能想起了什麼有趣的回憶。
「洗耳恭聽。」我的回答讓杭特笑得更開心了,甚至擦了擦自己的眼角。
在哈士奇還沒有緩過來之前,我拍了拍肩膀上的髒汙。剛剛在皇宮時沾上來的,都沒有注意到。看了眼手掌中灰濛濛的細小砂石,我吹了口氣,透過從觀景窗照映進來的光線,讓無數進行布朗運動的細小塵埃,清楚在我們眼前,顯現出飄盪的軌跡。
ns3.144.200.2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