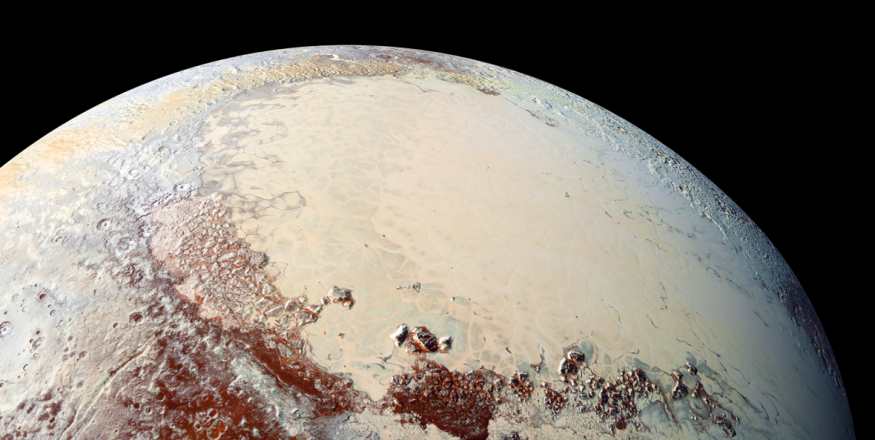落在法蘭丘區哨兵街裡、那以花崗岩砌成的阿卡姆憲報報社,是從1806年創刊以來所坐擁的兩層高辦公樓。二樓那喬治亞式的扇形窗裡,即使在下午也向外透出了橘光;老舊的木門只打開了左側,昏暗的室內燈在裡面淡淡透出,向站外映出了一個模糊的孤單人影。
我站在報社外面,再次看了看手中的精裝本後,便深深呼出胸中的一口氣,向前走去,推門進入報社。
「……麻煩你,」我仔細思考後,向接待員說。「請問是哪一位在處理艾爾頓‧懷特,與戴維斯‧阿米塔吉兩人失蹤的相關新聞呢?我有情報提供。」
「請問先生你是?」即使接待員問得客氣,但那保持冷淡的視線依然使人不快。「我替你通知負責的編緝,但要不要見你得由他決定。」
——我拿出教授的信件遞給她。
「請在那邊坐下稍等。」接過信件後,她就轉身推門走入被牆壁分割開的內間。
從報社大門中向我身後迎來的空氣與報社內裡因推門而透出的冷氣,在我的身邊湧出亂流。
教授的信中,並未提過有關這本書的一切。但當我正要進一步搜尋那把懷特最後的傳真引導至《紅死病的面具》的線索時,卻彷彿故意被某人隱去某個重要的環節,無法前進。
直到剛才,在警局花費過無用功後,我再次細翻手邊的所有事物。我把小說選集翻了又翻,腦裡卻總無法再確切的看得下任一個字;書本上沒有任何標籤,也沒有任何可以彰示所屬的證明。我隨後又回到了大學,進入附屬圖書館,拿出小說選集向管理員詢問;但管理員只是搖頭說這本小說,不曾在館藏之中。
「教授得到這本書這件事」,似乎沒有合理可解的理由;我苦惱的坐在大學外的長椅,再次翻開教授給我的信件,細細推敲。
我把它從頭到尾,重覆的閱讀了兩遍;當我開始漸漸理解到一件我早該注意到、但卻一直視而不見的事情後,我不禁對自己的愚昧,憤怒失笑。
「29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lSLy3kqrR
……29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VzoYuqsG2
自此所有我的探求能到達的,到此便中斷了。我曾去信報社尋求懷特幫助,卻久未得到懷特的回覆。後來再次向報社查詢,報社卻告知懷特於七月二十六日就動身前往河床鎮,查探教團襲擊事件後續,卻已失蹤十餘日。我希望你能答應我的請求,並前來取過報社交給我的,艾爾頓‧懷特出發前為事件整理,以及利用傳真機寄回報社的資料。我期待你的到來。29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9FnE3m1ef
……29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Hac26OhFY
」
報社裡有人把情報提供給教授。
我聳了聳直至剛才仍在發酸的肩。
V
「你好,我是亨利。亨利‧湯森特,《阿卡姆憲報》副編緝。」面前的男子伸手拉動椅子,坐在漆得潔白的木桌對面後,向我伸出右手——我輕輕一握。「請問你是教授的……?」
「從前的學生。」我從他手上接回信件,珍重的把它放回外套的內袋裡。我益發開始感激,教授給我留下了這封萬能的信。
亨利‧湯森特是個乾涸的男子。他那後退的髮線根部沾上了花白,頭髮就如丘陵深秋的草一樣不再光澤。細瞇著的眼線毫無神彩,和他那瘦削的身形一般,蠟黃的皮膚佈滿緊繃的皺紋,好像曾被風乾過。
這個臨時挪作會客室的房間相當簡陋。只消看見那堆滿雜沓紙品的四角便會知道,房間原應只是個雜物房。在餘下狹小的空間中勉強的放下一張桌子,餘下的兩方便用兩張木質的折椅填滿面對的空間,只餘下一段狹小的空間。暗淡的白熾燈照在白灰的牆壁再在房間內反射,映出了角落久未打理的塵埃與結網。
先行進入的房間我為了讓隨在我後面的湯森特能夠步進這擠迫的小隔間,只好坐在房間的裡側;湯森特關上了門、在桌子的另一方坐下後,便擋住了我通向門口的路。
「聽說在教授失蹤的當時,正要會客;想必那位客人便是你。」湯森特看著我的雙眼發問。「容我直入題目。聽說你有關於懷特和阿米塔吉教授的情報?」
「即使沒有見著教授,他卻依然留下了線索給我。」我吶然,用舌頭搓動發澀的上顎。「之後我到了教授的家,總算拿到了這個。」
我把《埃德加‧愛倫‧坡短篇小說選集》從公文袋中拿出,放在桌上。
他抬起了眉。
「教授給我的信中並未提到這本書,」我不等他說話,便自行續說。「教授一向身無長物。除跟工作有關的一切,他幾乎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消磨的事上。那麼,到底為甚麼會在寄信給我後、我來訪前的這幾天中,忽然拿到了這本書?」
「方便讓我看看這本書嗎?」湯森特向我伸出手;我把書在桌上向他推去。
「不,」湯森特苦笑。「麻煩你把書本反轉。」
我伸出手,把書本反轉,再置在桌上。
湯森特靠近了書本一點,確認了書背;然後,他笑著搖了搖頭。
「果然是被教授取走了。」湯森特苦笑,「怪不得我找不到。」
我壓低了一根眉,向他投去疑問的視線。
「這本書在幾天前還在這所報社裡。」湯森特再一瞥小說選集,「正確來說,在八月十五日下午,這本書在我的辦公桌上停留了十分鐘左右。」
「看看封背右下方。」湯森特用下巴指了指書本,「上面有著被庸碌的警察們,隨便以它墊著紙條寫下筆記的痕跡。我花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這書,那群警察卻毫不理會;我跑到警局取回那些檢走的東西時,他們愛理不理的,還膽敢一邊聽著電話,一邊寫字條。好辛苦說服了警察、從那邊討過來這本書後,才一轉眼,就被再次來訪、要討進一步關於懷特情報的教授偷偷帶走了。」
「從警察那邊討過來?」我重複他的話。
「這本書在八月十日凌晨,被警察從大學附屬醫院的隔離病房裡檢走。」湯森特點頭說,「在死亡的亞倫‧約漢森現場,」他補充。「八月九日晚上,當人看見他那受感染而病死的屍體時,置放在附近的這一本讀物差點就要隨著那兩具屍體一同焚毀了。要不是我馬上聯絡了警察把現場封鎖、將所有東西檢走,這本書就會永遠消失了。」
「你看過書的內容了嗎?」我問。
「沒有,」湯森特搖頭,毫不掩飾的露出古怪又無奈的表情。「我還沒有確實的碰過這本書呢。從警察那邊帶過來時,還好好的藏在密封袋裡。看見它就如此的曝露在外,我還依舊擔心傳染病的擴散——」
我在他面前直接打開了書。他馬上閉上嘴巴,屏住了呼吸。
「八月十五日下午直到八月十九日傍晚——要是這本書有甚麼寄宿著,那麼教授就不應該失蹤,而是劇死才對。」我笑了笑,開始翻動書頁。「話雖如此,但你的直覺仍然是對的。這本書的確有病——」
我把那一章攤在他的面前。
湯森特摘下眼鏡瞪大了眼睛;嘴中隱若可見,是在默唸章節的名稱。
就結論而言,和亨利‧湯森特的見面,也不算是全無收獲。
關於書本的出處,只能探至大學附屬醫院——但卻仍然並不屬於大學本身。之後我和湯森特一同移步至鄰街的一個小車庫;在車庫裡有一個小箱子,置放了另外數件從約漢森的死亡現場裡檢走的東西。但那全都只是一些普通的雜物,和紅死病毫不相關。
書本如果並不屬於大學,那麼可能屬於約漢森本人——或是約漢森從另外的某人手上得到。我忽然想起獨自來到阿卡姆,那最初就急死的病者。細心一想,我幾乎從未掌握到關於這個人的任何情報……
另一方面,懷特自失蹤以來,依然毫無消息。當我向湯森特繼續詢問關於在河床鎮出現的巫教派時,湯森特那苦惱的表情誇張得幾乎使我忍俊不禁。
回到報社,湯森特跑到一張堆滿雜物的桌子,翻找了片刻;然後他從取出了一張字條交給我。字條上寫著一個地址。
「懷特出發前往河床鎮前,到過這裡。」湯森特皺著眉說。「到過這裡辦了個假的證件——為了通過封鎖線。如果你需要繼續向著失蹤者的方向前行,那麼最終必定需要那個東西。」
我收下了字條,向他點了點頭。
「還有,你等等。」湯森特取出一枚名片,交給我。「上面記有我的電話。如果你查到甚麼新消息,請你告訴我吧。」
「……好的。」我把名片反轉,然後取過筆,在空白的一角寫上號碼。「不過,如果你留意到巫教派有甚麼新的行動,也請告訴我。」
我把寫下自己手提電話號碼的名片一角撕下,重新交給他。湯森特仔細的把寫在名片角落電話號碼看過一遍,然後放入名片夾中。
我把字條和名片一同放入外套的內袋中,然後離開了阿卡姆憲報報社。
當我再次回到街上時,八月二十日的日落早已悄悄結束了。黑暗再次籠罩了阿卡姆。
(本章完)29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zVyudfah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