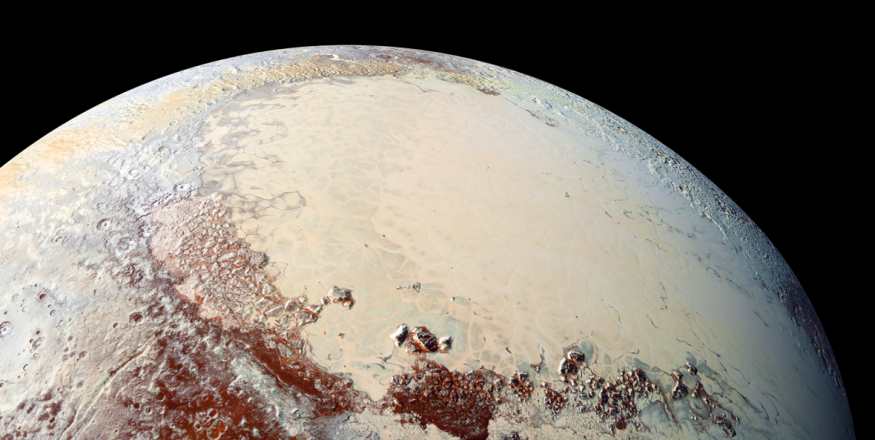當我再次從夢中清醒過來時,已經不再躺在原先的房間裡面了。我被陌生的拋棄在我熟悉的街區,但卻不曾久留的骯髒區域裡。從深夜下水道的坑蓋附近,溢出了污水,沾濕我身上的大衣,還有我唯一攜帶的——此行而得的,資料公文袋。我緊張從地上爬起查看,看見污水仍未滲入那些手寫的記錄裡時,我鬆一口氣。
大概有甚麼正在驅逐我。我在阿卡姆的旅店下榻,卻在入睡後,在北尾地區的貧民窟裡醒來。
搖晃著未曾從睡倦中完全醒來的身體,我緩緩站起。抬頭張望四處的同時,我開始再次思考,喚醒我混亂的大腦。
3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YLudkJyaA
I3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hxttdnFUA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那是三日前。我收到了來自米斯卡塔尼克大學的信件。畢業後我再沒有回去的大學,距今已隔五年,卻寄來了信件。那時我正好結束晨跑,手中那在家裡門前等待許久的牛奶卻讓我看見寄件人名稱時使我感到入口發酸。
戴維斯‧阿米塔吉教授在給我的信件裡,字跡因手腕發抖而有些難以辯認。我細細讀了兩次,確實地試圖思考教授在書寫此信時的心情。
「致親愛的學生:
許久不見卻無暇讓我為你帶上致誠問候。近來有些新聞,輾轉傳入我耳中。我急需請你,代替已經老邁的我,前往河床鎮調查一些關於巫教派的異聞。
撰聞的記者是艾爾頓‧懷特,那位和你交情相當好的同期。於七月二十二日的《阿卡姆憲報》上,他詳細寫到了河床鎮裡的特別閱覽室,遭到某個教團的襲擊。河床鎮裡自組的警備團,在兩小時後,他們終究還是發揮了應有的功用,教團離開了河床鎮。藏書經點算後,並沒有任何書藉遺失;事實剛好相反,在那被襲擊弄得一塌胡塗的書堆裡,圖書館理員發現對比於藏書列表,多了一本所屬不明、無法閱讀的書。
河床鎮警備團最後還是無法阻止那行為惡毒的侵略。在往後的一天內,河床鎮發生了極嚴重的傳染病感染。七月二十四日的早報上,繼續報導了在二十四小時內,出現了將近四十名因急病而死亡的病人。所有人的發病,全都從劇烈的頭痛開始,繼發癲癇,然後體表便出現大小不一的紅斑;不過十數分,紅斑裡的毛孔便會湧出血液,爾後大量失血死亡。他們從發病,到死亡的過程,最多不過半個小時。
政府封鎖了河床鎮,包括一切情報的外流。然而巫教派和那些致命的死與病似乎並沒有留在那幽暗的土地裡;過了不足一週,就有許多值得更用心懷疑的死亡消息從週遭的醫院傳開,也有了更多關於陌生人在小社區中走動而被認出的情報。最後,一個活人來到了大學醫院。
我從你另一位同期,亞倫‧約漢森——他現在是位醫生——裡,拿到了那個死人的血液樣本。在興奮的反復檢查下,發現的卻是令人失望又可怕的事實:那血液裡,並沒有任何我們所未知的細菌或病毒。當我隔日再次向約漢森尋求更多的樣本檢查時,卻被大學醫院告知,他那受感染的遺體,已和那位帶病者的遺體一同火化了。
自此所有我的探求能到達的,到此便中斷了。我曾去信報社尋求懷特幫助,卻久未得到懷特的回覆。後來再次向報社查詢,報社卻告知懷特於七月二十六日就動身前往河床鎮,查探教團襲擊事件後續,卻已失蹤十餘日。我希望你能答應我的請求,並前來取過報社交給我的,艾爾頓‧懷特出發前為事件整理,以及利用傳真機寄回報社的資料。我期待你的到來。
戴維斯‧阿米塔吉 敬上」
我喝下最後一口牛奶,便替開始打點替換的衣物。
阿卡姆市仍舊是個乾罕的地方,所有人都緊閉著他們的嘴唇。每個路過的人都只眯著眼睛掃過我,彷彿只要多看一眼或注視一秒,眼睛便會發澀。不遠處的荒野山腰上掠過那些小小牧場降下來的風,帶著屠宰的臭味與不安;五年前,我從這裡離開,但卻仍未能逃離。我常常夢回自己又到了此處,在童年迷路的深夜山地上,恐懼地聽著那些幽暗的灌木叢中,野生動物發出竊竊私語一般的聲音。
戴維斯‧阿米塔吉開始在米斯卡塔尼克大學任教時,早在我的出生以前。他那蒼白的臉孔上如同鑲嵌著巨大的眼球,使他的眼眶深深凹陷發紅,緊抿著幾乎看不見的嘴唇。在整個大學的歲月裡,他一直都負責我,與同學們的細菌學課程;但他的主要研究,卻是神秘生物學。記憶中的他時常揮動著手中的拐杖,敲打山地的岩塊,登上附近的野林,彷彿那衰老的外表只是化妝;我無法想像如今已九十的他,會是何種樣子。
進入大學時,太陽已經沉入山後。曾在這裡居住的年輕人們,早就漸漸開始拋棄阿卡姆市,如同我一樣;使得矗立在這裡,卻杳無人煙的大學被籠罩著一絲絲的不安與失調,如同無法用視線好好對焦的錯覺。教務處唯一的職員通知我,教授仍在他的房間裡,於是我便走入曾熟悉的幽暗走道,前往二樓。
越過了四分鐘,我終於來到了教授的門前。
然而在我的手觸及門把之前一瞬,裡面卻傳出玻璃破裂聲與劇烈的碰撞聲;我急著推開房門,看似脆弱的老舊木門卻像是被甚麼堵死了。聽著裡面的碰撞聲漸趨激烈,我開始慌亂,只好用力的撞門——但當在我終於把木門撞開的一瞬,裡面除了一地的凌亂外,誰都不在。
從門口往裡看面對的那堵牆上,記憶中原本應該被嵌入了一面窗戶;然而在眼前的牆壁已被完全破壞,就像是被強大力量從內而外扯裂一樣,甚至已看不見窗戶曾存在的痕跡,牆壁的四邊也被扯得變形。我走近牆壁,探頭到外面;那裡並沒有任何人落在外面的水泥鋪地上。甚至,也沒有一塊磚頭落在裡街上面。
我退回房間內,仔細打量牆壁的裂口;在斷裂處,有幾道留下來的血指痕。從我聽見房間裡傳出聲響,直到門被撞開前,才不過十來秒;房間內亦除了空氣中散佈上些許岩石碎裂的白色粉塵外,並沒有任何瓦礫的存在。到底剛剛……
在我思考的同時,一個公文袋映入我的眼簾。
那是一個有好些厚度的黃色公文袋,重重又方正的鼓起,上面用油性筆寫上了我的名字;我輕輕把它從凌亂的木質碎片和散落的書本亂堆中拾起,準備查看時,教務職員便走進了房間。
然後在混亂的警察訊問與教務職員的疑惑眼神中,我被帶到了阿卡姆市警局繼續被查問。在將八小時的調查後,那些慌亂的人們終於相信我毫無能力把整堵大學的牆壁破壞,再在瞬間把教授藏到他們無法找到的地方裡。
直到我被釋放時,已經是深夜了。
晚上的阿卡姆市幾乎沒有街燈,也沒有燈光。在光害剛好把星圖遮敝,但卻不足以照明前路的地方裡,我摸黑胡亂前進,最後到達了一家旅館。
我幾乎不記得旅館的名字,也不記得它長得如何。它骯髒得讓我只記得它在牆壁和所有傢俱表面,四角都蒙上了黑霉。然而這已是我的幸運了,之前在街上走動時我還在後悔,為甚麼讓他們這麼早就放我出來。我繳了一晚房錢,被櫃檯的老女人領到一樓盡頭的房間裡後,待她離開,倒在床上不久便睡著了。
3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DN7PPfWoL
II
我帶著仍然疲倦的頭腦,在黑暗中向燈光走動。
北尾地區的深夜,燈光都非常的低。它就像在你腰後從背後照過,在你面前投下被拉遠的影子。這貧民窟異常安靜卻帶著臭味,像是混合了一些大家都喜歡的化學品,燃點過後的餘燼。要離開貧民窟的方向,只需要向氣味最稀薄的地方走就好了。
我搖晃的身體幸運地沒有在貧民窟裡再次倒下,天知道這裡有多少理由讓我倒下。遠離了貧民窟後,我乘上了深宵的計程車,離開了北尾地區。3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75Iw85y7B
(本章完)3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SeFxP1ux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