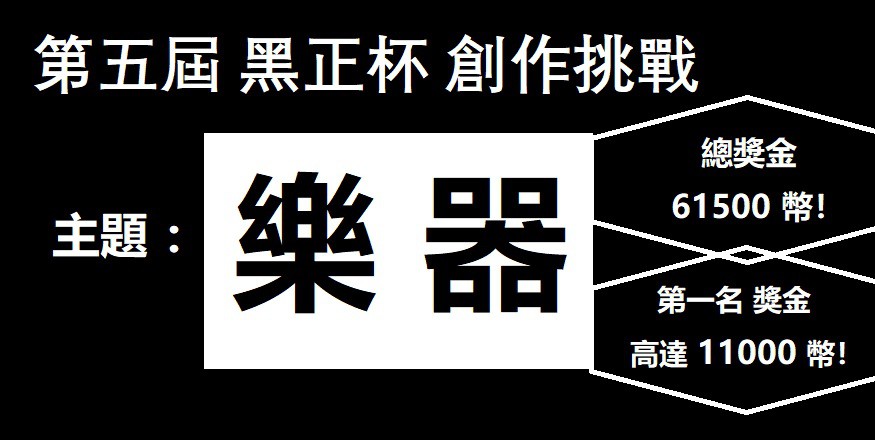東晉時期,天下割據,漢人朝廷偏安東南一隅,北方匈奴、鮮卑、柔然、羯、羌、氐等族紛紛入主中原,逐鹿天下。然而當此兵荒馬亂之時,細看之下,卻還是有不少太平靜好的年月。
夜空無雲,繁星閃爍,一輪彎月高高掛著,月光皎潔而微弱,默默映照在一片荒蕪的沙丘之上。這一片沙丘位處西北祁連山脈不遠,是天下各地經蘭州、西寧,出月牙、鳴沙,再西去波斯、歐、非等地的必經之處。這條延綿萬里之路,後世稱為西北絲路,是一條貫通東、西文化交流之路。
此地平日雖然荒蕪,但這一夜卻意外地聚集了一群人,帶著車馬物資,在此生了幾處營火,搭起幾座帳篷,看樣子是準備在此野宿一晚了。人雖然不少,但其實卻是有四夥素不相識的人,在此不期而遇。地方不寧,旅途凶險,於是大夥決定抱團同宿,以防不測。
夜風輕狂,不時卷起沙塵,嗚嗚襲人。眾人披著斗篷,分作數團,圍著營火而坐,一邊取暖,一邊烤著野味,淺酌酒水,相談甚歡。其中一堆營火旁,坐了四人,看來正便是這四夥人的首領。
其中一人模樣只三十出頭,臉上總是笑容可掬,禮貌地拱了拱手,自我介紹道:「在下姓錢,乃是一介行商,帶著十餘伙計,由長安而來,往波斯而去,為兩地互通有無,略盡棉力。今晚與諸位在此相逢,也是緣分,幸會、幸會。」
另一人身材削瘦,銀髮長鬚,看模樣已有六七十,衣著斯文,舉止儒雅,似是個飽學之士。他也一拱手,說道:「錢老闆客氣了。老夫姓朱,大晉人氏,本是一介書生,在建康教書為生,多年前奉皇命前往西域,傳我中土之儒學,揚我中華之文化。匆匆十年,白駒過隙,如今使命已達,遂領著弟子數人,回江南覆命。」他一頓,看了身旁另一人一眼,接著問道:「這位大爺相貌堂堂,器宇不凡,敢問是何處人氏?」
這人年約半百,衣著光鮮,面目不怒自威,捋着顎下長鬚,輕輕一笑,答道:「朱夫子過譽了。本官姓呂,只不過是我大秦涼州刺史梁大人麾下一個小小功曹,不值一提。本官本在涼州任職,此次只因出差敦煌,才會路經此地。」
朱夫子聞言一揚眉,問道:「如此說來,足下是個氐人?」
呂大人口中的「大秦」,史稱「前秦」,正是北方氐族人入侵中原建立的政權。「功曹」是個官職,是地方大員刺史大人的主要佐吏。晉國朝廷不敵外族入侵,這才不得已遷都江南,偏安一隅,朱夫子是大晉人氏,自詡為中原漢人正統,心裡自然對外族人有所排斥。這番心思呂大人自然曉得,當下毫不示弱,昂頭挺胸,說道:「正是!怎麼了?朱夫子難道是看不起我氐族人了?」
朱夫子滿腹慷慨言辭,正要脫口而出,轉頭看了身後呂大人的數十隨從一眼,個個虎背熊腰,彪悍魁梧,自己師徒幾個文弱書生,只怕惹不起,只好強行把話咽了回去。當下悶哼了一聲,轉頭又問最後一人道:「這位後生一人獨行,一直不曾說話,敢問是何處人氏?高姓大名?」
錢老闆和呂大人也跟著把目光轉向第四人,出於禮貌,他們雖然都強行忍著,但目光卻還是不由自主地瞟向了此人空蕩蕩的衣袖之上。此人是個年輕男子,看起來不過二十出頭,身材精練紮實,皮膚古銅黝黑,本是個挺討人喜歡的小伙子,只不過一條右臂卻似乎齊肩而斷,是個殘廢。夜風吹過,長袖飛舞,莎莎作響。四夥人馬當中,也只有此人獨自而來,沒有任何同伴。
面對三人奇異的目光,此人彷彿不以為意,又彷彿早已習慣,笑了笑道:「誠如諸位所見,在下是個天生殘廢,自娘親生下,便缺了一臂。父親心裡厭惡,於是為我取名叫『棄』,嫌棄之棄。十二歲時,父親喝得酩酊大醉,無故大發雷霆,更把我趕出家門。娘親不忍,臨走時叮囑兒子道:『身殘而心不殘,一樣可以成大器。』在下於是從此更名叫『器』,大器之器。」
三人聞言,彷彿都覺惻隱。錢老闆乾笑兩聲,說道:「兄臺侃侃而談,毫不避諱,想來是早已把事情看開,當真難能可貴。『器』也是個好名,卻還未請教貴姓?」
男子答道:「在下這姓,甚是罕有。」他一頓,左手撫胸,微微彎腰,行禮繼續道:「在下姓樂,單名一個器字!」
錢老闆失笑道:「樂器!這倒是個很特別的名字!」
朱夫子點點頭道:「的確特別,但自古以來,令祖上也曾出過不少名人。古時戰國有位名將,便叫作樂毅。後來漢朝時曹丞相麾下,也有位將軍,名叫樂進。再近些,我大晉渡江之前,也曾出過一位尚書令,名叫樂廣。」
樂器道:「朱夫子曉古通今,在下佩服,受教了。」
呂大人笑道:「名叫樂器,要是你還能彈奏一曲,那就更妙了!只可惜……」
只可惜無論是胡人的琵琶嗩吶,還是漢人的琴瑟箏篪,都很難以一隻手操作。他話沒說完,似也自覺失言,後半句便硬生生吞了回去,改口道:「只可惜匆匆出行,也不曾帶上一兩件樂器自娛。」
樂器依舊不以為意,大笑道:「哈哈哈,呂大人無需失落,實不相瞞,在下不但名叫樂器,人也正好就是一把樂器!」眾人大惑,樂器繼續解釋道:「在下別無長技,就只一張嘴,功夫不算丟人。自小以來,便能單憑一張嘴,模仿各種聲音,無論是市集的喧鬧,還是靜夜的蟬鳴,諸位要是閉上眼睛聆聽,絕分不出真假!」
錢老闆大感有趣,奇問道:「世上還有如此本事?」
樂器點頭道:「老天爺取走了在下一條手臂,卻還予了一把嗓子。在下雖能模仿各種聲音,但卻對各種樂曲情有獨鍾。自被趕出家門,在下走南闖北,周遊列國,只為了到各處聆聽天下各地、各國、各族的樂曲,收集各類五花八門的樂器聲音,到了夜闌人靜之時,自鳴自娛,宛若置身樂海,其樂無窮,十餘年來,在下是樂此不疲呀!」
呂大人皺眉搖頭道:「荒謬、荒謬,本官不信!」
樂器笑了笑,二話不說,舉起左手,做了個奇怪的手勢,掩住了嘴,閉眼深吸了一口氣,火光閃爍照耀之下,只見他指掌抖動,兩頰一鼓一缩地震動著,脖子上喉結更是活了過來似的不停上下彈跳了起來,突然之間,眾人便聽見了一股琴音,彈奏的是名曲《廣陵止息》,琴聲悠揚端莊,一音一調,皆與真琴無異。不但如此,從樂器口中,傳出來不止一把琴聲,而是由琴、箏、笙、筑等多種樂器合奏的美妙樂聲。這首曲子相傳乃漢時嵇康所著,講述戰國時齊國勇士聶政刺殺韓國相國韓傀的故事,曲風激昂肅穆,蒼涼悲壯,當此風沙露宿之夜聽來,更覺淒美。
曲聲響起,馬上引起一旁的隨從注意,紛紛放下手中肉食,圍了過來,臉上無不驚異萬分,又覺甚是受用,不知不覺沉溺於樂聲之中。良久,一曲奏罷,眾人才彷彿從夢中醒來,轟然喝彩,又驚又嘆。
呂大人撫掌讚道:「神乎其技,本官信了,信了!」
朱夫子眼珠一轉,心中有了計較,嘆道:「美乎妙乎!可是樂兄弟奇技固然神妙,但倘若沒有我漢族先哲傳下的這首曠世神曲,公子只怕也難免英雄無用武之地呀!此曲由我漢人所著,講述的是我中土千年以前的典故,曲中所用樂器,琴箏笙筑、鐘鼓箜篌,無一不是我華夏文化之精髓,想當年聶政刺韓傀之時,北方戎狄之輩,猶自蒙昧蠻荒、茹毛飲血!由此可見,我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絕非其他外族人所能比擬的呀!」
原來他對於適才呂大人一句搶白,始終耿耿於懷,此時借題發揮,心底的話終於一吐為快。他言下之意,呂大人當然聽得明白,當下心頭火起,瞪圓了眼,正想發難反駁,不料樂器卻已然搶著搖頭說道:「朱夫子此言差矣!各族樂曲各有長短,不能一概而論。若比作女子,漢人祖宗留下的聲音宛若豪門婦人,端莊典雅、雍容華貴;但中原以外諸胡族的樂曲卻勝在跳脫多變,大情大性,時如仗劍江湖的俠女,快意恩仇,時如刁蠻任性的小姐,嬌嬈媚俏;在下以為,這滾滾紅塵之中,無論是缺了哪種女子,都失色不少啊!」
如此比喻,把眾人都逗得樂了,本來略顯緊張的氣氛,緩和不少。樂器談起自己所好,意猶未盡,繼續說道:「天底下成百上千種樂器,各不相同,只有音調之別,沒有高下之分。比如漢人的瑤琴,松沉而曠遠,清冷入仙,讓人起遠古之思;波斯的琵琶,清脆圓潤,渾厚高亢,短音如開弓射箭,翻若驚鴻,長音如玉珠走盤,回味無窮;奚族的胡琴,哀怨蒼涼,低音嘶沉沙啞,高音若隱若現,絲絲縷縷,欲斷又連,如泣如訴,撥人心弦;羌族的羌笛,蕭索悲壯,婉轉多變,低音似苦思沉吟,高音卻撕心裂肺,一放一收,叫人懸念迭生!」
這時錢老闆興致大起,接著說道:「小兄弟對諸般樂器瞭如指掌,如數家珍,真不愧樂器之名!在下經年往返東西,曾經聽聞,在遠古時期,在比波斯更遙遠的國度,有一種『西塞拉琴』,其狀如琵琶,上有六弦,音如流水,圓潤細膩,傳言當今之琵琶,正是由此器演變而來。小兄弟可曾聽過這種琴?」
樂器嘆息搖頭道:「倘若日後有機緣,一定要找來聽聽。不過錢老闆倒是說到重點上了。其實樂曲本無國無界,宛若你我腳下沙子,單取一勺,誰能分清是漢是胡?昨日異國的西塞拉琴,成了今日波斯之琵琶;焉知今日波斯之琵琶,明日不會成為華夏之正音?各族樂器,交融混糅,互補長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集各家所長,共譜一曲,豈不美哉?」
錢老闆點頭嘆道:「在下行商東西兩地,見過不少各族人士。其實兩地百姓,並無多少族群分別之心,大多都能和平共處,只可惜天下悠悠,卻總有人出於各種原因,煽動民族情緒,唯恐天下不亂。倘若有朝一日,世人都能如小兄弟所言,放下成見,互補長短,融合發展,那就是天下大同了。」
樂器聞言一怔,突然大喜道:「好一句天下大同!實不相瞞,在下作了一曲,苦思多日,難求一名,這下好了,蒙錢老闆提點,此曲便取名為《天下大同》了,妙也、妙也!」
說罷,他又以手掩嘴,鼓動著咽喉腮子,開始「彈奏」了起來。這一次所奏,卻是一首眾人聞所未聞的曲子,果然如他所說,曲子以各族數十種樂器合奏而成,瑤琴胡琴馬頭琴,鑼鼓竽箏笙鈸鈴,排簫梆笛葫蘆絲,嗩吶哨角板鐘磬,不一而足,甚至一度還隱約出現了木魚、口哨等奇門樂器。雖然樂器眾多,但經他對樂曲浸淫多年的功底編撰出來,卻又繁而不雜,各種音調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曲風輕快歡樂,又不失深沉追思;一片欣榮繁盛之意,又隱含謙和穩重之心;一時如百鳥朝鳳,載歌載舞,一時又如君臨天下,浩氣衝天。此曲意境恢弘,氣勢龐大,包羅萬象,縱橫古今,實在不愧「天下大同」四個字。
圍觀眾人聽得如痴如醉,時而輕拍附和,時而肅然感懷,但一曲未罷,卻突聞一把聲音怒喝打斷道:「放肆!住口!」樂器停下一看,卻原來是朱夫子。只見他漲紅了臉,怒髮衝冠,厲聲怒罵道:「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堂堂華夏正音,被你玷污得烏煙瘴氣、不倫不類,子曰『禮崩樂壞』,此所指也!異族犯我中華國土,他日猶可重新奪回;但你如此曲風一旦出世,把我華夏化作夷狄,千年正統文化消磨殆盡,則我華夏再難有翻身之日!你身為漢人,卻不知廉恥,竟如此公然羞辱我華夏文化、出賣我華夏靈魂!氣煞我也、罪大惡極、氣煞我也!」
話音剛落,呂大人哈哈大笑,說道:「朱夫子呀,這也太小題大作了吧?不過區區一首曲子,便能顛覆你那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倘若當真如此脆弱,又豈值得你這般推崇?常言道真金不怕紅爐火,又言道宰相肚裡能撐船,夫子連一首樂曲也容不下,卻不知真正在羞辱你家華夏的,正就是夫子這般的自卑自棄,實在可笑,可笑呀!」
朱夫子怒不可遏,卻漲紅了臉,說不出半句話。這時樂器也顧不上朱夫子,轉頭對呂大人喜道:「如此說來,呂大人喜歡在下這首曲子?」
呂大人點點頭道:「我氐族人沒有朱夫子那般的迂腐!當今天下,各族混居,民族融合,乃大勢所趨,你這首樂曲,正好體現了此天下大勢!只不過,曲子好是好,卻略嫌成分不對!」
樂器追問:「是缺了意境?還是少了感情?願聞其詳!」
呂大人捋著鬍子,搖頭道:「那些本官一概不理,本官說的是成分,樂器的成分!」他一頓,繼續解釋道:「我涼州是個多元民族聚居之地,有六成漢人、三成氐人、半成鮮卑,其餘吐蕃、柔然、羯、羌等總佔半成。是以這首曲子也得稍作修改,須得有六成漢人樂器、三成氐人樂器、半成鮮卑樂器,如此類推。」
樂器皺眉撓頭,為難道:「可、可是如此一來,曲子就壞了!難道曲子之好壞,還不如其成分重要?」
呂大人板起臉道:「當然!成分關係國家之政、社稷之治,當然比曲子本身重要!非但樂曲,我衙門用人、軍隊徵兵、朝廷賑災、乃至大牢刑犯,都應按此成分處理,如此方才可真正體現朝廷對治下各族百姓一視同仁,不偏不倚!」
樂器搖頭苦笑,只覺不可理喻,無言以對。
另一邊,朱夫子見現場人多,不好發難,連連悶哼,忿忿領著自家弟子,躲進了帳篷。呂大人見樂器不認同自己的主張,悶悶不樂,也不再搭話。錢老闆甚喜樂器之才,拉著他說了幾句,邀他同行,樂器卻另有打算婉拒了。這一晚雖然弄得有些不歡而散,但總算沒出什麼大事。
次晨,四夥人馬分道揚鑣,各奔東西。樂器獨自上路,走了不遠,身後有人追上,回頭一看,卻原來是朱夫子師徒數人。正要開口招呼,朱夫子卻已厲聲罵道:「賣國小賊,留你不得!」話音未落,大夥一擁而上,七八個人把樂器圍毆至死,切下了頭顱,棄屍而去。可憐一首曠世鉅作《天下大同》,從此成為絕響。
話分兩頭,卻說錢老闆受樂器啟發,在行商旅途中不停物色各族樂器能手,收編入府,多年後組建了一支戲班子,融合各族戲、曲元素,新穎的曲調風格大受百姓歡迎,闖出了一番名堂,也為這中華大地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作出了潛移默化的貢獻。
呂大人回到涼州後,繼續堅持以民族成分論治理轄區,表面上似乎人人膺服,實際上卻導致人才埋沒,奸佞當政,冤獄叢生,人心背向,民怨日深。
再說朱夫子回到江南,不知如何,殺人之事洩漏出去,叫官府知道了。他正憂心焦慮,不料官府卻對其所作所為大肆表揚,把其事蹟傳抄全國,立為守護華夏正統之榜樣,激勵臣民擁護大晉正統,共赴國難,以期來日驅逐胡夷,重奪山河,北定中原。
嗚呼,可笑、可笑!可嘆、可嘆!天下各族人民,即便生前髮肤之色各異,死後白骨卻難道能分彼此?人民本不曾有分別之心,各族融合也有百利而無一害,卻可恨當權之人總愛煽動民族主義,似呂大人這般的成分論,根本無稽荒謬,此非不知民心,而是有意為之,以民族情緒分化百姓,維護權利。諸如朱夫子之輩,除了可恨,更為可憐,他們受惑偏執,繼而散播虛妄主義,與樂器相比,他們才真是官府手中的「器」!
如今時移世易,當年琵琶胡琴嗩吶等異族之器,早已成了華夏正音,然而天下族群分別之心卻從來有增無減,愈演愈烈。只問樂器的一首《天下大同》,何日方可輝煌再現?3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EsnAgfL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