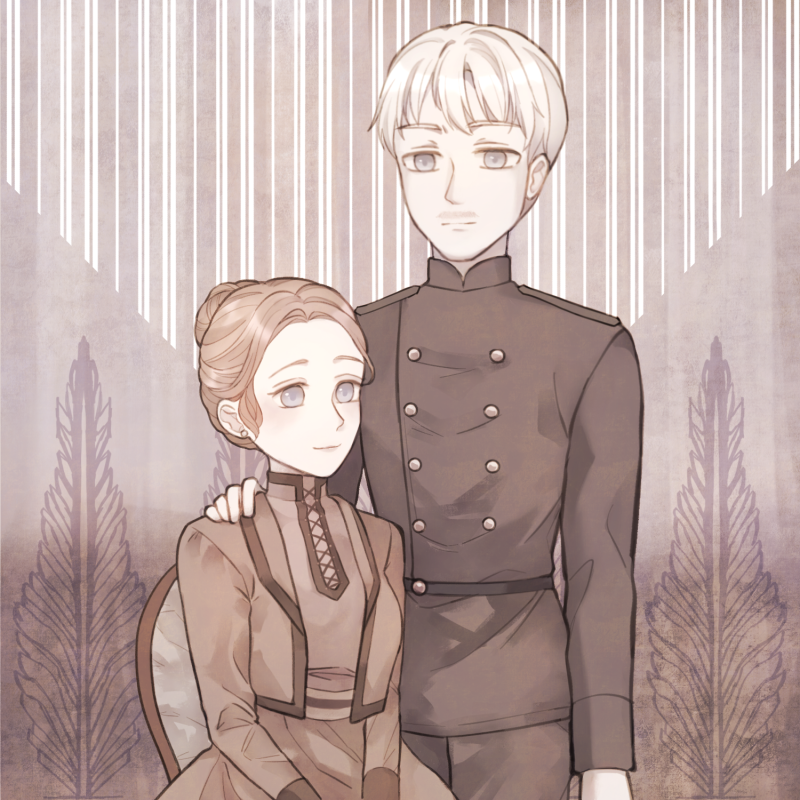 x
x
※本次配圖:維榭洛夫家的父母
作者前言:
上次被假帳號留言事件氣到忘記要放圖,原本要之後補放的,但一想人家夫妻在爭執,我卻放他們剛新婚時的合照,好像感覺怪怪的耶,所以就挪到下篇XD
當天色近晚時,躲藏在東側翼樓的人們悄悄地離開了大宅。彼嘉分次領著一或兩個人來到後門,其中一個工人在半路上回過頭,脫下帽子向母親致意。奧黛塔望著那些遠去的人影,想像他們回到家中與家人重聚,生起爐火回憶這段劫後餘生。
副官特魯別茨科伊在可以下床行走後,也回去了參謀部報到。奧黛塔好奇這位副官是否知曉自己並非公爵家唯一收留的傷患。如果有,那他似乎也佯裝不知情,除了表達感激之情外,他便什麼也不透露了。
維榭洛夫大宅裡的所有人都被要求封口,不許將這兩日家中發生的事情洩漏一個字出去。唯有男主人與女主人之間的隔閡反而靜默地延續下去。冷漠的煙硝味殘留在空氣中,也時不時提醒孩子們那一日的驚魂。他們只敢偷偷聚在一起,藉由彼此的證言與各種管道得來的消息,拼湊出事發經過。
協助夫人治療傷患的彼嘉和安東妮娜對當晚的事絕口不提;尼基塔不停裝傻充愣;膽小的瑪莎根本像個被嚇壞的孩子(奧黛塔頭一次意識到,大人有時候會和小孩一樣害怕);在當週放假的家庭教師們則早就被父親和母親輪番打點過了,只有好心又靦腆的斯特恩女士被奧黛塔和阿列克榭追問出一點東西。至於杜尼亞莎,老嬤嬤會擺出一副要把他們這些孩子一個個拎起來,丟進橡木桶裡刷洗乾淨的氣勢,根本沒有人敢多打擾她兩句。
在所有莫可奈何之中,值得小小慶幸的是,罷工結束後,父親難得有了幾天休假可以陪伴家人,偶爾也會叮囑學生的課業。家裡的氣氛雖然逐漸緩和了下來,但父親和母親仍然各自忙碌,甚少聚在一起講話,即便他們碰面了,也會立即想起有別的事要去做,彷彿對方的臉上寫著他們遺忘的待辦清單。
少了父母在壁爐邊的溫聲細語,讓姊妹倆都很不習慣。沒有雙親的陪伴和出外的機會,使她們膩在一起的時間變得比平常還要多,也更常去同康汀斯基兄弟們說話。
即便是最年幼的孩子也沒有了玩樂的興致。花園的小路被清空之後,他們會聚在奧黛塔最喜歡的小花園裡,觀望著牆外的城市緩慢地復原,等待晨雪再度在人們的腳下吱吱作響,而麵包坊和工廠的炊煙會升起一條條藍灰色的柱子 (註4),切斷灰白的天空。
然而,聖彼得堡只留給他們疲憊的沉默。街上再也沒有人歌唱《天佑沙皇》,因為沙皇用冷漠和鮮血證明自己再也不是人民慈愛的小爸爸了,一如上一個尼古拉一樣。(註5)
唯有送葬隊伍的歌聲,從早到晚都從未斷絕過。
革命意味著什麼呢?他們用還不成熟的生命去思忖著、想像著。帕維爾和吉賽拉年紀大到可以讀懂革命在書本上是怎麼被記述的了,所有的革命都是流血與衝突,但那與他們在那一晚所聽見、所看見的,那些唐突的衝擊,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奧黛塔和阿列克榭從家庭教師口中聽到的革命,僅只是輕輕地被一段描述帶過:普希金的朋友們投身了十二月黨人(註6)的革命,在沙皇冰冷的命令下,年輕的生命斷送在處刑台和西伯利亞的凍土上,卻沒有提及革命與戰爭一樣,會帶來槍響、傷口、憂心會失去所愛之人的懼怕,並撕裂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低沉哀泣的安魂曲持續了整整一週,有時直至深夜,仍然如幽魂般縈繞在人們耳邊,甚至鑽進孩子的夢境裡。奧黛塔開始夢見圍繞著她跳舞的斯芬克斯。人面獅身們口中唱著聖歌,卻跳著異教徒的舞蹈,火焰照耀牠們濃密的鬃毛、艷麗的面孔,以及尖銳的獅爪,美麗又恐怖,神秘而驚駭。
妳的謎語是什麼?左邊那隻藍眼的斯芬克斯高聲唱著。
守護妳的聖人是誰?右邊那隻斯芬克斯瞇起了牠的綠眼。
妳需要聖名與謎語,才能成為我們!才能成為俄羅斯人!不然就得流血!中間那隻狹長灰眼的斯芬克斯亮出獠牙,顫抖著舌尖喊道。
我沒有聖名,也沒有謎語。她只得驚慌地喊叫,卻忘了回答她不想流血。
斯芬克斯不知道是狂喜還是狂怒,舞蹈變得更加激烈。牠們屢次伸出爪子,奧黛塔害怕牠們會劃傷她,像對付一隻老鼠一樣輕而易舉地把她撕碎,但那些爪子幾乎不曾觸碰到她一吋。然而無處可逃的無助感,仍讓她難以呼吸。
當獅子的前爪真的快要碰到她時,槍聲便會響起,斯芬克斯們一隻接著一隻倒地,沒有傷口也沒有流血,彷彿只是昏睡過去一樣。
待最後一隻斯芬克斯也倒下後,她會聽見遠方有一隻鳥兒發出淒美、綿長的哭叫,雙翼鼓動的風聲宛若教堂的管風琴,離她越來越近──
奧黛塔喘著大氣,一身冷汗地醒來,胸口的阻塞感遲遲沒有消散,讓她連伸手去碰手搖鈴的力氣也沒有。她只能抓緊床單,憋住湧起的眼淚調整呼吸,往往要花上好一會才能睡回去。
她翻來覆去,瞥見稀微的月光微微照出牆角掛幔的圖案。掛幔上,長著少女臉孔的一對鳥兒安詳地棲坐在蘋果樹上,彼此為伴。她看著那對鳥兒,怔怔地眨去淚水,緩慢地吐氣。
幸好,這種夢一晚頂多發生一次,她第二次入睡後就沒再夢到了。
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DPzA7sd5g
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YBnZkTZvM
這凝滯混濁的空氣,在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夫婦來拜訪的那日下午又被攪亂了一次。他們登門的目的是為了道別,並帶來了一個不是太好的消息:謝爾蓋又得臨時借走教子,處理卸任莫斯科總督的交接事宜(註7),兩日後就要啟程。奧黛塔失望不已。父親好不容易才能有空在家裡待著的。
「如果您要帶爸爸走,那、那,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莫斯科!」她頓時跳起來,慌張地往父親身上撲去。「等您忙完之後,就要馬上讓爸爸回家!」
謝爾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黛特琳娜,妳確定要跟來嗎?」
「我要去!我要跟爸爸一起去!」她揚起頭,神色仍然慌亂,語氣卻無比認真。
「舅舅,別答應她。」迪米崔出聲反對,皺著眉滿是不贊同。然而謝爾蓋沉吟了一會,隨即爽快地應允了:
「那好。妳就和妳爸爸一起來我們家。」
迪米崔揉了揉小女兒的頭髮,不知道是出於煩躁還是擔心,看著她仰望自己的小巧臉蛋滿是懇求,卻又啞口無言。
「不要緊的,米提亞,多一個孩子而已。家裡的空房間多得是。」麗茲開口緩頰,順帶提議。「而且來我們家也好,她可以順便幫忙我寫一些慈善會的邀請卡,提早學一點怎麼打理事情。吉詩卡,妳也要一起來嗎?」
麗茲看向靜靜喝著茶的吉賽拉,含笑詢問。吉賽拉淺淺地搖頭。
「謝謝您,但是學校很快就要開學了。我就不去了。」
說完,她意有所指地朝妹妹斜睨了一眼。奧黛塔才想起來家教課程不久後也要復課了,尷尬地別開臉。
謝爾蓋把一切都看在眼裡,好笑地哼了哼氣,往一直安靜不出聲的塞西莉望去。她意識到謝爾蓋的視線,端莊地望了回去。
「塞西莉,妳願意把妳的丈夫和小女兒借給我們作客嗎?」
「如果只有兩週的話,」她溫聲說道,「只要您能在獻主節(註8)之前讓他們父女倆回家,那請您和伊麗莎白代替我好好管管他們。」
於是奧黛塔的莫斯科之行就這樣拍板定案了。她匆忙打包行李,對於到底要帶什麼東西猶豫不決,索性跑去找母親詢問。母親和姊姊恰好在整理舊東西,於是她湊上前去,卻被這滿箱的舊物給吸走了注意力。裡面有著母親過往少女時代的物品,有些還是從大海另一端的故鄉攜帶過來的。
「媽媽、媽媽,妳從哪裡學會治療的?」母親在整理舊物品的時候,奧黛塔湊到她身邊,好奇地問著。「在⋯⋯蘇格蘭嗎?」
她想起地圖,大西洋上叫做不列顛的島,島又分成了三塊。蘇格蘭在最北方,傑金斯先生則是來自中間那一塊叫英格蘭的地方。他們要怎麼從那麼遠的小島過來俄羅斯?英國就和世界盡頭一樣遠!
「是的。」母親語帶懷念,只要提到故鄉,她就會以這種語氣說話。「蘇格蘭有個叫愛丁堡的城市,我在那出生,但我在讀愛丁堡醫學院的時候,學院中途停課了(註9),我才跟妳們的外公過來聖彼得堡旁聽,之後才回到愛丁堡繼續讀書。」吉賽拉剛好從箱子裡找到一幀證書。「對,就是這個,親愛的,請交給我。謝謝妳。」
「愛丁堡的學院為什麼停課了?」吉賽拉敏銳地注意到這個轉折。
「他們決定不了大學到底要不要開放給女孩子。」
吉賽拉做了個厭煩這個老問題的鬼臉。
「那妳成為了醫生嗎?」奧黛塔望著母親,又看了看證書,眼裡閃爍著敬佩。「像沙巴諾娃(註10)一樣在醫院工作?」
「我⋯⋯曾經是。」母親罕見地遲疑了下。「現在不是了。」
「為什麼妳現在不是了?妳明明能做到跟醫生一樣的事。」吉賽拉從箱子裡找到更多的醫學書籍和筆記,拿起其中一本,輕輕撫著書封。
塞西莉神色迷惘地看著那箱教科書和筆記,每一本都覆滿了被反覆翻閱書寫的痕跡。
「發生了很多事情,大老鼠。有些我沒辦法改變,也沒辦法決定的事。有些⋯⋯讓我害怕可能會失去妳們的事,我必須有所選擇。」她把女兒們抱進懷裡,閉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氣,彷彿小小的她們身上藏著她已然失去的珍貴事物。
「但我很高興我有了妳們,我的驕傲和喜悅。」
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u8fhfS4BR
註4:這兩句同樣致敬了《奧涅金》1:35節:奧赫塔婦女提著奶罐走得急,晨雪在她腳下吱吱響起。/炊煙升起,像似藍色的柱子。奧赫塔是聖彼得堡東北郊區的一處地名,得名於注入涅瓦河的奧赫塔河。
註5:上一位尼古拉是指尼古拉一世,他和尼古拉二世的任期內都發生了革命,發生於尼古拉一世任期內的革命便是十二月黨人事件。
註6:十二月黨人事件是1825年由青年軍官所發起的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因發生在十二月,相關參與者被稱為十二月黨人。此次事件深深引響了俄羅斯社會,如普希金與列夫‧托爾斯泰等作家都有在作品中提及此事件,參與十二月黨人的起義者有許多人正是普希金的好友。
註7:在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之後,謝爾蓋大公辭去了莫斯科總督的職位,只保留軍區指揮權。
註8:獻主節,又稱聖燭節,是東正教的十二大節日之一,對應儒略曆的2月2日,是耶穌出生後四十天受洗禮的日子。
註9:愛丁堡大學醫學院雖然於1869年起有七名女性先鋒進入該校,就讀醫學課程,被稱為愛丁堡七人組或愛丁堡七姊妹(Seven against Edinburgh)但這七人被最高民事法院裁定不得錄取,也無法畢業或取得醫生資格,此事件獲得了社會大眾廣泛的關注,從此開始了英國女性爭取大學教育的漫漫長路。
愛丁堡醫學院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對於女性入學的政策,反覆在稍微放寬與徹底禁止之間擺盪,1886年成立的愛丁堡女子醫學院也時常因為金源不足關閉,也不敵英格利斯父女(Inglis)成立的愛丁堡女子大學醫學院以及其他開放女性入學的學校競爭。
註10:安娜.沙巴諾娃(А́нна Шаба́нова)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第一批取得醫學學位的女性之一,同時也是第一個被俄羅斯官方認可的婦女公共事業營運協會與慈善互助會的召集人。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KD4I33SEe
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dCgRSxizV
41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KZ1Q9R9aH
2024.11.25的更正
在描述關於愛丁堡醫學院的段落,我原本是寫塞西莉拿到了聖彼得堡女子醫學院的畢業證書,但因為我沒有查到當時的俄羅斯是否接受外籍女性入學並核可辦法證書,為保守起見,改成在聖彼得堡旁聽,之後才又回到愛丁堡學醫。
ns 15.158.61.17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