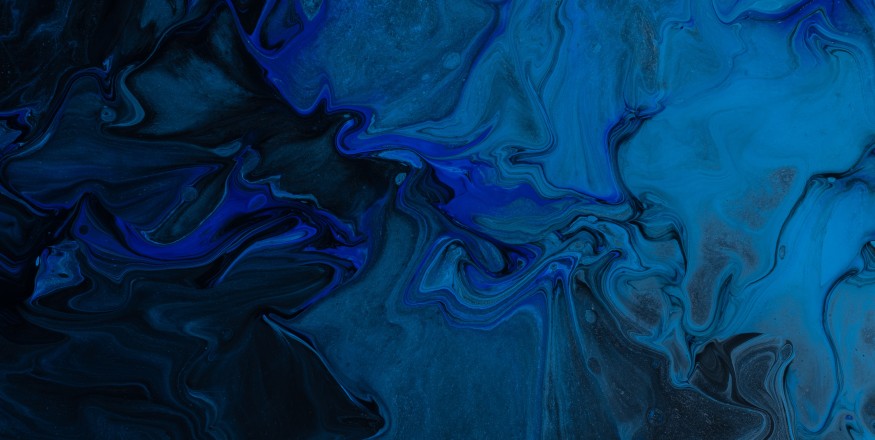/潜州者,积雪山北,落雁川南,罗多、大叶、大商三国之交界地也。天旱无雨,田荒地贫,以是中土人多以废城称之。元康三十三年,白蛇军自麟州来,破龙山、黑水、青衣三路贼兵,乃定居,自改元崇泽。又学《宣言》律令,均地权、办新学、勤课桑、砺甲兵,于是流民四集,商贾满路,十年而遂成公社。时虽有外寇略地,山贼反覆,终不致倾覆也。/
————《公社史》
/在潜州,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公社。孩童从小便被公社中的养育司管理,按照其生辰八字赐姓,随后被赐名。少年后,他们将被送入公塾念书,期间一边从事实习生产一边学习各类知识,这九年被称作义务启蒙。十六岁时,学童们会进行第一次分流,届时会有一部分少年加入一些长期专业领域,如驾车、考据、兵甲等。而少部分人又会继续读书,最终按照职业难度分别选择就业。当这些青年达到20岁,他们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字和号,随后便可以自由恋爱。公社中没有家庭,人对于爱情的专一程度全由自己决定。他们可以自由地恋爱和做爱,但是,他们并不会生下孩子。公社通过垄断接种的方式断绝了“私生”现象的产生。换而言之——一切的孩子都是公社的孩子,公社是一切人的父母。这种奇怪的方式似乎是为了断绝了人类的私心,以促使任何个体在死亡时不留下活的遗产。——公社便是如此繁盛起来的,当然,这些不可思议的点也成了周围诸国尤其是大叶王朝的皇帝谢狮所讽刺的对象。/
————《续白话宏祖游记·卷三》
/公社的建立人物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公社来自于白蛇教教主白百花和她背后的势力白蛇教。但是,由于白百花在崇泽四年七月大叶战场上的莫名失踪,这个说法变得难以推敲起来。其他少数人认为,公社来自于第一任公社领袖、中土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暴君——张若离,当然,世人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百家。据柳别清在《公社词谈》中的考据,百家似乎是前朝(也是中土最后一个大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商的官员。而据潜州地区流传下来的戏剧里曲描述,此人甚至有可能是商朝元康二十四年科举的探花(即旧时科举制度的第三名)。目前正史对这段历史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描述,班宪所著的《公社史》仅评论道:'立公社、扫诸合,有矢皇遗风。兴课桑,均地权,尧舜其由病诸。而后炼黑铁,立四十九座天塔,则劳民费力远甚于金塔长城运河矣。公社之治乱,大抵成在此人,败在此人尔。'/
/在更底层,一个故事是这么形容公社的构建的:那张若离原是汉人的一个探花,后在守城期间因不满接受洋人的殖民而与白蛇教结盟,最终被当时的麟州城主谢狮陷害,含冤而死。这时,有位神仙为他救世的决心感动,于是那位神仙施法让张若离复活。为让他能为天下众生考虑,那位神仙从每个人的身上都拔了一根头发,并用这些毛发编织出了一个新的肉体,好令他起死回生。——这便是百家名字的由来。而后,这位神仙将仙书传给了百家,这便是公社塔下所刻的《宣言》。当然,这个故事只是反映了善良的劳动人民的一个朴素的心愿,怪力乱神,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是完全不可考的。/
————《揽云亭别史·公社篇》
你又来了。是来继续听故事的吗,还是只是碰巧路过。哈,我已经给你讲了很多很多了,从我在那个小客栈开始,到酒镜山、雨园,从在京口守城,到遇见海客,这个故事已经很长了,太长了,你都厌倦了,对吧。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故事很快就结束了。用你们这边的词语说,大结局,很快就要迎来大结局了。当然,这样说也很不对,毕竟我还没有死,我还好好地活着呢。算啦!还是让我继续谈吧,现在已经谈到潜州城了。
我第一次路过潜州时,公社还十分繁荣。那时“私生现象”还没有那么普遍,整个公社被计划得井井有条。苍铃果、黄沙荆,这两位稀缺的草药便出现在潜州附近,那时距离我离开海客、独自出来寻药已经过去九年了。
向依行。这个名字早已被世人忘记,在我离开京城的一个月后,这座傲立了几百年的城市便被屠戮一空。据说皇宫的火烧了七天七夜,商江甚至因为抛投了太多的尸体而断流。海客遵守了他的承诺,我开始学习各类道术,了解神创造独影世界的原理,甚至后来我开始学习天界的物理规律。海客大叔说我学得很快,不出三年时间,他便惊讶地认为我在道术上已经超越了他。
似乎确实如此,我学会了通过现象的分析来诊断每一类的对象,悲鸣的鸟、枯残的荷叶、打着旋的溪水——我丧失了对一切事物的观感,他们在我的眼睛中,就像是一堆又一堆变来变去的变量。这个对象包含了哪些属性,又继承了什么基元,某个参数调整到了什么特殊的阈值,又拥有哪些必备的咒语。海客说我已达到了目无全牛的境界,于是我们相约十年后在意室的服务器中见面。那时他会提供“偷渡”的通道,当我从独影世界走出进入意室常规般服务器时,他会接我到外网里。十天时间攻陷意室并提供偷渡的隧道,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海客大叔说他会寻找所认识的所有海客一起帮忙,无论如何,十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那之后,我们便分开了。
冒险的故事我给你讲过,讲过很多。现在回头来看,我似乎真的是那一夜——端木姑娘离开的那一晚上才成熟的,又或者,是这十二年的日子让我一点点成熟。我终于隐去了自己的真名,可是他们却给我起出了新的名字,“麻袋道人”。每我去一个新地方,都会有无数人找我求道问药。不知过了多少年,他们又称我为菩萨,说我四处游历是为了度化世人。可我的心或许早就干裂碎了,早就麻木了吧,就像是一块粗糙的、深深扎入地底的颓懒的老树。无数次的陷阱已经把我的善心凝固成了一块坚冰,如果没有海客传给我的道术,或许我早已死掉了。我四处游历,又不过仅仅是在找寻那真经上所列的仙药,以及那个,——白蝌岛。
仙药并没有那么难寻。似乎是因为机缘,或别的一些事情,按部就班里,那些药材竟一点点地凑齐了。但是白蝌岛的踪迹却仍然是个迷。无数的传说和故事都提及过那个岛,可是白蝌岛又不曾露出哪怕一点点的痕迹。我曾经在烂陀山无影峰前听隐居的白蛇信徒说过白蛇遗蜕的事情,也曾在东海听自称是金矢皇时代的炼丹大师曲胡的子孙讲起过在白蝌岛上的趣闻,可是真正的白蝌岛,却仍然是渺无音讯。最后,在西方的一个饭馆里,我遇到了一个奴隶。那位奴隶向我谈起几百年前他的一位祖先。那位祖先曾经是一名僧人,后来异教军队入侵,烧了寺庙,那位僧人才不幸还俗。据他所说,当年他们寺庙曾经留过一位从东方而来不远万里孤身求法的僧人,那僧人曾经留下一本日记,而日记中则有对于白蝌岛的记载。
白蝌岛……我都有些灰心了。那奴隶口中的书籍早已被焚毁,可是那位名为笙商的僧人名字却让我印象深刻。最终,我终于找到了那位僧人,他自西土回返后,便一直待在一个简陋的、名为斯深寺的寺庙中。而斯深寺便在潜州。
在我到达斯深寺之前,我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黄沙荆,可那苍铃果却又不得不等到三九寒冬才能从高原的松树岭中摘到了。于是,我用道术化妆成和尚混进了斯深寺,开始不动声色地探寻起那僧人笙商的踪迹。
那斯深寺说是千年古寺,实则荒颓异常。公社里的公民都信奉积极入世的思想,虽每七日会去潜州的大佛寺中冥拜如来,但山边的如此小寺,就免不了香火凄凉了。寺中可怜,只有四五位从周边村落中出家而来的和尚,以及一位双目早已失明的方丈。
那方丈法号槁木,双目早已失明,但对待佛法却十分虔诚,每日诵经不断,日夜不免。我去拜见他时正是初秋,那时秋雁才刚刚开始南移,冰冷的秋雨一连下了七八天,直到我去时,太阳才有气无力地从诸多云彩中发出亮光来。槁木站在院中,双眼呆滞地望着天空,闻说有僧人远道而来的事情。
“是个麻袋和尚。”那位小和尚便是如此通融的,槁木听了也只是笑了笑,他冲我招招手,似乎是早已知道我就站在他旁边。他指了指那片天空,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小和尚似乎对他师父的这番异举早就见怪不怪,而我只能抬头看去,无数的变量都被中间的一个巨大的函数所释放,而释放出的内存又被拿来生成出大量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一经生成便欢呼跳跃,不知被分配到哪里去了。我该怎么样描述这个现象呢?我最终只能拿出之前在京城时端木琴他们所说的话:“我看到了一个大洞。”
“你看得见?”还未等他说话,小和尚便率先问出了声。
“这洞并不是洞。”我双手合十,模仿着和尚的样子。
槁木只是摆了摆手,让那小和尚退下,而后坐在椅子上,让我一齐坐下来。我知道,他肯定要说什么。
“贫僧……”他刚开口,就停了下来,无奈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对往事已经漫不关心一般。他说道:“贫僧原是麟州人士,自小便出家为僧,研习佛法。后来不过十年便熟记精研了四十二章佛经、通晓穷极各律论。或是尘缘未了,还俗后,曾在麟州的一座古峰内得见天地造化,窥得如来密藏。可那一窥……其代价便是老衲的这两个眼睛——”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凄凉地笑了笑。我望他不过中年,却自称老衲,也跟着笑了笑。
“从那之后,这眼睛便看不清任何事物了,仿佛是堕入了真正的无明。可每次我抬起头,我发现,我竟然能够看到天上,”他说这话时,又忍不住抬起头来看,“能够看到这天上突然多了那么一个大洞。他们都说我的眼睛是被太阳光给灼坏了,或许吧!多少年啦,我从江南躲到海北,又躲到西南,最终来到这里——我只见得天上的大洞越来越大,就像是一个早已烂了的伤口,怕是这天——”
“当然还有救。”我说道。
槁木听到这句话愣了愣,随即苦笑道:“我有一个朋友也说还有的救呢!”
“那……方丈难道不想听一听真相吗?实不相瞒,我来这斯深寺不过是为了求一旧物。为此,我可以将我所知全盘告诉方丈。”
“哦?”槁木将耳朵凑过来,“阁下千里迢迢而来,所为何物呢?”
“还是先让我讲出真相吧!”于是,我开始小声地给他讲起来。
那日我从下午给他讲到黄昏,都是一些他闻所未闻、却又不得不深信的故事。白蝌岛,他听到了这个名字,便也同我讲了关于白蝌遗蜕的经历。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小和尚又跑来说炊饭已熟时,他似乎才恍然大悟:“我知道你为什么过来啦!”
我和他一同吃了两碗斋饭,他便带我来到佛堂旁边的一个卧室中。“这就是当时三藏法师笙商的居所,现在被当作我的卧房。”他似乎有些尴尬,但我能理解,毕竟斯深寺只有这么大。“当年笙商西行归来后,便于此室内闭门不出,一心只翻译他所带来的三万卷经书。后来他双目失明,便自己口述,令其弟子记录,如此才将天下佛经以及诸新论翻译完成。”槁木叹了口气,“可即使如此,这些经书理论也不过三世便断绝了。”语罢,他便将床板拿开,那三万卷经书竟就在床板下!“可惜我再无缘分钻研这些经书,只是让弟子们先钻研,随后与他们讨论。如此进速虽慢,这些年却也看得七七八八了。”
“那……方丈可曾有什么线索?”
槁木摇了摇头,“除了《大裳西域记》中的一篇有零散的一丝描述之外,其他地方便再无线索了。”我便按照他的说法找到了那本《大裳西域记》,他似乎已经记下了书页,我翻到那页,书页上写道:
“國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慘烈。多暴龙难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喚。微有違犯灾祸目覩。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山行四百余里至热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狹。四面负山众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咸苦。洪濤浩汗驚波汩㴔。龙鱼杂处群怪间起。更有一巨龟。长二百余里长沉海中。时人说以三千六百年浮上而换一气。龟上有一岛。白岩所筑。谓之白蝌。时余尝试登之。岛上有荒洞。存金玉如来像。不可近观。乃记之而去。国人谈白蝌。言甚灵验。不日将复归海里。以是往來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
“大龟上的岛屿……”我那时才获得了白蝌岛的具体地址,“只是,那片岛真的还存在吗?”槁木没有说话,只是道了一声,阿弥陀佛。
我本以为到此便算圆满,谁知那时槁木又拿出了一样更重要的东西。也正是那件东西,救了我一命。
“那本西域记的书下,还压着一本佛经。阁下也一并取出吧。”他微笑着说道。
我便也将那本书拿出。其上只有四个大字:“然灯古经”。
“这是……”我纳罕道。
“打开看看便知了。”
我便打开——“这是,没有文字?”
槁木点了点头。“这本经书据说是当时笙商所翻译的最后一本经书。有人说这经非人类文字所能载,故本来无字,笙商所译亦无字。有人说笙商读罢这然灯古经,自觉无法翻译,故此经书无字。还有人说,笙商已翻译完毕,不过此经甚为高深难解,凡人难见,故无字。”他停顿了一下,“自老衲双眼失明后,这本经书常放大光明,余读之,乃是甚深微妙、不可思议之法门。既然阁下有如此宏愿,又能看到天上的洞,不若一试。日后转入他方佛土,必定功德无量。"
我便打开那本经书,用海客教我的道术看去,原来这经书内容竟是一行行的注释。其上所载是一个故事:十七号在创造了白蝌岛后,为了让此世的有心人可以得入天界,便提供了那炼药一方。可是药方仅是其一,在药方之外,这由人入天的原理却未曾彰显出来。当时十七号在构造独影世界时,为了降低生死的带来资源消耗,便构造了一个基于指针的简单软拷贝——这便是所谓的轮回。在这种理论下,人的三识将不得不经历意识上的大风暴。这些风暴本质上便是对意识诸对象的一种析构。总体上看,这样的析构主要有三次:在人将死时,天地之间自然的规律将会首先析构掉人的肉体,将其纠缠状态解除,如此介于新人和旧人之间的状态——中阴身将会继承人在三识中的各变量,返回给第二个析构函数。而后,在第二次析构中,宇宙将通过无量无边无数的幻想来让意识产生疲倦,最终实现对意识的混淆,这个通过混乱来抹灭信息的做法被称作去坍缩化。常人将在这一次析构中失去所有个性化的记忆,由此将意识回归至完整的分布中,而后这一分布的具体参数,也就是人的个性,将同该人的自我意念一起被传入到最后一个析构函数中。而这一次析构,就是新生了。第三次的析构本身,也是构造,它将从已有的人格分布中采样出新的人格,一般由于旧有人格在第二次析构中被混淆出了较一般的分布,所以轮回中常常包含各类变异。新人格和旧有的人格混合后将被作为初始化的参数传入到新人中作为最基本的意根。随着胎儿的发育,意识、记忆、以及剩余的诸色识将缓缓成熟,如此循环往复。
在这一套理论中,白蝌岛内可炼出的仙丹,本质上是一剂毒药。该药会提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触发析构函数,使得人经历死亡。只是与一般的毒药不同,这种毒药会为析构函数传递一个特殊的参数,——该参数自然是17号预留好的,这个参数使得在经历前两次析构后,所获得的诸识参数会被传入到额外的一个析构函数中。这个函数几乎没有被触发过,它将起到创造的作用!这个析构函数便是祂在第七天的杰作,它本质上是一个后门,一个真正的白蝌岛。这次析构将通过通讯协议捕捉被打散的诸识,并在意室公司服务器的一个隐藏角落里将诸识拼接,并构造出一个新的人。
我读到此处,才真正理解那日下午,海客所说的”比守城而死更难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了。
8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L8xMUte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