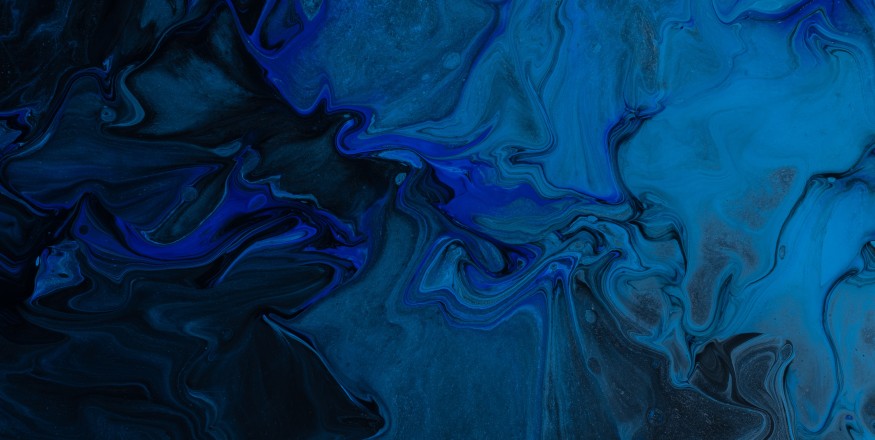她那时就坐在这样的长凳上,一十九岁左右,和现在一样。
而我呢不足十岁,正在柜台上发着呆。那时我一边晃着腿,一边看来往的商客和农夫端着煞人的高粱酒往粗红的脖颈里灌去,粗大的喉结就顺着从嘴角流出的酒水而上下蠕动。他们每喝下一口酒,快活似乎就能从那些粗大的毛孔里渗透出来,于是整个房间里都会布满笑声。那时,母亲总会嫌他们的笑声吵,而我似乎天生就喜欢这种氛围——这便也让我后半生的惩罚变得足够残酷了。那时的她,便如现在这般安静地坐在长凳上,只不过怀里揣着一把长剑——一把甚至比我还要高的长剑。2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WOeX4pON3
她只是静静地坐着,低头擦拭着那把剑,就像从说书人袖口中所抛出的那样、那些侠客那样,她周围似乎隔绝掉了所有的笑声,只剩下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异感觉。
没人招呼。
或许是天意,也可能是……命运,——当然,当时的我只当是一个玩笑,我抱着酒壶往她那边走去。我想为她添上一碗酒。
“不错嘛。”她看我过来,于是握着剑鞘的手松开,银铃摇晃,轻轻碰触到我的额头。那双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冰凉。我仍然朝后扯了扯头,因为我娘说过,不能给人摸头。
她倒也不介意,拾起碗啜了一口,便道:“加糖。”
“这是酒,不能加糖。” 我从未有见过有饮酒还要加糖的侠客,即使是女的。
“没有白糖嘛?”她站起身,似乎在找我父亲。
“有果子糖。”我把兜里的糖拿出来,投到了她的碗里。这时,我的脑袋结结实实吃了一个板栗,眼泪便莫名其妙地流了出来,我很快知道我需要哭出声了。一双大手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到了一边。“你的手脏不脏!”是老爹的声音。
“无妨。”她淡淡地说道。“是我要他加的。店里有白糖么?”
父亲迟疑了一下,她便知道,在这种店里,哪怕找到点白糖都是不可能的。
“那算了。”她从兜里掏出几块碎银,而后便对着窗外浓厚的叶子自斟自饮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真正的侠客。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她。
之后,老爹便骂了我一顿。他说那是江湖中人,我千万不能招惹,不然剑拔出来的一瞬间,人头就会掉到桌子底下的。他又说江湖上的大侠脾气都特别古怪,——尤其是女侠。而偏偏,这些女侠都是难得的消费主力,动不动就是成锭成锭的银子,故而好不容易出现几个这类顾客,若被我这种毛孩扫了兴,那么出去玩的事就再也别想了。
我都同意着老爹的话,因为我想出去玩。更何况除了跟私塾先生同流合污、逼着我读那些经书之外,老爹一直对我很好。并且他还知道很多故事:仙女落到地面和人类苦命的男孩恋爱的故事,一条大蟒蛇同和尚打架最后引发洪灾的故事,大侠们三拳打死了恶霸的故事......——永远永远都讲不完。那时我还没有像他故事里那样出门冒险,没有发现我们的世界的——真相,是啊,那时我才不过是一个孩子!我完全相信着老爹的话,——谁能料到后来我竟然有一天会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碰到你,给你絮絮叨叨地谈这些荒谬又离谱的故事呢!……算啦,还是继续吧。
或许是受老爹的影响,我很爱看那些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江湖”的传闻。可惜我家——酒镜村这个地方离任何一个江湖门派都太远太远,像我们酒馆,一年里路过的也不过是些赶路的商贩,罕有什么侠客。老百姓们就是天天下地干活,遇见地主老爷还要低三下四地问好,哪里有什么大侠和传世武功呢?
按照老爹的说法,以往绝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是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像我那么大的时候,天南地北会有大量的绿林好汉路过喝茶,那时门口的槐树下常常系着十多批快马,而屋内则满是正邪两派目不暇接的决斗。
“尤其是一个被华山派逐出师门的流浪汉,他当时每天都会来这里喝酒。如果喝得胃痛,他就会要一壶南山产的大青叶茶。”老爹抿着胡须说道,“给不给钱?当然给啦!那时有几个富家少爷,似乎是红叶山庄来的。红叶山庄,知道吗?离咱们这儿不到百里,被灭门后,现在连南墙都塌啦。嘿,当时那少爷在调戏一个道姑,结果被那流浪汉瞧见了,只用剑鞘就给赶出去了!”
“甚至不用出剑?”我眼前又映现出她怀里的那把长剑,那把比我还高的长剑。我甚至没有摸过剑呢。
“那当然。那时我也就八岁,还没有这个柜台高呢!踩在方凳上只露出两眼偷看,因为够不着还垫坏了家里的算盘。我亲眼看见那阔少把桌子掀翻,打坏了四个盘子、两个酒杯和一个陶罐。你爷爷让我数清楚点,因为打完架,咱们都会找他们要钱的。”
“那那个道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和流浪汉大侠在一起了?”
“怎么会!”老爹说道,“有情人自然难成眷属。那个道姑只是道谢便走啦,从此之后山遥路远,青灯古庵,谁知道她去哪里了呢?然后便是……二十多年前最精心动魄的一场战斗。那场战斗……”那场战斗被母亲叫我们吃饭的声音打断了,他停了下来,不再讲了。
“那场战斗怎么样?”
“没什么。”他只是温和地看着我。“你且去努力读书吧。后面我会告诉你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告诉你的。”他只是如此说道。
那时我不通人事,还不懂他的眼神意味着什么。“有情人自然难得眷属”,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尤其不懂“自然”这个词的含义。爹和娘他们算不算是有情人呢?似乎不是的。而那场战斗……想来想去,我心里最终仍念着那个往酒里放糖的大侠,她似乎是匆匆而过,要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去。我常常想着自己能否跟她一样,了无牵挂,就单纯地也拿着一把长剑,漫无目的地出去流浪,行侠仗义,九死一生。
我当然不敢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老爹对我的栽培路线再清楚不过,——读通四书五经,然后考一个大官。他很希望我有钱,但是又不希望成为他眼中的那些花钱如流水的侠客。
渐渐地,又过去了数年,我已经算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了。就当我几乎忘记她时,那年春天,她又来了。我那时已经长高了很多,两年前的梦里,一个温柔的女子微笑着帮我完成了第一次遗精。这个该怎么称呼呢?你们这里叫它青春期。那年的春雨下得很久,似乎是清明后的第五天,她又一次来了酒镜山,到了我们客栈。
“一壶酒,要最好的。”她说道,把旧迹斑斑的剑鞘放在桌上。
我便过去招呼。真奇怪,她同我记忆中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清冷的颜色,只是眉毛和发边沾满了蛛丝般的细雨。时间似乎并未在她身上引起过任何反应,她还是那个样子,就连那身衣服也是,全部都是侠客的样子,和那日了无区别、也和现在了无区别,一个十九岁的侠客的样子。
她接过我手中的酒,喝了一口,便问道:“有没有白糖?”
“有的。”我把袖中的纸包拿出来,放到桌上。已经过去这么久,她肯定在外面经历了很多吧。是啊,她的剑鞘已经如此破了。
“是你啊。”她似乎认出了我,“难得你还记得白糖。不错,服务周到。”他喝了一杯,便又倒上一杯。我又倒入白糖。
“你们这里生意怎么样?”
“还好。”我点点头。
她突然看了我一眼,似乎讶异于我的成熟,也可能是我的声音变了吧。她似乎这才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那就行。难得准备白糖。你这个客栈我罩着了。有空找我。”语罢,她用手指沾着酒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串符号。随后,她又从兜里拿出一小锭银子摆在桌上,便起身走了。只是走到门口时,她才又说道:“三年之后,我还会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如果想要什么,可以随时找我。”
那次见面只持续了两杯酒水的时间,而后她便骑上马,匆匆向西边奔去了。我望着桌上的水迹,不明所以,最后只能用毛笔抄在了帐簿上。从那之后,我也喜欢上了酒里加糖的味道,虽然我什么也尝不出来。
那时我便已经十六岁了。那天之后大概两个多月,也就是桑椹发黑变甜的季节,老爹便不再让我读书了。那时我才知道,他原来根本就不打算让我求学科举。所谓的衣锦还乡、入朝拜相、名扬京城都是唬人的,他只是打算让我学着认几个字,会算数,好继承他的这家小店。但是他又怕这么渺小的目标激发不起我的求学心,便夸大了对我的人生期许。
于是我——他们口中还小的孩子,便像地里的麦子那样突然间发黄、成熟了。在麦场边,我可以喝酒了,抽烟草了,也可以和成年劳力那样赌来赌去了。再也没人管我,生活似乎一下子就自由起来。那时我很少再去听说书的人讲江湖侠客的故事,父亲也早已不再哄我睡觉。这一切都似乎是下雨天里积攒的雾气,太阳一出,幻想便散得一干二净。有一次,我在柜台接待生意,突然看见媒婆走进我家后院。我知道,那是成亲的事。成亲,就是娶媳妇。我知道这是什么。我曾经和村里卖豆腐的刘二是生死兄弟,可他娶媳妇后,便活成了一个行尸走肉。成亲,娶媳妇,终于轮到我了。我知道的,这种事情人人都有,就像是故事里的侠客蒙冤处斩,伸长脖子,来这么一下。一辈子也就这一下,我知道的。可是要和谁结婚呢?正常的女孩我都不愿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娘肯定不了解这个想法。不过,老爹却似乎早就会意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常常催促他买白糖,还是因为我常常念叨那个奇怪的大侠,他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念头。他把母亲拦了下来。
这件事我寻觅到端倪还是在前面的故事里。那似乎是七月份的某个晚上,母亲看着弟弟在门口的槐树下乘凉,我则坐在一旁,熬着眼睛把账目算完。老爹又给弟弟讲起了那个故事。
“那是一把鱼肠宝剑,长三尺三寸,重七斤九两。据说是用北海渔民所钓大鲲的脊骨为边,在冰天雪地里淬上冷钢才得来的宝物呢。这剑锋利无比,并且——永远都不会生锈。那天,就在红叶山庄的少爷回去后的第三天,大批的剑客、杀手都汇聚到了我们这个小店,简直就称得上是人满为患!”
“人满为患!”弟弟趴在凳子上听老爹在讲,可我早就失去了对这些故事的兴趣。
“你要知道,这些杀手当然是在追杀那位流浪汉,那个名冠天下的华山弃徒,——他的名字是向野。红叶山庄要复仇,他们规划得很周密,寻常人看,他们就是一堆贩枣的商客,可是衣袖内里早就准备好刀剑了。向大侠就像往常一样,拎着一只烧鸡走过来,就在门外摆的桌子上要我们上酒,对,就是摆在这里的桌子。我准备把酒送过去,可是一把就被一个壮汉夺走了。他就拿着那罐酒,慢慢地走到屋子外面。”
“然后呢?”
“然后?在那个壮汉距他不足十步的地方,他突然拔出了那把剑!即使是在天气最热的中午,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寒气——那是一股生冷的、带死亡味道的、足以让人惊出汗来的寒意。当你看到那把剑时,你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只有白光,同空气连成一片的、和阳光融为一体的、亮闪闪的影子!就是在这样的光影下,大条大条的尸体都倒在了地上。只有一个。”
他讲到这里,刻意看了一眼我。弟弟已经抓紧了他的衣服,而我,同样地,一种强烈的、莫名的冲动吸引了我。我把账簿放下,吹灭蜡烛,只剩月光笼罩在他的脸上。
“仅剩的那个人,是一个女人。她三岁习拳、七岁练剑、十三岁时就打败红叶山庄的所有内门弟子成为了掌院,可谓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刀光剑影,浓云狂卷,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从桌边打到房顶上,从槐树枝上打到渔船上,从河边一直打到湖中心的小岛。后来……他们相爱了。”
“相爱?”弟弟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他可不是要去听这个。
“是的,相爱,然后诞下一子。”老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可是那子诞生不久,红叶山庄便假意求和,邀请向野和红径去山上做客,说那孩子是山庄的后代,从前的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然后,就在女孩带着孩子回到山上的时候……”
“换一个!”弟弟似乎对这个故事已经彻底失望了。“我要听神话。比如,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来的。”
“这个太深奥了。”娘开始拍打他的后背。时间已经不早了。
“如果你便要听,我可以给你讲一个。”老爹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似乎月光落在他脸上,就会激起一种奇特的、过往从来没有的魔力,这魔力让我产生了一丝害怕,我甚至都有点认不出他了,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讲了起来。2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DiYt0qu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