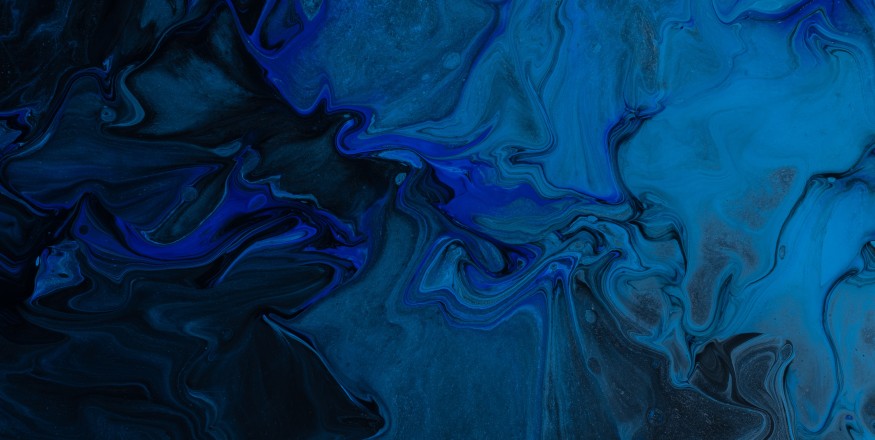/我们现在已经考虑了程序设计中的一些要素:使用过许多基本的算术操作,对这种操作进行组合,通过定义各种复合过程,对符合操作进行抽象。但是,即使是知道了这些,我们还不能说自己已经理解了如何去编程序。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学下象棋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此时已经知道了移动棋子的各种规则,但却还不知道典型的开局、战术和策略。就像初学象棋的人们那样,我们还不知道编程领域中各种有用的常见模式,缺少有关各种棋步的价值(值得定义哪些过程)的知识,缺少对所走棋步的各种后果(执行一个过程的效果)做出预期的经验。/
/能够看清楚所考虑的后果的能力,对于成为程序设计专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这种能力在所有综合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中的作用一样。/
——HGJ《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13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vkOeaZnSA
13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JgUiL5xda
三日过后,我们终于到了京口府。在这之前我也和端木姑娘流浪过很多座城,但没有一座,有如京口这般繁华、安逸、奢靡,这般气势恢宏。端木琴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天上有很多繁华的都市,但若在人间选一座,那独一无二的还是这京城。我没有去过天上,但我同意她的后半句。这里仿佛有一种魔力,似乎创世神对这座城市施加了什么魔法,无论外面将涌来多大的危机、多么强盛的敌人,无论走在外面有多少恐慌,——只要进了城,那么便会是无穷无尽的宴会和喧嚣、——以及任何凛冽的寒风都无法消散的烟火气。在这里,什么都有,但偏偏没有恐惧和谨慎的席位。这座城市就是如此立在这里的,它作为新统治王朝的首都也不过几百年,可是这几百年所积攒的自信,竟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气象。
“可这是个衰朽的王朝,很显然,”端木琴这么说道。“一路走来嘛,冰火两重天,这就是衰落最大的征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很快洋人就会从南方一路打上来,而罗多人也会从北方南下,上下夹击,”她做了一个手势,“对,就是这样上下夹击,我们的京城就势同累卵了。”
“……这种事情之前发生过吗?”
“之前自然没有发生过。洋人的海军、白蛇信徒、罗多势力……这些原本只是一些用来增长侠客经验的开胃菜。可是随着侠客数量的锐减,还有陈琦污染,这些势力便不由得猖獗了起来。”她指了指天空,“你能看到那里有什么吗?”
我便抬起头。
“那里有个洞。”
“有个洞?”
“‘天已经溃烂了,像一个伤疤。’当时意室的项目组长,也就是陈琦,他在自杀前留下了这句话。”周诗阳突然插了一嘴,“我们都看不到这个伤疤,可是天确实溃烂了,生出了一个大洞。我曾经试图从物理上侦测那个洞的所在,这当然失败了……谁也不知道污染的细节,或许唯一知道的人已经死掉了。”
大洞……我茫然地望着那片刚刚被手指着的天空,望见那里要透过鹅黄的柳叶,那里甚至还飘着风筝。在这种春日……他们说这天上破着一个大洞。
那日我们一起去守城将军那里报了名,守城将军叫张沸,他对我们十分恭敬。将军们一代代地传下来,似乎早知道每次罗多人南下时,都会有大量的侠客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到京城了。当然,我能看出,他早已知道此次守城凶多吉少了。这次前来赴难的侠客不过是以往的千百分之一,而到现在为止,所报名的侠客甚至不足一百个。
不足一百个……这还不是头疼的事情。他最害怕的还是自己守城将军的职务,两个月后,这个职务就要交给一位胸怀大志、为国为民的青年俊才了。如果是往日,将他的军职交由这位俊才倒算不上什么,令这些名家出身的青年天才们刷一刷履历,再换个体面的文职,“能文能武”也说得过去,可是如今大军压境,京口危如累卵,一堆埋怨便开始刺激得他眼圈发红了。
按照他的描述,京口的守城势力主要则有三股:国家军队和游侠自不再提,还有第三类,就是“道兵”。据张沸所说,所谓的“道兵”不过是一些善于讨好愚弄皇帝的方士,这些人还真就让皇帝相信他们可以请下来刀枪不入的天兵天将。于是皇帝给了这些道士以最高的恩遇。张沸对这一切很不开心,他只说了一半,如果把他的话补全,那么就是:这群道兵所拿的钱远远大于我们这群侠客的,而我们这些装点门面体现官民团结的侠客拿的俸禄又远远大于他这个将军,最后将军的俸禄是无数抱着兵器的士兵们的好几倍。
不过,我倒确实认识一位“道兵”,他没有一般道士那种风情俊朗的胡须,而是留着一大片凌乱的胡茬。那日我从那群道兵面前经过,他似乎看到了我,立马过来搭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了城墙的无人处。
“没想到那日酒镜山一别,你竟然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送死。”他朗笑道,随手拔了一根从墙缝中伸出头的狗尾巴草,叼在嘴里。我有些恍惚地望着他。他怎么知道酒镜山的事情?我记不起来我遇过他。
“记性真好。”他又拍了一下我的头,“当时我快饿死了,你给我一块锅饼,现在想起来了吧?我还告诉你前面有流民,给你指了指通往那棵大梧桐树的路,对不?”
“原来是你!”我从衣服里取出那本道经,“这本书是当时你让我保管的,现在给你。”
“不错。”他点了点头,“你没偷看吧?”
“当然没有!”
“看得出来,不然你就不会仍然拔不出首充送的那把剑了。”他似乎嘲讽一般说道,“这本道经对我而言很重要,你又帮了我一次,我可以再帮你一件事。话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因为你想假装道士,骗皇帝老子的吃喝。”
他闻言便哈哈大笑起来,“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他看着我,用食指指了指上方,“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来自天上。如果非要规定一个职业的话,那我就是一个hacker。”
“海客。”我复述这个词,“来自海外的……方士?”
他又笑了,“可以这么说。”
“那你会很多道术?”
“在你们的这个世界里,我确实会一些技术。你也可以称它们为道术,但是,记住,长生不老丹什么的还是算了,其他的愿望都可以提。”
“不,我不需要什么。”我答道,“我现在很幸福,很满足。如果我能在守城的时候战死,那就是再圆满不过的人生啦。我不能奢求更多,对吧?”
“‘奢求’,啧啧啧。”他看了我一眼,“爱上了天上的一个女孩?话说这类故事你应该听过很多吧,刘郎和郑女,童远和七仙女?如果你信我,就不如放弃,因为我敢打赌,你绝对泡不到她。”
“我……我没有!你不要乱说啊。”
“你之前肯定没谈过恋爱吧。拿这段感情当个开头,也算不错。”他吐出那棵草,仰头看着天说道:“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有一天,你不再脸红,当你能够隐藏自己所有的情绪时,才能算有点男人的样子。”他不再理我,只是便盯着天空,“那个洞,越来越大了。”
“洞?”
“看不到吗?”他用手指着那片天说道,“就是这里,红黑色的洞。几年前还不过一粒绿豆大小,现在则可以掉下来一块硬币了。”
“海客大叔, ”我也望着那片天,“你的道术,可以抵御住罗多人的进攻吗?”
“当然不可以。”他说道,“不过,我的道术可以在逃跑的同时也把你救出去。”
“那请不要救我!还是……让我一同死在这里吧。我想试一试——当侠客的感觉。”
“幼稚。”他摇了摇头,走了。
那之后我常常去向他请教天上的事。“天上没什么有意思的,所以大伙才愿意来你们这里玩。”他只是如此敷衍。也便是从来到京口起,我发现我可能是最特殊的侠客,因为我不是全神。
他们是在享受游历的感觉,而我确确实实是在漂泊。每次他们在闹市里追逐游荡,在酒馆里弹歌跳舞,在青楼间寻找男歌女妓,或聚在一起谈论天上的什么事时,我都觉得孤独。那时我会爬上醉梦楼的屋檐,要么看看星星,要么……看一看我的那把剑。京口的治安很好,巡行队日夜巡逻,没有需要我拔剑而出的时刻。而我曾经无数次试图拔出来那把剑,——那把我从小听着长大的剑,可惜每次我都失败了。
我曾经询问过端木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她只是如此说道,“首先把手放在剑柄上,然后握紧,如此一拔——”剑便出了鞘。
可是我做不到。不是力气的问题,我能确定如此。为此我想过很多种假设:会不会半神——本身就没有拔出手冲剑的能力?会不会父亲搞错了,我身上并没有神的血统?会不会正如一些传说和故事里那样,必须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当我拥有了充足的勇气,那把剑才能被拔出?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假说,不切实际的假说。我从来没有给除了端木琴之外的人说起过这件事。连剑都拔不出来的侠客……当张将军知道这件事时,他又会怎么想呢?
端木琴经常安慰我,那时她会用一种抱歉的表情,其实大可不必的。她说她也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人不能放弃,就算被各种东西踩在脚下,也要恶狠狠地咬着牙,拼尽力气去反击。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天上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渔民,这个渔民的运气很差,经常抓不到鱼。有一次他终于逮到机会在海里抓到了一条大鱼,这下子终于有个好收成了吧,可是在返途中却有无数的鲨鱼在打那条鱼的主意,可怜的渔人,最后等他回到岸边时,抓住的那条大鱼只剩下了骨头。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真不错,如果有一天我抓到了一条大鱼,即使我吃不到它的肉,我也要为这些骨头骄傲。
“不过,琴姑娘,天上也会有海吗?海水会不会漏下来?”
“当然有海。不会漏。”
“那么天上的海叫什么名字?”
“嗯……”她想了想,“应该叫‘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在后面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对那个海很有兴趣,它仿佛在我们世界的另外一面。在这半个月中,周诗阳日夜不停地在整个城市内外勘察着,照他所说,他是在找“漏洞”。如果让他找到漏洞,那么他就可以扭转战局,再为这个可怜的国家续一续命。很惭愧,我则沉迷上了饮酒。张沸引诱了我很多次,我经受不住他的劝导,便开了一个头,很坏的头。这群士兵甚至还作了一个饮酒歌,歌道:
“ /八月九,菊花开,桂香迭荡自天来。散落老树青苔上,此壤曾将天人埋。销锈剑,朽粱亭,一入愁肠三秋凛。有血染山夕云上,寒风吹得心头凉。卧荒骨,醉龙泉,此碗盛下千里缘。直到酒空无所有,沙场一醉梦闱园……/ ”
这首诗写得很粗俗,或者说……豪放。他们士兵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不豪放一点,简直都融入不进去。端木琴向来不与他们在一起喝酒,她参加过很多次的守城,我曾经问过她,之前守城时那些士兵都是什么样子。她说之前的那些将士她全都记不清了,更何况那些将士多半死在了城墙上,即使是剩下的人,此刻也已经老死了。
我相信她的话,她是神仙。那日她说在酒镜山下的雨园见面,我便同意,后来她说要我和她伪作夫妻,我便答应。我经常问她,她姐姐什么时候会来。她说等罗多的主力来京城之前,我一定可以再见到她。在我的记忆里,她甚至已经模糊难寻了。如果有一日,我真的可以再见到她,我又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符号,我又想起来那串符号,写在桌子上的水迹。在我第二次遇见她时,她曾经用手指沾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了一串符号。那串符号已经被我记下来了,可是没有什么用……她还会再回来吗?
罗多人的先锋已经到城下了。
13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OGZ4L05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