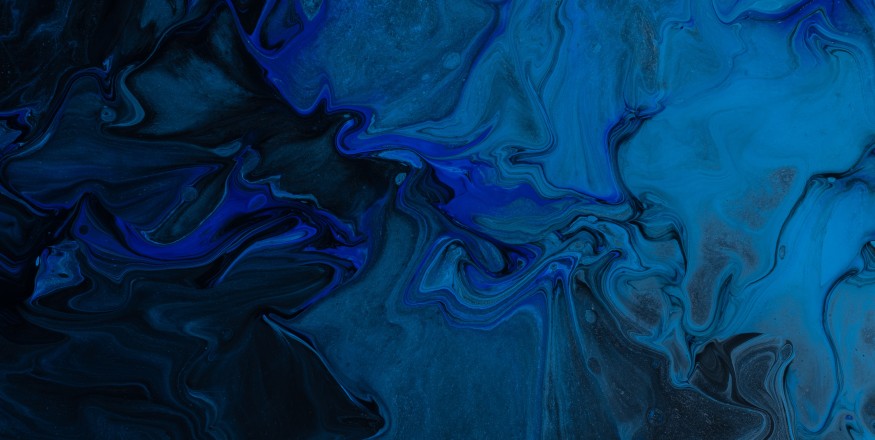不知爹对娘说了什么,如今我已十九,三年来,我娘再也没有提过结婚的事。江湖、大侠的传说早已散去,没有成家的我,每日便是经营着酒店。我成了村里伙伴中的异类,一个没有孩子、自然也没有妻子的人。我觉得这事情无所谓,仿佛我早已出过很远很远的门,早已看过这世上形形色色的东西了。当然,有时翻账簿,我还是会想起那日桌上的水迹。后来,莲子熟了。再后来,秋雁的清鸣也落入我的窗子。我躺在床上,有时秋雨刚过,蛙声聒得耳疼,却不知道她在哪里。可我还记得那串符号,那串用水写出来的符号,我不能理解它的含意。
转眼间,林中地上已开始结霜,我又被迫裹起棉衣,大雪沉默无声地落了下来,父亲每天都会从山上背下大堆的木头,冬天到了。
来往的商人一下子稀少了很多,甚至连附近的闲客也零星起来。屋外的桌椅都侧着,整齐地堆在过道里躲雪。屋内则搭了一只泥作的火盆,燃着一些柴火取暖。我手里拿着毛笔,沾着刚化开的墨去记一记今年的帐,老爹则在一旁看我记下的数目。幼弟已经是一个少年了,他在一旁慢声慢气地读书,时不时跺一跺冰凉的脚。老爹对他说的话和我一样:“好好念书,将来考学,做大官。”
那年冬天,她第三次来到了这里。那是酒镜山雪下得最大的一次,狼群都被逼出了山林。或许,第二年的雪下得更大,或许后面她又来过,又或许这次来的不是她。又或许——是吗?我又罗嗦了是吗?不要走,让我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吧。
“店家,温一碗热酒。”
那时的她自然是对着老爹说的。
可是老爹似乎会意一般看了我一眼。她摘下斗笠,没有任何变化,同记忆中完全一样。我看着她,回忆便像炉上的雪水,冒出了微不可察的气泡。时间,时间似乎在她那里静止了,无论是头发,眼角,还是那双冰凉的手,一切似乎都没有变过。只有那把剑,——时间让那把剑显得更加破旧了。她究竟有什么神通,才会让自己一直没有变化呢?或者只是错觉,记忆的错觉,或许只是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变动的错觉?
“愣什么呢?快去温酒啊!”老爹又踢了我一脚。
我登时醒悟,连忙开了一坛酒,倒了一杯,又放在置着烫开水的海碗里,径直端上去。她坐在那里掸着身上的雪,我便问:“加糖?”
“加糖?”她听到这句话,便笑了出来。那时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人了。如果是她,便是不会笑的。我果然还是认错人了,毕竟只见过两面,还隔了三年。我感到脸颊滚烫,连忙道歉。
“原来就是你啊。”她把剑拉开一个口子,用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我。“她呢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来不了了。”
“但是她托我传话,因为她发现,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给你传话。”
“这种方式?”
我那时只能疑惑地看着她。
可她见我没有回答,却似乎面有愠色了,于是又说道:“她还让我告诉你,她最近事情很多,你必须要再等到三年。”
“她想问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
“那,心上人有没有?”
“没有。不对——”
她拔出剑,寒光一闪,但她只拔出了一半,剑鞘又慢慢落了回去,发出温和的金属摩擦声。“她说,如果你愿意等的话,三年后去酒镜山上的雨园等。”末了,她又补了一句,“我是她表妹,你可以叫我端木琴。她的意思是,你可以不去。但是一旦决定要去,便要断绝同这个世界所有的联系,断绝一切的一切,因为在那里你会看到真相。 ”她缓缓将剑拉开,先冲我爹眨了个眼,而后说道:“当然,如果你想断绝,但是舍不得的话,我可以帮你。杀他们都不犯法。”
她仿佛看到了我攥着的拳头,于是笑了笑,把剑收了回去。“三年之后她会过来接你。你到时回复便好。”
她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便出门翻身往西,就这样在马的踱步中离开了。
“我不会去的,我要待在这里,待在家里。”我对老爹说道。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娘看了一眼老爹,老爹给了她一个眼神,似乎我娘便也如此会意了。他们不再看我,我有些疑惑。
我们就这样坐着,天色渐渐暗淡下去,远处的浓云有些发黄,雪歇了一阵子后,又开始下得紧了。
这时又有一行人似是赶路般走来。这六七人大都身着官服,为首的却穿一身青衣,他的脸似乎早被风霜刮得粗糙无比,毛孔里、头发上、身上的衣服间全都散着一股股的寒气。他率先进门,只是施礼,身后的一个干瘦的老头便说道:“店家好,我们从京口来,去鳞州,在这里歇歇脚,讨口酒喝。”说罢便对着为首的中年,朝着屋内背风且靠近火盘的长凳道:“张大人,请。”
你说什么,跑题了吗?确实是这样。可是这段又不得不讲,不然你就不会理解我为什么可以坐在你面前,不会理解为何我要大老远地来到你们这里,给你讲这个长长的故事啦!不然我或许……早已死去、老去、被遗忘掉,或者……污染掉。——污染是个奇怪的词?确实如此。算啦算啦,还是让我继续讲下去吧。
面对老者的话,那位姓张的人也不推脱,只是端坐在那里。老头又招呼身后着官服的几位同样围着桌子坐下。父亲不敢怠慢,早早地就把热酒和切好的肉冻端了上去。青衣人只是吃饭,喝酒,而老爹则示意娘和弟弟抓紧回屋去了。
似乎是因为气氛沉闷,那位身着青衣的年轻人只喝了几杯后,便提议出门赏雪。于是两个官差迅速跟上,三人便走出去了。
见他走后,便有一个官差道:“陈爷,咱为啥这么敬重他?不过是个失了势的书生,说是当钦差来查白蛇教的案子,但其实就是发配而已。”
回答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是怕被门外听见:“秦大人说了,此人大意不得。事不成,秦大人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呐。”
另一个人突然插进来大声说道:“怕什么!就他?这片地方我知道,方圆十里就只有这家酒店。待会儿出去,前面就是酒镜山,此山三脉交叠,走在山沟里,最好动手不过了!到时候,就看着这个!”他说罢,用手拍了拍腰间的刀。
“真的要动手?”却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
“这还有假!赵管家全都安排好了。”为首的道,“到时候说是偶遇白蛇匪徒,寡不敌众,不幸被杀!还算给他留了一个忠名。”
“那你们就不怕秦小姐不开心?到时候撒起气来,吃亏的不还是我们?”
这句话说出来,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才有人道:“不会有事吧?”
另一人大大咧咧答道:“王二、陈七不是跟着出去了,怕啥。”
又过了一会儿,迟迟没有看到三人回来的踪迹。几人不再交谈,只是互相交换了眼色,便最后在火盆上烤了烤手,将刀剑窝在腋间走出门去了。
这时雪花似乎小了一些,可是寒气仍然将火盆里的热量诛杀殆尽,门外一条长长的白色囚衣队列往西方走去,几个官兵一般的人坐在马上,绳索一连扭着七八个罪犯,队尾的马则拉着一条长板车,长板上已躺着四五个人的尸体。
我和弟弟都忍不住盯着这些门看,似乎是看出官爷没有进门的意思,父亲走上前去关上了门。
“外面冷。”他只是如此说道。
10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Z1R0KPM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