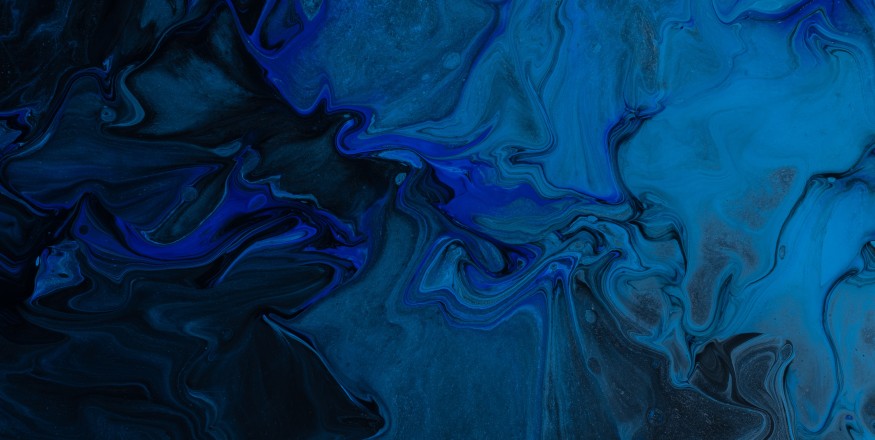张若离躺在马背上,寒风呼啸。庙内是白蛇教徒们吟诵的声音。在一众白蛇教徒中间,只一人身着白袍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地,似乎怔怔地望着女娲的石像看。
张若离只用眼睛掠过她,便又朝庙顶的茅草看去。可他不知道,仅这一瞥便也被这女子感觉到。她怆然地俯视着桌案上几个鲜血淋漓的头颅,不由得伸出手来看了看。她早已不知道,自己又是何时,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杨素说,面具戴久了,便会覆在脸上,再也揭不下来。
真的如此么。
蛇血香的气味仍然萦绕在庙里——这宛如香灰般微弱的气味便是从她身上散发而来。这是她生来便有的诅咒——除了她自己,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也不能消受的诅咒。即便是秦相下的一流高手,在这香气面前,也只能成为祭品。
听说你们要去桃花庵?我也要去。当她从庙外走入时,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我是要去成亲的,和桃花庵里的一个和尚,他叫桃木。于是她看到了道士诧异的表情,仿佛是无聊又庸俗的询问:和和尚成亲?
只是呢,那时她缓缓说道,带三个人过去,礼物有点太多了,所以不得不杀掉一些。
到这时,庙里的人连站都站不稳了。她先砍下了官差们的人头,然后欣赏起早已被困在中心的三人来。
张若离也便是在这时,才发现这些人青袍前纹着的白蛇。
是白蛇教。他内心忖道。
面前的女子看了三人一眼,张若离便知道,这至少是其中一位堂主了。他的任务便是来剿灭白蛇教,如今诏书还在他怀里呢。万一被搜出来,他的人头又如何保住呢?
恍惚间,他听到那女子说道: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ND7iM8Vft
“但是嘛,我们白蛇教都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杀人,更不会杀好人。一会儿我会依次问你们三个问题,如果你们答上来的话,命就保住了。”
蛇血香的雾气似乎还未散去,他深觉头昏脑胀,看了看旁边的何难,自然也是如此。
他们只见那女子先走到破破烂烂的道士面前,一双金瞳便盯着他说道:“我的问题很简单。现在,你告诉我,我心里在想什么?”
何难并没有说话。
那女子笑了笑,说道:“喂!即使你猜不出来,也要蒙一个的吧?”
“不,”虚弱的道士早已被蛇血香毒得立不起身,“我已经读到了,只是无法在这里说出来。”
“哦?有什么不能说?如果你真的猜了出来,就不妨告诉我。”
何难点了点头。“你在想,我根本就不爱他。我不想和他结婚。”
女孩咦了一声,似乎觉得十分惊讶。“你说错了。你自然说错了。不过……罢了,你不会死。”
她又走到那活死人安大全面前,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一粒纯白色的药丸,直接喂到了他嘴里。见后者咽了下去,她便笑吟吟道:“喂!你这个大汉。我不欺负你不识字。刚刚喂你的是颠倒众生丸。这药丸可以让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陷入幻觉,盗汗三升,欲仙欲死。你要是能够在这一炷香内直立不动,那就算你赢!”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oL0B2ldRf
那女子支着手站在一旁,仍然不怀好意地看着安大全。半柱香过去了,他果然一动不动。很快,一柱香的时间也过去了,安大全就像呆鸡一般站在那里,只是身上不停地流着恶汗。
“邪门!”女孩似乎有点挂不住面子了。她走到张若离的面前。
“大哥哥,对不住了。”张若离看到面前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小妹。而心脏,似乎已跳到了喉咙。“我必须要杀掉一个人,三个人都带过去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你看,他们……他们两个又偏偏过了我这关,所以我不得不给你一个最难最难的问题了。”她似乎一脸委屈,“对不起,大哥哥。”
这香药早已夺走了他的理智,却又似乎让他回想起什么。他试图用手指掐紧自己,来抑制胸口传来的悸动。突然,他碰到了一件冰冷的硬物——是那把剑。那把不锈钢剑就像行刑的令牌那样插在他的双手与后背中间。于是,一股奇特的热流传了进来,很快,他发现所中之毒竟莫名其妙地恢复了,他又有了力气,似乎可以站起来。他没有表露出异样,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命运是不可说的东西,倘若前两个人的问题让他碰上,此刻他的头颅早就会被摆放在石像前了。只是,妈妈……他觉得脑海里一片混沌,而问题已经开始了。
那女孩问道:“有一种动物,他头上长着既像羊又像牛一般的角,脖子伸长时有如长颈鹿,而耳朵也像大象一般雄壮。他躯体内流着蟾蜍一样碧绿的血,身上披满了银狐和孔雀那般美丽的羽毛。他有着狗一样的叫声,猪一样的鼻子,灰熊一般的利爪,还有蛇一样的尾巴……”
此时此刻,妈妈和小妹应该都睡了吧……小妹会听话吗?还有妻子,他妻子还在家里等他呢,谁知道他又接了这个旨意,来这边查案,谁知道——
“他如鸿雁般南北迁徙,像鲤鱼在下雨的河岸旁欢舞跳跃。他每日哒哒着蹄子在林间踱步,临死时又像乌鸦一样悲哀……”
“答案很简单,是人。”他说道,心里一阵惊奇。这个问题……他父亲之前问过他!
“这个不算!”女子似乎有些生气,紧接着又问道:“如果宇宙,如果四方上下、古往今来的这一切有一颗心的话,这颗心是什么?”
“是人。”
“那人的心又是什么?”
“是宇宙,是这四方上下、古往今来的一切。”
“这……也不算!”这回答似乎把眼前的白衣少女激怒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连续问了两个问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共工既已触不周山,天柱既已折,地维既已绝,天尚未落,女娲何必再炼石补天,多此一举?又人自泥胚而生,不足百年便一一归陨,女娲又何必劳苦伤神,自损精气造人?此番天地与你我,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nTP8RgEkB
这是她从来不敢问出的问题,她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她却盯着眼前的这个人,想要看看他究竟会作何解。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kL6sWDStb
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3A7fSPY07
而张若离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问题他父亲曾经问过他。后来,在他沉浸在犬吠和月光中而沉沉睡去的那个夜晚,那个他还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的夜晚,他父亲便永远地走了。去了哪里?他不知道,他妈妈也没有给他过具体的答复,只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时他才多少岁呀?刚刚学会说话?
儿子,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你和我,还有你娘,还有这条狗,以及这个太阳,咱们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他看见那个温和的中年人正坐在地上掰花生,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如此笑着逗着他。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34weWdKno
那时他答不上来,便反问:爸爸,你觉得是什么?于是男人是把手伸得很高,似乎是在指着整片天空,然后,他把手收了回来,放在嘴唇中间,鼻梁以下,一片黑色的杂草里。——嘘,他只是做了这个手势,而后便继续干活了。
张若离便也如此。他缓缓将背后的手挪到面前来,竖在唇间,露出吹箫的口风,做了一个噤声的姿势。
“嘘——”
他把手放下,仍然坐在那里,不再说话了。
白衣女孩终于呈现出巨大的惊讶和疑惑,似乎她已陷入到久久的出神中。过了一会,她才从惊讶中解脱道:“白蛇教东坛坛主白百花拜见。请问先生尊称?”
他便道:“行路商人,方爱财。”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何难在他耳边轻问道。
他没有说话。
“你回答了那个问题没有?还是说,那个动作,——就是回答?”
他苦涩地笑了笑,看着北风将雪花吹得四处乱飞。他的牙齿颤抖个不停,一声喷嚏打出来,才意识到自己或许已感冒了。
庙内。
信徒之间自然也在那里小声嘀咕。他们自然也不理解坛主为何良心发现。毕竟那种青年人,怎么看都不会是一个商人。白百花早已听到他们的嘀咕,只是她并没有说话。
当年白蛇教教主权紫阳肉身蜕去时,她曾经在场,那时她才不过是总角的孩童,可是那一幕——在教主临终前,各坛坛主都聚在石室里,门下天才杨素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这问题是附在他的耳朵上说的,所以她自然听不到。但她看到了同样的回复:食指竖放在两唇中间,这噤声的姿势。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教主的意思,您已解答了我的问题。您的解答,不是解答,所以才称得上是解答。语罢杨素便伏地长拜,而教主则坐在床上点了点头,断气而去了。
“坛主。”白百花从回忆中解脱出来,她微微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仪式开始了。
信徒们早已将人头摆作一排,围着石像,跪坐成圆。即使是在庙外的众人,也出神地望他们起来。
一阵阵轻奇的吟唱声从庙内传来,如同涟漪般散开。这些来自不同信徒的声音碰撞在一起,叠叠飘荡,接连不断。为首的歌道: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icf9GeEaw
“白蝌岛上。有彼白蛇。青眸回首。千年不语。一朝化石。山野崎岖。不见斯人。白发唏嘘……”
这吟唱声纷纷散开,形成一波又一波似浪潮又似雾雨般磅礴迷蒙的合奏。张若离躺在马上,寒风呼啸。在这片片诵声中,他只觉得昏昏欲眠,一路上的勾心斗角、那古怪道士所讲的乱七八糟的故事、自己的父亲、庙里的生死考验早已折磨得他疲倦至极。
不知何时,他便在这吟唱声中睡着了。
\\
待他醒来,红色的太阳正浮在东边萧索的榆树上。他的耳朵早已失去知觉,手脚也已冻僵,太阳穴处一阵阵地传来灼痛。前方的身影白衣黑发,头插白花,一身白衣镂空,由此又裹了棉袍。那人左顾右盼,悲伤的情绪似乎流转不停,她看着两边的风景,回过头时张若离才看见她的脸:——正是昨夜险些杀了他的白百花!
更奇怪的是,除去她之外,众人尽着黑红色的喜服,为首的几个手里还握着唢呐喇叭,张着铜锣、唢呐、长竽,而身后则是一辆又一辆堆满箱箧的车子。
何难见他醒了过来,便指了指右侧的山峦,这山在高峰处没有草树,裸出大块发白的岩石。石下是片片稀疏的木林,只是没有开花,看不出什么树。
“这就是贫道的目的地。”何难道。“山阳面有一个不大的小道庵,说是道庵,其实也有和尚,山上遍植桃花,当地人都叫它桃花庵。”
张若离点了点头,懒洋洋的太阳照在他身上,一身的血与气又慢慢开始恢复起来了。
9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QK766s3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