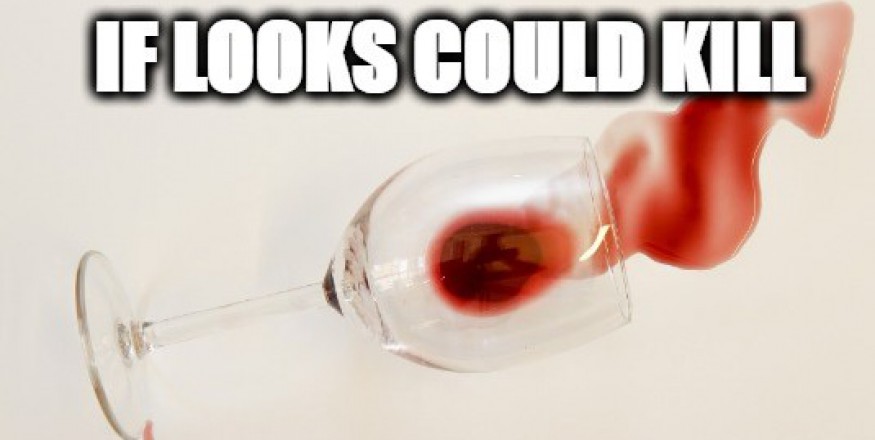老一輩的人會告訴你,台灣的夏天六月才真的開始。渥克常常納悶像這樣炎熱的五月到底為何不算夏天。這樣的氣溫讓他想到了一九九七年七月,西西里的聖羅莎莉亞節(Festa di Santa Rosalia)的遊行,渥克那個時候有另一個名字……
『萬歲!巴勒摩和聖羅莎莉亞!(Viva Palermo e Santa Rosalia!)』
……只是台灣的夏天有種熱帶叢林的氣息,緊緊貼著每一吋皮膚。渥克將綠茶的寶特瓶罐投入資源回收桶當中,他拿出他的皮夾,從裡面掏出一顆牙齒。那是一個西西里人死後全身上下唯一完整的部位。這個牙齒的主人有許多化名。其中最耐人尋味也最為人知的一個是『開瓶器』。那個西西里人曾經摧毀掉渥克所熟知的一切,只留下比地獄烈火還更熾熱的復仇火焰。
一九九七年,渥克在聖羅莎莉亞節用這股火焰毀滅了那個西西里人,渥克的靈魂也坐上了往海灘的末班車。他變成一個喪失痛覺的病患,世上的一切都像是百貨商場中擦身而過的陌生人,沒有事情能再引起他的興趣或注意。渥克那有親和力的笑依然魅力十足,如同一種必須的反應,幽默感變得像是禮儀。他的興趣則像是衣服,你總得選個你喜歡的來穿。就這樣老去,讓肉身追隨消逝的靈魂,逐漸死去。渥克不認為這個世界還有什麼事情讓他想多看幾眼。
直到一個高中生用汽車的速度駕駛柴洛基飛機。
『你會相信嗎?』渥克用西西里語問那顆牙齒。接著舉起牙齒到空中,好像希望那個曾被稱為開瓶器的西西里人看到這一幕。接著渥克走進塔台,扶著生鏽的樓梯扶手爬上二樓。渥克的腳步在如此空蕩的塔台內部完全沒發出任何的聲音,這也是渥克在黑手黨的歲月中留下來的一個痕跡。渥克把二樓某個架子一小塊區域上的灰塵,小心而俐落地用手指清除掉,並將牙齒放在上面。在渥克的世界中,開瓶器與他看著林延像表演魔術般將飛機飛得像隻蜻蜓,再看著他飛回來,完美無缺地降落龍岡機場。渥克指示著林延降落,心中並沒有任何的驚奇。畢竟一個達到傳奇飛行員成就的人,沒有道理不會降落。
*
回程中,他們不發一語。渥克蠻腦子幾乎都是剛剛的低速飛行(還有些部份是他要如何在混亂的車陣中避免錯過台北的交流道)。然而這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那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情,不是嗎?他會那樣飛就是會那樣飛,真正讓渥克想不透的是為什麼他要低速飛行。想學習開飛機很容易理解,許多人都有過飛行夢。想在三個月內學會開飛機很瘋狂,但也可以理解。但低速飛行......
『在這邊停車。』林延說道。渥克於是將他的日產(Nissan)車停在酷聖石和台北車站捷運的出口之間。
『你到底打算做什麼,傻鳥?』渥克操著吉隆坡口音的中文大聲問道。他現在坐在駕駛座,而林延已經站在捷運出口上了。
有那麼一瞬間,林延又感受到那種衝動了。那種想要將一切全盤托出的衝動。就如同當時他對陳昱瑋全盤托出般。但很快就消逝了,就像在路過的陌生人找到的某種熟識感。
『保重了。』林延走下樓梯,接著好像想到什麼忘了講,回頭說道:『安東尼奧。(Antonio)』 21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uNAH019tG
林延伴隨著此起彼落的喇叭聲繼續走下樓梯,留下已經忘記要掩飾驚愕的渥克──或是來自墨西哥的劊子手安東尼奧。
ns52.14.232.22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