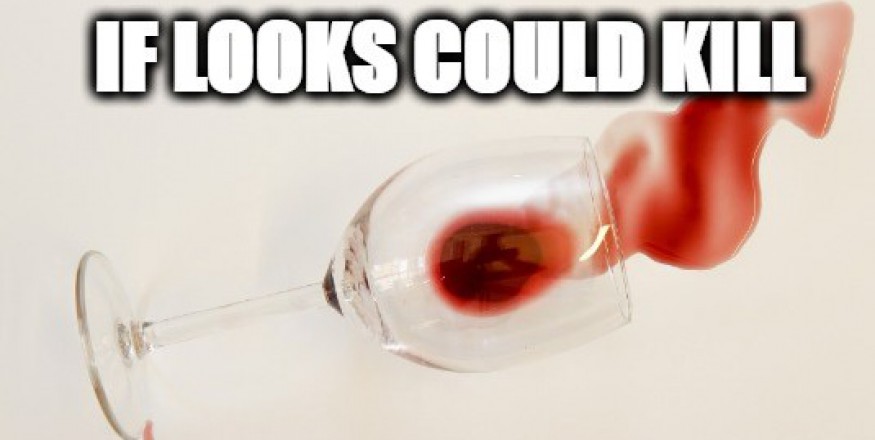『謝謝。』計程車司機在找錢之際,將一張觀世音菩薩的書籤與幾個十元硬幣交到林延手中。林延迅速地將書籤放在座位上,關上門前對司機投以強硬的眼神與微笑。
『這裡是住宅區。』亞倫看著林延背著Mizuno的白色高爾夫球袋,心中希望林延其實只想跟他去練習場打個兩小時高爾夫球。但亞倫始終是個軍人,他很清楚林延的球袋裡不可能只是幾支鐵桿和球。『你打算去哪裡?』
『搭捷運。』
『為什麼不叫車子停在捷運站下面?』
『監視攝影機太多了。』林延開始往前走,蟬的叫聲在山邊聽起來更宏亮,好像在集體嘲笑經過的他們。『走這幾條巷子到捷運站幾乎不會經過任何監視攝影機。』
『但是到了捷運站後還是有攝影機不是嗎?』
『沒錯,那裡有攝影機。』林延說。『但頂多在攝影機上看到我們從住宅區巷子中突然出現。他們一定先從附近的攝影機開始一台一台看。』
『他們是誰?』
林延沒有回答,繼續向前走。亞倫不是真的不知道他們是誰,就如同他知道林延接下來打算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是什麼慈善活動。
『那又如何?他們大可擴大範圍,最後你還是會被發現。』
『是我們都會被發現。』
『天殺的有什麼差別?』
林延繼續向前走,踩著越來越多的落葉,讓亞倫的話消失在空氣中。
『你有在聽我說話嗎?』亞倫大聲問道。『我說你──』
林延停了下來,側身回頭看著亞倫,雙眼中帶著掩蓋不住的憤怒與輕視。亞倫之前有注意到嗎?注意到這孩子這幾個月在輔導室的每一字每一句是如此的言不由衷嗎?最初林延來到他的輔導室的時候,他告訴亞倫他的問題,告訴他他是多麼想念他的父親,告訴他他暗戀班上的女生,告訴他的各種煩惱。亞倫當時覺得林延是個需要幫助的小男孩,甚至因此獲得不少成就感。
『我不會被發現的,』林延說。『正如同過去幾個月你沒發現我到底在想什麼一樣。』
現在亞倫站在山腳下邊的巷子中,看著林延那雙似乎看穿自己的眼睛,亞倫知道最需要幫助的其實是他自己。這麼多年來,亞倫幫助無數的人解答他們無法解答的問題,他從未想過他這麼做的目的。此時此刻亞倫徹底明瞭了,亞倫解答這麼多的問題,是為了解答自己的問題。
『其實你知道解決辦法吧,其實你一直都知道。』
亞倫無言以對,繼續跟著林延向前行,進入金面山登山口。
*
兩隻松鼠在亞倫和林延上方的樹不斷跳躍,像是在追著彼此的多毛大尾巴。他們已經在金面山步道之中走了二十分鐘。林延這幾個月到輔導室找他的畫面如同旋轉木馬般在亞倫腦中揮之不去,這種恍然大悟的刺痛感既真實又熟悉。林延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木偶,他準備了一個精美製作的小木偶讓亞倫去掌握,讓亞倫信以為真。在亞倫以為自己教會小木偶走路、克服各種困難後,林延在硬生生地將亞倫轉過來面對他,在一瞬間打破他幾個月來的幻覺,但同時也是讓他面對自己。對,亞倫一直在玩木偶,玩著這個叫做何浩平職業是學校輔導老師的木偶,玩著自己的木偶。當你是木偶師的時候,就會讓自己更不像是木偶。但這一切不過是心理防禦機制罷了,林延說的沒錯,亞倫一直都知道解決辦法。
『出院後就這樣在洛杉磯過了一星期』亞倫說,『那幾天我都做些什麼我已經忘了,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但我在等待時機。至於為什麼等待時機,而非立刻去行動呢?我想這之中不存在一個明確的邏輯,只是單純覺得立刻行動的話,形跡敗露的可能性就會大幅提高。』
『但事實上是,如果他們有心要監聽或者監視你,不管你何時行動結果都是會被發現.不是嗎?我當時有料想到這點嗎?我想我沒有,某方面的我大概認為自己騙過了克林,也騙過了美國政府。我對此深信不疑,我不就是這樣一路成功過來的嗎?對那個在聯考中成功考進成大,又成功以最優越的成績被選上派去美國受訓的年輕人來說,事情不可能會出差錯。』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要對抗的東西有多麼龐大,當時不知道,』亞倫轉頭望向林延。『現在還是不知道。』
『我盡可能地小心行事,我用公共電話打給報社,我沒有表明身分,甚至連我打算要講的事情都隻字未提。我除了和一個叫做佛萊迪(Freddy)的報社記者約了隔天早上十點在報社隔壁的咖啡廳,我什麼事情都沒講。沒提到我是試飛員,更沒提到我跟軍方的關係。有一陣子我很後悔沒在電話裡提供一點點蛛絲馬跡,或許可以為那些傢伙帶來一點麻煩。然而後來我很慶幸我沒有講出來,因為講出來意味著會牽連更多無辜的人。』
『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很完美,』亞倫停了下來,望向突然出現在左手邊的台北市風景,截彎取直後的基隆河流過人工規劃的河濱公園。『很顯然那次飛機意外沒有摧毀我的信心……也不應該摧毀掉我的信心,不是嗎?每次我回想過去,越是努力回想就越是讓記憶困惑,就像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你一旦靠的太近,你就會被自己吐出的水蒸氣模糊了視線,看不清楚鏡中的自己。』
『你明白那種感覺嗎?那種自以為計畫萬無一失的感覺?』亞倫回頭看同樣停下來等他的林延,林延並沒有將視線停留在風景上面,而是亞倫身上。亞倫嘆了一口氣,他竟然對一個高中生講出像這樣的話。雖然是個精明的高中生,但終究是高中生。
然而林延很清楚那種感覺。
ns 15.158.61.1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