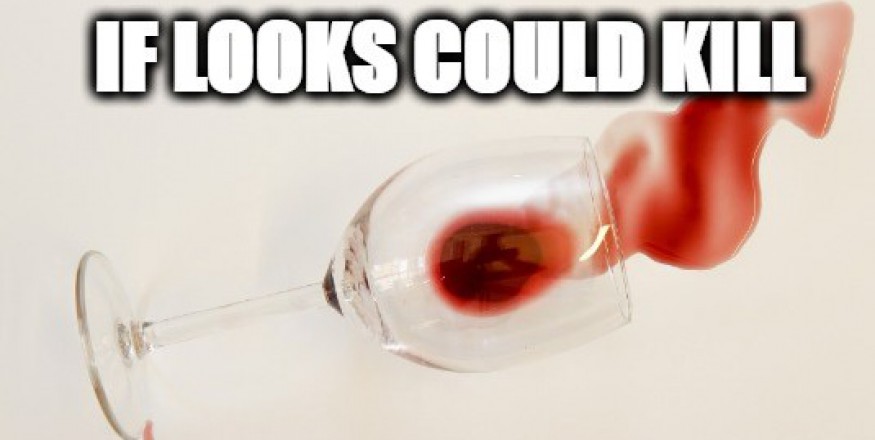加那米特拉・渥克推開寂寞芳心俱樂部的大門,不算太大且幾乎沒有任何客人的空間飄散著冷氣的味道與涼意,渥克直直走到他的老位子。左邊數來第二個位子,就是那個啤酒水龍頭正前方那個位子,不,渥克既不喜歡啤酒,也沒有對任何位子有終生不渝的情感。如果你問他他甚至會皺眉頭,渥克根本沒有注意到他總是坐那個位子。
『......關於六月底前海基會、海協會是否可能完成ECFA簽署?馬總統則表示......』晚上從來不會打開的電視,現在是打開的,除此之外白天的LH俱樂部(講英文的人通常都是這麼叫這個地方)並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酒保小島真楠轉了過來,一手撐著吧台,對渥克投以一個真誠的微笑。『午安。』渥克注意到凱特先生是店裡除了他唯一的客人,如果凱特先生算是客人的話。『今天來的真早。』
『我的學生因為腸胃炎臨時來不了了,晚餐前我沒有任何計畫。』
『晚餐後你打算做什麼呢?』
『那可是最高機密,』渥克挑眉回答。『一杯綠茶Highball。』
小島將架上的威士忌打開,倒入玻璃杯中。渥克其實不是第一次在白天的時候來寂寞芳心俱樂部,但在台北是第一次。他其實有一點驚訝這裡在白天也有開,渥克不過是抱著隨便試試的心情來開門的。就跟其他白天營業的酒吧一樣,整間店有一種帶著罪惡感的死氣沉沉。當然了,罪惡感都是來自於自己的內心,東西是不會有罪惡感的,就像命運的黑色幽默一樣。
台北的LH俱樂部不是渥克第一家去的,渥克在那之前去過錫拉庫薩的LH俱樂部,當時也是白天。對於當時是殺手的他,晚上的酒吧更像是職場,你光是看到那些老相識你就不能好好喝酒。雖然渥克的記憶可能不那麼可靠,然而兩間酒吧還是相似得莫名其妙。錫拉庫薩。渥克從皮夾拿出『開罐器』的牙齒,在西西里的往事與無數的殺戮浮上心頭。奇怪的是,似乎光是握著『開罐器』的牙齒就讓能讓他平靜下來。渥克已經幾年沒有回想起在西西里的種種,結果卻在這幾個星期想到兩次。說起來,錫拉庫薩的酒保好像也是日本人,名字他不知道。當然,就算渥克當時知道,現在也記不起來。但是那個日本酒保的臉,長的是什麼樣子呢?渥克回憶起二十七歲的自己,想起在錫拉庫薩的LH俱樂部點的酒,莫斯科騾子嗎?不對,他記得在那裡他們管那種酒叫另外個英文名字,莫斯科女孩?渥克逐漸想起來將莫斯科女孩遞過來的那雙手,那個日本酒保的手──
『你打算說那個牙齒的故事了嗎?』小島將綠茶Highball放在渥克前面,打斷了渥克的回憶。渥克笑著說了一聲不,大口喝酒。冰涼的綠茶混雜著不太濃厚的酒精進入渥克的喉嚨。
『那顯然不是你的智齒。』
『不是,』渥克說。『除了這個以外我無可奉告。』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們這邊總是歡迎更多的故事。』小島雙手撐在吧台上,露出燦爛的笑容。『一切都是為了凱特先生的善行。』
『凱特先生即便在白天也在睡覺。』渥克再喝一口綠茶Highball,台北有不少日式居酒屋提供這種酒,但是經過數次失敗的嘗試後,渥克認為這裡的還是最好喝。『他曾經醒來過嗎?』
『有,除了這個以外我無可奉告。』
渥克點點頭,然後開始一陣大笑,接著問道:『你喜歡綠茶Highball嗎?』
『還好,我個人不太贊同把綠茶跟酒精攪和在一起。』小島接著補充:『對兩邊都是一種褻瀆。』
『我以為所有日本人都喜歡綠茶Highball,』渥克搖了搖手中的酒,發出冰塊輕撞玻璃的聲響。『開罐器』曾說這個聲音是『天堂與地獄之間吊橋的晃動音』。
『我在日本出生的時候,』小島說。『還沒有人在喝綠茶Highball。』
『哇嘮,我不知道綠茶Highball是新發明。』
小島沒有答話,但是雙眼閃過一陣笑意。渥克注意到了,敏銳的洞察力也是他當殺手後留下來的眾多痕跡之一(也有可能跟他是飛行員有關,但誰知道呢?),但是他何必在意呢?渥克對於綠茶Highball的興趣僅限於酒本身,渥克疲憊的人生值得他在對歷史毫不知情的狀況下享受綠茶Highball。
『......這是非洲首度主辦世足賽,開幕戰也將由地主國南非迎戰墨西哥......』
但渥克無法看透林延。
兩個多星期過去了,渥克完全不知道林延在做什麼。林延很親切,為人著想,儘管和渥克過去所說不符,但他知道林延其實是那種總是會堅持在餐廳裡給小費的那種客人,還會帶著那種誰也無法抗拒的真摯微笑,那種可以為所有人帶來陽光的微笑。
但是林延不只是這樣,他心中深處藏著某種秘密。渥克很清楚,因為渥克自己也是帶著這種秘密活著的人。在誰也看不到的心靈的深淵中,存放著沒有辦法讓人知道的秘密。而有的時候,這個秘密會閃爍在雙眼之中,渴求著被理解與發現。那種強烈的目光,是幾乎可以殺人的眼神。林延讓他想到『開罐器』,同時也想到了自己。渥克是遇到了林延,才發現自己變得多麼像『開罐器』。沒錯,渥克學會『開罐器』的一切技術,然後殺死他,最後無可避免地成為了『開罐器』本人。
林延的音訊全無,讓渥克更加好奇他究竟在做什麼,他確定林延的飛行技術和知識絕對可以讓他順利拿到任何國家的飛行執照,但是──
『為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新聞主播的聲音似乎比先前急促。『據傳民航局的查核機剛未經許可從松山機場起飛,是否為被劫持則尚待釐清......』
渥克盯著電視,手中握著的牙齒掉落至桌上。他多年來的直覺告訴他,這跟林延絕對脫不了關係。
*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就快到了。』飛過基隆河與中山高速公路後,林延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拿下口罩,大口吸著瀰漫於駕駛艙內的難聞香水味。稍微將飛機左傾,讓公館山保持在右前方。從跑道正中央到跑道終點的距離,與跑道終點到黃虹穎的家的距離,大約都是二點五公里。不會有任何人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做什麼的。空軍無論是使用桃園機場還是龍潭機場,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到達這裡。而松山機場唯一的跑道他一直到剛剛都還在使用。
而即使戰鬥機抵達了這裡,空軍會在台北市上面將他們擊落嗎?或許遲早會,林延無法確定,但是林延知道他只要將事情進行的夠快就不需要擔心這些事情。
強勁的東風造成一點顛簸,這裡的風比中壢強上許多。林延還沒習慣這種風速,對於第二次開飛機的人來說,這也沒什麼好丟臉的。
『我的資料告訴我,你是個王牌試飛員,對吧,亞倫?』
『頂尖中的頂尖,孩子。』
『很好,』林延說。他可以感覺到他的雙手和額頭都在冒汗,他的心跳得飛快,林延這輩子第一次感覺到這麼興奮。『非常好。』
現在速度是每小時九十英哩,而高度為一百九十英呎。目標就在眼前。
ns 15.158.61.1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