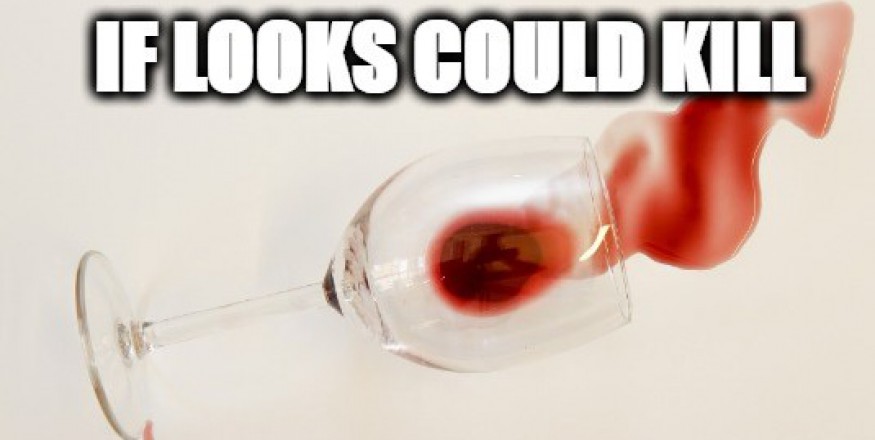拉起逃生把手後停下捷運所造成的急速停車,感受的力道比林延預想的小,但是那一點也無所謂。感謝滿腔熱血的物理老師,林延把數據計算得非常完美。
林延將他的雙人牌菜刀抽出來,迅速環視四周後,大部分人並沒有注意到列車的異常減速,也沒注意到他把菜刀拿出來。
『咦?』小聲的疑惑穿梭於車廂內部。『又停駛。』有些人苦笑了一下,有些人環視四周,但沒有人真的提出疑問,甚至沒有人注意到是他拉起緊急把手的。當然不會有人覺得奇怪,畢竟文湖線停駛就像釣到垃圾魚一樣稀鬆平常。
林延走向那名戴黑色帽子的男子──
列車完全停下來,『右側開門。』正如同林延的計算一樣,列車停在即將轉彎處,旁邊沒有鐵絲網護欄,同時又有一棵與軌道等高的樹。此刻,松山機場、基隆河和圓山大飯店一覽無遺,六月的夏日豔陽閃耀在河面上。
──車廂門打開,台北夏天的黏膩空氣與車廂過強的冷氣開始交互碰撞。林延從黑帽男子的後方用左手臂抓住他的脖子,捷運中人們的目光開始飄向他們。『等一下!你──』
林延在一瞬間將菜刀抵著黑帽男子的後頸,刀尖稍微刺入皮膚內,細小的血滴如調色盤上的顏料緩慢滲出。『再講一句話我就切開你的喉嚨。』林延那宛如上台報告的清晰聲音在黑帽男子耳邊說著,黑帽男子再也沒有講任何話,車廂中的人群開始往車廂的另一道打開中的門跑去,有人正在大喊一些『他有刀』之類的話,林延並沒有注意他們所講的話。現在的他只知道人們的反應如同他計畫的一樣。
『向前走。』林延對著黑帽男子說。『走出車門,到鐵軌邊緣。』
*
亞倫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切發生。
當他還沒來得及整理好思緒時,他聽到緊急對講機傳來嚴厲的聲音,好像在質問拉下緊急把手的原因。『亞倫!過去鐵軌邊緣,跳到樹上!』林延的英文蓋過對講機的內容,傳入亞倫耳中。
不同的語言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魔力。對亞倫來說,英文仍是他受訓的語言。他的身體在頭腦質疑之前就做出了行動。
亞倫往前走到車門,看著揹著高爾夫球袋的林延和那名黑帽男子跳到樹上作為緩衝,再跳到機場跑道的地面。亞倫站上鐵軌邊緣,看著松山機場的跑道,停著的飛機。在那一瞬間,那個景象解答了今天一整天的所有疑問。而毫無疑問地,接下來發生的事可以解開他這一生的所有疑問。
三十多年來,亞倫不只一次地想過,要是再一次讓他做選擇,他仍會放棄飛行嗎?亞倫過去不知道答案,但是他現在知道了。
王牌飛行員亞倫・吉恩茲拖著老邁何浩平的身軀,跳出捷運車廂。在那一刻,他比任何時候的自己都還年輕。
*
『你知道我們不應該在這裡做這種事。』
『沒有人會進來。』塔台長江敏在控制台旁邊的平台上一邊抱著暱稱東尼(Tony)的塔台員蔡雨新,一邊舌吻,雙手抓著東尼的年輕而健壯的後頸,外頭灑進的六月亞熱帶豔陽,照亮著她今天擦的亮紅色指甲油。東尼說的沒錯,江敏的確不該在這邊做這樣的事情。畢竟她還算是東尼的上司,某種層面上來說這樣可能違反職場倫理。但是台灣本來就充滿了亂七八糟的傳統,不是嗎?四十六歲(『虛歲四十七歲!』她似乎可以聽到她那敬愛不已又不希望時時相處在一起的母親在她腦中碎念。)的單身女性在台灣就像帶有原罪一樣。
『我應該看著螢幕。』東尼稍微推開她,但是也沒有太用力推開。眼神滿是困惑與掙扎,過去不知道有多少人成為他那雙眼的犧牲者。江敏越是深入思考,便越是想要佔有他。
『我會幫你看。』江敏帶著貪婪的眼神回答,接著繼續親吻東尼。她現在就是要,這個世界像是永遠繳不出租金的惡意房客,欠她這麼多這麼久,她沒道理打破一點點沒有人會注意到的小規矩(況且她真的有在看螢幕,下一班降落的飛機還有十五分鐘)。既然這個世界逼她從倫敦回來這個她一輩子水土不服的島嶼,她就要把一切搶回來。沒錯,沒有人可以打斷她生活中唯一的樂趣。
『松山塔台,午安,』無線電傳來了聲音,是航務組的人員。『有三名不明人士闖入W(Whiskey)滑行道。』
她在心裡翻了個白眼。沒錯,這個世界總是有方法可以剝奪你的樂趣。
*
林延的著地點和黑帽男有5公尺左右的距離,在林延最縝密的沙盤推演中(大多在午休時間),對方很有可能會趁著他落地的時候攻擊,因此揹著高爾夫球袋的林延落地後用最迅速的方式站起身。用一般速度起身的黑帽男,在還沒回過神來時林延的雙人牌菜刀就已經架在他的脖子上。
『往前走。』林延喊道,從基隆河灌進松山機場的大風陣陣吹來。在前方不遠處的南側停機坪,一台雙螺旋槳飛機就停在那裡,那是民航局的查核機。在數不清的早晨(與夢境中),林延從車廂中看了無數次的比奇超級空中國王(Beechcraft Super King Air)。林延突然感到一陣不寒而慄的詭異感覺,哪裡不對勁,林延暗忖。每一個步驟都在林延的計畫之中完美進行,不是嗎?
林延回頭一望,看到略顯疲累的亞倫,穿過草坪而來,留下乘客們在後方捷運車廂上目瞪口呆。一般人從那樣的高度的樹上跳下來可能沒有問題,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六十多歲的老人可以安全著地。
但林延也沒有懷疑太久,畢竟亞倫・吉恩茲從來就不是一般人。
*
『一號車,松山塔台呼叫。』江敏拿著望遠鏡說道。她那濃厚的伯明罕口音英文,在和她那個來自伯明罕的前男友分手後反而變本加厲,人們總是在離開某個朋友後,無意識地模仿他們行為或說話方式。無論是他們是好朋友還是大混球,當然,我們是不會隨便離開好朋友的,對吧?
『松山塔台,一號車,請講。』
江敏的望遠鏡中,有三個人穿越W滑行道,朝著西南方的二號停機坪前進。三個人都戴著口罩,其中兩個人帶著遮陽頭套,那種腳踏車騎士喜歡戴的那種難看款式,還有一個人揹著高爾夫球袋。文湖線車廂停在後方的軌道上,好像捷運車廂是高爾夫球場的發球台,而他們三個人正要朝著跑道中央前進打下一桿。
文湖線雖然在塔台肉眼可看得到的距離,然而文湖線三不五時就停駛,江敏實在不應該越過所有應該去注意的東西,去特別注意停下來的車廂。從航務組的人員得到的即時消息來聽,這三個人應該是從捷運車廂闖入機場內的。然而,在江敏還沒開始思考這件事情的可行性和荒謬程度時,江敏注意到了另一件事情:其中揹著高爾夫球袋的人拿刀架在另一個人的脖子上,兩個人用運動會的兩人三腳的方式緩緩前進。
『一號車,請至二號大坪。有三名人員闖入W(Whiskey)滑行道。』江敏感覺到她開始流手汗,她真的他媽的很需要一杯威士忌。『其中一人持有一把刀。』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