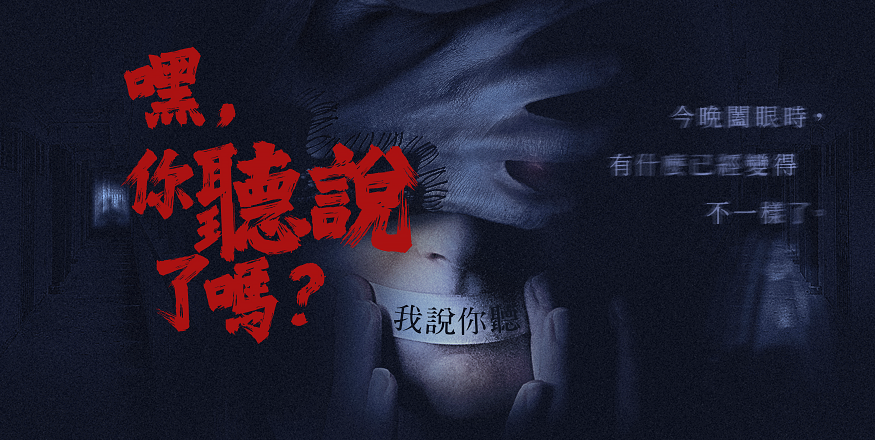眉月的短髮勾著下頷,雲鬢輕揭,珍珠耳串是夜空中的星子,嬝嬝婷婷的步履融進了夜幕,只留下旮旯角的一陣高跟鞋餘響,是午夜的夢囈,似是說了,卻又不知說了什麼。
趁著月亮寐在了雲榻,趁著清冷的街景,好在遠處的狗螺聲並不打擾,我們且說說芸娘,那個在老東城一間換作「金鑲坊」的華廈的女子的故事。
芸娘是給人做小的,她一直都知道,就算她生得再美也是一樣。
六歲的時候,她給瞎眼先生摸過骨,說她這一生沒有好姻緣,如果硬是成婚,終究是得離婚收場,大娘想著,女孩注定是賠錢貨,如果又沒個夫家依傍,和養雞鴨魚牛有什麼分別?大娘沒受過什麼教育,但那年的村婦大都會同大娘一個心思,於是便想找個由頭把她給賣了,只是那時候上頭抓得緊,大娘只得作罷,便趁一次外出的時候,把芸娘給扔了。
芸娘給一戶姓潘的人家給撿了去,本來在家裡做些粗活,侍奉侍奉潘老太太也還算得清閒,只是一次三少爺回家的時候,見了芸娘一面,便很是喜歡,於是央求潘老太太把人送給了她,潘老太太最疼這老三,所以便把芸娘給了出去。
自此,芸娘就養在了金鑲坊。
而金鑲坊的對街,有一間髮廊,金鑲坊的小姐們都會來這裡作頭髮,好比三樓和四樓的小姐是汪家的情人,只是不知道順位排第幾,但既然碰上了就沒給對方好眼色,兩個女孩楞是搶著讓老闆給他們作頭髮,把鈔票大大方方的擱在桌上,一張一張的往上疊,老闆雖然樂開了眼,卻又不敢真得罪誰,誰知道這些小姐們背後的先生是誰,她們私底下都喚她們為小太太,而金鑲坊,自然也被喚作小太太樓,因為既沒成婚、又沒名分,說是太太要給人笑話的!而當著年輕小姐們的面上,又不敢這樣喚人家,怕沒個準又惹得誰犯了心病。
每個小太太們留著最時髦的髮型、穿著最合身的旗袍、噴著最令人流連的香露、踩著細如針的根鞋,聲聲扎在男人的心尖,最好能疼得出血,讓那個他能連夜驅車來了金鑲坊,好偎在小太太的胸口好好療傷。
這裡的每個人都好似是芸娘,但芸娘,仍只是芸娘。
後來,政局動盪了,有頭有臉的人家坐船逃了,聽了風聲的小太太們,有點眼界、手頭又有點細軟的,早給賣了買通船夫,而其他傻傻的小太太,仍留在了金鑲坊,等著把她們捧在手裡的男人派車來接她,她們也不秤秤自己的斤兩,可如果秤了,她們這一生又該怎麼過下去呢?
沒走的幾個小太太,成了別人的小太太,而芸娘,仍在金鑲坊裡等著三少爺,不是因為他的錢財、不是他的溫潤、不是他的軟語、不是他的薄情與狡獪,自然也不是潘家那不負存的家世。
有人說,她只是負氣,負氣三少爺沒來接她、負氣她把首飾借給了某一樓的小太太,或許小太太換了船票,登了船奔著幸福去了。可或許,她只是在氣自己六歲那年的自己,少不更事的給瞎眼先生摸透了一生,但芸娘內心還是傳統的,或許每個小太太也曾魂牽夢縈那欠了一生一世的婚禮,不管如何,她終究沒有離開金鑲坊,儘管金鑲坊早已經改朝換代。
金鑲坊已經不是以前的小太太樓,小太太們衣裳的布料變得少了,金燦燦的首飾其實也只是外層鍍了層薄金,香水也變得俗艷,妝容也不在內斂,大厚的粉底才能遮住臉上、手上青紫的印子。花錢的大爺們不需要那種端莊中藏著悶騷,而最好是發自骨子底的淫靡而媚俗。
髮廊的型錄成了皮條客的審美,留在金鑲坊裡的小太太們也不在被一個男人眷養著,但他們必須記著每一個男人的面貌和習性,如果不想挨打。
但她們總歸是離不開樓裡。
直到有一日,芸娘遍體鱗傷的望著坐在床沿抽著事後菸的身子,他的身後是破舊的老鼠皮灰的窗簾,儘管破舊,卻能遮住了大半的陽光。
那一個瞬間,她不知道哪裡來的力量,竟將窗簾扯了下來,而男人點著菸,嘴裡對剛才芸娘的表現恣意地做出了評比,其他的小太太也成了他品評的對象,像品茶博士那樣。
芸娘將窗簾圍在了男人的脖子上,一陣劇烈的反抗和扭打,最終芸娘戰勝了命運,品茶博士甚至連褲子都來不及穿上,狼狽的瞪大雙眼地倒在了地上,一點也不文雅。
芸娘把老鼠皮灰的窗簾戴在了頭上,對著剛才打破的鏡子左照、右照,很是歡喜。
她覺得這一刻,她成了金鑲坊裡最美的,也是最後的一位新娘,想到這裡,她便把自己吊在了房樑上,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後來,越來越多小太太們和皮條客不知什麼緣故都死在了金鑲坊裡,連對街髮廊的生意都受到了影響,說是有披著窗簾的客人,吐著拖地的長舌頭說要讓人給她做頭髮。
最後連司機聽得客人要往金鑲坊一帶,都嚇得把客人趕下了車。
因為聽說金鑲坊裡,每晚都燈火通明,為一位披著頭紗的女子慶賀她的婚禮,只是,那個女子,到現在還沒找著她的夫婿... ...。
44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ba82rTj7M
44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W27RosM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