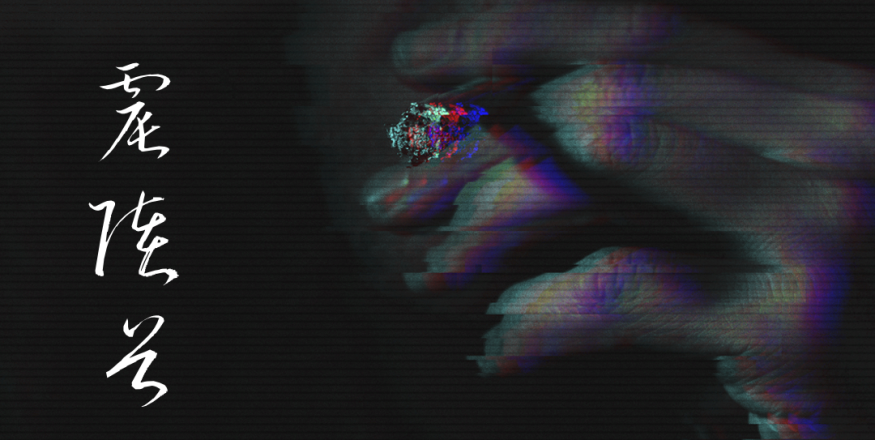名單公佈後短短一個月,很多人將會在舍堂絕跡,例如Kai Ching。
Kai Ching的去留不會觸動到任何人一條神經線,格格不入的命格註定是兩年宿,多一個月也不能。他離開,不會再承受多餘的目光,不會再見那傷心的天臺,不會再被床上、煙中的甜話欺瞞。牆外,人爾詐我虞,但群體活得零散,私人生活還可從社交生活分割;牆內,人仍舊詐虞,可惜牆薄室近,私人生活與社交生活交融不分。
活得多點自尊自愛;這是Kai Ching在這孤單敗壞的城中學到的唯一道理。
Kai Ching上星期一提早遷走。樓友便草率地聚了頓飯,歡送他和幾位大仙。宿堂的門楣下,他拍了一幀又一幀的合照,發了一張又一張的限時動態,廿四小時的時限給了他最後的曝光,好比如日中天的盛陽在黃昏時的餘暉瞬間消散在無垠的穹蒼。他抬頭瞻仰那看了兩年的四字門牌,回望朦朧的玻璃門後,奢望某一刻那個影響他餘光的人在轉角處竄出來,送上一個擁抱。
多等一刻的幻想,也不過自作多情。
Kai Ching縮身躲進後箱滿載的紅車,永別這城。
震陸首並非不知道Kai Ching離開,本來寫了一大段訊息給他,關於自己的悔過,關於自己的不智。但最後一刻,只怪他清醒得害羞,按實着「刪除」,消失半秒的直線向後回跳,把掏出來的心聲一一收割掉。我看着震陸首在黑牆紙前發愣,直到他透大氣,才知他沒猝死。
他最近編曲至凌晨,吃睡不安,彷彿靈魂寄宿在音樂之中,身體是乾竭的。
蒲月,宿堂的送別如黃河之水絡繹不絕。大仙留戀此處,恨不得一大疊百元紗灑在事務處,留宿一宵還一宵。直至職員三催四請,才把衣服抛進紅白藍。有些卻不恨留戀,早兩三天已低調搬離了。
我樓兩位大仙是後者,若不是空堂,我也不能送行。我坐在大堂老舊得脱皮的沙發呆視着廿袋等待運上車的紅白藍,隨人合照,剛好有另一女層送行,門牌便一時變得稀罕。
女的大仙在門牌前千嬌百媚,男的在路邊挺胸作勢。我在想,他日我走,我會想甚麼呢?我該是未發達,灑不了百元紗耍賴不走。
十三人聚首一堂,燈光一閃即逝。相片裏,燈籠難得收起嘴臉,在左上角撘着將離開的阿強,撐起了久久枯萎的蘋果肌;震陸首則在右下角最遠的距離莞爾,彷彿格格不入。
星期日,樓層本已冷清,現在又走了幾人。沒正事做,我也沒趣留下虛渡光陰,便了衣,想回家好好一睡。
走出房門,便聽到硬淨的膠袋的磨擦聲,窣窣窸窸,該是清潔工人(以前他們穿青綠的制服,人稱「青皮人」champion)打掃了。他們智力殘健,發生過太多次尷尬不當之事,所以他們打掃廁所前都被指示説要敲門,「有無人?入嚟做清潔!」問清楚才進去。
但我聽不到他們一貫響亮的口號,那便奇了⋯⋯我探頭前走,遠遠一雙纖幼的手臂小心翼翼地把摺成方磚的衣服放進行李箱。我走近他,他目無表情地回望我。我蹙眉:「去旅行?」他淺笑一下,身子靠後頂開了木門。裏頭空空如也。
「我move out啦。」他拉拉鏈,爽脆的升音愣住了我。
「你幾時話唔住㗎?我以為你好想留低㗎?」我還歷歷在目當日他在床上哭訴想留下來,不溑幾日便轉軚,如今還這麼低調而去。他低身拾起行李:「咁想唔想同應唔應該始終係兩回事。我都無咩好留戀,你⋯⋯你保重啦,我走啦。」
「我送你。」我孭着背囊,挑起一兩袋物件,隨他下去。
升降機裏頭我凝視着他蒼白的削腮,那張惡毒的嘴巴,他兩眼惺忪,眼皮頹喪地蓋過半個眼球,見我凝視不言,頷子一仰,俯視我問:「你望咩啫?」
「點解咁突然?有無人知?」
「無,得你知。」他一頓:「我走咗之後,你唔講出去,三日內都唔會有人主動揾我。因為永遠係我揾人,無人揾我。我最近先發覺我唔係我自己想象中重要。」他的話比平日説得平靜很多,散略了很多不必要、冗長生動的粗口。
我看着慢慢墜落的數字,升降機比平日慢了許多,他抬頭望着屏幕:「FM,我嗰日問你可唔可以幫我囈吓莊,你點答我我好記得。」
我沒答話,心如𨋢墜。
「我睇到你好唔情願。FM,我自問對你唔差,你私底下點同震蛋講我啲嘢我一路都唔揣測,我都唔想分化你哋兩個。我交個心出嚟為層樓好處處為你哋仆心仆命,但嗰日你敷衍我我睇得一清二楚。我住咗五年Hall,要識嘅人都識過囇樹敵都唔少,知人口面不知心我住多一個sem又點話?嗱,我可以繼續瞓單人房定閒打下台牌,我理得你哋點睇我。但係,如果得唔到大家嘅尊重,住落去又有乜為。」
此時,𨋢門打開。沒有巧合偶遇樓友的戲碼,大堂空空如也,只有不用錢的冷氣和常常捉人屈蛇的保安閪姐。他接過我手上的行李,我沒有跟他走,他亦沒有叫我隨行,孑然離去。
燈籠瘦削的背影消失在正在關上的狹縫。
太多的揣測是種自虐,精神自虐便壓挎了他留下的最後一根杜草。揣測那天我是否敷衍他、揣測我和震陸首的私聊、揣測我對他的態度,大抵這就是他經常提及的雙魚座特徵,疑心病。
燈籠走了後,他煞有介事地退出了麻雀群,人人立刻私訊向他問好,才知他退宿了,一時之間吵得沸沸揚揚,樓友司馬汗跟他本來就交好,便邀他回來,一番問好勞動,燈籠又回群了,還説明天有局便回來打。
我沒跟其他人説燈籠臨走前的話,或者我需要,但其實他的品性路人皆知,也用不着再加附錄。
大仙要走的都走了,早日新鮮的也褪去了一層稚氣,知道人情世故,知道清規戒律,留下的我們在大仙退宿的翌日立刻聚在一起,開了第一個樓會。
六月尾的樓會,公私事都會攤出來説,奈何上年燈籠跟震陸首不和,樓會如擂臺,前一句含沙射影,震後一句指名道姓,明爭暗鬥得旁人疲憊,正事也談不好。幸後兩人拍拖,通常兩人只有一人代表出席,樓會也不多,便無硝煙。
今日這個樓會只有我同年出席,震陸首留在房裏作歌,也不想打擾他是了。
「嗱,咁我哋就直入正題。」樓主白無常說話一向直接:「我哋層樓自從震蛋張poster之後已經被好多層議論,再加上上次同女層joint floor,Hall莊應該會想剔除一啲柒頭,洗好個招牌。換言之,我哋全部人都喺watchlist。」他吞了吞口水,又説:「今次樓會我除咗想傾分房,我仲想確立一個我哋層樓嘅保護機制。內部矛盾,內部解決。」
談到分房,十一樓的頭房近十二樓的洗衣機房,天花吵得可憐,但後房近後山多蚊蟲;有人偏愛後房清靜,有人偏愛頭房出入方便,傳統上大家都只會選一邊落腳,方便聚集,另一邊便由外地生入住。意見一時紛亂,磨擦了一會,便有人妥協了。
「無其他意見?」白無常雙掌一攤:「咁入正題——我知上年層樓嘅矛盾影響到大家嘅⋯⋯你明啦,㗩,但我作為樓主唔想今年都係咁。我希望樓友同樓友之間唔會互相欺騙,有啲咩唔鍾意嘅照直講。即使發生咩事,人哋一定會問我哋層樓發生咩事,我哋只要講返啲皮毛就得,問深入啲就話唔知。鎗口應該一致對外,我哋圍內自己屌。做到內部矛盾內部解決。」白無常專讀國際關係,這話零舍有味道。
「咁如果有人問起個QR code我哋應該點答?」我問。
「話條友輸咗個bet。多多都唔洗講。」
「其實有啲層已經知佢屌過邊個,咁講起可以點。」
「唔,答唔知。」白無常手掌直批:「總知大家唯一知道嘅事就係震蛋貼咗張QR code,其他一律唔知。」
「我想補充一樣嘢。」積舉起了手,説:「如果有人問起點解燈籠要quit呢,我哋都答唔知?」
白無常搔搔頭,低聲地吱吱唔唔,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吱唔甚麼;他舉頭,手直批:「因為佢要grad。如果有人再問佢係咪defer,你話唔係就得,因為我已經問過佢,佢本人係非常介意defer,佢想快啲擴大自己生意,defer好防礙成件事,所以呢個sum-sem佢讀咗好多cred。你答畢業就搞掂。」
我們恍然大悟,也不知道這説法有沒有漏洞算少了。
突然,咔一聲,木門推開震陸首走了進來。
「我想坦白一啲嘢。」他臉目無情地説:「燈籠件事無咁簡單。」
大家面面相覷,眉頭眼額之問看出大家同在思索一個問題。
他,在門外,聽了多久。
ns18.119.120.8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