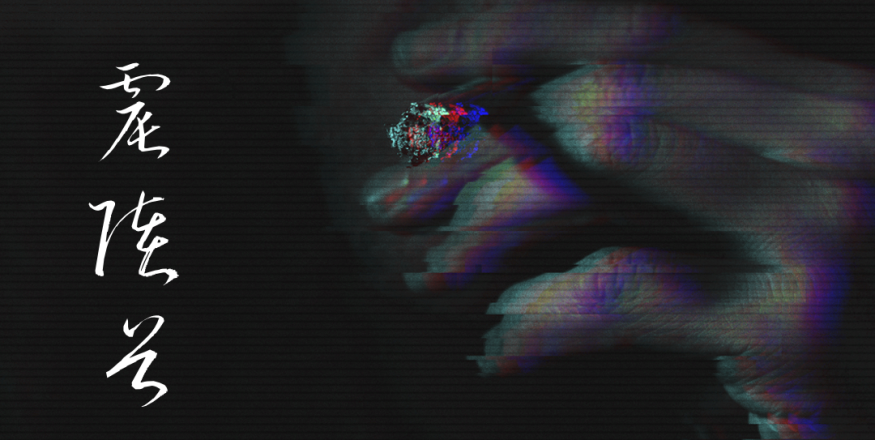我倒了杯水,眼前是一大疊未清洗的餐碟。三天前吃火鍋的殘渣還在,發出陣陣酸膄惡臭。倒走浮渣,去水位頓時酸嗆。洗水盤一旁的紅色大塑膠垃圾桶塞滿了昨夜的啤酒罐,彷彿酒罐仍能深處聽得到昨晚鴛鴦劈酒,鬼哭神嚎,迴盪在整間起居室。劈酒是恆常的聯樓活動,客人甚至會跨越舍堂,遠道以來,清晨方去。25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xQyaV26Jn4
Gin、 vodka、whiskey、Heineken⋯⋯苦澀混上甜的RedBull、可樂、益力多和維他檸檬茶。乾了一小杯又一小杯,酒氣熏天,淹去膄臭,眾人肚子漲漲,兩頰赤熱,辛辣的嗓子狂飆着粗口和嚎叫。
「開心返埋嚟!」「一!」「一!屌你老母!」「輸咗下五家飲,右邊接!」「一拳啊一拳,兩拳啊兩拳⋯⋯十拳——啊——十拳!屌你老尾——飲啦!」「五!」「五!」「五!五五!」「變快!屌!你飲!」「一人一個分手理由!」「閃!閃!飲!」「新加坡枚呯嘭猜啊!呯嘭剪啊!呯嘭猜啊!」吵吵鬧鬧,喝的喝,醉的醉,吐的吐。
男女梅花間竹坐,熏熏重重的秀髮垂在鬆弛的肩膀,臂膀一展,又抱了多少雙鎖骨。
我剛完成readmission interview,避過了激烈的灌酒遊戲,三時半,人潮已去了一半。坐到震陸首一旁的空座,他那雙肉頰痛紅,聲子變得靜悄悄的,跟臂彎中的女生談得眉頭飛舞。阿強也清醒,與一旁的女生促膝談心。遠處,有兩眼緊緊咬實震陸首,如貓眼暗淡中射出青光,女生的笑聲越響,青光越厲。震陸首不知是有意避看,還是樂極忘形,始終沒回視青光。我坐在震蛋的正斜方,見他雙腿不住地打震,看來他是知道的。
女生按着他的大腿,越掃向上,幽幽地説:「做咩啊,你好凍啊?」
震陸首雙腿一縮,燈籠呯一聲彈起:「屌你老尾你個姣屍躉篤發姣唔好喺呢度啊!」
全人望向他,酒凝半空,場面頃刻發冷。
「細路囡唔識野,我代佢飲。」一個濃妝豔抹的大仙按手在燈籠面前,舉手就是一整罐啤酒,傾轉酒罐,沒一滴流出。
燈籠眼睛依然瞪大,青光又烈又厲,大仙的酒罐放下,燈籠怒火未熄,睨瞋那女噴:「你老尾正臭閪。」抽身就走,一陣騷動,震陸首即時起身隨後。
起居室頓然冰冷如停屍間,阿強也停了泡妞,冷空氣中傳來外頭大堂的呼喝。
「你老尾可唔可以檢點啲啊!我睇撚實你你都可以同個臭閪咿唈,你有無放我在眼內!」
防火門隔開了他的回答,大家都大約而同壓低聲量,阿強卻回頭繼續陶醉於與少女談心,談得開眉笑眼。
「我理撚得係佢撩你定你撩個臭閪啊!你知唔撚知咩係避嫌㗎!」
接着呯一聲,呼喝聲拐進走廊,火藥果才漸漸息微。
酒桌上除了阿強和少女外,人人面面相覷,很快便散掉歸返了,酒罐都抛在我旁的紅色大塑膠垃圾桶。25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rEF8Fsg2O
我的雙手泡浸在潔白泡裏,手指竄動,碗碟擦得滋滋作響。向左一瞧,麻雀擱着,四角皆空,如若滿目瘡痍,定是大家都知燈籠的事所以怕了。我一邊洗擦,突然門開了,燈籠拖着人字拖進來,眼圈又深了一度,昨晚定是一通無眠夜。
他蹙起頹靡的散眉,説:「食唔食早餐?」他吃慣外賣,我問:「外賣?」他説:「出去食。民華。」
我哦了聲,更衣,便吸入玻璃外窒息的毒氣。
兩人並肩而行,前頭是一對情侶。他們牽着手,前後擺動,彷彿他們的手是天下的鐘擺,有説有笑的樣子,旁邊走來一個娜娜身影——男的手猝然鬆開:「喂曉娜!」三人互相打了個招呼,至曉娜走得老遠,男的手才重新纏繞起女的手。
燈籠默不作聲地一徑走着,我見他心事重重也不敢打擾。
良久,他才開口説:「出hall pool唔係咁簡單。」我沒插話,讓他的話繼續流下去,「拍拖係兩個人嘅事你話係咪呀?兩個人嘅事但係廿二層嘅人知有人知就有傳言,有啲仆街就會穿鑿附會話你乜話你乜。屌你老尾關你撚事咩!」
「咁無辦法啦。」我聳聳肩,也感無奈。「唔係呀,我覺得佢好似有第三者。」燈籠撐起眼眉,眼晴老大:「上次同佢出街——係未有太多人知——但係拍拖緊係要拖下手㗎啦,啊屌你老尾佢見到有人即刻甩開我隻手!屌你老尾我唔撚係你男朋友啊!佢話驚比人知,OK!屌——琴日見到Kai Ching又係咁!你話啦你話咩意思啦!」
「咁⋯⋯Kai Ching係尷尬啲嘅。」我不知道震陸首與Kai Ching的關係,若然兩位男友都覺自己才是正印,當時的情景想着也尷尬發麻。
「之後夜晚仲要同個姣婆四咿咿挹挹。」燈籠忍住了長篇大論的粗口,先點了餐,一份貼切的叉燒飯,然後繼續發洩。我頭一直點,聽着他訴苦,腦袋一直放空,話題越拉越遠,遠得他的快嘴追溯不了昨天的憤怨。吞下桌上的黯然,他的嘴巴才疲倦下來:「埋單走啦。」
啊,在舍堂拍拖複雜,是地方,還是人太複雜了⋯⋯
回來後,麻雀桌的四邊重新充滿了人氣,旁邊又站着幾人,好住不熱鬧。但我倆一進了來,吵鬧聲驀地停止。
「做咩事?」燈籠深知雀友習性,心知事有蹺蹺。
「莊啱啱傾完45% readmission rate,有人傳waiting list 有你⋯⋯」
燈籠立時大叫一聲,毒舌如雷打在舍堂的天頂,山搖地裂:「呢支莊係無腦爛焦閪嚟㗎!我住咗五年,quit乜撚嘢我啊!咩新絲蘿蔔皮夠輩份quit我啊屌你老母!我為咗間Hall撲心撲命嗰陣呢班柒頭毛都未生齊呀!」
燈籠還有credit未讀好,應該下學期才完成,將邁進第六年宿。其實發怒也是情理之中。
「同埋邊個傳啊?你老尾點會一晚就有waiting list!」
「屌——琴晚頂酒嗰條女係隔離Hall莊大仙,同Nat好friend㗎。」
聽罷,燈籠立刻衝進了震陸首的房間,勁雷劈開房門,雷聲響遍走廊:「你話同你Nat扑過野啊嘛!屌你拆掂佢啦!」
你話同你Nat扑過野啊嘛!
這句話迴蕩了整條走廊,高亢清晰。
印度供電不穩,因此街頭電工東駁西駁地偷電,形成縱橫交錯的偷電版圖;舍堂人際關係本已荒亂,貼在升降機的QR code,便是產生亂象的電工。
「你話同你Nat扑過野啊嘛!屌你拆掂佢啦!」我聽罷這句震耳欲聾的話,思緒都清了——
記憶裏,十二樓的相遇,我看到一件事的開端,就是電工進來駁電那一刻。
「其實,我都未睇過,真係唔知咩嚟。」
「你唔知?真唔真啊?」
「一齊睇囉。」其中一個女的拿起手機掃閲。
打破先例掃code的那位並非身材豐腴但樣子平庸的曉娜,而是一旁的Nat,那個五官標緻,在村口被男友鬆手的女生。燈籠冒犯了Nat,處於被退宿的懸崖,而他的伴侶作為一個第三者,固然先加利用。
舍堂教育有素,即使事關遠近,大家都遵循「事不關己,沾沾自喜」的態度。當然,對於泛泛之交,大家可以割席不理,但身為樓友的大家,還得考慮樓的名聲。Hall無秘密,卻樓有秘密。那天燈籠在joint-floor的怒罵已傳到了門外,樓的名譽掃地不過是時間問題,沒料報應來得如此之快,此刻還突然爆出如此驚人的消息。不涉事之人一旁吃花生吃得津津有味,但一眾樓友臉有難色,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該從何勸架。
我坐在起居室,陪同四位雀友,他們的牌突然打得很慢很靜,寂靜穿透牆壁,嘗試嗅點火藥味。不果,大家甚至停下來,站升降機旁聽,我插着袋垂頭從後聆聽。舍堂的公共空間都很有趣,是吵架聖地。
「喂係你同個姣閪咿挹我先鬧㗎喎呢件事你都有份,喂再講你係我男朋友幫我都係人之常情啊嘛?」
「我撚有同條囡咿挹啊!你咁多疑搞出禍被人quit係抵撚死!」
眾人都凝着氣,不約而同地低㕴:「仆街了。」尾隨一連串高低起伏的「G」。
「我抵死?你以為我無能力搞死埋你啊?」房間突然一大吵雜聲,呯一聲,震陸首揹着個小包,戴着口罩走出來,目露凶光地瞅我們五人一眼,按鍵,進了升降機。
升降機向下直飛,停滯數秒又飛動。窗外,一個肥頭胖身的身影沿着大路離開了。眾人不知道如何是好,麻雀也索然,於是大家紛紛回到自己的房間。我走過燈籠的門前,停了下來,遲疑半刻,然後推開了門。
他那雙通紅深邃的眼直直地望着我,説:「你仲入嚟做咩?」
「你無嘢呀嘛?」
「屌佢老母臭化爛焦閪⋯⋯」他也無力再罵一句完整的髒話。他坐在床邊,拿起一樽香薰猛吸,彷彿這是他的哮喘劑。燈籠扭成一團的臉容逐點逐點地鬆弛下來,他放下香薰又拿起電話不斷按鍵。我不敢打擾他,便靜靜地退至門外。
這晚,從不離開舍堂的震陸首沒有回來。探熱鎗般的麻雀枱又回歸了平靜。
我躺上床,事情挑撥着我的情緒,渾身不舒服。他們的吵鬧聲迴蕩在我的耳朵,揮之不去。
ns18.224.32.17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