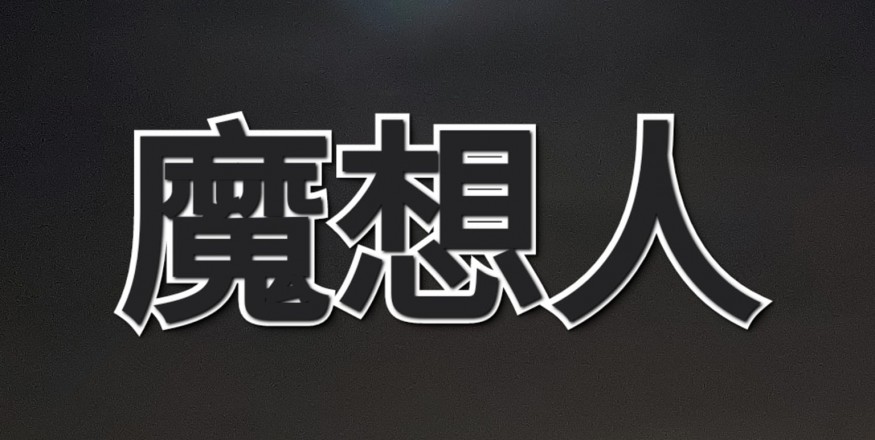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尹德瑪」。
這名字,是我母親在自殺前留給父親最後的一張紙條。她這番不負責任的行為把父親搞得又氣又急,卻夾雜著悲痛的五味雜陳。這紙條,我仍留在房間的抽屜裡,夾在日記本裡的最後一頁,早已泛黃皺爛,不仔細看還以為是誰寫錯的紙條然後揉爛被我給回收作紀念。
它看起來普通,卻又帶著懸疑和神秘感存留到現在。
或許在爸爸心中,一生摯愛突然消逝顯得有些措手不及。好幾年了,他不時會拿出藏在衣櫥底下的相簿,翻閱過去與他相愛的母親,每當撫摸著照片,都會不時露出一抹難以忘懷的微笑。
聽父親說,母親因久病厭世,在附近的防港橋上一躍而下。等接獲通報時,早已天人永隔,看到的是冰冷腫脹的遺體。對,那雙再也睜不開眼,甚至還有可能在陪我走上大半輩子的母親,就這樣不見了。而她在橋上,用醜陋的石頭壓住了那張紙條,並沒有多寫甚麼。尹德瑪,仍是父親最疑惑的問題。至今,卻用在我的名字上。
那時剛出生不到六個月的我,什麼都不會想,甚至只有嗷嗷待哺功能的小嬰兒,連個母親的照片都沒看過。殊不知讀上高中的我,尹德瑪這三個字仍把父親搞得焦頭爛額。明知道是我的名字,卻在他的筆電上不時看見關於尹德瑪這三個字的相關查詢,讓我覺得這名字附加在我身上有那麼些許難為情,無以復加的沉重更不用贅述形容。
這再普通不過的名字,不就是父親的姓再加上德瑪兩個字而已嗎?到底父親在想什麼?還是他對於母親所寫下的紙條深感疑惑?還是真有那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下雨天,突如其來的暴雨使我從沙發上驚醒。
我們住在公寓的第十層樓。空間雖小,卻夠我和父親兩個人生活。而我還有個姐姐,至今在國外留學,不常回來。
暴雨襲擊拍打窗戶,突顯著大廳沉重的氣息。家中不管四季交替,這樣的氣氛似乎一成不變。
父親是個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上班族。除了上課日。假日只要一起床,我就是唯一一個顧家的人了。
我是個「自稱」的網路小說家,但實際說起來,什麼都不是。這只是我的興趣。我還沒有半部作品,甚至前功盡棄的殘作也不少,中肯來說還只是個練習生。
老實說我是個三分鐘熱度的高中生。我對於這樣的年紀沒有太大的青春蕩漾,朋友也很少。我承認自己孤僻、難搞,有人想試圖接近我和我聊天,我還會想迴避。你們說這樣的個性是不是難相處?前提是我並無對那些友善之人產生厭煩的念頭。也許在未來他們會有任何解讀及誤解,或者他們本身就是帶著惡意接近,只是我巧妙地躲過他們。
我不符合人類對於同學該互相友好的那種期待,但我也不是那種冷漠型的人。或許是種矛盾吧?讓我覺得我只是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團體生活,學校生活。我時常待在家裡,偶而拖著筆電袋到咖啡廳假裝當文青,擺本書在旁邊然後上網。
我自認為格格不入於這個世界,所以我的腦袋另開創了「悠閒」這個空間世界的念頭。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有精神異想等等之類的症狀,而我自己雖然也不清楚,但我並未提供那些不懂我的人進入悠閒世界的許可証,所以就讓他們在「現實」世界慢慢質疑吧。
我老覺得我是外星人,因為我總能提出一些旁人無法去理解的立場及價值觀,而我卻感到稀鬆平常,大家都認為我是神經病。而我創造了悠閒這個世界,我也明瞭,當別人對我失去了信任或者我對人類失去信任時,還有個立足休息之地能供我避難,撫慰我對於人僅存的一點希望。
不過在眾多嘲弄及質疑的聲浪之中,在我的世界裡,仍是有幾個被我發下許可證的人。不是他們被我審核過,也不是因為他們同意我的觀點。我沒有那個資格,也沒有那樣的權利、地位。而是他們擁有深度的同理心,打從我心裡深深感受。我感受到他們的沉穩、智慧。
「和伊凡」、「陳義成」
他們在一團混亂之中將我解救出去。遠離同學的嘲弄,遠離同儕之間的愛恨情仇,遠離磨合,遠離只有他們認為的正常,才能加入那群團體中,做他們眼中的正常人,有質感,不低俗,開得起玩笑,然後要一起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族群。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他們身上我無法看到這樣的作為。所以當他們遇到痛苦哀號抱怨,我身上的惡意念就隨之加深,那股加深的惡念在心裡咆哮,爽快的笑聲只能隱藏於心中,面容中我早已套下面具,他們看不見我的笑顏。即使經過他們身旁,我仍選擇無視,因為是他們讓我學會冷漠。
我很恐怖吧?我就像顆定時炸彈對吧?認為我有反社會人格對吧?認為我會隨時發作對吧?
「唉…」我的惡念頭只有在自視甚高的人中才會蓄起那股能量。吸取他們的能量,那股負面、報復。
自視甚高與自信不同,我分辨得出來。我也渴望在人生中遇見有愛的人,善良的人,能夠把我引向光明的人。只是人生往往不能成立在完美之上,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一些氣你的人,只有少數勸你的人,更極為少數就是愛你的、懂你的人。更何況有些家庭,家人彼此視為陌生人一樣。如果你說至少有家人愛你,請好好想想,那些沒品嘗過這般幸福的人,在家人的定義中,會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我也慶幸自己…在親情這方面,是幸福的。
我,尹德瑪,自從認識了人心,就不斷在吸取那些能量。我的眼眸逐漸變色,變的渾沌暗沉,聲音也漸漸變得低沉枯燥。父親因為我的名字將自己搞得狼狽。每當他上班前,都會拿起一把梳子,洗面乳,將浴室的門反鎖,著上他在社會上必須立足必備的面容出門。
梳起一抹油頭,宛如重生。「阿德,我上班去了。」他露出一抹笑容。我對他並無任何反應。我只是冷冷地點頭,因為我知道,這是面具。
聽說母親生前,我們一家是快樂的。我想嘗試,我想體會。這家庭即使對我關愛,但擺起另一種面容、現實,這家庭仍是苦惱沉悶。我姊尹慧是家中懂事的小孩,深得母親及父親疼愛。聽說在母親自殺後,料理完母親後事後的幾個月,幾乎都足不出戶,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哭泣,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最後是老爸請阿姨將她帶走,將姐姐開導後,再送回家。
聽說她們出了個國,回來姐姐的情況才比較好。
我的心已不再單純,照著自己的模樣,被現實摧殘的模樣,自我的不勝唏噓,每個人各自體會的苦痛、歷練。與小時候那什麼都還不會設想的自己,成天和糖果餅乾好朋友打作一夥的日子。
「不給糖果就不跟你好了喔~」
我遞糖果。「好啦好啦!給你一顆,跟我好喔…」
「來,那我也分你一顆糖果,跟你好。」
將糖果含入口中。「哈密瓜耶!」
「你給我香蕉的口味,剛好我喜歡香蕉的口味耶。」他接著說:「哈密瓜是我最愛的哦!剛好有兩個,一個給你。」
「謝謝你。」我再從口袋裡掏出一顆。「那我再請你吃一顆糖果。」
溢於言表的驚喜充斥著美好。「謝謝你。」
1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cJtbrFUnW
「哇…某人看那什麼的書阿,痾…阿不是好棒棒,博學多聞。」他說著:「再好的書給某人看也是爛書,嘖嘖,成績又不好,跟人家看甚麼知識相關的書阿,矮額,要看甚麼書名,以後連碰都不要碰,怕會有衰運纏身。掃把星。」
那群女生交頭接耳的笑著。「陳叡文,你好壞哦!」
正當我心裡充斥著希望,以為有人要幫我打抱不平…
「應該要把那本書燒掉阿,傷了我們的眼睛。」
另外一個女生附和:「是阿,外星人啊!不適合看人類的書,眼睛那麼大顆,去看眼科稍微縫一下啊。看了就刺眼,人類很反感的知道嗎?X牲。」那個女生驚呼了一下。「阿!我自己消音了。我要督促聲音高昂阿~等等音樂課還要唱歌考試。」
旁邊的陳叡文假裝撞到我順勢將我的書給推了出去。書掉到了地上。「阿!同學。」他看了我一眼,頓了一下。「哎!」他轉向那群女生,悄悄地說:「外…星…」發出長長的歎聲。「長得那麼噁心,早點死一死,省得傷了我們的眼睛。」
鐘聲一響,他們一哄而散,充斥著不屑的眼神,目標針對的仍是我。窸窣的話語不絕於耳,每到下課就是以挑釁我為樂趣。我的心跳似乎正在加快,四周變得虛幻,有一度我還確認我正身處在這地方嗎?還是假象?
我招誰惹誰,我招誰惹誰?人類怎麼那麼的可惡…我的心一道道被割傷,那黑色的養分開始入侵,我變得不敢相信,總覺得有靈魂要試圖占據我的身軀,展開對於無辜之者所產生的報復念頭。
我必須讓光明去抗衡黑暗,但內心的黑暗卻無法忍受縱容。我不可讓黑色的我無地自容,更不能讓白色的光明讓自己軟弱。靈魂正在蠢蠢欲動,我開始分裂成好幾個細胞,佔據著社會的能量所傳遞給我的思維,要我用行動去改變,推翻,鬧大。以我個性我無法實際去完全做到,只能在內心撕扯。
ns18.116.98.10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