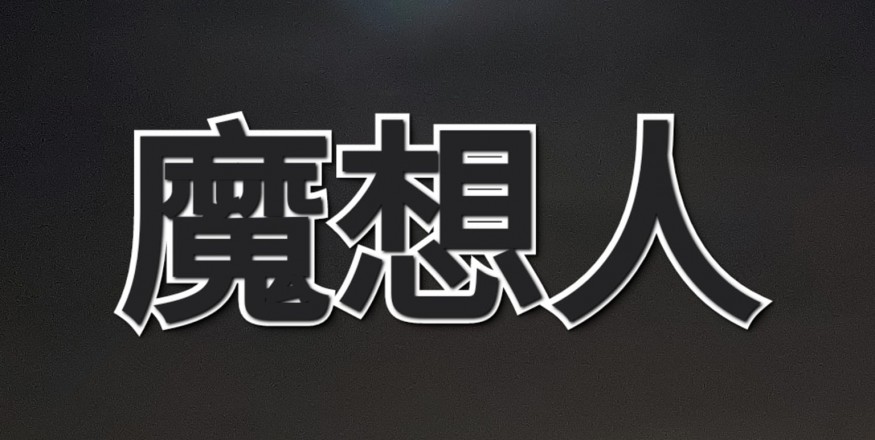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義成,發生什麼事情?」我問道。
「我好像也經歷過那樣的事情…」他神情緊張的看著我們。「我好像記起來一些什麼了。每當游露說的那些歷史,我內心就像在被觸及一樣,感同身受,彷彿經歷過那樣的事情,每個言語都彷彿歷歷在目。」
這時迪貝爾從一旁的書堆裡翻出一本外文書。裡面參雜著英文還有別國語言,老舊泛黃的頁面感覺的出來這本書齡比我還要長壽。他不斷翻閱著,彷彿有印象自己曾經看過些什麼,與這件事情有關。
「找到了!」他把頁面轉給我們看。「時間空窗,這是來自北歐某個叫作西維拉古的小鎮所流傳的古老巫咒。」
「迪貝爾,你翻給我們看也沒用啊,我又看不懂外文。」義成皺著眉頭說。
「這是一種魔咒。我在想當初觸碰到的那股震波和靜電,或許就是原因。但以我這個歲數,我也無法見到我父母最後一面了。」
「所以我嚴格說來,已經80多歲了,如今被困在這個年輕軀殼裡,停止了生長。」義成好像拼命的在回憶些什麼。
「你在想什麼?義成。」
他嘴角顫抖地說著:「等等,我在想我怎麼醒來的,我怎麼開始的。」
這一切太過於離奇了,所有人全沉浸在這難以解釋的氛圍下不斷思考討論著。包括在結界外,依舊是否受到時間空窗的影響?或許與當初的震波有關,而不是結界的問題。
這時迪貝爾合起書。他緩緩闔上眼,深吐一口氣。「好,關於肉身的事情就到這。」接著他望向我。「這次為了找你來,是要你準備好…」
「準備好?」
他突然這麼說,使我有點不知所措。但仔細聽來,確實不會是什麼好事。
「我知道這麼說會讓你很害怕。」他說:「但你來到這的目的有兩個。」
「兩個?哪兩個?」
「一個是幫助我們摧毀掉祭場。」他吱吱嗚嗚,並且猶豫不決地說著:「另一個……你是祭品。」
「祭品?」我驚呼一聲。
他和義成兩個同時間點頭。
「垂克,老實跟你說吧,我和伊凡將你帶到這,其實是游露的指示,不是為了確保你的安全。在三天後的晚上,將是大月圓。大月圓周遭的磁場環境將會使巫力充斥在滿值的狀態,趁著天享祭典時將你殺掉。只因為你們魔想人會為世間帶來災厄。」義成接著說:「但現在都什麼時代了,游露好像都變了。」
「所以殺死四主的事情…其實是要將我殺死對吧?」
他沉默的點頭。「只是我的內心一直覺得不妥。整個過程我的內心一直懸在半空中,就像一顆無法落地的石頭,很不踏實。垂克,對不起,我欺騙了你。」他懊悔的低下頭,眼淚不自覺的落到地面。
此刻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感覺這之中充斥著無法釐清的面紗。
我將視線移向迪貝爾。「貝爾,你跟義成是怎麼認識的?」
「這說來話長。」
我點頭,想聽他繼續說,並安慰著一旁的義成。至少我現在很明白,義成將不會站在游露那邊,而我對游露也漸漸開始產生戒心了。
「對於上次大月圓的祭典,我早已忘記是何時了。但其實我一直都在遠處觀察著藥巫村的一舉一動。自從那場突襲村莊之後,整個村莊的人參雜著閒雜人等,感覺沒了以前的純樸,而是一種光怪陸離。直到某天祭場突然燃起了熊熊火光,我從山腰往下俯視,那圓形的祭場彷彿正在為某個慶典而準備,燃燒了好幾個夜晚,早上再熄燼。好在我的兄弟姊妹前去那頭幫我探查情況,並且和我道述了即將有人被活祭的狀況。那時我才知道,這個村莊已經被外力佔據了。但好在我的兄弟姊妹協助了那位女子脫離被活祭的處境,也就是你的母親。那時候活祭已經算是很不人道的行為了,現在都2019年了,我竟然不敢相信還有活祭這回事。」他接著說:「直到在活祭事件後沒多久的某個早上,那是我逃離村莊後首次遇見人類。他們不像迷路,而是貪玩發現了這個新地方。那兩個人就是義成跟伊凡。而魔想人的事情也是他們倆告訴我的。」
義成彷彿在回憶當時,接著說:「我還記得那天。我和伊凡偷溜出結界,跑到這片亂葬崗來,有個自稱守墓人的迪貝爾帶我們去四處認識人家的墳頭。墳頭喔!你沒有搞錯,是墳頭,搞得像在跟街坊鄰居打招呼。但很神奇的是,當下有人就在我耳邊回應。後來我們到迪貝爾的家拜訪,現在依舊如出一轍,完全沒有變。」他接著問向迪貝爾:「迪貝爾…」
「嗯?」
「我還是跟那時候一模一樣對吧?」
他點頭。
「那我呢?」迪貝爾反問道。
義成點頭。
「是說…如果時間空窗的魔咒被解除的話,那我們會怎麼樣?」
迪貝爾停頓了下來。「我們也會回歸正常。」
「瞬間老化的意思嗎?」
迪貝爾默默地點頭,但卻不敢明顯的點。「身體狀況會惡化的很快。」
「如果我的身體還硬朗…」義成嚥下一口氣。「我是不是還有活著的機會?」
「或許。我們可能平常生活都還不錯,但難保突然老化,所有病症會讓自己的身體瞬間難以承受。所以…我們雖然樂觀,但當這一切恢復正常,也要有在原地老死,瞬間病死的心理準備。」
義成突然露出一抹絕望的微笑,彷彿在生命之中,大半輩子都在被無情的捉弄。義成說:「所以垂克,我很抱歉你的母親是以自殺告終。但這次,就算我們化為一灘爛骨頭,也要終結掉這個儀式。我多年來對游露的質疑是沒錯的,這場戲我也快演到爛掉了。雖然她的面容有在變老,但這個村莊有太多不尋常的地方。我覺得自己已經快被層層的謊言給蒙蔽住了,快要失去了方向。我只能任由迷濛的片段去慢慢恢復自己原有的記憶。」
我拍著他的背,很能明白他被蒙蔽在時間之內的謊言,甚至包括時間以外的事情。一切都像場夢一樣虛而不實。
「那我該怎麼做?」我問道。其實我也很不明白,也對於執行感到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殺掉她。」
「燒掉祭場。」
他們倆近乎同一時間脫口而出,但答案卻不一致。
我對義成突如其來的答案感到瞠目結舌。「義成…就算是這樣,我也不敢這麼做。那是殺人,殺人會被判刑的你知道嗎?」
他歇斯底里,不安地說著:「不行,我一直待在這會讓我回去變得更不自然,到時候一定會被起疑。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們說,我親眼目睹活祭前夕…」這時義成的瞳孔突然睜大了,他一臉恍然大悟的望著我們。「我想起來了。」
「想起什麼?」迪貝爾問道。
「我的年紀和游露只差十幾歲而已,然後我醒來後卻叫她阿嬤。確實那時的她是要我跟伊凡叫她阿嬤。只不過游露之前的性格並沒有像現在那麼瘋癲,仔細想想感覺判若兩人。」
「那在突襲事件之前你和游露是什麼關係?」我接續問道。
他的神情凝重,緊皺著眉頭,眼神不斷飄忽,彷彿正在一一理清前後的記憶,然後重整。「她…她是領養我的恩人。我的父母在一場意外中死去,而游露因為無法生育,所以一直都沒有後代,進而將我領養。」
迪貝爾說:「那你還記得事情發生前一刻,還有醒來後,發生了什麼嗎?」
他彷彿開通了記憶的閘門,談起過去的事情時,眼神突然變得炯炯有神。「當時我和游露一起去鄰居家送菜的途中,遇到了頭目一行人,他們正準備離開藥巫村,前往台東二次拜訪巫者。他們走後,村內隨即就遭到襲擊,彷彿是有人刻意預謀的。就像迪貝爾說的,那些人身後確實能看到一道煙霧連接著脊椎,像蛇一樣從別人身後突襲。手上的武器不斷刺殺著我們的族人,血洗村內。大家慌亂逃竄,卻沒能倖免。還有人無故吐了黑水,嘴巴裡滿是蟲子竄出,整座村子被弄得烏煙瘴氣。一個盤著頭髮的女人,身上穿著米色連身巫袍,手上還握著一把被蟲蛀的枯老木杖。她站在入口處敲了一下,一道無法承受的電擊將我們都電暈了。我倒在地上,隱約能感覺到腳步聲。過沒多久,我什麼感覺都沒了。」
「後來你是怎麼醒的?」
「醒來後,我發現我躺在祭場周邊的屋子外。游露和村民坐在旁邊俯看著我,等待著我醒來。我腦袋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包括原本沒想起來的那場屠殺都變得模糊。游露只是說我暈倒,許多村民只是受了傷。雖然有人因此送命,但村內大多人都沒有什麼大礙。而那些突襲者早已被擊退。後來發生那件事情之後,整個祭場就被禁用了。那裏圍成一圈的石磚屋都被上了鎖,再也沒有人去動它。」
「這聽起來好像跟游露說的有些出入。」我拼命的回想昨天游露跟我說的那些事情,卻與義成所回想的兜不起來。「那頭目呢?」
「僅剩頭目一個人回來,估計其他人已經遇害。但頭目沒過幾天就死了。」他說:「後來頭目在先前寫好的遺書中,有明確表示若在位者死亡,將由德瑪游露接任這個村子的主導權。」
「所以頭目是被下了詛咒嗎?」
「對。」他點頭,接著滔滔不絕地繼續說著:「後來我在游露的介紹下,認識了和伊凡,她說這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的遠親,所以我們後來都以兄弟互稱。長期下來,我們被游露的故事給洗腦,被她指派做任何事,那些回顧過去的歷史真假參半,甚至在活祭前夕,我在她身後看到與四主相同的黑影。」
迪貝爾在一旁思考了一會。「那些石磚屋一定有很大的問題。」
義成認同的點頭。「只是那都被上鎖了。」
「一定有鑰匙。」
我深吸了一口氣,因為我知道我是深思熟慮過後才做這個決定的。「我打算明早闖進游露的房間找看看鑰匙。既然主導權在她手上,勢必有那個機會能找到。」我問向義成。「明天游露有要做什麼事情嗎?」
「這幾天她都在為大月圓祭典做族人的首飾,估計明天是會在家。」他沉思了一會。「不然這樣好了,明天我趁著四下無人,去她的菜園放火。」
「這樣好嗎?」
「幫你抓緊空餘的時間去找鑰匙不好嗎?」他接著說:「菜沒了可以再種,你沒了直接種到土裡。你要選哪個,垂克?」
我點頭,只能選擇再讓游露多種一次菜。
只見他神情不安的樣子,似乎又有更多的記憶湧現在他的腦海中。「而且…我還覺得有個可能,如果不是我失憶了,就是村裡面的人大多都是侵入者。」
「你的意思是…」
「我猜想沒錯的話,估計伊凡和瑞足他們都是。」他說:「雖然我無法完全肯定,但那些曾經熟悉的面孔從剛才一直回想,都未曾在村內出現過。」
「太棒了,你能找回來一些記憶已經很厲害了。這對我們未來的處境會有進展。」迪貝爾緊握著拳頭,難掩興奮的模樣。「我希望能逃離這裡回到英國。」
雖然迪貝爾這麼說著,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如果破解了這個魔咒,他們最終的結果不是病死就是老死,若能承受的了身體機能瞬間老化崩潰,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身體一次性累積反饋,勢必會引發很痛苦的過程。光想到這個,就突然渾身不自在。
「只是我們不能讓垂克變成手無寸鐵的祭品。」迪貝爾嚴肅地說:「我們得在大月圓前讓你擁有防衛攻擊的能力。」
「你是要我攻擊游露和村民嗎?」我疑惑問道。
「我不希望這是主要目的,但有必要時,絕對要懂得防衛。」
義成眼神認真地盯著我說:「垂克,被當祭品的人,他們不會跟你玩家家酒。他們似乎要魔想人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迪貝爾露出一抹想到主意的微笑,攀住我的肩膀。「我讓那些兄弟姊妹來提升你的攻擊和防禦能力吧!」
聽到這句話,此刻的我瞬間顫起一片疙瘩。這意味著,我即將看到鬼魂。
「這是個好辦法。」義成附和道:「只不過他得半夜來這。」
「雖然很恐怖,但義成就麻煩你帶路了。」
「沒有喔,我沒有要來。」
「叫我半夜一個人來墳墓?」我驚訝地指著自己。
他們倆很有默契地點頭。
「可以不要嗎?」此刻我的尿意湧上,心跳加快,感覺未知的恐懼逐漸襲滿全身。
「可以啊,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迪貝爾擤了擤鼻頭。「第一是過來,第二是跟祂們一起當兄弟姊妹。我沒開玩笑,祂們應該會很開心。」
「那我還是來好了。」我硬著頭皮選了第一個選項,即便我快尿出來了。
我和迪貝爾借了廁所。他的廁所位於房子的左側,在一片樹蔭下,一個自製的簡便廁所。當我打開門,一股難以形容的阿摩尼亞味撲鼻而來。這裡馬桶底下是條小水溝,沿著小水溝那些排泄物就會被沖走。好吧,我得承認現在要在這久待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更不用說大半夜頂著不安的心情來上廁所。我在想迪貝爾半夜上廁所時應該和那些兄弟姊妹聊得很開心才是。
結束拜訪迪貝爾,迪貝爾在路口送別了我們。但今天大半夜十二點,依照約定,我還要再過來,而且聽他的要求,持續訓練最多兩個小時,並且會讓我看到那些兄弟姊妹。我秉持著好奇但又害怕的心態,依舊點頭接受。畢竟我不想那麼早就跟人稱兄道弟,在夜總會開趴。
我們偷偷摸摸的回到了結界裡,一切都裝作若無其事,但其實我們都默默的在佈局著一切。
這時伊凡他們早已回到了家裡,幫忙游露洗地瓜菜葉。
趁著游露在廚房切東西,我偷偷的望向游露一樓的房間,她確實沒有隨手關門的習慣。我假裝好奇的向室內探頭。一眼望去,右手邊一個深色書櫃和書桌並排在一塊,靠窗的地方擺著一座衣櫥,檯燈好像都沒有那個習慣關掉。一張床舖,棉被也是沒有摺好。看起來很正常的房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異樣。
直到傍晚,一切都很正常。
夕陽西下,天邊的雲被染成通紅一片。我在三樓房間望著窗外不遠處的圓形祭場,那裡似乎有些人正在點火。光是這個舉動,不免讓我擔心後續的行動是否會因此揭穿。
上方白色缺角的月亮彷彿像是沙漏般,計時著我壽命將至的秒數。吸進一口空氣中飄散的濕氣,像是踩入沼泥般難受。我指的是此刻內心的狀態。
「喂!」這時底下有個小小的氣音呼喚聲叫著。
我往下一望,義成拿著一綑繩子在手中晃了晃,並示意我安靜。接著他隨即跑走。我滿腹疑惑地不曉得他要做什麼,也不曉得未來自己該怎麼辦。我的意思是,我對大月圓那天感到恐懼,我不曉得自己會遭受到怎樣的對待。畢竟此刻的游露裝作若無其事,我們也不可能在這時無故拆穿她,若是提早將這一切攤牌,她後續勢必會有更多的舉動,甚至可以全盤否認這一切,因為我們沒有證據。這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故作冷靜,讓她察覺不到異狀。
此時義成偷偷摸摸的跑進我的房間,拿著一綑繩子。他氣喘吁吁地講不出話,將繩子扔到我床上。他在門外東張西望,確認沒有任何動靜之後,將門關了起來,然後鎖上。
「義成,你要幹嘛?」我問道。
他喘息了一會後,打開窗戶,往下探去。「三樓高。」
我彷彿明白他要做什麼了。
「你要確定欸!三樓高,你要我垂降下去?」
「我跟你說,我家門邊有掛門鈴,晚上如果偷跑出去,我阿嬤一定會知道的。因為這是她自己用的。」
「她用這個做什麼?」
「防止小偷。」
「天啊…」
「而且她淺眠,晚上很容易醒來上廁所裝水,或者是半夜看個電視再去睡覺。」他說完後,緊接著抱住床上的繩子,將繩子一端死死綁牢在一個床腳,接著他把另一頭從窗戶扔下。
繩子像一條飛蛇一樣,旋轉般地垂飛下去,然後啪的一聲落在樹葉堆上。
樓下立刻傳來講話聲。「什麼聲音啊?」
「不知道欸。」伊凡回道:「我去看看。」
我和義成兩個人瞬間倒吸一口氣,眼神透露著絕望的凝視。
只見廚房後的鋁門被打開了,伊凡探頭沿著繩子往上一望,和我們四目相對,並且露出一抹詭異的眼神。這時我還能聽到後面廚房洗水槽洗菜葉,水流到外面水溝的潺潺流水聲。
「完蛋了,我應該要緩慢垂降下去才是。」
伊凡依舊不解地凝視著我。
此刻游露在樓下喊道:「伊凡~是什麼聲音?」
「哦!一隻松鼠從樹上掉下來啦,跑走了。」
「哦,趕快關起來,蚊子很多。」
「好。」
我們鬆了一口氣,然後趕快將繩子往上拉回來。
「算了,我原本想說你一個人應該綁床腳做的到,但我錯了。我晚上會來幫你,我也不知道後天還是哪天,游露會怎麼將你送到祭場上。有可能你熟知戰鬥防禦的技巧得要快一點,時間很趕。」
我頻頻點頭,因為我知道,他是這裡唯一願意幫我的人。
這時敲門聲隨之而來。
我走到門邊,喘了幾口氣,冷靜地將門緩緩打開。
只見伊凡站在門外,然後一副納悶的表情走了進來,將門反鎖起來。「你們在做什麼?」
「我…我們想玩生存遊戲啊!」義凡露出僵硬的表情回道。
他瞥了我一眼,然後我使勁點頭。
「你們要是被阿嬤知道你們就完蛋了,很危險知道嗎?」
我們像是聽著長輩的話,絲毫不敢有任何一句吭聲,然後點頭。
接著他轉開門把,然後對我露出一抹詭譎且不太善意的微笑,「注意一點,垂克。」
他走下樓,我望向義成的表情就知道,這狀況似乎不太妙。好像完全露餡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這麼做,硬著頭皮冒險也要保護自己。
轉眼,夜晚襲蓋整片天空,祭場的光線更加鮮明,不遠處的高山更加深色,像被蓋了一片巨大黑布,不讓你瞧見任何一絲真面目。詭異的是,沒有任何人靠近祭場那個地方,彷彿所有負念都在結界外試圖靠近、遊走,任由木頭去維持那正在啃食的大火,一股難以形容的詭異攀滿全身,身上的疙瘩瞬間竄起。隨著吃完晚飯,我和游露他們在路邊散步。即便知情很多事情,卻要假裝淡定,就像此刻的游露一樣,她就是個正常的老阿嬤,全身上下沒有一絲任何能讓你懷疑的地方。
我們經過通往圓形祭場的那條路。我停在岔路口,凝視著遠方那頭正在燃燒的火焰,硬著頭皮問:「游露,那火焰是做什麼?」
「那個啊,那是大月圓時,天享祭典前幾夜會續火,代表著守護藥巫村燈火通明,平安無虞。」
「那負念會敢靠近那裡嗎?」
她露出慈祥的微笑,但她嘴角的那抹微笑,卻不知道是在打什麼主意。「當然不會,他們大月圓時,會對祭場感到害怕。但這幾天我們也不要靠近那,因為晚上時,神靈會在那吸聚火的能量。」
「神靈喔…」
她點頭。
接著我望向入口處的地方,指著那頭。「所以負念祂們都在結界外盯著我對不對?」
游露並沒有回話,只是將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著我別再說了。
夜晚十一點,距離要攀繩還剩下一個小時。我做好準備,手機、小手電筒隨時帶著,腰間繫了一副刀鞘,裡面裝著剛才義成給我的防魔短刀,聽說這是游露在突襲事件之前做給他的一把刀,雖然大小像一把水果刀一樣長,但刀柄上刻畫的符文,能有鎮魔妖以及負念的作用。
我們在三樓靜靜的聽著樓下的動靜,一切的舉止都顯得小心謹慎。
阿嬤還在一樓看電視,隱約能聽到電視播放的聲音,而二樓房間依舊是沒有任何動靜。
「義成,我提早出發好了。」我小小聲地說。
「也好,希望游露不會上樓查看。」
「希望如此。」
到了房間,我們將繩子綁在床腳,老實說,這比我在火車上遇到魔神還要緊張。因為我不知道這繩子穩不穩固,甚至沒有任何安全配套措施,如果摔下去不只露餡,甚至還會危及我的生命安全。
「你放心,我會抓穩的。」義成跟我保證。
我緊抓著繩子,開始冒著生命危險垂降。而義成則是在房內幫我使勁吃奶的力氣拉繩。雖然有綁在床腳,但總是要有人拉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一步一步的沿著繩子,踩牆往下溜去。
終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順利到了一樓地面。在此刻,我們雙方都鬆了口氣。即便是這樣,我依舊不能鬆懈。我還有一段路程要走,我希望在今晚就能學到那些精隨。然後不要明天再重複那樣的冒險了。
隨著主要外圍的街道往上走去,行經一片大果園。我憑著記憶直直往前走,是一個偏上坡的道路。回想起早上光是用走的就要很長的時間了,更不用說在夜晚,舉著手電筒照路的艱辛路途,會花更多時間。
到了陰暗處,所有視線全被黑暗給覆蓋住,所有聽覺全部聚集在我的呼吸和腳步聲。感覺周遭的風吹草動,都會被放大好幾倍。我唯一的指引,就只剩手中的手電筒跟手機。我拿著手電筒以外,還舉著手機的手電筒功能,雙重照映,雖然沒有多大的功效,但確實在近距離的方面上是有一些用處的。
隨著走到一處雜草叢生的地方,前方只留了一條小道路。我想起,只要踏過這個地方,就是結界外了。我有點害怕踏出結界外後,會遭遇到怎樣的情況。但以最糟的情況來比較好了,我覺得此刻的狀態應該還不算很嚴重。
我在結界裡佇足了有幾分鐘。調整好心態跟想法以後,再度將手電筒往前照,只要踏出了這步,我就要面對未知的危機襲來。但為了要讓自己有反抗能力,我必須和迪貝爾赴約。沒錯,人比鬼還可怕,我只要一直帶著這樣的心態去想就好了。負念、魔神,還有我這天生招魔的體質,感覺隨時都會排山倒海向我撲來。
ns3.17.65.10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