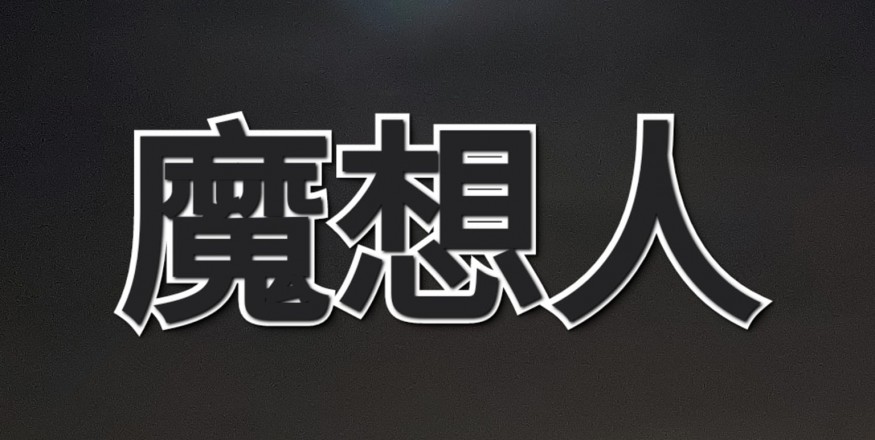車子速度減緩,停在門口。前方有個穿著紅色披肩的阿嬤帶頭朝我們走來。她的面色嚴肅、腳步沉重,臉上的皺紋和身材透露著歷盡風霜的過去,感覺整個氛圍凝結在她的腳下,不斷地觀察著我們。當然我能夠理解,她是針對著我來的。畢竟伊凡他們也沒甚麼好觀察的。
她叼著一支菸,在車前吞雲吐霧,將手遮蓋在額頭上望著車內想看清楚車內的畫面。
身後的村民緩步跟隨著,整群圍繞在我們車子周圍,使著好奇的目光不斷注視車裡,好像我們是被圍觀的動物一樣。
瑞足率先將車門打開,然後繞過車後,然後給車外的阿嬤一個擁抱。接著瑞足的爸爸開車門,很自然地跟居民招呼問好。接著義成跟伊凡接續下了車,把包包遞給一個男子,男子順手接過,轉身將包包帶走。然後他們倆一派自然地向游露阿嬤問好後,便待在一旁看著我。
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下車,所有人都將視線放在我身上,讓我感覺有些不安,甚至不自在。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看著我的心態到底是什麼,帶著敵意?善意?我不知道,只感覺那眉頭一皺的表情在所有人身上難以辨認。
阿嬤走上前,用腳熄掉菸,將嘴裡的菸氣轉向旁邊吐掉。她仔細地靠近端詳著我。「恩…有像你的媽媽。歡迎你,德瑪垂克。」
「謝謝阿嬤。」
「叫我游露就好。」
這時所有人一哄而散,彷彿我不再那麼值得被探討和觀察。不過從我想的那樣看來,他們應該是覺得我長得滿身魔氣,背後跟了好幾個怨靈之類的,然後黑眼圈要比熊貓再黑,眼神再更銳利邪惡。殊不知其實我和一般人長得沒兩樣。但話說回來,我對游露的想像原本也是像他們那樣,總在見面前會在腦中預設幻想一些模樣。
「游露你好。」
她點頭,露出一抹慈祥的微笑,搭著我的肩。「走吧,我帶你去庇護所。」她的語氣和昨晚為了追連續劇然後大罵義成的樣子落差很大。
就這樣,我們朝著入口走去。眼看前方有好幾座老式透天,周圍包覆著樹林。是的,就和一般住戶一樣,大家單純的生活著,沒有絲毫詭異的氛圍和舉止。大家回到自己的生活,小孩子依舊天真的玩樂著、長輩在樹下閒話家常。當然,我不安的內心也漸漸平靜下來,就像是來到新的環境居住。不知何時,我才能再見到父親。
我們繼續往裏頭走去,我四處觀望了一下,發現左側還有一條道路,逕直的道路是通往一個廣場。廣場上有一個搭建的大火篝,周圍圍繞著一整座石磚屋。那頭沒有任何一個人,空蕩蕩的,好像沒事不會通往那個地方。
這時義成搔了搔腿。「好癢阿,最近蚊蟲真的很多。」
「對啊。」伊凡附和道。
「山裡面本來就這樣子了,等等回去擦藥就好了,嫌東嫌西。」游露回道。
義成不耐煩的翻了個白眼。
「對了,垂克,以前你的奶奶就是住這邊。」游露說。
我驚訝地回道:「真的嗎?」
她點頭。「這要回溯到很久以前。有一段故事。」
「我很想聽看看。」
「進到屋子我慢慢說給你聽。」
我內心既好奇又興奮的點頭。「好啊!」
就這樣,我們走到了位於整排老透天的中間棟。游露拉開門,領著我們走進屋子。裡面的地磚就像我們以前地板常看到的黑白相間石子圖,穿著襪子踏進去腳底仍會竄出一陣寒意。
游露坐到椅子上立刻使喚義成。「成欸!幫我把這茶壺拿去加熱水。」她把茶壺遞給義成。只見義成不甘不願的接過。「伊凡,把那個白色杯子洗一洗拿過來。」
「好。」相對起來伊凡比較順從的多。
我站了起來。「游露,我也一起去幫忙好了。」
她傾身向前將我壓了下去。「哎!不用。」
直到他們將杯子洗乾淨,然後茶壺沖了一壺熱騰騰冒煙的擺在眼前。游露旁邊還擺了一個水壺正在燒,周圍環繞著茶香。這有一種即將要說故事的氛圍,我有一種感覺,她要說的這個故事,與我很有關。
這時他們倆坐定位,彷彿也很想聽聽看游露即將要說的故事。
「垂克,你知道為何你要叫做德瑪嗎?」
我搖頭。
「最初德瑪家族其實主要派系為藥巫,副派系為招喚,在宜花山區建居,造福山居里民,治癒了許多得病的困苦人,以善為本,造福人民。嚴格說來,你也算是藥巫的一份子。在20世紀後,由德瑪第五代沐霖和培恩爭藥巫一職,只要上了藥巫,就能帶領整個村莊。只不過在藥巫徵試過程中出現評分不公,培恩以高分勝過沐霖。沐霖不滿對方考試中疑似作弊,便在考試後率領一群人群情抗議。但教師們依舊不採信沐霖的說詞,並且以不服考試結果,而擅自帶頭作亂,將沐霖逐出藥巫村。最後沐霖率領著一群人脫離東部森林,搬遷至西部平原田莊『雲林』的扛心村,與藥巫反目成仇,加入了弄蠱派系。後來聽說在他們定居的十年後,村內引發了內鬥。在一場蠱蟲鬥法之後,許多人逃離了詛咒之地,遠離被詛咒的紛爭,回到了東部尋求歸家。但藥巫頭目深怕歸來者另有目的,並將他們驅逐。頭目雖然這麼做,但他也是為了保護藥巫村良善人民的性命,也深怕成為西部弄蠱派系的洩恨目標。但頭目並未因此憎恨他們,而是怕他們歸家的舉動引發兩派族群紛爭,進而報復。後來頭目派遣了一位巫者,帶領無家可歸的歸來者遷至台東山谷,另闢藥巫村。但沒想到巫者卻將自身巫術(黑念、藥巫)技能繼承給歸來者,等同於授予創造了新的派系。」
「所以妳的意思是,我的祖母曾經目睹這事情的經過?」
「何止目睹,她就是當事人。」
「當事人?」
「魔想人就是被授予的身份,透過血脈傳承,如今你也是當事人。」她嘆了口氣,啜了口茶接著說:「那時候我們頭目得知新的派系出現,氣到快要中風,並招集了一群人搭火車到台東要找巫者理論。但到那裏的時候,看到那片他們居住的山谷充斥著『黑煙』,不得不先行撤退。其實巫者早率領了一群人在門口堵他們,僅靠著那股怨念就嚇退頭目一行人,更不用說硬碰硬會遇上什麼糟糕事。」
「那你是怎麼認識我祖母的?」我疑惑問道。
「雖然黑念派系我們無法接近,但好說歹說曾經也是藥巫的同村,只是經歷了分裂過後,不得已隨著家人離開。那情感不是加入了別的派系就能忘掉的。有些時候,並不是某些人能決定的,更不是在自願的狀況下接受的。」游露幫我續茶後說:「我跟你的祖母惠昭曾經也是很要好的玩伴,那時候還小,根本沒辦法決定甚至選擇,只能跟著家人隨波逐流。」
我點了點頭,不知道為何,聽完後內心有些許的感慨。
「後來頭目再次回到台東山谷時,他們的聚落早已搬遷走了,留下殘破不堪的屋子和雜物。」
「所以他們不知去向了?」
「那時候什麼都沒留下,估計遷往某個山區,或者四散在台灣各處也說不定。」游露說著:「頭目還為此開了族群會議,甚至語重下達了誅殺令。」
「殺了黑念派系的人?他為何要這麼做?」
「原以為頭目會手下留情,但頭目終究害怕萬一黑念派系四散到各處,會造成不小的影響和事件發生。我還是能理解頭目的決定,畢竟這攸關整個大局。」
「那妳是怎麼找到我的?」我擔憂的說:「所以你們找我來是要…」我深怕她為了把我找來,是要對我不利。
「惠昭曾經有偷偷私下回來找我,那時候她和我分享她女兒結婚的喜悅,但也向我透露了很多關於黑念派系的事情。就好比關於血脈相承、分裂的巫毒派,甚至她女兒,也就是妳母親所定居的地方『台中』。」
「她為什麼要透露這些?」
「她說凡事被魔想繼承的血脈,勢必會遭到厄運和負念的侵襲。所以要我來保護你。」她說:「你是不是鮮少聽到你父親談到關於你祖母惠昭的事情?」
我點頭,回想起以前到現在,確實很少聽過父親提及她。
「這麼說好了,最壞的結果,就是你的祖母和母親都是遭逢魔的毒手而離世。」她惋惜地說:「慶幸的是,你的阿姨和你姊姊,都有幸能躲過這一切。只不過我很抱歉,魔的血脈傳到的是你。」
「那該怎麼終結魔這樣的東西?」
「你身上應該有傳承石吧?」
她這麼一說,我從包包裡掏出裂開的傳承石給她看。石頭上還殘留著我的血跡。「當初我母親自殺時,她在橋上用這顆石頭壓著她的遺言。」
游露接過傳承石,並且仔細地端詳。「這就是當初巫者繼承給你祖母的傳承石。傳承石上有四個靈魂,我們稱祂們為黑念四主。怨、暴力、貪婪、僥倖,代表著四種不同的特性。這顆石頭裂開,與祂們有絕對的關係。不是因為你身上有絕對的怨力,而是祂們集結著各方的負念正在延著血脈吞噬魔想人。」
我對此深信不疑。我更相信母親的死與魔有絕對的關係。再加上這路途中遇到的種種詭異事件,我的內心就像種下了不定時炸彈,感覺周圍隨時會襲來不可預測的危機。
「為什麼巫者要這麼做?」我依舊不解地問道。
「當被繼承為魔想人,必定是與魔結定了契約。魔需要血脈,祂需要更有資質的肉身延續身上的意念。負念覬覦著祂的能量,因此成為魔想人必定遭受到各種危機發生。想必巫者身為魔想人,一定是預知了自己的死劫,所以才轉移給了你們家族延續。但相對的,轉移的代價就是死亡。」
「所以我轉移了,我的性命也會不保?」我問道。
游露回:「雖然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從古至今,大家也不知道如何轉移。」
我失望又緊張地看著她。「真的沒有辦法了嗎?」
「讓我看看你的第三個眼珠吧!」她將食指伸過來。
我完全無法理解她即將要做什麼。甚至她所說的第三個眼珠到底是什麼。
我一頭霧水回道:「第三個眼珠是什麼?」
她指著我的額頭。「你被封閉的眼珠子。」她二話不說地將食指壓在我的額頭上,並示意要我安靜不要說話。
只見游露閉上眼,彷彿周圍的聲音都靜止了下來。我的眉心有一股熱感,一種濕氣與熱氣被滲透進的熱感,像是有東西在我的腦袋鑽來鑽去,尋找什麼。而來源則是游露的食指,好似一道紅外線有條序的感應些什麼。這時我才相信,游露身上身帶著的法力,是我必須對她崇敬的。因為只有她能夠保護我了。
她睜開了眼,眼神變得嚴肅。「逃了三個…」
「什麼意思?」義成問道。
「僥倖、暴力、貪婪,這三個最不安份的靈魂正在四處亂竄。而怨,正在你的內心裡沉睡著。這三個勢必到外頭興風作浪,他們正在蒐集著人心鼓動的特性,一個個的吞噬掉與他們僥倖、暴力、貪婪相同的氣息,進而強化自身的能量。」
「游露,老實說我還是不太清楚。」
「你的出生,釋放了傳承石裡的四個靈魂。這四個靈魂分別代表了僥倖、暴力、貪婪、怨的特性。打從你出生後,祂們一直都在守護你。」
「怎麼聽起來都不是特別正向的性格?」
「你就是負面的代表啊,哪來正向?」她冷笑了一下。「你有聽過善良的魔想人嗎?」
我被她的回答給堵的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暴力,會去噬取施行暴力的人心;僥倖,會去噬取僥倖的內心;貪婪,會去噬取竊賊、小偷,甚至手腳不乾淨的人的心,進而強化祂們內心所需的能量,這樣應該能理解了吧?」
我點頭。「那…怨呢?」
「我要做的就是殺掉這四個…」
「可是怨還沉睡在裡面,阿嬤。」伊凡問道。
她一臉不安地望向我。「可能我會考慮這樣做,但是…」她似乎沒有講得很明,像是在自我對話,又像是在跟我們對話。
「妳在說什麼?」
「怨這個特性一直塵封在你的內心,唯有喚醒他,才能將另外三個引誘回來。因為另外三個與祂是共念,也就是一體的。如果能藉由你喚醒怨念,成功率將會大增。但讓我最擔憂的是,這可能會引來一場災厄。」
「災厄…」我們異口同聲說道。
我的祖母和母親死於魔中,而下個會是我。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感覺,世世代代被厄運糾纏不清,好像一直處在被詛咒的狀態下。就學時無時無刻被針對、霸凌,彷彿要試圖將我內心的那個魔給喚出來。好似冥冥之中有人正在操控著我的命運,讓我無法順利脫身。這狀況只會越來越糟糕,並不會因為我脫離了學校而改善。
「所以我的生命會就此停在這個年紀嗎?」我沉重的道出這個問題。但我其實很明白,甚至也為之後斷下覺悟。但我還需要時間去沉澱。
游露嘆了口氣,以喝茶替代回答。「垂克!勇敢點,你是男子漢。」儘管她嘴裡替我打氣著,卻仍能隱隱看見游露的嘴角正在不安穩地顫抖。
「看來…」
此時義成拍了拍我的背。「不管怎樣,我們都會幫你一把的。」
這時伊凡望向義成,好似在疑惑著什麼。
「不管如何,在庇護所這段時間,切記不要踏出門口。你的活動範圍就是待在這個村裡面,想做什麼都行,但就是不能踏出門口。」
我謹記的點頭。「好。」
「阿嬤,我剛都忘記告訴妳了。」伊凡突然想起了什麼,接續問道:「阿鹿叔叔認識了一個黑念系的朋友。」
她點點頭,並沒有任何驚訝的反應。
「其實我們昨晚遭受了一場意外。」
這時游露眼神顯露好奇,但卻沒有任何驚恐。「嗯?什麼意外?」
「我們差點被他的朋友給襲擊。」
「妳說在火車上?」
伊凡搖了搖頭。「阿鹿開車來載我們,帶我們去他朋友家借住一晚,結果當晚隨即就遭到襲擊。」
「並不意外。可見黑念系早已外流到別的地方。我在猜想第二次頭目去找他們的時候,估計巫者已經死了。魔想人就是最直接的證據。」
「阿嬤,妳都不會關心我們有沒有怎麼樣?」
「你們命很強的,我不需要擔心。」她很肯定地說著,也難怪她那麼放心地派這兩兄弟來找我。
伊凡很失望地嘆了口氣,很明顯她需要游露的在乎和關心。
「結果是誰救了我們妳知道嗎?」義成說:「是三個小偷欸,是三個小偷喔!扯不扯。而且跟我們一樣是有巫術派系的小偷!重點是那傢伙房子裡面放了一堆水晶。」
「那傢伙是負念,水晶食魔。」
「阿嬤妳怎麼知道?」義成驚訝的問道:「妳怎麼知道她叫作水晶食魔?」
「那位小姐的靈魂已經不在了,只是骨肉軀殼。居住在她體內的是魔。」她彷彿能藉由事情發生的口述,去倒放我們曾經發生的片段,以及所看見的人事物。「負念最愛抓這種已故的黑念派系人類作為宿殼,正好能續用還未散盡的巫力。」
「這點我身為半個巫師竟然都察覺不出來。」義成一臉自責的說著。
「你們察覺不出來是正常的。她會用特別的香氣去掩蓋負念的氣味。那是他的巢穴,傻不隆咚的。」
我突然回想起當初一進屋,屋子瀰漫的那種香味,起初還覺得很特別,但現在想想非常的不尋常。「難怪我一進到屋子裡面就有薰香的氣味。」
「那是魔神仔的其中一種負念化身,透過水晶耗噬你們的體力,然後拿菜刀像殺人魔一樣一片一片將你們啃食殆盡。你們身上擁有巫力,每個血液、神經、肉身,都沾染著這樣的氣。更不用說魔想人是他夢寐以求的主餐。」
「所以他吃了魔想人,巫力就會大增?」
游露搖了搖頭。「主要是吃掉他身上的黑念四主,就是當初與巫者締結血脈契約的那個魔。要是這四個覺醒並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共主。當四主共同覺醒變成共主,將會變成一個新的特性『肆虐』。」
「這…跟颱風一樣,聽起來很恐怖。」我驚恐地看向游露。
「心智脆弱的人類將被掌控,到時候整個社會變得更亂,發了狂似的毫無規矩,沒有任何底線,人類的良善終將被啃食殆盡,沒有了自我,暴力跟血液、貪婪、僥倖無止盡的在這社會上演。」她嘆了口氣。「唉~該說這是人的天性,還是魔的本性呢?如果沒有道德拘束,這一切很難說呢。」
3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1bNNVtw9wA
3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wOXHy2SUt
註釋:
共主 - 黑念四主共同覺醒並聚合在一塊的『形體』。
黑念四主 - 傳承石所附著的四個特性的靈魂 『暴力』、『貪婪』、『僥倖』、『怨』。
宿殼 - 已故之人的屍體。
負念 - 陰氣與負面念頭所產生之物,以人類怪物形體現形。
第三個眼珠- 俗稱第三隻眼,即是松果體,在眉心處。在菩薩或佛祖的眉心處都有出現,他們稱之為『白毫』。
ns18.116.36.2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