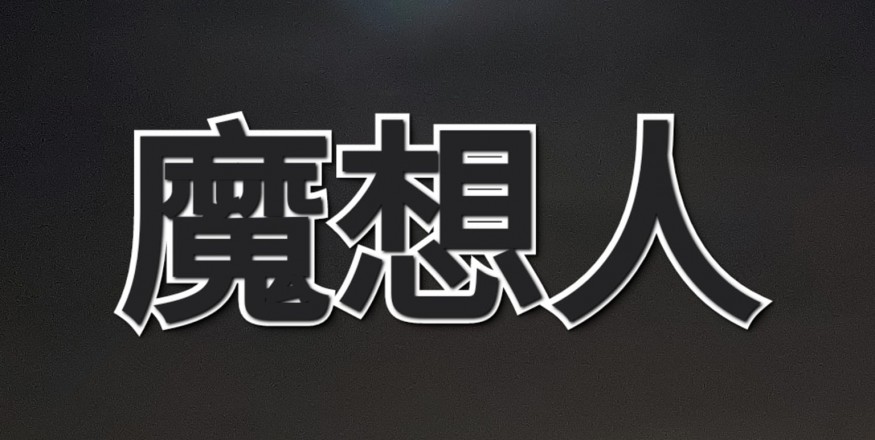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是誰…到底有沒有放火燒了我的菜園?」游露拿著棍子質問著我們。當然伊凡例外,因為他當時正在跟游露看電視,旁邊還放了一籃祭典首飾。「我聽附近鄰居說有看到你們兩個其中一個跑去燒菜園。
「游露,我那時候在睡覺。」
她指著義成毫無疑問的把問題歸咎在他身上。「一定是你!你一直以來都是讓我最頭痛的。」
義成感到厭煩的拖著長音回道:「不~是~我~難道妳除了我就沒有其他人這個答案嗎?還有,阿嬤我問妳,他們有證有據嗎?都什麼年代了,聽人家以訛傳訛就可以這樣汙衊我嗎?叫他們去調監視器阿,叫阿!叫阿!」
游露整張臉氣的火冒三丈,猛力的吸氣,一巴掌朝他揮了下去。「沒大沒小的孩子,滾!」
義成一氣之下衝出門外。「妳根本不是我認識的游露,我就是從外面撿來的!」
他要去哪,我也不知道。但站在原地若有所思的游露,看起來確實跟一般的阿嬤沒有兩樣。我被搞濛了。會不會是我誤會她什麼了,導致我們幾個卯起來抽絲剝繭地調查,或許事情就真的很單純,只是單純要為我做祝福儀式而已,什麼殺了我、活祭的這件事情,在這個年代,完全不符合時態。況且她也說了,真正該死的是那四主,但卻又跟迪貝爾書上的五主相互矛盾。這下我被弄得頭很痛、很亂。
即便是這樣,對於義成辛苦得來的鑰匙,我不能因此就這樣前功盡棄。今晚,也就是快接近大月圓前夕,我將探究那些圍繞著篝火的石磚屋。
義成說謊說的很真實,所有言行舉止都很像他沒做過一樣。無辜的眼神、矢口否認的意志、受盡皮肉之痛仍面不改色。
我坐在房間,心情有些沉悶,此時門外響起敲門聲。
「請進。」
伊凡打開門,拿了兩杯茶走進來,遞給我。「幫你泡了一杯茶。」
我接過。「謝謝。」
他指著床邊。「可以坐嗎?」
我點頭,同意他坐下。「坐啊,這也不是我家,只是暫住的。」
他坐了下來,喘了口氣說:「你還好嗎?」他啜飲了一口茶。「你看起來很不開心,是不是義成的關係?」
「這還能開心的起來嗎?義成被趕出去,一大早又發生這事情。家裡面烏煙瘴氣的,怎麼可能開心的起來。況且你看游露火大起來的模樣,跟雷公降世沒兩樣。」
「是他先說謊騙游露的啊。」
「你怎麼知道他是說謊?」
他笑了笑說:「我認識義成多久了,還能不清楚他的性格?」
「也是…」我點頭,又接著猶疑了一下。「不對阿,就算是這樣,附近街坊鄰居總該要拿出證據吧?」
他專注地看著我,語重心長說道:「德瑪垂克,我很明白義成的樣子。一個愛說謊的人,他不會全盤說謊。有時他會站在自己的立場去替自己辯護,有時客觀地為人設想,但這一切都是在鋪設他後續的目的。在謊言摻雜著事實是他們的基本功,因為能夠增加別人對他的可信度。但和一個人相處下來,所謂的經驗,才是看清楚事實的媒介。必須被他騙過,才可以理解他的套路。雖然他這次謊言開大了,但我也相信他並不全然是在說謊。」
「什麼意思?」
他走到房門前,準備離開。「越正常的人,越不正常。」他打開門後,向我揮手。「掰啦!杯子記得拿去洗。」
我對他這番話感到匪夷所思,難道義成才是這起事件裡面說謊的人?包括之前那些事情?但是…人人都會說謊啊。我們不喜歡被欺騙的感覺,卻也會欺騙別人。他所說的「越正常的人,越『不正常』。」,這樣聽下來,整個村子應該只有義成最『正常』了。
今天我在房間待了一整天,用手機和老爸聊了很久。我告訴老爸很好、沒事,他也傳了一張微笑的自拍照給我,他說如果想他就可以和他視訊或是看看他的照片,在上班以外的時候可以找他傾訴。我不敢和老爸透露太多事情,只因為,我希望他能專注在生活上面,不要替我擔心太多。這輩子,他替我們兩姊弟操煩的夠多了,如今我要自己面對這些事情,去解決它。
傍晚,義成回來了。他把房門關起,那個力道,彷彿還在氣頭上。
我走出房間,敲了敲他的門。「陳義成,你在裡面嗎?」我內心有點忐忑不安,但房內依舊沒半點聲音。
我緩緩地打開門,從門外瞄了進去。
只見義成癱在地上,視線直盯著天花板,彷彿沒了知覺,眼白通紅,啜泣著。淚水順著太陽穴流到地板上,感覺十分悲傷。
我沒經過他的同意走進房裡,他依舊毫無任何反應。
「你沒事吧?」我關心,走到他旁邊坐下問道:「你怎麼哭了……」
他立刻起身抱住我,依舊啜泣著。「對不起……」
我被他的反應嚇到有些不知所措,雙臂夾了起來,卻能感覺到他身上一股沸騰的悲傷感。
「怎麼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如果我當初沒有帶你回來就好了。」他刻意緊閉嘴巴,不想讓自己哭得更大聲。「再過沒多久就是大月圓了,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你…」
此刻的我內心很平靜。「義成,我是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我。我也知道自己再去訓練也無事於補了。我總覺得這一切不需要擔心,自然的反抗、安然的死亡,但今晚,我必須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查清石磚屋的事情。你們為了我做了很多,幫我處理那些霸凌的人我一直惦記著,從沒有忘記。若要離開,也要我報答完你再離開。你願意相信我嗎?」我直盯著他的眼睛。
他眼泛著淚光,眼神中帶著一道期盼,直視我的雙眼點頭。
「今天就算你不願意相信我,我的初心依然不變。」我說:「未來我們要收拾好情緒,用腦袋跟勇氣面對眼前的事情。」
「好,這我最拿手的。」他自信滿滿的破涕為笑,然後還把鼻涕抹在袖子上。
我看見旁邊放了一包衛生紙,直接遞給他。「義成,你再髒一點沒關係。」
「哈哈,好啊!那我再髒一點啊。」
「我意思是叫你不要這麼髒啦!聽不懂人話?」就在這時,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對了,義成…那把防魔刀……被我弄壞了。」
他收起眼淚,用袖子把地板的眼淚抹乾。「沒事的,遇到魔神仔刀子壞掉是很正常的。我都忘記跟你說了。」
「你還有武器嗎?」我接著問道:「防身要用的。」
他搖了搖頭。「邪方劍?」
「我能用嗎?」
「試試看。」他將我的手拉靠向他。我的掌心朝上,他在我掌心上平放著,並且緊握著拳頭。就在此時,一道黑霧從他的指縫內往外竄,延伸成一把劍,只見他輕輕放開手,一把帶著紫色混濁霧氣的劍攤在我手中,感覺起來輕飄飄的。但是正當我要握住劍柄時,那把劍又順著我的指縫往下飄走,散成一道煙霧了。
「我記得之前我還可以用那把劍斬殺長髮妖魔…」
「那是你用黑煙才接的起來。」
「我想起來了,我的神識可以透過黑煙轉移到別的角度攻擊。這是黑念派系的共通技能對吧?」
他點頭。
「但我還是需要武器…」我說。
「菜刀?」他試問。
「菜刀?你在跟我開玩笑嗎?難道沒有一點像樣的武器嗎?」
「真的沒了。但我只能說,最好的武器就是你的怨力了。既然你擁有這些技能,你應該要學會善用它。」
「但重點是我無法隨時想用就用啊。」
「垂克,人在被激發潛能的狀態下,比起拿刀子,比起訓練千百遍的攻擊技能,會更加的有爆發性。尤其你又是被霸凌到大的人,想必怨力會更重。就像當初在火車上面一樣,我親眼看見你親手製造了兩顆震動球體,夾擊了蛇頭人的腦袋。」
他這麼一說,我才回想起這件事情。確有其事。
「所以我該空手去嗎?」
他思索了一會。「痾……等等幫你帶菜刀好了。放心,我會幫你準備刀套。」
「好吧,將就用了。我很後悔丟掉迪貝爾給我的那把劍。」
他擺出一副很無言的眼神。
接著他起身,打開房門,在門外四處探了一下,確認周遭沒人後,再將門關上,鎖了起來。
他在我旁邊坐了下來,深呼吸了一口氣。
「你怎麼了?」
他臉色凝重地看著我。「你知道我為什麼哭嗎?」
我搖頭。
「我想起你母親在活祭的前一夜,我跟隨著德瑪游露到一處茅草屋探望你母親。她被綁手綁腳,頭髮凌亂不堪,好幾天沒洗澡。恐懼的眼淚在月光的照映下顯得特別詭異。游露在你母親身上指指點點,彷彿在下什麼咒語。她自稱那是在為祭品祈福,也不准我們對外說出口。雖然你母親逃過了祭典,卻沒逃過內心的恐懼,選擇自殺身亡。當時所有人對祭典一事彷彿很有默契般的,一致對內外都三緘其口,彷彿有股無形的力量正在威脅著所有人。而游露對我們的說法是,魔想人會害了這世界,只要你們還活著,黑暗的力量將會四處奔竄。」他接著說:「我只是害怕,我又會看到同樣的畫面。」
一想到自己的母親被如此的對待,即便對她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內心卻像是被刀子割一樣。我無法想像當時母親所要面對的恐懼,一幅用無知所創作的畫。一幅來自過去、宗教、崇拜,在現今會讓人感到瞠目結舌的經過,確實上演在人類最盲從的時代,來自不安與恐懼,尋求安身所崇拜的信仰,在超自然底下的卑微,然後供起不知善與惡,比自己要更加權威的能量。在慘叫聲下的祝福,所有人連結起共同的動作、眼神,也將忘記自己的模樣。
「我絕不會讓這件事情重演。」我緊握拳頭,並烙下狠話。
「我希望你會是終結這一切的人。」
我眼神帶自信地看著他。「會的。」
「話說垂克,你還記得我拿鑰匙給你的時候嗎?」
我點頭說:「記得阿,怎麼了?」
「你不是拍了迪貝爾的書給我看。」
「對。」
「那個貌似逃的部首,又貌似言的部首。」他悄悄的靠近我,緩慢的說:「我今天用謊言測試游露……」
我好像懂了些什麼。
「在我說謊的時候…」他露出一抹凝重,卻又自信的笑容。「祂出來吸了……」
我睜大著眼,確定聽懂了什麼。我愣住,然後馬上回過神來。「所以第五主是謊言?」
他很篤定的點了點頭。「謊字,言部,那個單詞就是謊言。」
「你怎麼會突然想到謊言?」
「因為我總覺得游露正在編造一些非事實的東西呼嚨我們。包括她在掩蓋一些事情。」
夜晚,祭場燃起熊熊火光。月光更加的圓亮,望著卻不禁有股不安感襲來。
我們下了一樓一如往常地吃著晚飯。這之中我不斷地在觀察著游露。她的神情與模樣。
「垂克,多吃一點,今天買的肉很好吃。」游露夾了幾片豬肉給我。
「謝謝游露。」
她露出一抹微笑。「話說…再過一兩天就是天享祭典了。垂克,那天你是主角,你值得受到更好的祝福。」她一說完,我不禁顫起滿身疙瘩。這種氛圍就不對勁啦。
「呵呵…是啊。」
接著她轉頭望向義成,一改早上的氣焰,溫和的說:「義成,對不起,早上游露誤會你了,有人說他看錯了,所以不是你。」
「本來…」他示意性的望著我,彷彿要我仔細看看游露。「本來就不是我,我行事正大光明,也不會做這種縱火事。我常常偷偷幫游露澆菜園就算了,也常常幫街頭巷尾鄰居,那時候火車上也是我救了垂克。游露妳不知道就算了,還汙衊我。」
這時一道黑影緩慢從游露身後現出,那透明而晦暗的靈體,拉長了高度,猛吸著義成身上所瀰漫的謊言之氣,神情感到有些滿足。而游露的眼神頓時像失了魂般的楞在那,一動也不動。但僅此一會,游露回過神回道:「確實,游露真的很不應該。」她有別於以往和義成粗魯的互動。我在想,會不會是大月圓-天享祭典的日子將近,而她的真面目也快顯露了出來。
我打了一身冷顫,剛才游露的眼神和舉動,宛如一隻傀儡,任由謊言操控著她。她就像一身毫無靈魂的皮囊,露出生硬的表情和舉動。我和伊凡對到了眼,他卻彷彿視而不見般的,沒有任何表現,一擺常態的吃著碗中的飯菜。
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Cu4CO7KeU
吃飽飯,我洗了個澡。刷了牙,洗了臉,將自己的雙眼清洗乾淨。我凝視著自己的模樣,在滿是霧氣的浴室,對自己喃喃自道:「垂克,你準備好了嗎?」
此時有個聲音從我內心竄出。「你應該要有信心,只要有我在,你放心。」我內心突然自我朗讀了這句話,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因為不需任何言語,不需發出聲音。
「你是誰?」我問道。
「你很明白呀,我是你的怨念。」
「你有名字嗎?」
「我叫張文,跟你的經歷很相像,被叫掃把星,後來被爺爺背叛之後,上吊在荔枝樹下。所以我這輩子最恨別人欺瞞我。」
「也難怪迪貝爾會說出那樣子的話。」
「你也在她面前讓我難堪了,讓我遇上了謊言。」
「游露一定是被控制了。」我說。
「是不是控制還很難說,我早已感覺不到那位叫作游露的生命徵象了。」
我一回神,看著鏡中的自己,瞳孔變小,眼瞼周遭不斷冒出詭異的黑煙。我嘗試著呼叫張文,他再也沒有給予我任何的回應。而在一紮眼後,那詭異的現象又消失不見了。
午夜,樓下的鐘聲彷彿示意著我應該出發了。
一樣的,這次也是拉著繩子垂降。但這次的目的地並不是在亂葬崗,而是我眼前的圓形祭場。我要一探那石磚屋裡頭的真相。
義成把刀套繫在我的腰間,然後我穿了一件藍色格子襯衫擋住。
我緩緩的下降,義成依舊使盡力氣幫我安全落地。我解開繩子,和義成揮手告別後,便朝著後面的樹林走去。
一路上,我小心翼翼,在安靜的樹林裡行走,踩著落葉的聲音更加響亮清脆。我左顧右盼,即使還沒亮出刀子防備,卻早已握緊拳頭,呈攻擊姿態應付可能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危機。
好在這路上都沒有任何危險的事情。
我在樹幹後探出一顆頭,朝著祭場的方向望去。沿著左邊掃視到右邊,在黑夜中除了那旺盛的火焰以外,似乎沒有任何人在這地方駐守著。
確認沒人後,我亮出鑰匙,伏低身驅,朝著最右手邊的屋子前進。
眼前的石磚屋觸摸起來格外冰涼,而我拿起鑰匙不斷試鎖。經過日曬雨淋,生鏽斑駁的鎖頭,在鑰匙插進去時有點難轉。我東張西望,又得專注在開鎖上。就在這時,喀!的一聲,其中一把鑰匙對應了這個鎖頭,解開了。我拆開鎖頭,在開門前緊張得喘了口氣,感覺四周的空氣更顯得冰涼。即使中間的篝火正在燃燒著,卻無法掃除我心中的一絲寒意。
我緩緩地把鐵門打開,一股無法形容陳年已久的惡臭味撲鼻而來。我的內心興起一種不好的預感,抽起口袋的手機,開啟手電筒功能向前一照。前方映入眼簾的,是堆疊在一塊的人類骨骸。參差不齊的堆疊方式,褪色的血染衣物覆蓋在骨骸之間。我倒抽了一口氣,跑出石磚屋。接著我早已管不了是否有人,內心泛起一股無法控制的憤怒與慌張,朝著左手邊的屋子奔去,然後快速地試鎖。
打開了鎖頭,一開門,我立馬將手機往裡頭照去。一模一樣堆疊的骨骸,一模一樣的凌亂。我向外倒退了幾步,只見月光照映在屋外,一道黑影出現在我身後。月光拉長了影子的高度,在我轉過身之際,一把鈍器朝我腦袋重擊。我意識瞬間一片迷濛,然後倒在地上,將我帶入毫無知覺的黑暗中。
我身處在一座環繞著山嵐的森林裡,陽光從樹林間映下,金黃色的光澤緊貼在樹葉表面,微風撫過大樹之間,響起沙沙作響的清脆聲。我站在樹林間的斜坡處,樹根攀附交錯地面,腳底下彷彿剛下過雨般的潮濕,臉上感覺得出來一股難以形容的溼氣。嗅了嗅,還有股來自地面的泥土味。
這時前方不遠處傳來緩慢的腳步聲,那道踩踏聲很明顯是往我這個方向走來。我驚慌的躲在一根大樹後偷偷觀察著,觀察前方那個在樹林中忽隱忽現的黑影。
她停了下來。秀長的頭髮,在山嵐之間迷濛的影子,像是不斷地在尋找什麼。「尹德瑪…尹德瑪…」
她正在呼喊我的名字,而不是垂克。
我下意識的走了出去。
那抹微笑是如此的熟悉,但我卻沒看過這個女生。
她發現了我,朝我走來,我卻不會感到有所恐懼。
「妳是?」我問道,並退後了一步。
「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母親。」她使著心疼的眼神將我摟在懷裡,身上有一股花香。
我推開她。「我好像沒看過妳……所以…」
「我知道。」她眼泛著淚光,不捨的看著我。「我的孩子都這麼大了。」
「我對妳很陌生。」我很不滿的跟她說:「如果妳真的是我的母親,妳知道我父親經歷了多少痛苦嗎?打從我有意識以來,他一直惦記著妳。父親其實很痛苦,他不知道妳為何要自殺。他對於妳自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人都消瘦了不少。」
「我也不願意。」她神情低落的回道:「妳的外婆背叛了我…在我出生前,她繼承了巫者,並且與巫者締結了契約,正式成為魔想人。」
「後來呢?」
「妳的外婆生下了我,將我扶養長大至成年。但在我產下你之後沒多久,妳的外婆就把我送到藥巫村,要讓我見一位她的好姊妹,游露。」
「德瑪游露…」
她點了點頭。「這位德瑪游露,其實早已經死了。」
「死了!」我驚呼了一聲,並且回想起怨念曾對我說過的:「他早已感覺不到游露的生命徵象。」
「後來我才發現母親是要帶我去藥巫村獻祭。」她接著說:「而在囚禁期間,謊言也向我現出了他的真面目。」
「外婆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在承接魔想人的契約上,魔想人只能有一個,所以在孩子成年有後代之後,就會帶孩子去獻祭……」
「那不生就好啦!」
此時,一陣大霧襲來,耳邊嗡嗡作響,宛如一場風暴過境。
睜開眼,我發現自己躺在屋子裏面,而身上還殘有一股花香味。
此時外頭一陣呼救聲,這聲音很熟悉,是義成。他大喊著,嘴裡五句有四句不離三字經。我立馬起身,在黑暗中環顧四周,這股惡臭很熟悉,是擺放骨骸的屋子。
我將手觸摸在門上,外頭眾多整齊劃一的呢喃聲使我顫起一身疙瘩。
隨著一陣凌亂的腳步聲,就在此時,門被打開了。
有兩個人穿著黑白相間的披肩,脖子上掛著游露所做的首飾。他們架住我,繞過圍成一圈的小篝火,然後從小入口進去。篝火中間立著一根木柱,義成被懸吊在上方。而此刻他們拿著粗繩將我反綁在木柱上,我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
只見在篝火外,所有人盤坐在地圍成一圈,他們全穿著披肩,頸上佩戴著首飾,面向我們喃唸著聽不懂的咒文。我仰望天空,天氣好到一個清澈,星點滿佈夜幕,而月亮卻出奇的大又圓。
這時一個穿著連帽米色斗篷的人朝我們走來,手握著一把被蟲啃食嚴重的木杖。他身旁跟著兩個穿著紅色斗篷的人,至始至終,那兩個都低著頭,以低調的型態行動著。
那個身穿米色斗篷的人停在篝火前,目視著我們。「噓~睡了很久了吧,今天是天享祭典喔!」
義成依舊嚷嚷著。
這時呢喃聲在指示下停止了。
「你還記得我嗎?上面那位。」
我抬頭望向義成,只見他楞住幾秒後,又開始罵道:「你到底是誰?你這個傢伙,快放開我。」
這時他掀開帽子,一雙銀白透光的眼眸,彷彿能照亮黑暗的四周。他中間的瞳孔又黑又小,一副中分的髮型,雙手杵著木杖,凹陷的臉頰在我們之間微笑著。「你忘記我了嗎?人類不是最愛說謊了?還是說…」他把帽子拉了回去,蓋住頭後,又掀了開來。這時游露的臉蛋出現在我們面前。「你比較想看到你最愛的游露小姐。」
「你為什麼要冒充游露?」義成大喊。
「嘖嘖嘖…我沒冒充她啊,我只是藉著她的皮囊玩了幾十年,玩到這天來臨。」他咧開一抹大大的笑容,然後把目標轉向我。「垂克你好啊,我心心念念的垂克啊……我就說你也是我族的一份子。你好好地環顧周圍這些人,他們全都是你黑念派系的同親啊,懷念嗎?」他接著又換回自己的面貌。
「所以你佔據了藥巫村,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垂下了笑容,卻一副無關緊要的模樣。「我跟你說啊,我最愛說謊了。我生前是個騙子,在每個鄉鎮四處行騙,騙到我都不愁吃穿了。但後面我被人打死在路邊,原因是我太愛騙人了……」
「我問你為何要佔據藥巫村!」
他依舊我行我素地說著:「後來我死後,巫者將我封印到石頭裡,我哪知道我變鬼後,覺醒的那麼快。我率先醒了,然後四處吸取愛騙人的人類,滿街~都是~」
「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嗎?」
「我正在回答!耐心聽我說完。」他繼續接著說:「後來巫者出意外死了,我就藉著他的皮囊在市區小騙了一下,哇~香的嘞。所以說,人啊~真的見了個眼界就會忘記時間流逝非常的快,熟悉整個環境、文化,沉浸在裡頭,非常自我的活在自欺欺人的狀態下。後來,頭目把我找去藥巫村學了一些藥巫的技術,非常的不錯,環境也很好,想讓我在村裡值醫,並且幫我立名巫醫。原本我滿心歡喜的想接受頭目的邀約,那時幾乎快要定下來了。想不到後來頭目要我領著一堆外來客去別的地方另闢新的藥巫村。要命啦!要命啦!我的腿快被走斷了。他還跟我說那是前藥巫村的什麼分裂的,搞什麼歸家,背叛後再討人情,很高招欸。好在我進藥巫村前,有承接了巫者的黑念術,我也算是勤奮勤學的好學生,在黑念術這塊鑽研有佳。別說我只會騙人什麼的,要我認真起來你們應該都要逃了。」
「所以你因為頭目的出爾反爾,就侵略了藥巫村?」
「算是吧,我最恨別人出爾反爾,比起騙人,這更加窩囊。但我也算是心地善良啦,藥巫村的村民死後,我還有給他們好幾間房子住呢!」他指著周遭的石磚屋。
「你這無恥的傢伙。」義成咬牙怒道。
他吃了一隻木杖上的蠕蟲,咀嚼說道:「但總歸一句,主要還是因為傳承石吧。」
「傳承石…」
「你的外婆承接了魔想人的身份,而與我締結了繼承的契約。」她把一旁穿紅色巫袍的人的帽子翻開。「你應該連看都沒看過她吧?」
一個滿頭白髮,老皺的臉,依舊低著頭不敢見人,微微顫抖的女人,她盤起包包頭,臉色有些不安。
「她是你的外婆,惠昭。」
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
「契約內有共同約定,必須不斷繼承後代,找到那個身帶與傳承石有共鳴的人,至傳承石碎裂,然後四主覺醒,才算圓滿。但什麼是圓滿呢?就是不包含我,四主要全部成為我的附屬品。」他狂妄地笑著。「但來侵略藥巫村可是黑念派系大家的主意唷!我可沒有隨便給意見。」
「難怪我覺得那個盤著頭的怎麼那麼熟悉,原來就是妳這個老太婆!」義成掛在上面怒喊道。
「哦!對了,那時候巫者的身驅不堪使用了,我是藉著惠昭的身體來的。」他四處張望了一下。「看了看這裡的地理位置,大月圓確實能滿溢著巫力。」
這時外婆忍受不住,捶向一旁的謊言,大哭喊道:「你欺騙我!你把女兒還給我!你說什麼女兒有後代,必須得獻祭,這分明就是你欺騙我!」
謊言一把抓住外婆,外婆痛的大喊一聲。
「魔想人只能有一個……但我沒有說妳女兒是魔想人阿。妳一直堅信妳女兒是魔想人,是不是妳在養育她的過程中,其實一直都在流口水想把妳女兒給獻祭掉?」
「妳在說什麼東西啊?」
「我只是說了妳女兒有巫力,要妳好好觀察一下,並且小心為重。妳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你說這麼做我才能保持魔想人的地位!」
「看來妳為了地位連家人都出賣的掉……」他嘆了口氣。「唉~連我這種最會騙人的都覺得可悲啊。」他指著我。「看到沒,妳眼前這個外孫,才是會奪取妳地位的人。現在去殺了他,把他最後一個怨念取出來。」
「外婆!」我死命地搖頭。
這時我眼中看見的外婆,她顫抖著,然後瞳孔像被控制住般的舉起刀朝我衝來。此時一道影子掠過,她手中的刀子被奪走了。
一陣詭異的冷風吹過。
「已經過來了…」謊言說著。
「這刀子蠻亮的,我就收起來了。」
「貪婪先生阿,你……」謊言還沒說完,他身後地面浮出了一個靈體,靈體後揹著另一個靈體,背後的靈體抓住謊言的頭髮,接著前方的靈體一拳揮出,謊言被擊飛,撞到旁邊的篝火。
這時現場開始引發動亂,所有黑念派系的人全部圍攻。周圍開始竄起黑煙,像隻有意識的大手朝著對方攻擊。
「義成!邪方劍!」我喊道。
「你不能用!」
我閉上眼,開始想著使我怨念更深的事情。「丟!下!來!」
這時我的背後竄起一道黑煙,我的視覺意識藉著黑煙看見上方的義成將製好的邪方劍扔下。我的意識接起,然後砍斷義成手上的繩子,接著我也砍斷自己的繩子後,意識回到自己身上。
我們兩個接續落地,一堆人在混亂中不停打鬥。
義成此時招喚出一堆男子,男子舉起甩棍四處奔竄揮打,踢開周遭的篝火,波及到旁邊的人。
此刻我的怨念彷彿覺醒了起來,面對眼前的謊言,感覺怒氣與怨氣值正在上升當中。「垂克,把你的意識交給我吧。」張文在內心說。
「好。」我接著對義成喊道:「義成!」
義成看到我的臉,完全愣住了。「垂克!你的眼睛在發光還在冒煙欸~」
「別廢話,邪方劍丟給我。」
他二話不說將邪方劍製了出來,朝我扔來。我接過,然後一把衝向謊言,朝他揮砍過去。謊言朝地面敲擊,木杖瞬間自帶電流,朝我揮來。我蹲低身子,從他手臂旁掠過,一陣背後刺擊,刺穿了他的身體。他依舊無痛無癢的回頭對我笑著,立刻竄出黑煙朝我襲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躲過,竄出黑煙飛向他身後,拎住他的衣領甩了出去。他跌落地,在第一時間朝我衝來,完全沒有任何冷靜的時間。我們使著武器鏗鏘作響,那把木杖看似不堪使用,但打擊起來卻感受到十分有力。
就在此時,他將木杖往下一震,電流竄的我腳底酥麻,完全沒了知覺。「怨念張文對吧?等等再來收拾你。」
我跌坐在地上,眼看著謊言正在尋找下個目標,完全不把我看在眼裡。
突然一陣巨響從藥巫村入口處方向傳來。我眼看著迪貝爾率領一群亂葬崗亡魂。他們身帶著武器,各個有備而來。他們停在那頭,士兵舉起劍,所有鬼不分男女老少全往這衝來,朝著黑念派系攻擊(除了我以外)。
就在這時,暴力和僥倖被一道黑矛刺穿,靈魂開始蒸發成氣體,接著被謊言給吸進身體裡。
望向貪婪,祂不斷地在地面上撿拾著武器,低下身子尋找哪把武器比較珍貴。這時,謊言發現了祂。貪婪望向祂,兩個人四目相對,然後眼神中發出星星般的閃爍,嘴邊樂的揚起嘴角。
正當謊言準備刺向祂時,祂一招閃過扔開武器,接著上前奪走黑矛。「又亮又黑又亮又黑~」
此時謊言朝著祂準備竄起黑煙攻擊,貪婪張大著嘴似乎發現遠處有更好的武器,立馬回過頭。「嘿!這還你。」祂朝著謊言擲射過去,正中祂的心臟。祂拔開,嘴裡嚷嚷著:「你…你是故意的吧?」
正當貪婪撿到更好的武器時,謊言立馬衝上前一把將黑矛插進祂的身體裡。貪婪化為一道煙霧消失在空氣中,然後被謊言吸入身體裡。
接著他將視線移向我,「你…是最後一個了,張文。」朝我走來。
眼看著祂慢步地向我走來,眼神中透露著勢在必得。
這時我的身體突然沒了力氣,倒在地上,然後眼前迷濛的出現了一個人影,這僅此短暫的片段之後,又清醒了。
我睜開眼,從混亂中爬了起來。只見敏捷的身手在不遠處互相打鬥,那兩個不相上下,激鬥出強大的力道。謊言在經過黑念派系的人時,不斷吸取那些人的黑煙,接著那個人就倒地不起。
「祂彷彿在吸能量一樣。」
只見祂每經過一個就在吸取他們的能量,而另一個漸漸趨近於下風,直到謊言怒吼了一聲,脊椎竄出了好幾道黑煙,將另一個靈魂架住。謊言露出得手般的笑容看了我一眼。「你的張文…我拿了!」
「張文!」我喊道。
祂將黑矛刺進張文的體內,張文隨即化為一道氣體,被謊言給吸進了身體。
這時謊言彷彿全身都在震動,在月光的照射下,化為一道風,順著篝火的方向刮起一道宛如龍捲風的氣流。所有人見狀,急忙著退後,然後漸漸仰望著那道風越颳越大,身體四肢被風組成。此刻烏雲開始聚集,天空落下閃雷,一陣傾盆大雨瞬間傾瀉而下。
眼前的怪物正在咆哮著,眼神中發出不寒而慄的光。
就在這時,所有人身上的煙黑全都被眼前的怪物給吸進去了。
這時一個穿著袍子的人站在我旁邊,仔細一看,是伊凡。而他旁邊,還有一個雛形所帶來的人。那個人手捧著一個罈子,看似正在等待著什麼。
我驚訝道:「伊凡!」
他露出一抹微笑回道:「等祂心臟完全組成。」
就在這時,很多東西都被眼前的這個颶風怪物給吸進去。祂張大著嘴,彷彿在炫耀自己的威力。
「可以了,丟!」伊凡對旁邊的人說。
旁邊的人照著伊凡的指示將罈子扔出去。那罈子摔到地面後,伴隨許多黑色顆粒吸入祂的嘴裡。
我好奇的向伊凡問道:「這位是誰啊?」
「我的好朋友。」他露出一抹驕傲的微笑。
就在此刻,前頭的怪物彷彿被噎住了什麼,緊抱住心臟,眼神開的猙獰。
「垂克…」伊凡默默地望著我。
「恩?」
「我很高興認識你。」
剎那間,那道颶風怪物彷彿被炸了開來,一道震波伴隨著電流朝我們衝擊而來。身體顫起一陣酥麻,感覺所有毛細孔全被鎖閉了起來。
直到四周都安靜了下來,我嘗試著緩緩的睜開眼,山邊的晨曦彷彿正要升起,夜幕的一角被染上了淺藍。環顧著四周,一群人癱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包括我身旁的伊凡,仔細一看,老了許多。我走向迪貝爾和黑念系的人,全都變老,完全斷了氣。
我強忍著淚水,周圍一片狼藉。
就在這時,一道倉促的咳嗽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循著無數的屍體,找到了聲音的來源。「義成!」
他顫抖著身軀,然後蒼白的頭髮,還有垂下的眼皮望著我,話說起來有些無力。「垂克……」
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qQCO2jh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