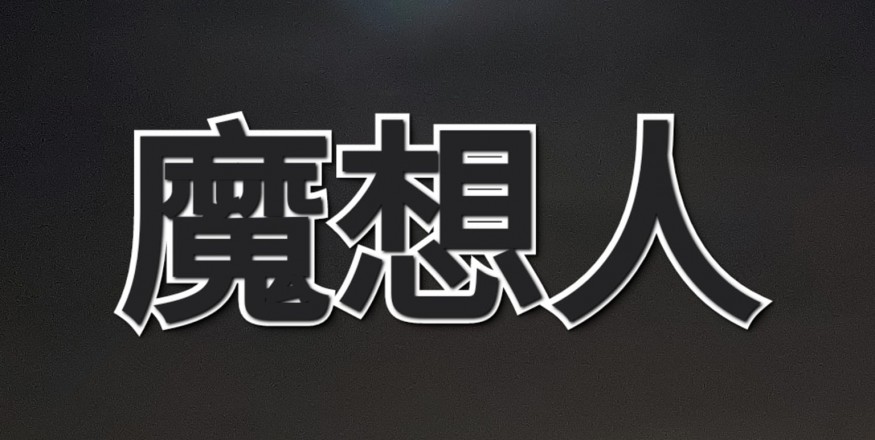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聽起來感覺有點恐怖…守墓人。」我內心感覺有些不對勁。
「他沒那麼恐怖啦。」他說:「他只是專門在墓地看守的警衛而已。你這樣想就好了。」
「是這樣嗎?」我半信半疑地問道。因為他越講後面那句話,我越覺得事有蹊蹺。況且,把這件事情視為秘密,是能單純到哪去。
他肯定的點頭。
我接著問道:「話說…游露一直在說的天享祭典到底是什麼?」
只見他遲疑了一會,然後將視線轉向我。「因應你的到來,我們即將要做一場驅魔祭典。」
「原來如此。」我接著望向窗外,並指著那頭。「所以那個地方就是未來要驅魔祭典的地方嗎?」我不知怎麼了,感覺想去那地方看看。
他看向我指的那個地方,點頭道:「是啊。」
我拿起旁邊的水壺,打算到一樓裝水。「好了,我等等差不多要睡覺了,你也早點睡吧。」
他點了點頭。「好吧,你…就早點睡吧,明天早上我帶你去走走。」他說完後,便走回自己的房間。
我拿著水壺下樓,隱約能聽見一樓有電視播放的聲音。我戰戰兢兢的一步一步下樓,然後悄悄從一樓走廊邊往客廳探去。只見游露啃著芭樂,亂糟糟的白髮披在肩上,打結在一塊,像極了一個毫無目的,不知道接下來要去哪嚇人的女鬼。好吧,我內心這麼想,至少沒有說出來的失禮。但在我眼前的這副景象,確實很貼切呀!
這時游露彷彿瞥見我躲在走廊偷看,她便向我招了招手。「過來啊,垂克。」
我走向她,手握著水壺,然後說道:「我…下來裝水。」
「哦,還沒睡啊?」
「阿我人在這啊游露,現在還沒,下來裝水。」
這時後頭突然哇的一聲,我瞬間把水壺扔了出去,不偏不倚砸中了游露的臉。她緩慢地咀嚼著芭樂,把啃一半的芭樂重重地放在桌上,看得出來超級不爽,後面的聲音顯然是義成跟伊凡的。
游露抄起手邊的棍子起身朝我丟來。「你們這兩個臭小子!」然後不偏不倚地砸中我。我知道絕對砸不到他們,因為那該死的兩兄弟躲在我身後躲得扎扎實實的,然後我負責幫他們擋子彈。
「阿嬤,開個玩笑嘛!」義成喊道。
「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小孩,打擾我看世道(台語劇)就算了,還讓垂克拿水瓶丟我,你們是活膩了是不是?」
我尷尬地撿起水瓶。「阿嬤對不起。」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地回道。
「垂克啊,你不用對不起。義成這傢伙欠教訓。」
「阿嬤我沒嚇喔。」伊凡在一旁立刻撇清。
「我知道啦。」他指著義成。「你給我皮繃緊一點。」
義成對他做了個鬼臉。
「既然你們三個都在這了,那我就告訴你們一些事情吧。」阿嬤的口氣瞬間轉為沉重地,手上拿著遙控器,然後將頻道轉為新聞台。
接下來為您播報一則今日下午發生的新聞。在台北新店的一處公寓老宅,發生了一起虐童案。三歲陳姓女童因為哭鬧,繼父受不了女童的哭鬧聲,竟持起棍棒毆打女童。儘管母親努力的護著小孩,女童依舊被繼父拖至別處毆打。母親索性持起手機,拍下繼父毆打女童的證據。以下畫面可以看到,女子躲在角落將手機架好後,便上前護著女童,導致兩人雙雙重傷,而女童的傷勢比較嚴重,頭部有好幾道明顯嚴重的撕裂傷,目前已被送往就近的大醫院救治。
「看到了嗎?」只見游露問我們。
我們三個在電視前面面相覷。伊凡問:「你們有看到什麼嗎?」
「沒有阿。」
「太可惡了吧!女童被毆打。」我一股氣從心裡往上衝。
「你們仔細看那位繼父的身後。」
我們三個同時將視線轉向電視上正在毆打孩子的繼父。「有!」我看見他身後有個黑影慢慢顯現,並露出一抹微笑,殘忍地看著眼前的一切。那個黑影並沒有任何舉動,但像是在繼父的背後吸著什麼。隨著畫面越來越暴力,那個黑影越發清楚。只見隨著無法讓人接受的哀號透進耳裡,他們倆也看見了電視上我所表述的那個黑影。很清楚。那個模樣,讓我想起了在水晶食魔住處的那三個人,一模一樣。
我從桌上拿過遙控器,轉到別台新聞。
剛好新聞從藝人專訪轉換為社會新聞。這次是超商偷竊案。
以下監視器畫面,可以看見劉姓男子在超商內駐足徘徊,行跡可疑。他先是在櫃台購買了一個袋子,然後循著飲料櫃不斷躲避超商人員的視線,將商品一個個撈進袋內,最後在熟食區裝了個茶葉蛋,再到零食區偷了幾包零食後,假裝到櫃檯結帳排隊。直到在前兩個客人結完帳時,他順勢與結完帳的客人併行而去。但這一舉一動,早已被監視器拍得一清二楚。
我能看見他身後有兩個黑影不斷地在背後吸著他。我很明白這個身型跟樣態,跟我看見的那三個『小偷』一模一樣。祂們像是氣體,又像是實體,但在媒體形容影像的畫面,似乎凡人完全看不出任何詭異的形體正在跟隨他們。「這…這就是我在水晶食魔家裡面看到的那三個。」
游露點了點頭。「沒錯。暴力、貪婪、僥倖,祂們如影隨形。包括今天早上的銀行搶案祂們都有份。」
「妳的意思是,祂們掌控著這些人去做這些事嗎?」我疑惑問道。
游露搖了搖頭。「相反的,是人的心使祂們出現,趁著人心散發出這樣的意念,嗜食那些人的念頭。會壯大祂們,壯大貪婪、暴力、僥倖,因此許多案件層出不窮,不能是祂們的原因,而是人心因此去壯大這些意念的出現。」
「那祂們吸收了這些念頭,壯大了自己,會做出什麼事情?」
「社會很亂,並不是因為祂們。但祂們卻在為『你』的甦醒而鋪路。」
「我?」
「你內心沉睡的那個『怨』力,祂們需要更多能量才得以駕馭祂,否則無法成為共主。」
「所以妳才因此想要消滅掉祂們對吧?」
游露點頭,並從櫃子的角落旁,提出一把被刀鞘包覆住的武器。「這把刻魔刀是唯一能殺掉共主或者四主的武器。以黑剋黑,以暗吞噬掉黑暗。」
「那該怎麼殺掉祂們?」
「除非內心的怨醒來,否則祂們三個都會持續為成為共主的那天做準備。」游露說。
「媽呀,這聽起來太沉重了。」伊凡說:「我先去睡了。」
「總該有個方式讓祂甦醒吧?」我疑惑地問。
「只能讓老天安排了,這種事情說再多都道不盡。」游露嘆氣回道:「快去睡吧。」
我在游露面前晃了晃水瓶。「那…那我去廚房裝水。」即便如此,我內心依舊納悶著該如何叫醒怨的這個特性。
游露點頭,然後繼續啃著芭樂,轉回她愛看的台劇。
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9yUr5y9V7
隔天早上,義成來敲了我的房門。我提起惺忪的雙眼,並沒有忘記今天他要帶我去認識這個村子。在我盥洗完後,換了套新衣服,游露一大早煮了鍋白稀飯,我們這樣簡單就著醬瓜、豆腐乳解決了一餐。喔對,今天早上伊凡依舊沒有要陪同我們,因為他等會要跟阿嬤去附近採地瓜葉順便種點東西。反倒是瑞足一大早跑來游露家蹭早飯,閒到自己提出可以陪同的要求,甚至吃飯期間,話匣子一開就無法停下來,跟他那跳舞的熱勁一樣無法停息。這樣看來,伊凡與他的奶奶感情比較深厚,凡事都以游露為優先。
吃完了早飯,我只帶了一支手機就出門了。
義成領著我們到周圍晃晃。說老實的,除了那個圓形廣場,其它地方確實跟一般村莊沒什麼兩樣,唯一能值得一提的就是這裡的純樸與善良,每個村民所展露的熱情與笑容,感受到無比的溫暖。
「昨天有沒有吃到游露煮的拿手菜?」瑞足一臉羨慕道。
「有,迎賓菜,超豐盛的。」
「昨天跟朋友去跳舞,根本沒吃到,游露煮的菜真的不是蓋的。」
「我同意。」我回道。
「欸!義成,叫游露今天再煮一頓迎賓菜給我,我過去跳舞給她看。」
「白痴喔,她叫你去吃辣椒啦!」義成笑道:「誰叫你是我們村裡的小辣椒。」
「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什麼意思啦?」
「叫你回家吃飯的意思啦!」義成大喊,並且跳上他的背。「叫你不要再來我家蹭飯聽到沒有!飯會被你吃光,蹭飯王。」
「去我家撈米就好啦!又沒說不給你們撈,是你們自己不來。」
「是你自己說的喔!到時候阿伯罵我,我就說是瑞足說的。到時候你就不要反悔。」
「說我說的幹嘛?你就說阿嬤叫你來撈的就好了啊,笨喔!」瑞足喊道:「我爸最怕阿嬤了。」
「好!今天就去你家撈米。」
我們幾個有說有笑的,在沿途有許多村民蹲坐在門口撥豆子、打發時間聊天,甚至騎車下山準備辦事的,還有遛狗的。悅耳的鳥叫聲,沒有多餘的雜音,充斥著小朋友的嬉鬧聲,一切是很單純美好。順著果園往上走去,似乎是一個圓環狀的村子,中間分布著不同類型的屋子,無形中彷彿在告知著每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可以有多好的房子能住。大家毫無隔閡的見面就打招呼,整個鄰里好像都對每個人的身分瞭若指掌,沒有任何一點隱私。但他們似乎也不是很在意,因為對彼此的善意都感到信任。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這讓我覺得我除了身上的負面以外,我還是有對善良所期盼的那個光明面。光是這麼想,我的內心就舒坦了不少。
這時天空下起了一陣一陣的毛毛細雨,有些雲層很明顯的掠過這片區域,有點灰暗,陽光卻又在這之間忽隱忽現。一陣涼意迎面吹來,能感受到即將快下大雨的天氣。遠處山邊的天空綿延著一片尚未化開的深灰,彷彿那頭正在下著傾盆大雨,半空中瀰漫著淡淡的白色霧氣,估計看起來像是正在飄雨。
瑞足仰望著天空,細雨不斷地打在他臉上。「看來今天不太適合出門,我先回家囉!掰掰。」他二話不說向另一頭奔去,頭也不回地,很突然地就離開了。
僅留著我們兩個愣在原地,還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哦不,是我,義成看起來倒是蠻淡定的。
「他就這樣丟我們兩個在這?」我不解地問。
「是沒差啦,我原本就沒有要讓他跟啦!」他接著說:「反正我本來的計畫又沒有他。是說現在也逛得差不多,大致上整個村莊大概就是這樣,實際上也沒有太特別的。」
我點頭。實際上來看,確實是這樣沒錯。
「你應該是要帶我去找守墓人對吧?」我謹記著,並沒有因為他帶我四處走走而忘記今天的目的。
他四處張望,像是害怕有人聽見,並點頭。一直以來,總覺得他的神情有些不對勁。我無從說起,也無從猜測到他的心思。我只知道,打從在學校,他的神情一直都很不對勁。
他領著我往上坡走,這條道路沿著果園呈微微的斜坡,往下坡處望去則可看見入口處。他東張西望著,好似不能讓人發現我們正要去的地方。我其實有些緊張,我緊張的是義成是不是有別的目的,或者他口中的守墓人,本身又帶著什麼目的。
陽光夾雜著間歇性陰雨,我們朝著烏雲密布的那座山頭走。越是靠近,內心卻越發的沉重。毛毛細雨打在臉上,彷彿面前的風雨正在逐漸增強。
「義成,要不要撤退啦?感覺等等會有大雨欸。」
他從口袋裡掏出兩個輕便雨衣。「我都準備好了。我住在這那麼久,我比誰都還會看天氣,這種天氣時常都有,所以不需要擔心。」
我接過雨衣,套了上去,看來他沒有想要撤退的打算。我並沒有多說些什麼,但這天氣確實讓人感到五味雜陳。不曉得怎麼說,那種陰晴不定的感覺,悶熱夾雜著雨水,一下太陽出來又躲了起來。我向來都很討厭這種天氣,穿起雨衣更是將汗水和皮膚沾黏的特別透實。
越往後面走,路面更顯得顛簸。雖然爬坡高度緩了不少,但路上的小石地卻沒有特別整過。整路上碎石子在我們腳下喀拉喀拉的響著,每踩一步,鞋底與石子摩擦的聲音不絕於耳。
細雨打在臉上,更痛的是眼角,不斷被雨浸濕。我用手抹開眼前模糊不清的視線,跟隨著義成前進。
「還要多久啊?」我問。
他比了個二。「大約還有兩公里。」
「兩…兩公里!」
他點頭後,便持續淡定的走著。
就這樣,我們其實也走了不曉得走了多久時間。在經過一段上坡處後,義成停了下來,便低頭望下地面。他神情顯得猶豫不決,但卻又鼓起勇氣向前跨了一腳。
他踏過了,然後回頭望向我。「走吧。」
我跟著望向地面。「這腳底下有什麼嗎?」
「結界線,能抵禦妖魔鬼怪的咒語。」他接著說:「游露說這是為了要保護你的。但是,我並不確定。我也不懂為何要大費周章保護一個魔想人,總之先去找守墓人吧。你注意安全。」
「好。」
前方是一座樹林,茂盛陰暗的樹林。兩側大樹能掩蓋住直射的陽光。但現在是陰天,前方更是昏暗不清。我深吸一口氣,緊跟著義成。義成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黑暗,那片黑暗無時無刻會使人有竄出鬼怪的任何想像。
我小心翼翼地跟隨著,義成更是全神貫注在周圍,因為踏出了結界,說不定早有魑魅魍魎在暗處鎖定著我們。更不用說肖想魔想人的肉跟四主。雖然我身上只剩一主,而且那個主也還未覺醒。但我並不理解那些壞東西正在打量著什麼主意。
好在過了這段陰暗處,前方似乎充斥著陽光。那片剛才看到的昏暗烏雲似乎散開了,一道刺眼陽光迎面撲向我,呼吸多了一份緩和與自在,與剛才屏氣沉重的路程有著天壤之別。
我吐了一口氣。「終於。」
那道刺眼陽光激的我睜不太開眼。直到陽光被一片烏雲給擋住,我的雙眼向前定睛一看,映入眼簾的則是整片荒廢的亂葬崗。
墓地雜草叢生,裂開的墓碑東倒西歪,看起來多年沒人管理。儘管陽光直射在這片大地上,看起來風和日麗。但周遭的氛圍仍舊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先不用提及我了,我真不能理解為何守墓人還有勇氣待在這片荒廢的土地上。是說,他待在這是為了什麼?對他來說有什麼好處?我不太懂。
我們持續朝前方走著,周遭的這些雜草早已長得快有一個人高。能看見倒臥碎裂的墓碑分佈隱藏在某些雜草中,由此可見,這些墓已經被遺棄很久了‧
這裡地勢平緩,但路上依舊顛簸。我們朝著遠處的那頭走去,沿途可見亂葬崗。就這麼一條路,沒有任何其它路能讓你選擇。若是下雨天來,勢必會卡在路中央動彈不得,因為地上的乾土將會化為泥濘讓你動彈不得。
路途揚起沙塵,隱約在左前方一百多公尺處的斜坡樹下有一棟破舊小屋。若不定睛一看,還會以為是沒人住的廢墟儲藏室。但當我們越走越近時,才發現這棟屋子可以容納不少東西。雖然窗戶破損、燈光昏暗,但義成確實往那道門的方向走去沒錯。
我們走到了門前。
「是這嗎?」我仍舊納悶地問道。
他點頭後,敲了敲門。「有人在嗎?」
這時門內出現一個低沉的聲音。他緩緩開門,一隻眼睛從門縫中露了出來,彷彿正在試探防備著。「哦!」他這反應好像認識義成。確實,義成都認識他了,他有什麼理由好不認出他來。
他打開門,眼前是一個中年外國人,目測差不多快30歲。這張臉龐近乎讓我瞠目結舌。對欸,高挺的五官、白皙的皮膚,在我面前的確實是個外國人沒錯。他看起來並不好,臉色略顯憔悴,穿著一件卡其色長褲還有破爛的白色衛生衣。
「迪貝爾,你還好吧?」義成問道。
他拖著一雙黑眼圈回道:「那些兄弟姊妹搞得我整晚沒睡,」他轉過頭看向我。「這位…」
「這位就是你在等的魔想人後代。」
我驚訝的望向義成,我對他這番介紹感到不可思議。應該是說,這話聽起來像是策畫已久。
眼前的外國人開心的再把門打得更開,然後雙手把我握住,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你好,我叫迪貝爾,我是從英國來的巫術研究者。我…我真的太高興認識你了。」很明顯他往後梳的髮型顯得有些老派但紳士,但想必頭髮不經常打理,導致那往後梳的頭髮開始雜亂,導致現在這副德性。
我尷尬地介紹自己。「你好…我叫垂克。」就算如此,我依舊納悶地將視線瞥向義成。「現在…是什麼回事啊?」
「先進去吧!」義成說。
迪貝爾猜測了一下義成的眼神。「痾!歡迎請進請進。」他敞開大門,並且對門外東張西望了一會,彷彿害怕有什麼東西正在監視著他。
走進房子裡,裡面只有一張小床。床邊堆疊著破爛的外文書籍,地板上倒著一只皮箱,旁邊曬著皺皺爛爛的衣物,吊衣服的線看似也快支撐不住,彎成一道微笑。一顆暗黃色的燈泡就是他仰賴視線的唯一來源。因為就算大白天,在大樹下的屋子也很難照進陽光。
他尷尬地說:「不好意思喔,我這什麼都沒有,連個像樣的桌椅都沒能招待你們坐著。」
「沒關係沒關係。」我好奇地說:「迪貝爾先生,你的中文很好欸,你應該來台灣非常久了吧?」
他彷彿對時間沒甚麼觀念,笑笑說:「我好像也忘記自己待多久了,但和別人交談對我來說可是輕而易舉。」他立刻從一旁撈出一根捲起的地墊鋪在地板上。「地墊可以吧?」
「沒問題。」
我們席地而坐,三個人圍在一起。從進門開始,義成就突然安靜了下來。我不知道為什麼,甚至為何迪貝爾先生正在等魔想人。
「我剛從門口對話聽起來,你們應該都在等我對吧?」
義成變得一本正經地點頭。
「為什麼?」
「這要從那場突襲說起…」義成臉色凝重地說。
「突襲?」我問道。
「頭目第二次帶領村人去台東尋找巫者,發現人去樓空的那次。那次原以為事情能夠有個圓滿的交代,甚至可以達成共識。殊不知,黑念派系的人早已暗中守在藥巫村外準備突襲。好險村裡的人都學有巫術防身攻擊,那場突襲才沒有死傷慘重。」
「那這樣很好啊,問題出在哪?」我納悶問道。這聽來確實是個好結局,並無不妥。
「是,這樣確實沒問題。」義成指著迪貝爾。「但迪貝爾有問題。」
我望向迪貝爾,不禁冒出所有的問號。
迪貝爾一副不安的緊皺眉頭,望向某處彷彿正在回憶著什麼,卻又顯得有些吃力。「1954年,我大學畢業沒多久,特地搭飛機來到台灣,前來拜訪藥巫村。那時候我好像還記得,當時我正在探究東西方的巫術文化,特意學了中文還有各國語言,也因此到過許多國家,但並不是所有巫村都願意見人的。」他嘆了口氣繼續說:「但藥巫村不一樣。他們很熱情,並且不吝嗇的向我介紹藥巫的各種知識,甚至願意讓我在村子內待幾天,空出了一間草屋讓我住。他們將善良用於行醫救人,卻在巫藥技術方面也出奇的嚴格。但好像某天,街上浩浩蕩蕩的,頭目帶了好幾個人像是要出村去見人。沒過多久,一群眼上塗著黑色炭灰的人配戴著武器衝進村內,開始斬殺村人,放火燒了整座村。但我的眼珠子看到的不只如此,他們除了手拿武器以外,背上的脊椎還竄出一條黑色氣體,能夠支配著自己的意識去攻擊別人。我第一次看見那種黑巫術,不用藉著武器和拳腳,那條黑煙就像能夠隨時飛到別人身邊,進行突襲。有的更厲害,能夠身體與黑煙雙重合作攻擊。我死命衝進樹林裡,往後山的方向跑,逃離哀鴻遍野的村莊。當時我感受到一道震波將我推倒,身上開始產生靜電。我硬著頭皮繼續跑。直到我到了亂葬崗,一片無人祭祀的亂葬崗。我的陰陽眼告訴我,跟祂們住在一塊很吵,但會很安全。就這樣,我在這邊建造了自己的屋子,住了起來。」
我專心地在聽,然後看了看迪貝爾。他保養的真好。
「起初那場突襲結束了,我正打算回村子查看情況。」他看著窗外。「但窗外那些鬼魂兄弟姊妹們直接包圍我的屋子,要我別再回去了。比起自己,我更相信他們的直覺。至今,也是如此。」
我端詳他整個面容,然後手臂,包括整個身體的體格狀態。接著我下意識地捏起他的手臂肉,食指與拇指正在按壓測試觸感。
他驚訝地問我:「你在幹嘛?」
我回道:「你說你1954年那年大學畢業沒多久?」
他理所當然地點頭,聲音依舊像年輕人一樣明亮清脆。「對啊,怎麼了嗎?」
我望向義成,義成竟然對這一點質疑都沒有。
我拿起手機給他看。「你看過這玩意嗎?」
他一臉驚訝的手抖。「這…這甚麼東西啊?會發光!」
「手機啊!」我跟義成不約而同說,並且覺得這玩意一點都不新奇。
我舉起手機將他的面容拍給他看。「這你的照片。」
他嚇到倒退了幾步,作勢要打我。「嘿!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做手機?連聽都沒聽過!竟然還可以拍照。」
我點頭。
「你知道現在是西元多少年嗎?」
他思索了一下,依舊對時間無解。「現在是幾年?」
「2019年。」
他睜大著眼睛,然後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將目標轉向義成,近乎崩潰般地喊道:「你為什麼遇見我的時候沒有告訴我?為什麼?為什麼?」他掩面哭泣著。「2019年…我的父母已經死了。」
「你的面容,太詭異了。」我不安地再次拿起手機給他看。「不知道該說你保養得很好,還是整個時空將你卡在這個型態,讓你忘記了年齡與身體的流逝。」
這時一旁的義成開始發愣,感覺他的神情有些不對勁。「我…我也…」
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38kHrlf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