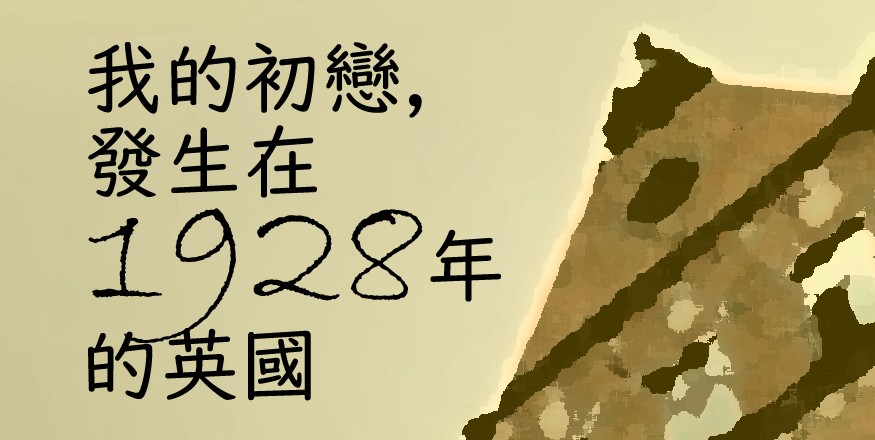愛德華漸漸回復意識,但不管他如何努力睜大眼睛,四周依舊漆黑一片。他首先想到自己應該被轟炸機炸中了,也許已經到了天堂,不,應該是地獄。愛德華覺得自己應該下地獄。接着他嗅到泥土味、燒焦的木材味,還有斐瑞熟悉的氣味。不,不是地獄,斐瑞不會下地獄,他應該在天堂。而且天堂不該漆黑一片,像個可怕的密室,或者新埋在地下的棺材。他們該是身處因遭受轟炸而塌下的房子內,建材倒下來了卻沒有壓中他們,只是將他們困在此地。愛德華緊了緊他的手,確定他仍然緊握着斐瑞的手——那隻手仍然溫熱,也仍然有脈搏在躍動着。
被困在倒塌樓房的建材下面,不見天日。愛德華的驚恐症差點便發作了,但當他一想到跟自己在一起的是斐瑞,不知怎的,他一點都不害怕了,甚至覺得就這樣死了也了無遺憾。
「斐瑞?」愛德華想叫醒他,以確保他真的安全無恙。然而沒有得到回應。「斐瑞?」愛德華再次掉進恐懼的深淵,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跟斐瑞死在一塊兒,但不能獨活而失去了他。
「我……沒事。」黑暗中傳來斐瑞沙啞的聲音,他緊了緊愛德華的手,以告知他是平安的。
「感謝主。」愛德華軟癱下來。「我無法經歷在一天之內,以為失去了你兩次。」
「你剛才以為失去了我?」斐瑞問。「所以哭了?」
「你不該以身犯險。不值得為了救我而喪失性命。」
「噢,愛德華。」斐瑞突然翻身過來,抱住了他。「為了你,要我死十次也可以。」
「別……別說這種話!」愛德華也抱住了他。「不許死!我妹妹剛剛才從鬼門關跨回來,你絕不可以在那附近徘徊,我在這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人,你們誰都不許死!」
「愛德華,你真的是愛德華?」斐瑞用盡力氣緊緊抱住眼前人。「我還以為你不愛我了。我以為,你十二年前就拋棄了我。」
「不,我不是想拋棄你,只是……」愛德華艱難地吞嚥。「我很愛你,所以不想讓你受苦,我們在一起不會有好結果……」
「沒有你的人生,也一樣痛苦。」斐瑞撫揉着愛德華的背部,嗓音顯示出他內心的傷痕累累。「你明白嗎?沒有你的每一天,都像活在地獄一樣。」
「我知道,我也一樣。我也是每天過着地獄般的日子。」愛德華摸索着他的臉,顫着聲說。「對不起……真的對不起……」
幸好在黑暗中,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否則他們絕無可能把這樣的心聲說出來。
「求求你,不要再推開我或迴避我好不好?」斐瑞貪婪地埋在愛德華的頸側,聞着他的氣味。「不要再離開我,永遠不。」
「嗯,好的。」愛德華讓斐瑞爬到他身上,那令人懷念的身體重量教他安心又釋然。「我不會再離開你,我許諾。」
斐瑞壓着愛德華,低頭吻下去。一個漆黑細小的密封環境,那麼令人懷念地,好像回到了中學時代,被同學作弄受困於操場的儲物室內,斐瑞也曾壓着愛德華,然後是他們嘴唇的初次接觸。
愛德華環抱着身上的人,任他放肆地搗攪着自己的唇舌。他們一邊深吻一邊飢渴地撫摸着對方,一邊互相輾磨着彼此的身體,讓狹小的空間充滿了喘息聲和呻吟聲。
劫後餘生的慰藉,加上被壓抑多年的思念和感情被一下子釋放出來,他們都被剎那間點燃的愛慾沖昏了頭腦,都忘了身處何時何地,只是不由自主地扒掉愛人的衣物,要更多更多赤裸裸的肌膚相親,才能彌補過去被糟蹋掉的十二年光陰。
「我愛你,我愛你……」斐瑞吻着身下人的胸膛,然後一路吻到肚臍,再吻到情人的硬挺。
「呃——」被情人含進火熱的口腔中時,愛德華嗚咽着。「我也愛你。」他撫摸着斐瑞的頭髮,任由他在自己身下吞吐着,已酥軟得無法動彈。
斐瑞把手指伸到愛德華嘴邊,讓他含弄,愛德華就把它們弄得濕潤透。斐瑞用濕潤的手指替愛德華稍作擴張,便急不及待把分身頂撞進去,是有點粗糙不適,是不夠溫柔體貼,但置身荒僻之地,他們都等得太久了,已管不了那麼多。
「啊——」愛德華在被完全填滿的一剎那,叫了出來。
「很痛?」
「不,繼續……」愛德華在狹窄的環境中扭動着,一條腿搭上了斐瑞後腰,這角度令他們進行得更順利。
「愛德華……」斐瑞進出着那個他思念無比的小穴,那麼的緊緻,像未經人事。他抱緊身下人,不停吻着他。
愛德華也抱緊斐瑞,讓二人被汗水緊緊黏貼在一起。「用力點……噓……再深一點……」
斐瑞捏着愛德華的臀肉,把他下半身抱起來緊貼着自己,然後拼命撞擊進去。
愛德華的陰莖太敏感了,受不了不斷的磨擦,便摟着身上人的頭頸,在汗水和喘息聲中登上極樂境界。他很久沒試過,頭腦裏空白一片,只有無盡的幸福和滿足。
甜蜜的小穴在不斷收縮,斐瑞置身其中像要發狂般再抽插數下,便抱緊愛德華射了出來。
他們渾身汗濕地摟抱在一起,無法言語的快樂。
# # #
「冷了,穿衣服吧。」
不知道躺了多久,他們終於回到現實。
「我們,剛剛在倫敦市中心的大街旁……」
「……做愛了。」
他們一邊大笑,一邊穿回了衣服。
「正確點來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倫敦,一個戰爭廢墟下。」愛德華回復了他理性冷靜的揶揄風格。
「我們會不會死在這兒?」
「也許。」
「也許這樣更好。」斐瑞摸索着,找到愛德華的手,便緊拉着不放。
愛德華知道斐瑞是在擔心,回到現實世界後,他們剛才的快樂便會中止。他只能緊了緊他的手,用愛撫來安慰他的情人。
沉默了一會後。
「我們代表蘇格蘭場和大英政府,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斃。」
「你身上有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求救的東西?」
斐瑞摸索了一會,然後愛德華聽到黑暗中傳來一下刺耳的警哨聲。「這個行不行?」
「好極了。」
愛德華拿過那支警哨,以摩斯密碼的節奏,不斷吹出「S.O.S」的哨子聲。
一個半小時後,終於獲得救援人員的注意。
當頭頂的頹垣敗瓦被清除,將近黎明的晨光透進地底。斐瑞感到愛德華馬上放開了手——放開了他們從剛才就一直牽着的手,並隨即退了開去。
斐瑞望着愛德華站在一個體面的社交距離,一個他們怎也無法逾越的距離。他知道這是必要的,在公眾視線之前。但他想在愛德華眼中找到半點蛛絲馬跡,證明剛才黑暗中的一切真的有發生過,愛德華真的對他許下了諾言。
但愛德華始終沒有望向他。
# # #
之後,又是沒完沒了的工作。
真的看不出來,那天在黑暗中的事情,是實實在在的發生過。
一切好像回到了起點,他們沒有做愛、沒有牽手,愛德華沒有為了斐瑞哭、斐瑞沒有救過愛德華,愛德華沒有責備過斐瑞、斐瑞沒有重要事情隱瞞過愛德華……他們工作,偶爾對望,互有感覺而裝作沒有,繼續工作。
斐瑞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也許工作和社會地位,對愛德華來說就是比較重要。
所以當他要到哀綠綺思俱樂部跟愛德華開會時,也並沒有過多的預期。所以也才會在愛德華握着他的手時,驚訝得叫了出來。
愛德華沒有說話,只是拉他起來,帶他進入那個書櫃後的暗室。
當門關上後,房間內又再漆黑一片。
斐瑞感到愛德華把他壓在牆上,不顧一切地吻着他,又激烈又深情。他高興得雙腿發軟,只能緊緊摟抱住愛德華,跟他沒命似地深吻着。
他們再次扒光了對方的衣服。
這次愛德華把斐瑞帶到一張溫軟的大床上,手上有潤滑油。
「這次換我來,好不好?」愛德華在他頸伴的低聲耳語,已教斐瑞興奮得渾身發抖。
「嗯,好的……」
愛德華很溫柔地開拓着斐瑞,並不停親吻他。斐瑞仰面躺着,很想看看愛德華此刻情動的表情,但這房間沒有一線光源,伸手不見五指。
啊,原來如此。
他們就是不見得光。
只有藏身在不見光的縫隙裏,愛德華才會承認他們的關係。
斐瑞任由愛德華做帶領的一方——他突然想起亞瑟,愛德華的「性玩具」。在斐瑞之前,一直在黑暗中「招待」愛德華的,是亞瑟,那個長得很像斐瑞的年輕人。也許亞瑟之前就是躺在這兒,斐瑞如今躺着的位置,任憑「主人」玩弄。
愛德華進入了斐瑞,斐瑞抱住他,讓他自由馳騁着自己的身體。性愛的快感很讓人分心,但斐瑞仍是想到自己如今代替了亞瑟的位置這件事。也許亞瑟最初就是斐瑞的替身,但愛德華並不愛他,只是把他當成「性玩具」。也許愛德華仍然愛着斐瑞,但他們的關係並不能曝光,斐瑞也只能成為他不為人知的「性玩具」……
「你在想什麼?」愛德華低吼着。從他凌亂的節奏可以看出,他已經很接近了。
「沒有……」斐瑞用嘴堵住了他。他希望用性快感阻止自己思考,忘記他們的關係就是只能如此。他現在和愛德華在一起,用最神聖的儀式在結合彼此,他還有什麼要埋怨呢?他應該很知足了。
當他們雙雙高潮過後,兩具沾滿汗水的身體,並排躺着,在喘息。
「就……這樣,沒有關係的。」斐瑞想表現得寬宏大量,但仍忍不住洩出了一絲苦澀。「真的。」他只好心虛地再強調。
「什麼意思?」
「就……這樣。」斐瑞指了指四周,才想起他們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只好解釋。「我可以代替亞瑟,做他一向做的事。」
「什麼?」愛德華好像很震驚。
「這樣的關係我也能接受,真的。」
「不是這樣的,斐瑞……」愛德華坐了起來。
「不用為難的,我明白你的處境,我們的身份實在不能幹出這樣的事,即使往後都要偷偷摸摸又有什麼大不了呢?」斐瑞站了起來,慌亂地想要找回他的衣服。
「斐瑞……」愛德華追了過來,一把從身後抱住了他。「不是這樣的。」
斐瑞不知道怎麼辦。他的情人正親密地摟抱着他,下巴就擱在他肩膀上。這該是個甜蜜的姿勢。但他心裏一片茫然,想到前境,竟差點掉下淚來。
「不是這樣的。」愛德華喃喃地又再重覆。「亞瑟不是你想的那樣。」
愛德華急着要解釋的,竟不是斐瑞的疑慮,而是替亞瑟說話——斐瑞的心痛上加痛。
「亞瑟從來沒有跟我做過,我們剛才做的事。」
聽到這句話,斐瑞就懵了——他們沒有做愛?那麼愛德華聘請亞瑟來做什麼?
啪的一聲,愛德華把房間的燈亮着了,眼前的景像嚇了斐瑞一跳。
要說斐瑞身為一個警察,刑具他看過不少,因工作需要也經常慣見人性暴力的陰暗面。但他現在身處的地方,分明是一間刑房,放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即使是他也仍感到恐怖陰森。
是的,他一向誤以為這只是間普通的臥室,因為上次一瞥而殘留的印象。但他忘了當時房間內並沒有亮燈,只是透過辦公室那邊的光線照射進來,依稀看見了床的輪廓,加上亞瑟當時身穿晨褸的裝束,主觀上就認定了這裏是他們秘密纏綿之地。
如今光線充足,可見那是張比醫院病床更簡陋的鐵床,床具都是白色的,而床頭床尾的鐵枝上,都備有束縛手腳的皮帶鐵扣。床頭有一個絲絨托盤,上面放着五根粗幼款式不一的鞭子。牆角站着一個中世紀人形刑具,雖然現在是閉合狀態像個擺設,但斐瑞看過書上的照片,知道內藏殺人尖刺。其他地方擺放着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玻璃櫃和鐵箱,可見的都展示着不同功用的刑具,有利刃型的、有綑綁型的、有毆打型的……
而最嚇人的,是斐瑞現在看得見裸露的愛德華,才驚覺他身上佈滿大大小小、縱橫交錯的傷痕,大部份是瘀傷,也有少部份是輕微的割損,雖然大都已在褪色階段,仍教人觸目驚心。
「為什麼會這樣?」斐瑞拉住愛德華,仔細打量着他的愛人,心痛他曾受過的皮肉之苦。「還痛嗎?」
「不痛了。」愛德華只是別過臉,順手拿門後掛着的晨褸穿上,也遞了另一件給斐瑞。
斐瑞匆匆披上,接着查根究底。「到底怎麼回事?」他感到憤怒異常,誓要把傷害愛德華的人煎皮拆骨。但當他看見愛德華穿回了衣服,他發現那些傷痕都落在十分巧妙的位置,能完美地被衣物遮掩住,所以斐瑞才一直沒有發現。他訝異地瞪着愛德華。「是誰做的?亞瑟?」
愛德華點了點頭。「這才是我聘請他的原因。他在色情俱樂部裏,可是施虐遊戲的專家。」
「遊戲?」斐瑞怒吼着。「這算那門子的遊戲?是你嶄新的性癖好?」
愛德華苦笑着搖了搖頭。「雖然對色情俱樂部那些顧客來說,這的確是種特殊性癖好。但對於我不是。」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摧殘自己?」斐瑞生氣地叫着。
「最初希望作為一種治療。」
「治療?」斐瑞乾瞪着眼。
「你應該知道,那些犯了嚴重猥褻罪的同性戀者,會被送往接受那幾種治療。除了注射荷爾蒙,體罰一樣可以令人性慾減退。」
斐瑞突然感到毛髮倒豎,一陣心寒。
「肉體上的疼痛,其實比起心靈上的痛苦,舒服多了。」愛德華還笑得出。「只要性慾一出現,就接受體罰,把性慾跟痛苦的潛意識連結在一起……」
「巴夫洛夫制約。」
「對,往後只要一有性慾就會條件反射地聯想到痛苦,漸漸戒除好男色的天性。」
「你成功了嗎?」斐瑞感到心臟絞痛,但欲哭無淚。「你還特地找來一個酷似我的行刑手?」
「對。他的外表能挑起我的慾望,我覺得這樣能夠事半功倍。」愛德華苦笑。「但剛剛發生的事情,很明顯證實了這個療法根本一點用處也沒有。」
「你說『最初』是一種療法,後來呢?」即使是斐瑞,也感到自己的聲音很陌生很遙遠。
「我很痛苦,我的身份、地位、職業和家人,都需要我潔身自愛成為一個體面的人,當然更不能幹違法的事。我用盡方法希望能改變我自己這天生的墮落嗜好,但卻不得要領。」他頓了頓,吞嚥了一下。「特別在你重新出現在我面前之後,我發覺這療法真的毫無效果。」
「所以呢?」斐瑞感到自己在發抖,並且搖搖欲墜。
「所以,這變成了一種中世紀式的自我鞭笞贖罪。」愛德華說。「別被滿室的刑具嚇怕了,其實大部份只是裝飾,常用的也就只有那幾條鞭子。」
「為什麼你還可以說得那麼輕描淡寫?」
「因為比起思念你的痛苦,那些皮肉之苦真的不算什麼。」
斐瑞睜大眼,瞪着愛德華。「可是……可是跟我在一起的念頭,令你羞愧得要自我凌虐。我們這種戀愛關係、肉體關係,害你痛苦得要鞭打自己千百回,也想要把它戒除……我們……我的存在,令你那麼愧疚,那麼抬不起頭做人……」斐瑞哭了出來。「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為什麼……」
愛德華一把抱住他,緊緊地。「因為我愛你。即使我死後要下地獄,即使我們的關係會令我死後承受地獄之火、千刀萬剮,我也不捨得放手。不!我試過放手,但之後過的日子,比生活在地獄更加難受。所以,即使我會為此賠上所有,我也不能失去你!」
斐瑞在愛德華的懷抱裏顫抖着,因為他在飲泣。愛德華輕輕撫摸着他的頭髮,斐瑞終於抱住了愛德華,痛哭失聲。
「對不起,我們現在只能維持一段不見光的關係。」愛德華說。
斐瑞搖了搖頭,擦乾眼淚。
「但我想這不會是永遠的。」
「什麼意思?」斐瑞退開一點,看着愛德華。
「你說過的,我這麼聰明,一定會想到辦法的。」
「你想做什麼?」
「我現在已經是大英政府的一份子,假以時日,說不定我真的能成為『大英政府』。」
斐瑞只是皺着眉頭看他。
「我想通了。像我們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少,像我爸爸、像特務叔叔,更有王爾德、柴可夫斯基這些名人,還有羅馬時代的眾多英雄好漢,我並不覺得他們都是可鄙之人,反之,他們對社會都有很大貢獻。」
斐瑞點了點頭,仍不知道愛德華想說什麼。
「假如這些人都是上帝創造的,上帝為什麼要把天賦賜與違背祂旨意的人?看樣子,還比較像是上帝的祝福多於詛咒吧?」愛德華雙眼閃閃發亮地看着斐瑞。「我們現在觸犯的,其實只是人間的法律,是人創造出來的,會隨着時代轉變而修改的。」
「對,羅馬時代這種事情也不是犯法的。」
「所以我可以從修改法律着手,去改變世人的看法,令他們明白我們根本沒有犯罪。」
「真的嗎?這真是太好了!」
「當然,這肯定是場漫長的戰爭。」愛德華頓了頓。「而且要先打完了我們眼前這場真槍實彈的真戰事,才有空間去着手。」
「我相信你。」斐瑞終於笑了。「你一定會成功的。」
「我也相信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
ns 15.158.6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