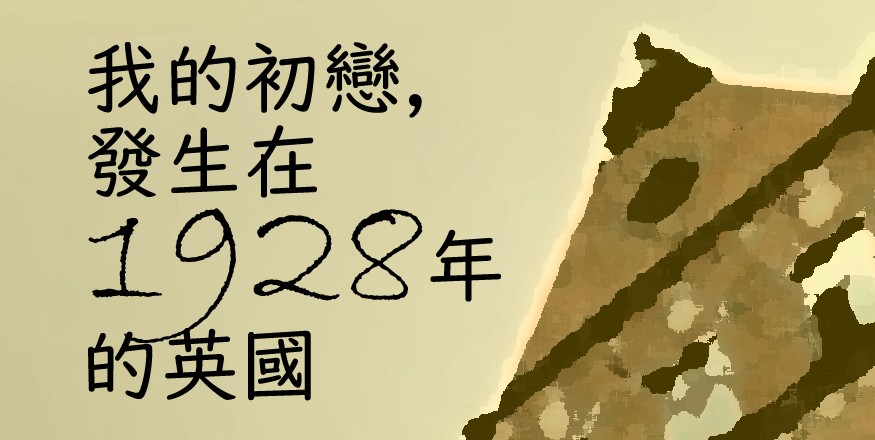在接下來的週末,斐瑞出席了莫法特先生的葬禮。想必莫法特夫人也有將此事通知了斐瑞的父親,至令他父親千叮萬囑斐瑞要把自己的未婚妻也帶上。那天他就跟伊莉莎白並肩站在一起,置身一堆親友群當中,遠遠看着莫法特一家三口站在儀式的主人家位置。
愛德華臉色蒼白地肅然直立着,始終一言不發。他沒有哭,貫徹他一向的「冰人」偽裝面具,又或者,他已經在之前把眼淚都流光了。
雪莉卻紅腫着眼睛和鼻子,小手一直緊緊抓住身旁哥哥的袖子,把自己盡力地躲到哥哥身後,似乎在迴避着她的母親。
莫法特夫人儘管鐵青着臉,卻在努力扮演一位傷心遺孀的角色——她在宣示主權,展示自己才是莫法特家女主人的位置。
莫法特先生的死因被輕輕帶過,政府內部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要將此事淡化處理。斐瑞恍然大悟,才明白這裏面可能牽涉了什麼私底下的交易,以減輕刑期來交換一張保密協議,因此『嚴重猥褻罪』的內情並沒有被曝光,而罪犯卻被輕判了。
這就是骯髒的政治,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
斐瑞在回去的路上,看見了守在墳場的四名保安,以及遠遠撐着拐杖佝僂着身軀在憑弔着的一個黑衣男子。他知道那應該就是莫法特先生的情人兼工作伙伴,那名傳說中的特務叔叔。他們為了國家出生入死,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並非在殲滅恐怖份子時英勇殉國,卻被一名恐同瘋漢射殺,導致天人永隔。
斐瑞突然感到一陣心慌意亂——他不知道假如自己受傷或重病,在彌留之際,愛德華卻被阻止前來見他最後一面,他到時是否承受得了。更不願意去想像,他們之中誰人先走一步,卻連參加對方葬禮的資格都被剝奪,那時會怎麼樣。最恐怖的是,這種情況是有極大機會發生的,幾乎就等於他們的未來現實。
伊莉莎白這時緊了緊他的手。「時代總會向前走的,這一刻的現實不代表永遠。」
斐瑞苦笑了一下。「想不到你還會安慰人。」
「我也想不到你願意做我兒子的父親。」她笑了笑。「算是報答你,做個賢妻良母是難不到我的。」
「謝了。」
斐瑞卻不知道莫法特夫人的眼睛一直追隨着他們的背影,並藉機向愛德華冷嘲熱諷一番。
「瞧人家跟未婚妻有說有笑,多麼融洽。」她說。「眼前明擺着兩條路——要麼像你爸爸那樣弄得妻離子散、死不瞑目;要麼輕輕鬆鬆像個正常人一樣結婚生子,幸福美滿。你的同學比你聰明,他選了更易走的那一條路。」
愛德華死瞪着地面,咬着唇始終不發一言。
# # #
愛德華沒有出席斐瑞的婚禮,原因是他還在哀悼期不便出席。
身穿婚紗的伊莉莎白美艷動人,在場賓客都向新郎投來艷羨的目光。
斐瑞在整個儀式當中都可說是頭昏腦脹的,只在眾人推動下才完成了所有步驟。他一半的心思在為缺席的愛德華擔心,顯得心不在焉;一半也可說是為新娘今天的扮相而驚艷,並對於自己正在迎娶這樣一位美女感到脫離現實而飄飄然。
他們在眾目睽睽下親吻——斐瑞驚異於自己仍會為親吻伊莉莎白而心跳加速。隨即他記起上次在診療室,他甚至因為伊莉莎白的撫摸而瞬間產生生理反應。他可以確定自己真的不是同性戀,也許是雙性戀,他喜歡男人,但他也喜歡女人。而他真的有喜歡過伊莉莎白,他眼下正在迎娶的女子,現在已經是他的妻子了。
斐瑞突然感到一陣遲到的不安。
他決定跟伊莉莎白結婚的時候,一點都沒有想到過,自己其實也喜歡伊莉莎白。他們曾經是男女朋友,也曾經有過親暱舉動。在後台更衣室那天,要不是碰上愛德華,斐瑞也說不准發展下去他會不會跟伊莉莎白偷嚐了雲雨情。
伊莉莎白在診療室甚至對斐瑞說過,她有想過跟他「假戲真做」。
想到這裏,斐瑞竟感到腹股溝傳來一種熟悉的熱度,一種令人尷尬的熱度。
太危險了。斐瑞至此才明瞭到,自己剛幹了一件多麼危險的事。他跟自己有好感的絕色美女結婚了,而他們曾經都不介意甚或有意跟對方發生親密關係。而結婚儀式過後,他們正在回家途中——回到那間由斐瑞父親出資租住的新居,他們的新家。今晚是備受賓客祝福的新婚之夜,即是新郞新娘的初夜。他們將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不止今晚,餘生都將會如此。
斐瑞突然忐忑得想要作嘔。他之前怎麼會遺漏這一切?曾經對伊莉莎白表現出妒嫉的愛德華,對這一切為何不置一詞?他將作何感想?難道因為這樣,他今晚才缺席的嗎?
斐瑞覺得自己好像辜負了愛德華的信任,做了一個背叛他的決定。他羞憤得無地自容,並且感到極度悔疚。
但一切都以比斐瑞想像容易得多的方式結束了——伊莉莎白到家以後,只是輕輕吻了吻斐瑞臉龐道了聲「晚安,辛苦了」,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關起門。留下一臉茫然的斐瑞在客廳呆站。
他嘲諷自己想多了。伊莉莎白並沒有要試圖色誘他,因此他預備好了的半打嚴詞拒絕的說話也用不上了。就跟之前約好的,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房間,這段婚姻是假的,只是對於他們各自戀情的一個掩飾保護。
斐瑞回到自己的房間,關起門,然後脫光了自己。他想着愛德華,然後在床上給自己擼了一發——想像今晚是他和愛德華的新婚之夜,這想法令他性趣更濃。
事後,他重重舒了口氣。
他最愛的仍然是愛德華。
儘管美麗的新婚妻子就在一牆之隔,這是個孤男寡女的新婚之夜。他最思念的仍是愛德華,他打手搶的對象仍然是愛德華。
就這樣,斐瑞心安理得地睡着了。
# # #
斐瑞被吵醒了,然後他睜大了眼,發現吵醒他的是些「淫聲穢語」——由隔壁傳過來。
他才發現自己仍然一絲不掛,他匆匆忙忙套上衣服穿上褲子,開門出去看過究竟。
「不!」他聽見伊莉莎白在房間內大叫。「停下!」
斐瑞上前去開門,但門卻上了鎖,於是他改為拍門。「誰在裏面?伊莉莎白,你還好嗎?」
然後房裏靜了下來,過了一會,聽見伊莉莎白顫着聲回答。「我很好。」
「真的嗎?」斐瑞覺得單憑她的語氣很令人懷疑,還思考着是否要撞開房門。
然而他聽見房內傳來一陣匆忙的雜聲,不久門就被打開了,一個滿臉鬚根的中年男人走了出來,衣衫不整,滿眼紅絲。穿着睡袍的伊莉莎白也跟在他身後走了出來,但男人回頭看了她一眼便大皺眉頭,馬上拿了件晨褸替她披上並嚴嚴拉上前襟。
「斐瑞,這是我的文學老師,諾亞.海恩曼。」伊莉莎白替他們介紹。「諾亞,這是斐瑞.德桑。」
「現在是你的丈夫。」海恩曼酸溜溜地補充。
「親愛的,別這樣。」伊莉莎白肆無忌憚地捧着她老師的臉親了一口。「你知道我愛的是你。」
「幸會。」海恩曼只好裝模作樣地向斐瑞伸出手。
斐瑞伸手跟他握了握。「幸會。」他盡力擺出一個友好的笑臉。
但海恩曼毫不領情,只冷冷瞥了他一眼,便轉身跟伊莉莎白說:「那麼下次見。」
「下次見。」伊莉莎白送他走時,原只想禮貌地吻別,但海恩曼摟抱着她跟她深深地親吻,越抱越緊並跟她貼身磨蹭着,直吻得她忍不住發出呻吟,他才戀戀不捨地放開了她。
斐瑞一早別開了視線,依舊聽得滿臉通紅。
伊莉莎白終於送走了海恩曼,然後尷尬地看着斐瑞。「抱歉,希望你不介意,我把鎖匙給了諾亞,讓他隨時可以上來。」
「啊,不會。」斐瑞為自己沒有感到一絲絲妒忌而舒了口氣,他這刻只想把自己的鎖匙也給愛德華配備一條,並想吻得他透不過氣來就像剛才那另一對示範的那樣。「看來他真的很愛你,很着緊你。」他笑了笑。
「有時候是覺得他妒忌心太強了。」她也笑了笑。「但他真的愛我。」
# # #
傍晚,斐瑞到後山去了。他非常非常想念愛德華,希望會在這兒碰見他。
遠遠看見愛德華就站在那棵大樹下沉思,斐瑞不動聲息地走近,然後在他驟不及防的當兒進行偷襲,一把吻住了他。
愛德華嚇了一跳,嘴唇慌張地張開了,讓斐瑞得以長驅直進,深入探索。他摟抱住愛德華,跟他熱情地磨蹭着,把他抵在樹幹上,腿迫進了他的兩腿之間,手從腰間摸到了臀部,一邊又探上了領口把那裏的鈕扣解開,撫摸裏面的肌膚。
愛德華最初被嚇着了,僵硬地任憑斐瑞擺佈。但很快他就投入進來,以斐瑞的大腿磨蹭着自己的硬挺,並拉出了他的襯衣下擺,好讓自己把雙手伸進去仔細撫摸。
斐瑞已硬得發痛,把愛德華夾在自己和樹幹之間推擠着,彼此磨蹭着對方的勃起。
「啊~」愛德華輕輕推開了斐瑞,終於找回了呼吸。
「我好想你。」斐瑞沒有放開他,只抵着他的嘴唇說完,又堵住了他的口。愛德華在他的嘴裏發出陣陣呻吟,每一下都直擊斐瑞的下體,他實在等不了,就在樹下解開了愛德華的皮帶,拉下他的褲鏈把自己的手伸進去,握住了愛德華火熱的硬挺。
愛德華捉住了他的手腕,顫着聲說:「我們在戶外。」
斐瑞興奮地抵着愛德華的肩膀,嘴唇就在愛德華耳伴:「後山鬧鬼,沒有人會來這裏的。」
「可是……」
「我已經等得太久了。」斐瑞沒有理會愛德華半推半就的掙扎,只是無法忍耐地吸吮着他的脖子,並解開了愛德華的襯衣讓他的吸吮途徑可延續到愛德華的胸前和肚臍。
愛德華只是倚着樹幹大口喘着氣,然後無力地輕抓斐瑞的髮絲,讓蹲下來的他把自己的分身含進去,吞吐着形成了一道閃閃生輝的水光。
斐瑞太懷念愛德華的味道和他在自己身下的反應了。現在這樣根本不夠,他把愛德華的長褲連內褲褪至大腿,然後從褸袋掏出潤滑劑,沾上了手指再把手指埋進愛德華的臀縫裏去。
天色早就沉下來了,暮色包裹着他們,就像愛德華緊緻的小穴包裹着斐瑞的手指。他知道要不是愛德華靠着樹幹,他早就站不住了。
當夜色降臨,星星都出來了,愛德華任由自己被斐瑞放倒地上。斐瑞把兩人的大褸舖在地上作氈子,讓已被斐瑞剝得半裸的愛德華躺在上面。斐瑞仍只是衣衫不整的程度而已,他急急解開褲頭把自己的硬挺釋放出來,然後提起愛德華的腿,把自己擠身進去,進入了那個他日思夜想的洞穴。
「我真的好想你。」斐瑞壓倒在愛德華身上,用力地抽插着他,然後嘴唇又回到愛德華唇上,探進濕潤的舌頭跟對方苦苦糾纏。
愛德華被堵住了嘴,只能緊緊抱住身上的人,兩條長腿圈在對方身上,然後隨着斐瑞抽插自己的節奏被操得上下晃動着。
後山的野草一直在生長,長度足以遮掩着兩人野合的身影。在夜色漸濃的夜晚,即使有人路過,也只會聽到一些可疑的動靜,而無法看見任何畫面,讓後山有一個等着找情人的寂寞鬼魂的傳說,更加迫真。
「叫出來!」斐瑞喘息着看向滿臉通紅的愛德華,只見他咬着唇隱忍着不發出任何聲響。斐瑞呼吸着他脖頸的氣味。「求你了!」
愛德華放開了自己的嘴唇,任自己隨着斐瑞猛烈的撞擊而發出羞人的呻吟和哭喊聲。他感覺他們淫穢的聲浪,就在這後山迴盪着、流傳着……
斐瑞的手指用力地掐進了愛德華的臀肉裏,相信力度會留下數天的瘀青。愛德華抵受不住自己的勃起無人照顧,於是一隻手伸到兩人之間,擼動着自己。但斐瑞一把捉住了他,把愛德華的雙手都釘在他的頭頂,讓愛德華感覺自己加倍脆弱。他看向斐瑞被色慾染紅了的臉頰,他那饑渴的眼神,還有下身粗暴的抽插,都令愛德華覺得他想把自己吞進肚裏去。
「我要把你操得射出來!」斐瑞嘶啞地說。他加強了力量和速度,並自然而然地在高潮蘊釀的當兒,張口咬住了愛德華的肩頭。
愛德華閉上眼睛,讓自己單憑感覺記住這一切——在荒野山頭晚間陰涼的微風、粗糙的雜草和泥土就在身下、他們大褸的氣味和躺在上面的觸感、壓在身上愛人的熱度、被操到地上去那種激情的快感和微微的麻痛,還有斐瑞咬住自己肩頭那陣又刺痛又感受到疼愛和着緊的古怪感受……
「咬大力點!」愛德華突然叫喊道。「咬我!」
斐瑞被愛德華色情的嗓音刺激得猛烈射了出來,但同一時間他忍不住張口深深地咬了進去,咬進了愛德華的血肉裏。
愛德華被這一咬,同時感覺到斐瑞把熱滾的精液都射進了自己體內,並持續地抱住自己打顫。於是愛德華也激烈地射了出來。
他們仍然糾纏在一塊,在大口地喘着氣,直到稍稍平息。斐瑞退了出來,躺到愛德華旁邊去,拉起身下的大褸欲包裹住半裸的愛德華。
「你流血了……」斐瑞嚇了一跳,想不到剛才自己那一咬,會令愛德華傷得那麼深。他伸手輕撫那旁邊的皮肉。「對不起。」他心痛極了,眼下沒有任何消毒工具,他只好把流下來的血吸吮掉,然後掏出手帕替愛德華按着傷口止血。
「我也咬過你一口,我們扯平了。」愛德華看着他,笑了笑。
斐瑞想起他們如何在那個漆黑的儲物室中第一次親密接觸,還有事後愛德華替他細心包紮傷口,即使剛經歷了一場目眩神蕩的激烈野戰,斐瑞仍是臉紅了。
愛德華撫着斐瑞的臉,把他這少年害羞的神態刻進了自己的記憶中。然後他捲曲起自己,埋進了斐瑞的懷裏。斐瑞用大褸包裹着他,但一隻手仍然可以伸進去,撫弄着愛德華赤裸的肌膚。斐瑞覺得自己很幸福,很心滿意足。他不知道愛德華把頭埋進自己的頷下,是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
愛德華從斐瑞來到之前就一直站在樹下,在想着他們再見面的光景會是如何,在斐瑞新婚之後。
愛德華不是傻子,他知道斐瑞不是同性戀,他知道斐瑞對伊莉莎白有性慾,這一切甚至在他們開始之前就已經一一證實過了。伊莉莎白是個嬌豔欲滴的美女,如今是斐瑞法律上的妻子,每天晚上他們都會孤男寡女獨處一室。斐瑞跟伊莉莎白互有好感,更是彼此的前度,而且二人都是性慾旺盛的年紀。愛德華親眼看見過伊莉莎白在眾目睽睽下主動色誘斐瑞,即使那時她只是做戲,她已有親密情人,但她一點也不害羞或猶豫。這一切一切加起來,足夠令愛德華感覺不安。
雖然,愛德華相信斐瑞是真的愛他,他相信斐瑞仍會為了他把持住自己。但他的意志被擊潰也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愛德華預計婚禮上漂亮的新娘和之後極度考驗忍耐力的新婚之夜,會令斐瑞慾火焚身。假如他在第一晚把持得住自己,也會在看見愛德華的第一眼把自己抑壓的慾望傾瀉出來。
就像剛才發生的那樣。前所未有的瘋狂和暴烈。
愛德華把苦澀吞嚥進喉嚨。他記得斐瑞說過,他最初想交女朋友,因為他對愛德華的慾望無處發洩。
「你點起了我的慾望,當我的慾望無處宣洩,只能找個替代品了。」這句話又在愛德華腦裏迴盪了。只是由沾沾自喜變成了百味紛陳。
他如今成了伊莉莎白的替代品了。
很好。新婚之後的初夜。
愛德華也感覺到劇痛,也落了紅。就像一個新娘。
愛德華想做斐瑞的新娘,跟他組織一個家。但這是這輩子都不可能的事。
「在想什麼?」斐瑞擁着愛德華,輕撫他背部的曲線,手又不安份地落到了他的屁股。愛德華感到斐瑞的手指又伸進了他仍然濕軟的小穴,在搗弄才不久之前留在那兒的濃稠液體。
愛德華心頭一蕩,突然又被激起了慾望——他們就是沒有明天的,他們是犯了「Labouchere Amendment」(嚴重猥褻罪)的罪人,只能得快樂時且快樂。
愛德華很想回到阿當、夏娃的伊甸園,在未吃禁果之前,人類還沒有犯罪的槪念。那裏人人赤裸,沒有罪惡感。於是他又伸手開始解斐瑞的襯衣鈕釦,他希望他們今次可以完全赤條條地再幹一次。以天為被,以地為床。
「你幹什麼?」斐瑞被愛德華的大膽和熱情嚇了一跳。但他沒有阻止他,而愛德華已經把他的褲子都拉下來了。「愛德華?」
愛德華也剝光了自己,然後腳就纏上了斐瑞。他抱着斐瑞,口唇在他耳伴說:「操我,再一次!」他的手又撫上了斐瑞的硬挺,那裏在愛德華的挑逗下早就重新豎立起來了。
沒有人能拒絕這樣的一個愛德華。
於是斐瑞一個翻身把愛德華按倒,再次壓在他身上,把自己的一部份再次深埋進去,進入他愛人的體內。
# # #
斐瑞把新配的門匙給了愛德華。他覺得很開心,覺得一個新天新地正在眼前等着自己——一個可以跟喜歡的人自由歡好的空間,一個堂皇的藉口完美地瞞騙了世人的眼睛。
他哼着歌把大門打開。現在已經很晚了,他想伊莉莎白也許已經入睡了。
然後大門打開之後,斐瑞驚呆了。只見血水流了一地,快要滲出門口了。
他沿着血路走,在沙發後面發現臉色蒼白的伊莉莎白,正捧着自己的肚子,驚慌失措地坐在地上,坐在她自己的血泊之中。她的睡袍,早就染紅了。
她惶恐地望向斐瑞,伸出手。「救……救我!」7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CdGATkZ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