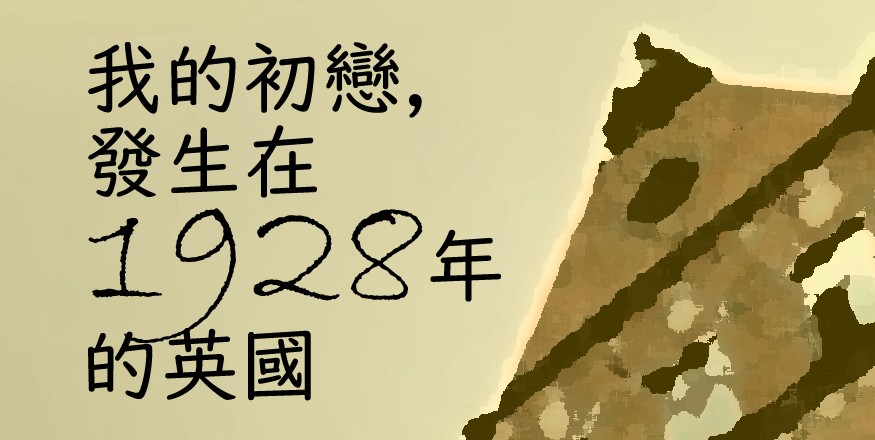伊莉莎白跟斐瑞由謾罵轉為冷戰,她不在家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到後來甚至提着行李離開,也許打算跟哪個打得火熱的姘頭住到一塊兒吧。斐瑞也樂得家裏清靜下來,他們真的相處不來。正好趁這個時候,好好整理自己,讓舊日污煙瘴氣的糊塗帳翻過一頁,他該好好重新做人了。
每個月跟愛德華的公事聚會,是斐瑞感到既難捱但又暗暗期待的一天。他不會再奢想他們之間能再有什麼,只是再見愛德華一面也是好的。他喜歡投入工作時的愛德華,那個深思着的冷峻側面透示出他的智慧,他的冰人模式讓斐瑞感到熟悉又親切。唯一讓他鬧心的部份,只是那個叫瑪麗蓮的秘書偶爾的出出入入,和愛德華那種只有在她面前才表露出來的調情腔調。
幾個月下來,他們現在就好像一般的上司和下屬的關係。斐瑞仰慕和敬佩愛德華,沒有其他了。國難當前,也容不下更多的什麼,他們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敵人的攻擊開始了,戰事越來越頻繁和猛烈,老弱婦孺都到鄉郊避戰去了,壯健男丁都去了參軍,倫敦市面一片蕭條萎靡,只餘一些偷雞摸狗的污合之眾在趁火打劫。蘇格蘭場在這當兒,就要幫助政府把市內的治安和秩序整頓好,以維持國家的運作和體面。
眼見愛德華為了國事終日在辦公室埋頭苦幹,因精神長期繃緊而容顏憔悴、滿臉鬍渣的樣子,斐瑞更感到自己應該多出一分力,能多幫一個人就要多幫一個人,好分擔他上級的重擔。
事實上這段日子,斐瑞率領蘇格蘭場眾手足東奔西跑,的確幫助了許多無助的市民。他們把老弱婦孺帶到收容所,替他們找到派發食物用品的慈善團體,還把一批想避難的人送上火車。他們將一些宵小之輩繩之於法,關進監牢裏,以免他們再去騷擾侵害倫敦市民。他們把因戰爭而受傷的傷者送往醫院,把被頹垣敗瓦圍困的市民救出,並四出巡邏以給被戰火嚇怕的同胞重建信心。
罪案並不會因為打仗而停止發生,因此他們仍是有查案的時候。因着兵荒馬亂的時勢,環境證供很易遭受破壞,證物和證人越發難尋,導致破案率低下。而這時候,在那堆無賴遊民當中,據說冒起了一名叫作查理的搗亂份子。別組的警員早就領教過這位查理的胡作妄為,並叮囑其他手足要小心此人,因為聽聞倫敦一帶的流氓都對他言聽計從,是名影響力很大的危險人物。
但斐瑞第一次見到查理,對他的觀感卻跟聽回來的很不一樣——查理比他想像的年輕、瘦弱很多,簡直像個營養不良的中學生,一點不像是眾流氓的首領或話事人。而且他很髒,比一般流浪漢還要蓬頭垢面,一頭又長又卷的凌亂黑髮連眼睛都遮蓋住了。他也比傳聞的講理,往往只是在案發現場指指點點,提示辦案人員遺漏了的地方,並不是意在騷擾或破壞。雖然他的態度的確跟傳聞中的一樣盛氣凌人,一副目中無人的狂傲模樣,但他的說話也不只是一味胡扯,斐瑞發現跟隨他的指示往往會找到破案關鍵。
斐瑞開始留意這個年輕人,暗自打算將來有機會的話,或許可以讓查理參與到他負責的案件中來。
但查理還是被逮捕了,罪名是吸毒及身藏違禁藥物。由於他的骯髒外表和臭氣薰天的體味,蘇格蘭場的警員都避之則吉,於是斐瑞得嘗所願接手了問話的工作——他承認他是有點私心,他喜歡這位富有偵探頭腦的年輕人,而且查理的狂傲令他想起了中學時代的愛德華。在這個紛亂的大時代,替國家挽救一個年輕有為的靈魂,怎也比把他迫上歪路一去不返的好。斐瑞希望能跟這位查理好好談一談,或許他能把查理引上正路。
「你這個模樣,會把你經過的地方都變成垃圾場。」斐瑞在羈留室對仍因嗑藥而神智不清的查理說。「所以請恕我冒犯了。」他拿出一把剪刀,二話不說就開始把查理頭上過長的頭髮剪掉。
「喂,你幹什麼?!」查理才反應過來,拼命掙扎,但受藥力影響而且體質瘦弱,始終不夠斐瑞大力。「你這混蛋!停手!」
斐瑞快手剪完了,又拿過來就近的一條消防喉,一開水就往查理身上猛噴。
「操你娘的!幹什麼鬼?快停下!」查理瞬間被猛烈的水柱噴得渾身濕透,情急之下雙手抱胸,人也清醒多了。「你這狗糧養的死警察,要幹什麼?!」
「你——難道是……」教斐瑞呆住的是,查理寬鬆的衣服因為濕透了而黏在身上,令「他」苗條的身材曲線展露無遺。「——是個女孩子?」
「操你娘的女孩子!」查理仍在罵,但感覺很是心虛——她的聲線是一種低沉的中性嗓音,說話時也故意壓低嗓子故作粗豪狀,說是男生是可以,但一但認定是女生,也不是不行的。
為免她尷尬,斐瑞也不好說些什麼,只是把一疊乾淨衣服和毛巾拋給查理。「換了它,假如你想離開的話。」說罷他就轉身離去並帶上門,並確保她換衣服期間沒有外人進去。
# # #
「這簡直難看得要死!」查理似乎對自己的新造型非常不滿,一看見斐瑞就投訴過沒停。「你不能把人當作是羊,我的頭髮不是羊毛可以給你亂剪的。還有這身衣服一點兒品味也沒有,簡直是年度最差配搭,給狗穿狗也會跑掉。」
「難道你之前的乞丐流浪漢造型會更有品味?」斐瑞只覺好笑。
「至少那是我的選擇,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查理說。「這國家怎麼了?變極權統治了嗎?市民穿什麼留什麼髮型都沒有自由了?」
「自由的前題,是你沒有影響到別人的權益。很明顯,你身上的臭味和外觀已經達到影響市容和污染環境的地步。」斐瑞說。「而且你已經被捕,一個罪犯是沒有人身自由的,這是常識。」
「還沒被定罪以前,所有疑犯都被假定無罪,這才是常識。」查理一臉不屑。「諒你這死警察也不會明白何謂法治的了,因為我見過的警察,全都智商零蛋,毫無常識。」
「好了,不跟你胡扯了,以下是錄取口供環節——閣下有權保持緘默,但所講說話,將被筆錄及成為呈堂證供。姓名?」
「雪莉.莫法特。」
「什麼?」斐瑞以為自己聽錯了。
「S-H-I-R-L-E-Y,雪莉,M-O-F-F-A-T,莫法特。」查理翻了翻白眼。「廿六個字母學會了沒有?要不要握着你的手教你寫字?」
「只是……你的姓氏有點冷門。」斐瑞不動聲色,想先套取雪莉的口供才再作打算。「年齡?」
「18。」
「你還差三年才成年,還沒有完全的自由權利,你的監護人呢?」
「死了。」
「先旨聲明,給假口供是犯法的。」
雪莉翻了個白眼。「母親獨自到蘇塞克斯避戰去了。有個一早斷絕了關係的兄長,我也不知道如何聯絡他。所以在倫敦,我只是一個人,沒有任何親人朋友。」
斐瑞完全想像不到,雪莉怎會弄至如斯田地,而她哥哥跟她又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要幫助雪莉,也許不用急於表露自己認識他們兩兄妹的實情,先獲取她的信任才是首要任務。
「你被捕時人贓並獲,並有警員作證,因此罪成機會很大。但由於你是初犯而且未成年,只需接受警司警誡就可保釋回家。問題是你的監護人好像都無法前來保釋你?那麼你想在羈留室留宿嗎?」斐瑞看見雪莉臉有難色。「抑或我們來個交易?」
「什麼交易?」雪莉警戒地看着他。「你要錢?」
「不,我只是要你合作。」斐瑞說。「我知道你很愛在案發現場流連和對現場的蛛絲馬跡發表意見,你想做警察?」
「不,我只是喜歡偵破犯罪案件。」
「你希望之後仍有這種機會嗎?」
「你讓我繼續出現在犯罪現場?」
「只限我負責的案件,我樂意聽聽你的意見。」斐瑞見到雪莉的雙眼頓時發亮。
「條件是?」
「讓我做你的暫代監護人。你知道警司警誡不用留案底?但需要接受警方和監護人監察直到成年。我可以一人分飾兩角,一併擔當這兩個角色。」
「那麼我要怎麼做?」
「假如你很不滿意你現在的衣著和髮型,我可以陪你到城裏去再弄一次。」斐瑞笑了笑。「但你此後要依時向我報告行蹤和動態,最重要的當然是——不可以再濫藥。」
「你有案件會通知我?」
「看你表現而定。」斐瑞頓了頓,加重語氣。「要是你給我抓到再次犯事的證據,我可以即時把你再關進羈留室!」
# # #
斐瑞一直在愛德華工作的辦公大樓門外徘徊——他是來過許多次沒錯,但沒有預約卻是首次,斐瑞也是頭一次以私人身份到來。他不知道這樣子是否恰當,但又覺得自己有義務向舊友報告一下他離家出走的妹妹的行蹤。但愛德華事務繁忙,他是否有空接見自己?或者自己在這兒等待,是否有等得到愛德華下班的一刻?
在斐瑞猶豫之際,愛德華混雜在下班的人群中出來了。當愛德華第一眼看見他,斐瑞發誓他看見了一絲錯愕和不知所措在愛德華臉上閃現,但只一秒間,愛德華就把冰人面具重新戴上。
這會是夕陽映照下的錯覺嗎?
他們只是站着,中間隔着下班的人流,遙遙對望,彷彿疑惑自己應否向對方走過去。
也可能只是斐瑞覺得時間變慢了。可能只是一會兒,愛德華就走到他面前來。
「你在等我?」
斐瑞努力抑制着臉紅的衝動,畢竟已是個大男人,但仍帶點靦腆神情。「是的。你下班後有空嗎?」
「我……原本有個約會。」愛德華尷尬地看了看錶。
「不會阻你太久。」斐瑞趕忙說。「只是有些突發事情,想要知會你一聲。」
「好吧。」愛德華說。「你跟我來。」
不一會,一輛黑色轎車就停在門前,愛德華請斐瑞先上車,然後也進入車廂跟他並排而坐。
斐瑞痛恨自己仍像個少年人,竟因跟心儀對象並排坐而心跳加速,他只能騙自己說那是因為暈車浪——但這種感覺很久沒有了,他好像回到十多歲,感到自己又活過來了。
「你太太不會等着你回家吃晚飯嗎?」愛德華故作輕鬆地跟他閒話家常起來。
她早跟漢子跑了,斐瑞想回答,而且一個忙於偷漢子的妻子又怎會有空去為丈夫煮晚飯呢?但這樣說好像有點突兀,也不符合一般成年人社交的體面原則。於是他改口:「她為了避戰,去了鄉間投靠親戚。」
「哦。」
「所以家裏就我一個人了。」斐瑞勉力笑了笑。
「可惜早約了人,不然可以請你吃頓飯。」
「下次吧。」
言談間,轎車已抵達一所名叫哀綠綺思的俱樂部門前。愛德華把斐瑞帶到了一間書房模樣的房間,請他坐下。
「要來一杯嗎?」愛德華徑自斟起酒來。
「好的。」斐瑞一邊觀察着,發現這裏似是愛德華的另一間辦公室,因為書桌上堆滿了文件,還有標記着符號和小旗的地圖和地球儀。愛德華把酒杯遞給他,他接過。「你還真辛苦啊,工作忙過不停。」
「非常時期嘛。」愛德華苦笑了一下,搖了搖手中的酒杯。「好了,是什麼事?」
斐瑞吞嚥了一下,感到有點難以啟齒。「雪莉還好嗎?」
「她……」愛德華猶豫了一下。「她跟媽媽回了老家避戰,我想她還不錯?老實說,我已經很久沒回過家了,我想她能照顧好自己。」他聳了聳肩,然後呻了口酒。「她是我的天才妹妹呀。」
「她離家出走了。」
「什麼?」好一會兒,愛德華才反應過來,然後他看着斐瑞。「你說什麼?」
「她昨天被逮捕了,被關到羈留室,是我問的話。」
「什麼?」愛德華真的很震驚,他平時不會重複自己的說話。「她犯了什麼事?」
「吸毒。身藏違禁藥物。」
愛德華只是張口結舌地、怔怔地看着他。
斐瑞真的擔心起來了,他拍了拍愛德華的手背。「愛德華?」
愛德華慌張地望着斐瑞,表情跟雪莉小時候失蹤那次一模一樣。
「深呼吸,鎮靜點。」斐瑞按揉着愛德華冰凍的手掌。「她沒事,我有好好照顧她。」
「告訴我詳情。」愛德華無助又無力地看着斐瑞,並用力捉緊他的手,像抓緊一條救命稻草。
於是斐瑞把事情始末一五一十告訴了愛德華。包括雪莉現在混的地方有多污穢不堪、她那身附帶惡臭的女扮男裝流浪漢造型,而且沾染了不良嗜好已好一段日子。也包括雪莉驚人的觀察力和偵探頭腦、斐瑞已帶雪莉到城裏理了髮和添置了新衣並給了她一點零用傍身,但雪莉說什麼也不肯告訴斐瑞她的住處也不肯讓斐瑞替她租住房間。斐瑞暫時只能讓雪莉答應會準時向他報到,而他為了贏取雪莉的信任,也沒有顯露自己是他哥哥的舊相識。
「我要去找她。」愛德華馬上站起來,就要衝出去。「把她鎖回家!」
但斐瑞拼命拉住他。「那只會弄巧反拙!她連被捕了也不願找你來保釋,又怎麼會讓你干涉她的生活?」
「我就算用繩子縛着她,也不能讓她再胡作非為下去!」愛德華非常衝動,斐瑞只能用雙臂捆住他。
「她已經是個大人了,你不能再這樣專制!」
「我是他家長,我就有責任來教好她!」
「愛德華!你們不能再硬碰硬下去了,雪莉是個吃軟不吃硬的孩子,你這樣只會毀了她!不要重蹈你媽媽的覆轍!」斐瑞感到愛德華在他懷中僵住了,停止了掙扎。於是他繼續勸說。「你妹妹是個人類,不是國家政策,不能讓你隨心所欲地進行規劃。即使你的出發點再好,你為她設想的一切都對,但人不是數學公式,不是算對了就能跟着走的。那孩子好不容易才找到查案這個興趣,你應該讓她好好發展,讓這個好的興趣去代替壞的那個。即使你對她期望再高,為她安排的道路再好,也未必是她心裏想要的,你強要她遵從你的安排只會引來更大反彈。你就不能相信她一次嗎?」
愛德華靜默下來。斐瑞才意識到自己的姿勢近似在摟抱着愛德華,彼此都能感覺到大家的呼吸心跳。他正疑惑着是否可以放開愛德華時,發現愛德華正微微發着抖,直到他聽見他連牙關都打起顫來了。
「愛德華?」斐瑞懷疑愛德華又病發了,一邊搓揉着他的臂膀一邊抱緊了他。「好點了沒有?」
愛德華在斐瑞懷中開始發軟和抽搐。斐瑞抱着他,焦急又無助,一切仿似在重演,斐瑞在愛德華身上摸索着找藥,然後在他的內袋找到藥片給他服下。愛德華就在他懷裏喘息呻吟着,滿頭大汗。斐瑞告戒自己感覺不該那麼飄飄然,但他看着懷中病人微啟的嘴唇,就情不自禁想要幫他進行人工呼吸。
「你在幹什麼?」愛德華虛弱地問,手無力地抵住斐瑞。
「我……」斐瑞覺得昏頭轉向,只想吻下去。
愛德華在這時握住了桌上的搖鈴,搖響了它。
房間內一個書櫃竟然動了起來,原來那是一扇暗門,通往跟這間書房相連的一間暗室。一位身穿晨褸、像剛睡醒的男子從裏面出來——要斐瑞形容的話,他會說那男子長得像是年輕版的自己,就像自己剛進警校時那個模樣。
「莫法特先生?」男子詢問。
「扶我回房間休息。」愛德華向那男子說。
於是男子上前,從斐瑞手上接過愛德華,把愛德華的手臂繞過他的肩膀,扶着他向暗室走去。
「你先回去。」愛德華回頭跟斐瑞說,接着點頭致意。「雪莉暫時拜託你了。謝謝。」
斐瑞看着那男子親熱地摟抱着愛德華,然後二人消失在那組書櫃後面。他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忐忑不安又妒嫉痛心的感受——那個人實在太像自己了,而且他表現得跟愛德華關係非比尋常。在暗門打開的一瞬,斐瑞隱約瞥見裏面極度昏暗,像是一間睡房的佈置。而那個人身穿晨褸。
難道說,愛德華跟那個人有着什麼不足為外人道的曖昧關係?而那個人那麼像斐瑞,是否意味着,愛德華對斐瑞仍有點什麼情意結?
斐瑞靜靜地站着,想聽聽裏面是否會傳來什麼聲響,但最後什麼都沒聽見。
# # #
再見愛德華,是半個月後的黃昏。當斐瑞從警署出來,正準備下班回家,那輛小黑車就在路旁等着他。
「我已經暗地裏調查過舍妹的情況,承蒙你的關照,我知道她的表現已經大有改善,並參與到蘇格蘭場的案件中去。」當斐瑞坐進車裏後,愛德華就對他說。
「對,雪莉她很厲害,已經連續替我們破解了兩宗一直膠着的案子。」
「可是,她仍然在沾染那些惡習。」
「哎……」斐瑞慚愧地垂下了頭。「我一直在軟硬兼施地勸她,但她以乎被什麼事情困擾着,只要一沒了有趣的案件,她就沉溺不已,無法自拔。」他看了看愛德華。「你覺得是不是尋求專業協助比較好?」
「專業協助當然較恰當,但你上次也說得很對,我怕硬來會惹來她更大的反彈和反感。」愛德華沉吟半晌。「她還未知悉你的身份?」
斐瑞搖了搖頭。
「我希望你可以親自幫助她。」愛德華看着他,接着從外套內袋掏出一張沒寫銀碼的支票,遞給斐瑞。「當然我會支付你全部開支,也會提供專業的咨詢援助。」他再把一張卡片交到斐瑞手上,上面印有一名戒毒專員的姓名和聯絡方法。
斐瑞皺了皺眉,把支票交回愛德華手上。
「我知道這麻煩了你,但難得雪莉信任你……」愛德華為難地看着斐瑞。「我真誠的希望你可以予以考慮。」他把支票推回來。
「你在用上級的身份命令我嗎?」斐瑞問。
「不是,我……」
「那麼,這個別提了。」斐瑞把支票撕碎。「我照顧雪莉,因為她是你妹妹,而你是我朋友。」他望着愛德華,看見愛德華眼中有點什麼一閃而過。
最終他們相視一笑。
「謝謝你。」愛德華說。
「不用謝。」斐瑞回答。「可是,你們關係到底怎麼會變成這樣?雪莉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愛德華在搜索着詞彙。「我們的關係在海外已經很惡劣,都怪我工作太忙,無暇顧及她的成長——我不是個稱職的好哥哥。」他苦笑了一下。「然後在香港的時候,在她就讀寄宿學校的日子,她不知怎的跟一名來自英國的兵哥搭上了,並且打得火熱,也許可以用難捨難離來形容。」
斐瑞瞪大了眼,想不到反叛、邋遢的雪莉原來也有這樣的一面。他當然也想到自己跟愛德華就讀寄宿學校時那段難捨難離的過去,莫法特家相隔十歲的兩兄妹竟然都有着相似的情史,真令人感到不勝唏噓又仿如隔世。
「但那位派駐香港的兵哥在英國已有一名妻子,我們母親對這種關係的立場你應該不會陌生。」愛德華頓了頓。「所以雪莉經歷了我和母親的留難,後來因為打仗我們一家都回到英國來了,而她的心上人仍然留在香港。」
斐瑞為雪莉的經歷感到心痛,為跟愛人分隔異地的痛苦感到深深的共鳴。他看着自己曾經的心上人。「你說,你也跟你的母親一起,阻止他們的戀情?」
「人家是有名份的關係,難道你叫我支持妹妹去當別人的第三者,去破壞別人的婚姻嗎?」愛德華沒有迴避跟他對望。「而且我妹妹還沒有成年,跟男人未婚私通是不道德的行為,不管在英國,或者英國的殖民地。我跟媽媽都不會希望雪莉做出這種事情。」
斐瑞張口結舌。
「那個人在認識雪莉之前是有老婆的,卻背着妻子哄我妹妹跟他上床。」愛德華始終盯着眼前人。「你希望我怎麼做?鼓勵自己妹妹當一個有婦之夫的秘密情人?支持她為了一時激情,不惜去破壞別人神聖的婚姻誓詞?」
斐瑞開始搞不清楚,愛德華是不是借意在控訴他跟伊莉莎白的婚姻,或者闡明愛德華自己的立場,於是他急於辯解。「那個人愛着你妹妹的吧?也許他根本不想結婚?也許他不惜做違背道德的事,也想跟你妹妹一直在一起?」
「也許他只是跟雪莉玩玩,只想留一個美好回憶。」愛德華冷冷地說。「無論如何,客觀事實就是他跟另一個女人結了婚,餘生都會跟她廝守在一起。雪莉也從來沒有打算跟他認真,她也支持他跟妻子在一起,她是自願離開香港的,只是她一貫無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才導致了失控。」他終於轉開了視線。「莫法特家的人不該這麼失禮,因此她必須好起來,好維持家族的體面。」
那個冷冰冰、不近人情的冰人又回來了,斐瑞感到很心寒。「家族的體面比起個人感情更重要?你妹妹經歷的傷痛,難道你完全無動於衷?」
「對。情感是種不利因素。雪莉必須學會無動於衷,才會成熟起來,成為大人。這是她的成長一課。」
「你做得到嗎?對任何事都無動於衷?」
「嚴守禮節和社會規範,是一名莫法特的基本修養。」
「那麼那天從卧室出來,那名穿着晨褸的男子是什麼人?」斐瑞迫視着愛德華。「為什麼他跟我那麼像?」
「他叫亞瑟,是我的助理。」
「穿着晨褸的助理?」
「瑪麗蓮是我工作上的助理,亞瑟是我私生活的助理。」愛德華冷冷地看着斐瑞。「你也可以換個說法,叫他作有錢人的玩物。」
「玩物?」斐瑞瞪着他。
「用金錢買回來的消遣玩意。」愛德華續道。「一種不牽涉感情的性交易。」
「性……交易?」斐瑞完全沒想到他會如此坦白。
「但我不會讓你找到證據控告我的,探長。」愛德華說。「他就只是一時的秘密消遣,完全不會影響到莫法特家的聲譽,我跟瑪麗蓮也絕對不會讓他這麼做。」
斐瑞突然覺得愛德華手上的戒指閃閃發亮,刺得他目眩。
「很高興跟你會面,請恕我沒空跟你晚飯了。」愛德華替斐瑞打開車門,下了逐客令。
斐瑞收好卡片,點點頭。「我會聯絡這位專員,請放心。」他瞪着車上的人。「莫法特先生。」
斐瑞離開了那個令人窒息的車廂,頭也不回地走遠了。
他不知道愛德華一直躲在車窗後望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無蹤,才囑咐司機把車子駛走。6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K0mexpm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