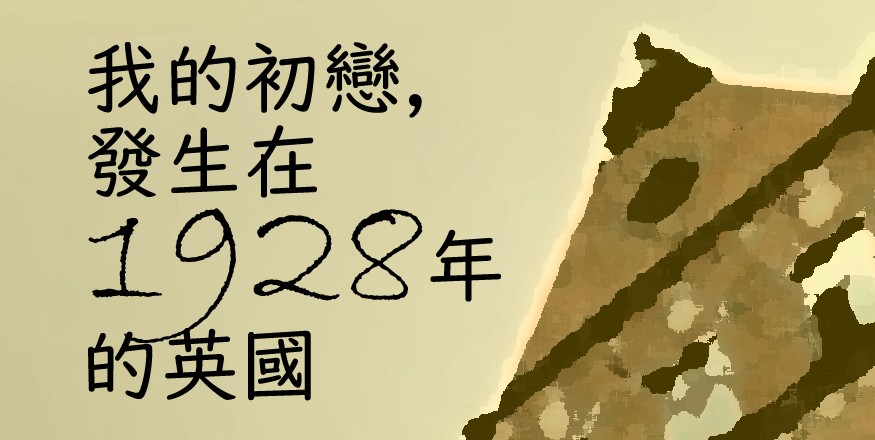1928年——好像跟往年沒有什麼不同的一個年份,只是今年斐瑞告別初中,升上高中了。10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NZPI7cLXO
由兒童踏入青少年的界線,人言人殊,尤其對於遲熟的男生更是如此,假如就讀的是所保守的英國寄宿男校,就更加難說了。但斐瑞十分肯定升上高中那年,他就步進了青春期,除了因為聲線開始變得低沉,偶然會長出兩顆青春豆,還因為他開始對性有了興趣。那是一段十分青澀羞怯的歲月,跟幾個性意識同樣剛剛甦醒的男同學一起,站到圖書館的生物科書架前,對着一張女性身體結構或性器官橫切面的插圖指指點點、嘻嘻哈哈,已是他們當時覺得最大膽、最淫穢的壞事情了。沒辦法,昨天還是個孩子,很難在一夜之間就長大成人。這就是個尷尬的年齡。
那一年令斐瑞最深刻的記憶,是學期初來了個插班生,他叫愛德華.莫法特,一個滲着貴族味道的名字。而且人如其名,他跟其他平民百姓總是格格不入,像個冷冰冰的用雪雕成的局外人,冷眼旁觀着一切,身邊的人和事都好像跟他沒有關係,他就活在自己的頭腦中。
斐瑞還記得當愛德華踏進班房,在班主任的介紹下,他冷冷地掃視了課室一圈,目光餘波瞥到了斐瑞——斐瑞跟那雙冰冷但彷彿馬上看透你的眼睛對望了兩秒——他感到自己心裏一震,不知道是因為感覺太冰冷令他心裏也要打個寒顫,還是尚有什麼別的古怪原因。總之他心裏之後一直恍惚着,像被什麼東西燙傷。
全班同學馬上竊竊私語,都在討論着愛德華,覺得他是個怪人,誰要是跟他坐一塊兒就倒楣了。然後班主任向斐瑞身旁的空位一指——天殺的!他就是那個倒楣鬼!一整個學年都要坐在這個冰人身旁嗎?那豈不是要冷傷風,說不定還會染上肺炎……
# # #
跟愛德華同坐了一個星期,斐瑞仍然健康良好,沒患傷風感冒也沒有得上肺炎。這並不是說愛德華熱情了一分一毫,他依舊是目中無人的冷傲非常,這可能只是說明斐瑞抵抗力良好。整整一個星期裏,冰人愛德華跟斐瑞說過的話,不會超過一隻手的指頭數目,而且都是毫無意義的「麻煩讓一讓」、「你的書本過了界」、「不,謝謝」一類。
這樣一個怪人當然不會受同學歡迎,事實上班裏較頑皮的那幫人正想方設法作弄愛德華,令他出醜人前。但不知怎地,儘管愛德華常常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看,就是個如假包換的書呆子模樣,但他的反應卻敏捷得像頭頂後腦腳底都各長了一隻眼,輕易避過了頂在門頂的粉刷,也沒有在座椅被人拉走時坐下,更沒有被攔在桌與桌之間的橡根繩絆倒。
這些特別為愛德華而設的陷阱都起不了作用,反而令不知情的班主任枉受無妄之災,先被門頂掉下來的粉刷弄得滿頭白粉,復被腳踝邊的橡根繩絆倒跌過四腳朝天。最後她大發雷霆,訓斥了全班一頓,還決定取消過往全班投票選班長的傳統,直接任命最守紀律的愛德華作為這一學年的班長,希望他能督促同學們遵守秩序。這個災難性的結果,令全班對愛德華更是含恨在心。
在斐瑞眼中,這一幕幕可算驚心動魄,他不敢想像要是開罪了全班的人是自己,他該怎麼辦,是不是唯有轉校自保?但冰人愛德華就是對這一切毫不上心,彷彿在他心裏有更重要的大事等着要辦,同學們的爭強好勝根本算不上什麼。
幸好愛德華對人那麼冷漠,斐瑞即使不跟他說話,也不會覺得自己加入了欺凌他的行列——為了自保他的確不能跟愛德華多說話,否則一旦被懷疑是愛德華的「朋友」,斐瑞可就水洗不清了,面前只有跟愛德華一同被欺凌一途——但他確實無意在愛德華身上再踹一腳,斐瑞雖說不上喜歡愛德華,但也不討厭他,反而不齒那些仗勢凌人、以多欺小的搞事者,但斐瑞卻又沒有勇氣作出反抗,不敢讓人知悉他有跟大伙兒不一樣的想法。
自開學以來,斐瑞就在暗自擔心愛德華但又忙着與他撇清關係的心理交戰中渡過,都忘了關心一下自己的室友山姆一直處於感冒狀態,並且持續不癒。直到山姆身上長出了皮疹,再在隔天轉變成膿泡,校醫才診斷出來那可不是感冒那麼簡單。
# # #
「太恐怖了,那樣子簡直像地獄來的惡魔……」
「好噁心啊,只是聽聽別人的描述,我就想吐了……」
全校都在對山姆的病情議論紛紛,因為那是一種在英國日趨罕見的烈性傳染病——天花。1798年,天花曾經在英國奪去了八萬條性命,然而自1842年起,英國的學童普遍都會接種牛痘,成功阻止了天花疫症的傳播。而山姆卻是萬中無一的不幸個案,他的父親是派駐印度的外交人員,他在印度出生,到就學年齡才回來英國入讀中學,所以從來沒有接種過牛痘。想來他身上的天花病毒,就是在暑假時到印度探望父親時傳染上的。
由於這傳染病殺傷力驚人,患者外表可怖,且民間流傳着太多這惡疾的恐怖傳說和歷史,不管校內大多數學生其實早已接種牛痘,全校仍是人心惶惶,家長都恐怕孩子待在學校不安全。校方唯有把山姆的房間封鎖,並把附近所有設施徹底清潔消毒。
於是斐瑞理所當然不會再住在那個房間,他被遷移至一個無人入住的新宿位——竟然是愛德華的隔鄰床位!
「嗨,想不到又做了你的隔鄰。」既然房間內只有兩人,斐瑞終於有膽跟愛德華搭訕了。
但愛德華只是冷冷瞥了這位新同房一眼,又埋首到自己的書本中去了。斐瑞唯有嘆息一聲,自顧自的把行李收拾好。
# # #
斐瑞猜不到的是,山姆的病情急轉直下,再也沒法回到這所學校,跟這裏的師生再說一句話。
他更猜不到的是,現在人們看他的眼神,比望向愛德華的更厭惡疏離——就因為他曾跟山姆同房,他們都怕斐瑞會染上天花,再傳染給其他人。
「白痴。」愛德華難得吐出一句評語。
「什麼?」斐瑞對愛德華主動跟自己說話有點受寵若驚。
愛德華翻了翻白眼,繼續低頭看書。「全部都是小丑魚。」
「我不明白。」斐瑞靠近一點希望愛德華能進一步解釋他的說話,順道偷看他到底在看什麼書。然後斐瑞碰到了愛德華的手肘,愛德華突然像觸電般把手甩開。
「哦,對不起。」斐瑞也退開來,靦腆地。「我知道大家都怕我會傳染。」他沮喪地以為連獨一無二的愛德華也誤信謠言排擠自己。
「不。」愛德華有點不好意思,重新靠過來把手輕輕搭在斐瑞肩上。「只是我不習慣被人入侵我的私人空間,不是嫌棄你,請別誤會。」
「哦。」斐瑞怔怔地望着愛德華。「你跟我說過最長的一個句子。」
愛德華再次翻了翻白眼,捲起了自己的衣袖。「大家都接種了牛痘,還怕傳染什麼的有沒有常識?」
斐瑞捲起衣袖發現自己臂上也有相似的疤痕。「這個疤就是牛痘?」
愛德華復又坐下,回首書本中。「沒知識的也該到圖書館去翻翻資料吧,一群白痴!」
「那什麼是小丑魚?」
「整天渾渾噩噩,口部開開合合,不用思考,只會吃魚糧——不就是那幫人的寫照麼?」愛德華一本正經的解釋。「小丑就是只會插科打諢,成不了大事的角色呀!」
斐瑞被愛德華生動形象的形容逗笑了。愛德華轉頭瞪了他一眼,好像不太習慣有人因為自己的說話而發笑。
「其實你也不盡是個冰人。」斐瑞笑說。「你還會發火呢!」
愛德華皺起眉頭。「什麼冰人?」
「小丑魚們給你起的綽號啊!」
「無聊!」
「誰叫你整天撲克臉,態度冷冰冰的。」斐瑞說。「就不能輕鬆一點,開開玩笑嗎?」
「我從不說多餘的話,不做多餘的事。」
斐瑞只好再次嘆了口氣,並告訴自己,今天冰人破天荒跟他說了那麼多話,已經是創世紀般的大進步了。
# # #
死亡對於這個年紀的青少年來說,本該遙不可及,斐瑞從沒想過會這麼快就出席同齡人的追思會。
只是在學校禮堂舉辦的追思會,不是親身參加的葬禮,因為大家對這個病仍然太過忌諱,山姆的遺體被匆匆火化下葬,紀念儀式只是象徵性地做做樣子。太可悲了,一個年輕的靈魂,就這樣遭受冷淡的對待,倉促告別人世。但斐瑞也沒有太多餘力去悼念他的前室友,他倒是該先替自己着急,他被全校孤立已經兩個星期了。
青春的生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不是該活潑樂天,快樂無憂的嗎?怎麼會跟疾病、死亡、孤獨、恐懼這些連在一起,這些應該是成年人、老年人去擔心的問題。斐瑞從來不是個愛思考的孩子,他情願把時間花在戶外活動和跟朋友吹牛開玩笑,一班人圍在一起起哄湊熱鬧才是他最愛幹的事。他從來都是個合群的人,身邊總是圍繞着一群豬朋狗友一起嘻哈玩樂,雖然沒有一個算是深交知己,但他總不愁寂寞。怎麼玩伴們可以統統一夜之間說變就變,翻臉不認人?
唯一跟斐瑞仍有眼神接觸、肯開口講兩句話的人,就只餘同房兼同桌的愛德華,他們甚至有時會有不經意的輕微身體接觸,像是擦身而過,或拿東西時碰到手肘之類。斐瑞仍然擔心愛德華會介意這些觸碰,只是二人交集的機會太多而難以避免。但愛德華雖然表現拘謹,卻沒有再像上次那麼大反應,就像為了叫孤立無援的斐瑞放心,愛德華壓抑了自己的本能反應去接受這些觸碰。斐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多了,平常的他一定不會想得那麼深入,但現在他太閒了,除了觀察愛德華已沒有什麼可做,而愛德華這種心思和努力竟然讓他有點感動。
斐瑞當然還觀察到其他東西,像愛德華患有強迫症,他的東西必須要平衡地放置,只要有一點兒歪斜他必會忍不住伸手去改正。後來,可能他對斐瑞的戒心減輕了,他有時連斐瑞的東西也會忍不住手去改正,而斐瑞也會由得他——有個人替自己把東西弄得更方正整潔,何樂而不為?
至於愛德華在看那堆書,都是些讓斐瑞看一看封面便悶出鳥來的深奧東西,歷史、軍事、政治、文史哲等等都包含在內,愛德華就這樣可以整天一動不動背脊筆直地埋首在這堆書當中。而其中一本似乎令他百看不厭的,是本叫《君王論》的小書,愛德華把書頁都翻破了,簡直至愛不釋手的地步。
斐瑞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研究一個孤癖怪人竟然成了他唯一的娛樂和可做的事,這種日子還不知要過上多久。每天,他就行屍走肉地去上課、去飯堂,逗留儘量少的時間,免得要遭受其他人歧視的目光。其他時間他就像被判刑的罪犯回到監倉,只能悶悶不樂地跟沉默寡言的愛德華困在一塊兒。最慘的莫過於上體育課,這本來是斐瑞最愛的科目,但自傳染病疑雲發生後,根本就沒人肯跟他一組,他最後只能跟永遠落單的愛德華同組,而愛德華似乎是個極度厭惡運動的人,任何運動他都總是敷衍了事,令熱愛體育的斐瑞沒趣極了。
「你就不能積極一點嗎?」這天大伙兒在田徑場上熱身時,斐瑞終於忍不住問愛德華。
「為了什麼?」
「因為體育很好玩啊,大汗淋漓地舒展一下,令人身心暢快!」
愛德華露出噁心的表情:「冒汗已經夠噁心了,動來動去更不知為了什麼,浪費時間!」
「你整天窩在房裏,就不怕悶壞嗎?動一動,頭腦也清晰些吧!」
「錯!通常越是四肢發達的人,越是頭腦簡單。」愛德華意有所指地瞥了瞥斐瑞。
斐瑞翻了翻白眼,快被他氣瘋了。
就在這時,老師叫同學把熱身用的豆袋放回儲物室,因為要開始短跑和跨欄練習了。同學們把目光投向斐瑞和愛德華身上,示意不受歡迎的二人把這雜活幹了去。斐瑞嘆了口氣,認命似地彎身把散落地上的豆袋拾起。愛德華也樂得跑少一點,把斐瑞拾起的豆袋接了過去,便逕自往儲物室走去。被雙重欺凌的斐瑞覺得自己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運才落得今天這下場,把餘下的豆袋都撿起了,也跟隨愛德華走進了儲物室。
斐瑞不知道他的霉運才剛開始。當他們把豆袋都放回去,正要轉身回田徑場時,儲物室的門被卡嚓一聲關上了,連電燈也被關上。斐瑞摸黑前行,跌跌撞撞地找到門把手,卻發現外面被什麼東西堵住了,門根本推不開。
「該死的!」斐瑞這次真的憤怒了。「他們把我們關這兒了!」
但愛德華沒有回應。黑漆漆的儲物室裏,只有沉重急速的呼吸聲。
斐瑞擔心起來,呼喚:「愛德華?你還好嗎?」一邊摸索前行,希望找到愛德華的所在。
始終得不到愛德華回答,斐瑞循着呼吸聲走去,感到聲音越來越大了,現在他甚至感覺到愛德華的氣息就吹噴在自己的皮膚上,距離應該夠接近了,於是他伸出手。「愛德華,你到底怎麼了?」
「呀……嗯……」愛德華似乎想說什麼,但只能發出一些模糊的發音。
「愛德華?」斐瑞仍然在摸索,突然一隻汗濕的手緊緊抓住了他,嚇了他一跳。愛德華所在的位置很低,可能正坐在地上,於是斐瑞蹲下來,手摸索着撫上愛德華的肩膀,揉捏着希望他能放鬆下來。但斐瑞感覺到愛德華顫抖得很厲害並且一片汗濕,呼吸也越發不順。「告訴我,什麼事?」斐瑞掃過愛德華的背部,只覺他的運動衣都被冷汗浸濕了。
「……藥。」愛德華極努力才能口齒不清地吐出這個字。
「在哪兒?」斐瑞焦急問道。但愛德華根本回答不了他,牙齒開始不受控制地磕磕碰碰,四肢更抽搐起來。斐瑞很害怕,怕愛德華傷到自己,他曾聽說過有人就這樣活生生把自己的舌頭都咬了下來。他只好把愛德華按在地上,盡力壓制住他的活動範圍,一隻拳頭伸進他口裏讓他咬着,然後也顧不上禮儀,另一隻手拼命在他身上摸索,翻找每個明暗口袋,希望找到愛德華說的什麼藥。
斐瑞從來沒有跟誰有過這麼親密的接觸,他心裏感到很尷尬,更不願細想漆黑中自己到底摸錯了哪些讓人臉紅的地方,身下在掙扎的還是那個嚴肅正經的愛德華……但他不能細想,救人要緊!他再磨磨蹭蹭的,怕愛德華快要窒息了。
「哇!」被愛德華咬得很痛,斐瑞的手想來已經在流血,但他沒有把手抽出來。「找到了!」斐瑞興奮地說。他翻出了愛德華的錢包,並在裏面摸出了一排藥丸,然後取出一顆塞進愛德華的嘴裏。
愛德華吞了下去,但他仍在抽搐啊!斐瑞拼命按着他,然後愛德華猛烈地抖動了一輪,就靜了下來。
「愛德華?」斐瑞輕拍他,發現他失去了知覺,大驚。他摸上愛德華汗濕冰冷的臉龐,探了探他的鼻息,幸好尚未斷氣,但也氣若游絲了。
斐瑞突然無名火起,震怒於那班無知的欺凌者,要是愛德華出了什麼事,他們真是難辭其咎。他站起來,走回門口,大力拍打着門,大叫:「救命啊!有沒有人?我們被鎖在裏面。有人昏倒了!」但沒有回應,就好像這麼大的一所校園,所有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斐瑞和愛德華兩人相依為命。「救命啊!有沒有人?」任斐瑞如何聲嘶力竭,根本就沒有回應。
斐瑞只好頹然回到愛德華身邊,再度檢查他的狀況,摸上去他遍體冰涼,一動不動,真的變了個名符其實的「冰人」了。斐瑞心裏一慌,擔心愛德華會就此死去——想起來,當初何嘗不是以為前任同房山姆只是普通感冒,又怎想到他會就這樣死去。假如現任同房愛德華今次又遇上不幸,那斐瑞不是成了名符其實的「瘟神」了嗎?
斐瑞努力回想他學過、目睹過的任何急救辦法,終於被他想起了人工呼吸這招。尷尬是難免的了,幸好這裏伸手不見五指,另一個生物更是處於昏迷狀態——不,他真的要停止胡思亂想趕緊開始了,不然另一個生物恐怕快要變成死物了。
斐瑞沉下身子,深吸一口氣憋着,移向他以為是愛德華嘴唇的地方——但碰壁了,他的嘴降落在愛德華的頸窩,滿口滿鼻都是愛德華的味道,斐瑞嗆住了。
斐瑞搖搖頭鎮靜自己,再接再厲,向上緩緩移動,又意外地親了愛德華的下巴一下,才真正找上了愛德華的嘴——他再深吸一口氣,對住愛德華的嘴吐進去,重復地,他一邊用手按下他的胸口,一邊吹進氧氣。
大概一兩分鐘後,愛德華動了動——該死的,他的嘴唇動了動,擦過了斐瑞壓下去的嘴唇——斐瑞渾身顫了顫,媽呀,那可是他的初吻呢,竟然給了愛德華!
「愛德華?」壓下尷尬的感覺,斐瑞詢問愛德華的情況。「你還好嗎?」他拉住了愛德華的手,發現仍是那麼的冰冷,但愛德華已能輕輕回握他。
「呃……」愛德華聲音微弱,於是斐瑞低下了頭,把耳朵湊到他嘴唇上面——該死的,愛德華微啟的嘴唇又擦過了斐瑞的耳廓,讓斐瑞又打了個寒顫。別再讓愛德華碰到他的耳或臉,因為它們現在一定熱得像火燒。
「你需要什麼?」斐瑞硬着頭皮問道。
「好冷……」愛德華只是吐出了這些字。
當然冷了,他的衣服都被冷汗濕透了,他現在又是弱不禁風的時候,這樣下去說不定會得肺炎。斐瑞左思右想,無論多麼尷尬,他也要把他想到的暫緩方案說出來。
「把你的衣服都脫了,它們都濕透了,會生病的。」斐瑞說着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塞給愛德華。「先穿上我的。」
黑暗中愛德華似乎在動,但斐瑞不知道他是否正照着自己的話去做,這裏太他媽的黑了。斐瑞心裏正詛咒着,手插進褲袋,卻摸到了些什麼——是暑假時,跟幾個豬朋狗友到河邊去偷偷學抽煙的殘留物——一盒火柴,和一包抽剩一支的香煙。
斐瑞沒有細想,隨即啪一聲劃着了一根火柴,短暫地照亮了齷齪的小儲物室,讓他看見了正在脫掉運動上衣的半裸着上身的愛德華。
「啊!」斐瑞呆了呆,被自己拿着的火柴燒到手,於是他馬上把火柴丟了,火光又熄滅了。「原來我有一盒火柴。」他只好不好意思地宣佈。
愛德華沒有回答他,黑暗中只聽見窸窸窣窣的布料摩擦聲,看來他正在穿衣服。「謝謝。」愛德華的聲音小得不能再小,但斐瑞清晰聽見了。
「你還好嗎?」斐瑞問。
「嗯。」愛德華的聲線微弱而顫抖。
「你還很冷嗎?」斐瑞擔心不已,下意識伸出手去摸他,發現愛德華仍然抖得很厲害,身體仍然冰凍。
斐瑞情急之下又劃着了一根火柴,照亮了穿着自己運動外套的愛德華的蒼白容顏和冷得牙關打顫的可憐模樣。
火光又滅了。斐瑞不再猶豫,上前抱住了發抖的愛德華,並不斷擦着他的手臂,希望為他帶來那怕一丁點的暖意。他感到愛德華先是僵硬了一下,然後慢慢軟下來,後來他乾脆虛弱地靠倒在斐瑞身上,手鬆鬆地圍在斐瑞腰間。
他們就這樣彆扭地擁抱着取暖,誰也沒有再開口。
愛德華的氣息輕輕吹噴在斐瑞胸前,愛德華的氣味再次觸動了斐瑞的感官,他們以這樣子的形態被困在這裏本該讓人煩躁不安,但沒有。奇怪的,斐瑞感到了一種安心的暖意緩緩擴散開來,感覺這樣很舒服、安全。慢慢地,愛德華的身體停止了顫抖,不再像冰一樣冰冷,漸漸暖和起來。
本來任務完成,這時候他們可以分開來了,但沒有,他們都沒有動。又這樣抱着,過了一段寧靜的時間。
黑暗之中,靜得聽得見彼此的心跳。不知是誰開始的,心跳聲怦怦的來得越來越快,越來越響,讓人感到越來越手足無措。
斐瑞首先放開了愛德華,然後打趣地掩飾尷尬:「哈,你要不要來支煙?」
原本他只是隨口問問,他以為品學兼優的愛德華一定會說不,不料愛德華卻回答:「好的。」
斐瑞只好慌慌張張地掏出那唯一一支香煙,以他學過的方法含在嘴裏,用火柴點燃。當他把煙遞給愛德華時,才想起來:「噢,煙嘴被我含過了,但只餘下這支……」他還沒支吾完,愛德華就爽快地接過了煙,手勢純熟地抽了起來。
「別傻了,好像剛才你的嘴唇就沒碰到過我的。」愛德華冷冷地說。
斐瑞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臟,霎時又怦怦亂撞了——愛德華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是揶揄我乘人之危非禮了他?但他好像又不介意……而且嘴巴也毒回來了,看來他也沒有大礙了——斐瑞想到這裏,只好又嘆了口氣。
「來吧。」愛德華把煙遞回給他,斐瑞於是也接口抽了起來。
他們就這樣抽着同一支煙,打發餘下的時間。
直到兩小時後,學校已經下課,別的運動學會要來儲物室拿設備開始課外活動,那道該死的門才被打開。
那時候愛德華的衣服已風乾,被穿回身上。斐瑞也拿回了自己的外套。他們都好像很有默契地不提發生了什麼事,只假裝是兩個曠課的學生躲在這兒抽煙。
斐瑞的那盒火柴都被燒光了,他覺得他們當時挺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孤立無援和絕望冰冷中,燃燒了一些璀璨奪目的帶有夢幻色彩的東西,但又不太清楚那是什麼。至少他們沒有死掉,不像那個可憐的小女孩。
此外,在火光的起與滅間,斐瑞還瞥見了一個愛德華的小秘密——他的錢包內藏着一張照片,是一個可愛小女孩正笑容燦爛地跟一隻寵物犬抱在一起。那樣的品味和喜好都太不愛德華了,難道說「冰人」還有那麼溫情脈脈、會惦記着一個小女孩的時候?那是誰,是他的妹妹嗎?
當兩人回到房間時,斐瑞還收到了一個意外驚喜——愛德華竟然親自幫他消毒傷口,還用上他那條昂貴的手帕來為他細心包紮——儘管傷口的確是愛德華弄出來的,那麼體貼的愛德華倒還是斐瑞第一次看見的。
至於在儲物室內,愛德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斐瑞不敢問,愛德華也一直沒有說。10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gwPw02T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