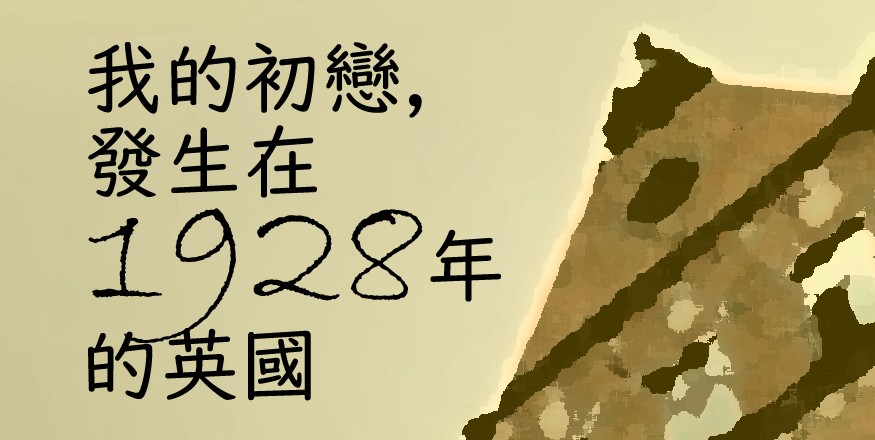聖誕和新年假期,轉瞬即逝。在愛德華和斐瑞回到學校以前,愛德華決定要去面對那件他一直在逃避的事。
「雪莉。」愛德華進入了妹妹的房間,在她床上坐下來。
「什麼事?」雪莉卻捧着書本沒有抬起頭,只想以不耐煩的語氣把哥哥打發掉。
「我要告訴你鐵鈎船長的事。」
雪莉這才抬起頭來。「鐵鈎船長怎麼了?」
「牠死了。」
雪莉難以置信地睜大眼,手上的書掉了下來。
「因為牠之前遇上了意外,受了重傷,沒有辦法醫治,為了令牠減少痛苦,我們對牠進行了人道毀滅(Animal euthanasia)。」
雪莉儘管不懂希臘語,但也知道"euthanasia"源於希臘文,有「好的死亡」或「無痛苦的死亡」的含意。這表示,他們把鐵鈎船長殺了。想到這裏,她的淚水已忍不住流下來。
愛德華看着雪莉睜着那雙無辜的大眼睛望着自己,不停湧出眼淚,似在無聲地控訴,心痛不已。他上前把雪莉擁進懷中。「死亡是人生的一部份。你總要學會面對的。生、老、病、死,我們無一能幸免。」
「可是我還沒有當上海盜……」雪莉哽咽着說。「我說過要帶鐵鈎船長去尋寶的……」
「牠生前你那麼疼愛牠,牠會知道的,牠會感激你的友誼。」
「可是……」雪莉泣不成聲。「可是牠是我唯一的……朋友……」
「將來你一定會結識另一位好朋友的。」愛德華輕吻雪莉的前額,撫摸着她的卷髮。「哥哥知道得比你多,所以知道會有那麼一天的。」
「可是……」雪莉摟住哥哥,哭濕了他的前襟。「你不是說過外面的人都是小丑魚嗎?還有誰會跟我玩?」
「也有很有趣的小丑魚存在,或者也有小丑魚其實很聰明的呢?」愛德華抱緊她。
「不!不!不!你騙人!」雪莉哭道。「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人!我認識的小孩全都是蠢材,只會懷疑和嘲笑我說的東西,動輒就以大欺小想用拳頭堵住我的嘴,只有鐵鈎船長會耐心聽我說話,會跟着我去冒險!」
「也會有人肯耐心聽你說話,跟着你去冒險的。」
「不會有!」
「哥哥就認識了一個這樣的朋友。他也只是條小丑魚,但他會耐心聽哥哥說話,跟我一起去冒險。」
「……你帶回來過聖誕那個小丑魚哥哥?」
「是的。我原本也以為自己在學校不會交到朋友,但卻跟他做了好朋友呢。」
「我也會交到好朋友?」雪莉吞嚥了一下,開始止住了哭聲。
「當然。」愛德華補充了一句:「我也會永遠在你身邊的。」
「騙子。」雪莉氣鼓鼓地說,卻仍然摟住她的哥哥。「你今天就要走了。」
「我即使回到寄宿學校,我的身份也不會變,我仍然是你的哥哥。」他輕掃雪莉的背部。「永遠是你的哥哥。」
雪莉在哥哥溫暖的懷抱裏,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她又哽咽起來:「鐵鈎船長……」
愛德華就那樣安慰着她,直到她哭累了睡着了,才悄悄掩門離去。
那天黃昏,雪莉出奇地聽話,到愛德華和斐瑞要告別時,她也乖乖地吻別了他們。
雪莉始終沒有想起那一段可怕的經歷,令愛德華舒了一口氣。把鐵鈎船長之死的真相告訴她,也許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雪莉並沒有像上次那樣大發雷霆,當愛德華告訴她鐵鈎船長去了一個更開心的地方居住,雪莉對所有人都不瞅不睬了一個月,並對家裏所有東西都大肆破壞一番。當時大家都以為雪莉只是任性,現在回想起來,她可能是覺得被最好的朋友背叛和遺棄了,鐵鈎船長違背了牠要跟雪莉一起做海盜去冒險的承諾。這一次把真相告訴她,不錯雪莉是非常傷心,但她學着去接受死亡的成熟表現,卻令愛德華另眼相看。也許他真的一直低估了自己的妹妹,雪莉遠比她表現的懂事明理。
然而目送着二人離去的,除了雪莉童稚無害的目光,尚有一雙充滿了猜疑的眼睛。
# # #
當愛德華和斐瑞回到學校宿舍,在大堂的當眼位置,貼出了一份關於「Labouchere Amendment」的通告——「Labouchere Amendment」就是俗稱的「嚴重猥褻罪」,禁止兩個男性間的「嚴重不當行為」,這是一個廣泛的包含了幾乎所有男同性戀行為的定義。
愛德華和斐瑞偷偷互望了一眼,彼此保持着正常社交的距離,心裏都不約而同捏了一把冷汗。
難道伊莉莎白已然向校方檢舉了二人?這疑惑一時升上他們心頭。
但很快他們便知道了答案。原來在剛過去的假期,被校方捉到兩個男生在宿舍發生性行為,結果二人雙雙被勒令停學並遭強制送往接受「治療」。而校方聯同警方,決定於接下來的新學期,嚴打校內歪風——不單接受匿名舉報同性戀學生,誰要是能提供可靠證據或出面作證,還可獲校方記錄一個優點。
二人回到房間以後,都商量着往後可要加倍小心了,盡可能都不要一起出現在人前,就只於房間內見面,或相約到後山才會合。
那天晚上一如愛德華所料,舍監真的進行了突擊檢查,所以當房門被校方無聲無息地開鎖時,暴露在猛然亮起的燈光底下的只有兩位規規矩矩地在睡覺的學生,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
舍監很快就滿意地離去了。
「他還會再回來嗎?」斐瑞悄聲問道。
「我想今晚不會了。」愛德華小聲說,並且悄悄翻身下床,赤着腳來到了斐瑞的床邊。斐瑞早掀起了被角,在等着他。
愛德華鑽進被窩,抱住了他的新任男朋友,並在他耳邊輕聲說:「你說過今晚讓我們交換看看?」
斐瑞害羞地點點頭,並感到愛德華的硬挺已透過薄薄的睡褲布料戳刺到自己臀上了。他轉過頭來,跟愛德華接吻。
愛德華邊吻着他,邊把手探進斐瑞睡衣內撫摸。斐瑞發現愛德華的技巧進步得很快,他一邊玩弄着斐瑞的乳頭,一隻手探進睡褲裏去握住了斐瑞的分身,然後不消一會就讓斐瑞興奮得渾身顫抖了。
愛德華起來脫掉了自己的睡衣,斐瑞也脫去了自己的,然後愛德華把斐瑞的睡褲連內褲拉到了大腿,自己則躑在他兩腿間,俯下身去輕吻愛人的陽物。
斐瑞簡直受不了這樣的柔情挑逗,但他絕不能發出聲音,只能咬住枕頭一角,輕輕挽住愛德華的髮尾,任由他在身下緩緩吞吐着自己的分身。
愛德華一邊用唇舌瓦解了斐瑞的自制力,一邊旋開了剛才一同帶過來的瓶子,把手指蘸上軟膏,按壓在斐瑞的後穴上。起初仍能感覺到斐瑞的抗拒,漸漸地他就放鬆下來,容許愛德華進入多些、再多些。
後來愛德華乾脆把他們兩人的最後衣物都脫去了,然後爬上前用自己的口堵住了斐瑞的,兩隻手指已能在斐瑞身體裏自由進出了,而自斐瑞口裏發出的無法忍耐的零碎呻吟,已教愛德華硬得發痛並且把前液滴落在愛人身上。他連忙加進了第三隻手指,希望斐瑞的通道快點足夠容納他。
「我想……可以了。」斐瑞小聲說。
「我想看着你。」愛德華把手指抽了出來。
斐瑞點點頭,抱住了愛德華。愛德華把他的腿拉得更開,然後扶着自己的硬挺,對準了男友的穴口,緩緩進入。斐瑞首次體驗被人進入的感覺,這跟上次他進入愛德華體內真的很不同,上一次他是既興奮又衝動,被進入卻是很親密的感覺。
愛德華做得很溫柔,在緩慢抽插着的同時,他們繼續愛撫親吻對方。這種親密的感覺令他們進行得更持久,比上一次血氣方剛的盲勁更能感受到對方的愛意。
愛德華在吸吮斐瑞的頸側,而斐瑞能感受愛德華的陽物在內裏頂撞着自己那一點,令他被快感充盈全身。斐瑞只得咬着愛德華的肩膀才不至叫喊出聲,然後他雙腿用力夾着愛德華,把自己努力迎向他。愛德華也加大了撞擊的力度,更快地進出,令二人間的快感逐漸騰升。
他們都想把這一刻盡量延長,都忍着要射的衝動,只是在忘我的拍擊之中,都用力捏着對方的手臂、背部、臀部、大腿等,在多番刺激下,他們終於同時射了出來,然後氣喘噓噓、汗流浹背地疊作一團。
「很厲害啊……」斐瑞累死了,但仍忍不住說。
「我學東西一向很快。」愛德華笑了出來。
「我也不會輸給你的。」斐瑞不甘示弱。
「要比賽嗎?」
# # #
事後回想,他們都覺得他們那段日子一定是瘋了。但有道是年少輕狂,年輕,本該就是盡情叛逆的歲月。在學校最嚴打同性戀的時期,他們卻是打得最火熱、愛得最猖狂的日子。學校的線眼廣佈各處,他們卻總是找得到保安漏洞,不止在宿舍和後山密會,還試過偷偷在無人的圖書館、實驗室、浴室、保健室、甚至校長室做愛。
他們積極地研究各種方式和姿勢的技巧和感受,互相比拼,看誰學得更快,做得更好。
而除了睡房和後山,最受歡迎的做愛勝地,是禮堂後台的更衣間。那兒在沒有活動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無人會到的。而且愛德華總想報復斐瑞曾跟伊莉莎白在此親熱一事。此外,他們那趟「有實無名」的「第一次」也是發生在這兒的呢,很有特殊意義。
「說老實話,那時候你想的到底是誰?」當愛德華被斐瑞推擠在牆上磨蹭着時,忍不住問了這個想問很久的問題。
「哪時候?」斐瑞開始解開愛德華的褲頭,把手探進去玩弄他的臀瓣,頭腦發熱得不清楚他在問什麼。
「在這兒,當你跟伊莉莎白親熱不遂,然後我借故吻你的時候。」斐瑞沾了軟膏的手指已伸進了那道狹逢,並想推進那個小穴,愛德華變得氣息不穩。
「想的當然是你。」斐瑞吻咬着愛德華的耳垂和頸項,把手指探得越來越入,並把愛德華的褲子拉下來,隨便在地上團成一團,以露出圓渾的屁股供他揉捏。
「可是……」愛德華只得貼着牆壁來摩擦,以緩解他的渴望。「可是我吻你以前,你已經勃起了吧?因為她……哦……」斐瑞單憑手指就找到了那一點。
為了懲罰愛德華老是說過不停,斐瑞狠狠地搗攪着他的後庭。「但無論我是吻着她、或者壓着她,我想的都是你。」他一隻手在抽插着他,另一隻手在揉捏愛撫愛德華的臀部、大腿根、雙球和乳頭。「我腦子裏都是在拿你跟她比較啊,像是你比較高、胸比較平、手掌比較大,但撫摸挑逗的技巧都是你比較好……」
斐瑞已經開始用兩隻手指在操他,但愛德華仍是奮力要回話。「你吻她、壓着她,然後你勃起了……」他仍然抹不去心底的妒忌。
「我只是個正常的男人。」斐瑞更大力地推壓着愛德華,匆匆抽回了手指,將自己的硬挺釋放出來,抵着愛德華的股縫滑動。「你點起了我的慾望,當我的慾望無處宣洩,只能找個替代品了。」
「那一天,當替代品的,倒底是我還是她?」愛德華已在慾望邊緣顫抖着喘息着,但仍糾纏不休。
斐瑞生氣交織着慾火,猛然就將自己推了進去,馬上完全進入了愛德華的身體。「為何到了今天,你仍要問這樣的蠢話?」他開始猛烈抽插着他,每次都猛然抽拔出來,再用力衝擊回去,令更衣間迴盪着淫穢的肉體拍擊聲。
「呀……」愛德華被進攻得無法言語,只能按着牆壁拼命喘氣,讓背後壓着他的人予取予求。
斐瑞用盡他的力氣去佔有他深深愛着的人,他崇拜仰慕的室友。「難道你感受不到的嗎?天才?」
愛德華感受得到,雖然肢體動作那樣的粗暴、淫穢,但斐瑞的佔有慾,斐瑞對他的着緊和愛意,都透過行動清晰地表達出來了。於是愛德華也推着牆壁向後迎合着他,令更衣間只剩下了喘息、呻吟和肉體撞擊聲。兩具青春的肉體在愉悅地宣洩着他們多餘的精力,讓慾望的汗水在彼此身上閃閃生輝。
「我愛你,傻瓜。」斐瑞輕吻他的後頸。
「我也愛你。」愛德華轉過頭來,想跟他接吻。
斐瑞放開了他,退了出來,讓他們可以面對面接吻,就像「第一次」時一樣。斐瑞把愛德華強吻着推向桌子,然後把他壓在桌子上,像當日。
「那一天,讓我這樣失控的,是你。」斐瑞說着提起了愛德華的腿,重新進入了他,用力操着他,並繼續他們的吻。
愛德華用腿緊緊圈住了斐瑞,感受他像當日那樣壓在自己身上,強吻自己,而他現在甚至在自己身體裏面了。他感覺到愛人的身體在自己的體內活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們緊緊地連合在一起。這種強烈的愛意,他深深感受得到。
他已經完全沒有疑慮了,他們屬於彼此,發狂地、喪失理智地相愛着,就在此時此地。
# # #
在學校瘋狂抓捕同性戀學生的日子,愛德華跟斐瑞一直過着他們的秘密戀人生活,從沒露出過半點蛛絲馬跡。對未來的擔心偶爾會略過心頭,但他們此刻打得火熱,想將來太遙遠了,不如專心沉醉在眼前的溫存纏綿。
基於早些時候莫法特家對斐瑞的招待,德桑家希望禮尚往來,遂提出了邀請愛德華回家同渡週末的建議。愛德華第一次來到男朋友的住處,卻並非第一次看見斐瑞的父親德桑先生——他父親曾作為警方代表,到他們學校來辦過講座,主要是講解「Labouchere Amendment」(嚴重猥褻罪)的具體內容和禁止事項,解釋何謂「嚴重不當行為」,以及同性戀對社會的危害等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當然是以「室友」和「同學」的身份回家的,亦刻意避免了太親暱的肢體動作。
「今晚愛德華就睡在哥哥房間吧?」斐瑞在午飯時主動提議。他雖然想愛德華跟自己睡在一起,但那麼太令人可疑了,而且他也沒信心他們可以在共處一室時按捺得住。
「真不巧,你哥哥今晚也回來睡啊。」德桑先生卻回答。
「什麼?他不是正在警校接受訓練嗎?」
「偶爾也要回來家裏看看吧。」德桑太太插口。
「那麼愛德華睡哪兒?家裏沒有空房間,你們就別招呼人家回來喇!」斐瑞生氣極了。
「你們不是室友嗎?擠一點,都一起睡你房間也可以吧?」他媽媽提出。
「可是我房間裏只有一張單人床……」
「不要緊,我睡地上也可以。」愛德華露出客套的外交笑容。
於是,惡夢就這麼定下來了。
# # #
進入斐瑞房間之後,愛德華四處打量。斐瑞突然覺得很赤裸,愛德華想必用他的方法,已推斷出斐瑞的整個童年和青春期生涯了,因為他就一直住在這個房間。
「充滿了你的氣味。」愛德華閉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氣。
斐瑞臉紅了。「男孩子房間就這麼髒,可能有點怪味……不過你這個有強迫症的完美主義者,房間當然跟我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貶意的。」愛德華張開眼睛,望着他。「只是覺得這個房間很斐瑞,令人很有親切感。」他笑了笑。
斐瑞看着他,也跟着靦腆地笑了。
他帶男朋友回家了,還來到自己的房間裏來,他們今天晚上還要睡在一起,這可真是做夢也想像不到的呢。他想起不久之前,自己還連自慰都不懂,結果卻在想着愛德華時射了出來,就在眼前這張床上……斐瑞想着想着,又臉紅到耳尖去了。
「哦。」愛德華了然於胸的樣子。「你在這床上打過飛機來吧?想着我打的?」他樂開懷了。
「哪有?」斐瑞還想強辯,但卻連脖子根都紅透了。
「沒旁人在,就認了吧。我那麼有吸引力。」
「少臭美了。」
他們說着說着開始嬉戲地動手動腳,但當遠處傳來了腳步聲,他們便馬上分開了,然後小心地保持了大家之間的距離。
之後德桑太太送來了被舖,愛德華也老老實實地睡在地上,他也怕跟斐瑞同睡一床,他會按捺不住自己。
但熱戀的魔力是不容少覷的。尤其當那發生在血氣方剛的少年人身上。
他們各自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都睡不着覺,心跳聲卻越來越響亮。他們都悄悄向對方靠攏了,都不忍分開得太遠。斐瑞在床沿垂下了手,愛德華拉住了它的兩隻指頭。
「我們這樣子睡,可以嗎?」斐瑞小聲說,試着合上眼睛。
「嗯,可以試試看。」愛德華也試着閉上眼,以氣聲回答。
然而他們誰也沒睡着,只是不停地磨蹭着對方的手腕,並且呼吸越來越粗重。
「不行,這樣子睡,半夜裏一定會弄髒被舖。」愛德華突然睜開眼,想到了遺精的問題。
「那怎麼辦?」斐瑞惶恐地看着他。
「你鎖好了門沒有?」愛德華瞥向腳尾的房門。
「鎖了。」斐瑞回答。
「那麼我們用最安靜的方式替對方吸出來,好不好?」愛德華提議。
「好的,這方法最乾手淨腳。」
於是斐瑞坐到了床沿,無聲無息地褪下了自己的睡褲,讓跪在自己身前的愛德華把他的硬挺吞了進去,熟練地吞吐着。幸虧斐瑞早有準備,咬住了被角才沒有呻吟出聲,天呀,愛德華這樣子太性感了,他的嘴唇磨擦着斐瑞的柱身那感覺實在磨人,而他們現在在斐瑞的家,雙親和哥哥就在隔鄰,他們卻在斐瑞的睡房裏做着這種違法的、社會不容的事情。他深愛着的愛德華,正跪在斐瑞的床前,溫柔地替他吸出來,這感覺真好得叫人發瘋了……
轟的一聲,房門被打開了,他們震驚地轉過頭,看見德桑先生手裏拿着鎖匙,站在門前瞪着他們。
斐瑞馬上把睡褲拉起,穿上。愛德華旋即退開來,迅速抹了抹濕潤紅腫的嘴角。
德桑先生進來,重新關上了門,開了燈,並向二人呼喝道:「你們兩個,站過來!」
二人無奈站起來,在單薄的衣料下,他們的勃起都無所遁形,在睡褲前支起兩個小帳篷。
「你們知道你們犯下的,是嚴重猥褻罪吧?」
二人無言地點了點頭。
「你們該感謝我現在是以斐瑞父親的身份在說話,要是以我的職業身份說的話,我該馬上將你們逮捕!」二人都低下了頭,不敢望向德桑先生那銳利的眼神。「小莫法特先生,我們這種出身的平民實在沒有資格教訓你些什麼,畢竟我想貴為莫法特家族的公子,令堂必有嚴厲管教你們。老實說,這次要不是收到令堂的來信,我真的不敢想像你們兩個竟敢幹出這樣的事!」
愛德華跟斐瑞都大吃一驚,原來是莫法特夫人寫了告密信給斐瑞的父親,他們才設計了這趟週末之行,設局令他們的關係曝光。
德桑先生仍然看着愛德華。「令堂當會插手此事,我也會把教育的責任交回給她,這次我就只會給你一個口頭警告,你自己的前途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他看向自己的兒子。「而你,我會馬上替你辦退學手續,你下學年就轉到你哥哥的警校就讀吧。」
斐瑞大驚失色。「可是爸爸,我還有一年就畢業了!」
「反正你將來也打算當警察,文法中學念不念完有什麼大不了?」
「這樣無緣無故地退學,不是更惹人懷疑嗎?」斐瑞據理力爭。
「德桑先生,我保證我們不會再犯了!」愛德華幫口求情。「求你讓他念完中學好嗎?」
聽到「不會再犯」幾個字,斐瑞不知怎的腦袋已一片空白,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覺。
「我母親一定會替我申請調房的,我們不會再住在同一間宿舍,我們不再是室友,請你放心,我們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愛德華的每句說話,都像向斐瑞射出一發子彈。「我們只是……一時好奇。」
「我還是不相信你。」父親嚴厲地盯着自己,斐瑞卻只是目定口呆地站着。「假如你要繼續留在那間學校,就要接受醫治同性戀的療程。」
不用轉校的唯一曙光出現了,但代價是接受治療——斐瑞知道那些「治療」,因為校內有些被捉過正着的同性戀學生,就是被送到那些地方去。他見過他們被送回來後的神情,好像遇見了世界上最可怕的遭遇。他也聽說過,有些孩子簡直受不了,最後自殺身亡。
他看向愛德華,愛德華正臉色發白地朝他搖了搖頭,眼裏充滿恐懼——愛德華不想他受苦,即便代價是他們就此被分開,他也不願斐瑞為了留在自己身邊而受苦。想到這裏,斐瑞便有了決定。
「好的。」
「你願意轉校?」
「不,我願意接受治療。」6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aqNqkYO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