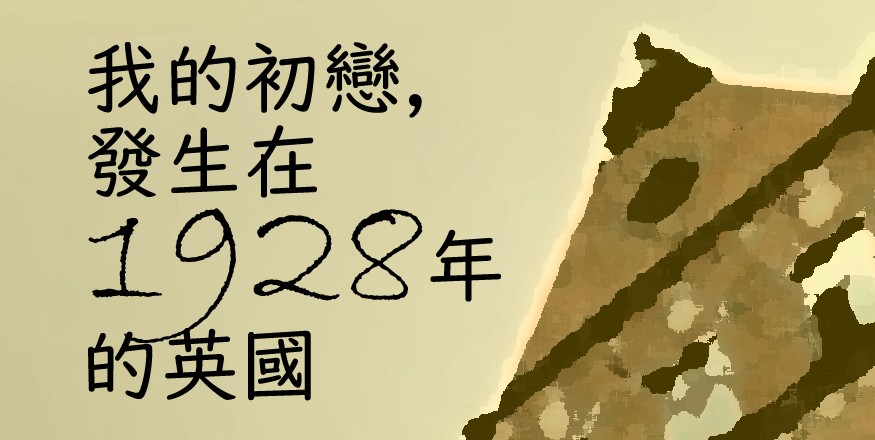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鐵鈎船長呢?」雪莉醒來時,問出來的問題讓大家都嚇了一跳。「愛德華你為什麼回家來了?被學校踹出來了嗎?」她笑嘻嘻地,盯着哥哥眨了眨眼睛。當她注意到爸爸也在時,好像真的很吃驚。「噢,連爸爸也回來了,難道今天是聖誕節?」
這天其實是平安夜,明天便是聖誕節,雪莉卻似乎把日子都忘記了,連愛犬早已不在的記憶也沒有了,她的時間就停留在鐵鈎船長生前。
「醫生,為什麼會這樣?」當大家退至門外時,莫法特夫人焦急地問道。
「看來她是短暫失憶了。」醫生托了托眼鏡回答說。「可能是發高燒的後遺症,這在年紀小的兒童身上偶有發生。也有可能是見證過什麼可怖場面或事件,驚嚇過度而產生了創傷性心理補償,潛意式抑制着對恐怖事件的記憶,於是這段時間裏的經歷就可能暫時記不起來了。」
「意思是遲些就會記起來嗎?」莫法特先生問道。
「有可能晚一點就會記起來,也有可能一輩子也失去了這段記憶。」醫生說。「也有些情況是病人過了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想起來,突然有天遇見了什麼類似的場景,才一下子啟動了過去的記憶,想起了一切。」
愛德華跟莫法特先生早把血衣和證物都藏起來了。但現在的問題是,他該怎麼回答雪莉她的寵物狗去了哪裏?照舊作個故事來欺騙她?還是如實相告?答案又會不會再度刺激雪莉,讓她恢復那段可怕的記憶?
# # #
「今天是平安夜啊。」家裏一角,難得的寧靜,斐瑞在幫着愛德華裝飾聖誕樹,把包裝精美的禮物一份份圍放在樹下,替這座暗湧迭宕的大宅粉飾着些許太平。「雪莉也可以下床了,大家也終於可以放鬆一些了吧?」
「這份是我私下給你的。」愛德華神秘兮兮地塞給斐瑞一份很輕的長方形禮物。
「是什麼?」斐瑞感愕然。
「是你說的,聖誕禮物該要自己挑,這樣才有驚喜和意義。」愛德華笑了笑,向斐瑞單了單眼。
斐瑞竟有點臉紅起來。「可是我卻沒有準備啊……」
「不用了。」愛德華把另一份厚重很多的禮物遞給他。「你替我把這個交給雪莉吧。」
「連雪莉的份你也準備了?」斐瑞很高興。「明明說『毫無意義』、『不會買禮物』的人不是你嗎?到底是什麼時候買的?」
「愛德華……」雪莉揉着惺忪的睡眼,穿着睡袍出現在他們身後。「鐵鈎船長到底哪裏去了?」
愛德華回頭擠出一個微笑,握緊的拳頭卻攥得指節都發白了。
斐瑞搶先替他解圍,躑下身朝雪莉招招手叫她過來,禮物卻藏在身後。「雪莉,你哥哥有禮物給你啊!」
「禮物?」雪莉猶豫着走過來,皺起眉頭看着她的哥哥。「是耍我的嗎?你不是最討厭聖誕節嗎?」
愛德華咳了一聲以掩飾他的尷尬,但斐瑞就只是把禮物往他手裏塞,他只好接過來遞給雪莉。「沒耍你,這是給你的。」
「是什麼我也不怕,休想又騙我……」雪莉皺着眉頭接過禮物,便就地拆開禮物紙——手上的東西卻讓她瞪大了眼,露出驚奇又讚嘆的表情——竟是一整套古董版的兒童百科全書,就是每次到舊書店她都愛不釋手地翻過沒完的那一套。
「免得你每次去都翻人家的鎮店之寶,反正早晚被你翻壞了也是找我賠償,不如整套買給你好了。」愛德華說。
「愛德華……」雪莉看着他,一臉不壞好意。
「又怎麼了?」愛德華不耐煩地彎下腰來看着他的小妹妹。不料雪莉卻趁機拉住他的衣領,把愛德華拉下來,往他臉上親了一口。
「謝謝哥哥。」雪莉壞壞地一笑,便捧着她的戰利品返回房間去了,想來是想馬上翻看過夠。
「哈,她很喜歡呢!」斐瑞最喜歡看這兩兄妹的溫馨場面。
「笨小孩。」愛德華倒是一臉難為情,卻借冷嘲熱諷來掩飾。「這套書可有夠她忙上一陣子了。」
「那麼你送給我的又是什麼?」斐瑞說着便要伸手去拆。
「不要在這兒拆開。」愛德華想把禮物搶回來。
「不用難為情啊!」斐瑞笑了笑。「我已經知道禮物是在書店買的,難道買給我的是本情詩?」
「別胡說!」愛德華還要去搶。
斐瑞終於把禮物拆開,發現竟是荷馬所著的《伊利亞特》,愣住。「呃,為什麼送我這個?」
愛德華卻只是紅着臉一言不發地走開了。
斐瑞不明所以地翻動着內頁,發現扉頁上有愛德華的筆跡「紀念Achilles和Patroclus」。
那天下午斐瑞就窩在莫法特家的書房,欲查明Achilles和Patroclus是誰,還有愛德華送他《伊利亞特》的真意。當他明瞭一切後,發現表面像個冰雕般的愛德華內心竟蘊含着這般熾熱的情感,簡直感動得不能言語——Achilles和Patroclus在《伊利亞特》中擁有一段深厚的友誼;事實上,柏拉圖和好些古代哲人作家,更認為他們其實是情人關係,更讚頌他們是戀人們的模範。在《伊利亞特》的描述中,希臘第一勇士Achilles對旁人冷酷而高傲,唯獨對摯友Patroclus卻不是這樣。Patroclus被Hector所殺,那時候Achilles明知自己如果殺了Hector,自己就會死,但仍然要為Patroclus報仇。按Achilles的遺願,他的骨灰最後和Patroclus的骨灰混合在一起,埋在同一個墓穴裏——愛德華將這段真摰感人的友誼,或戀情,比喻作他自己和斐瑞的情誼,那可不止是一段初戀那麼單純,那是一段可歌可泣至死不渝的愛情啊。
斐瑞內心激動不已,一方面擔心自己不知是否可以回饋愛德華的厚愛,一方面又為被這樣一個天才深深愛着而覺得幸福不已。
# # #
這個平安夜大家似乎過得很平安——莫法特夫婦之間的氣氛還是有點僵,但至少沒有惡言相向。夫婦倆跟斐瑞和愛德華也分別閒話家常了數句。而雪莉則乖乖地沉醉在她的新書之中。
當愛德華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後,還在想,這可能已經是今個聖誕節能過得最好的狀況了。他沒料到半夜裏他的房間還有訪客。
「愛德華,你睡了嗎?」隨着兩下極輕的敲門聲,斐瑞悄悄開了門探頭進來。
「還沒有。」愛德華揚了揚眉毛。
於是斐瑞放輕腳步溜進來,關上門,然後把一盤東西放在小几上。
「這是什麼?」
斐瑞把罩子揭開,露出一盤布甸。
愛德華皺了皺眉:「我不愛吃甜的,甜膩膩的感覺很噁心。」
斐瑞的樣子有點失望:「但現在是聖誕節啊,一定要吃聖誕布甸!」他強把愛德華拉過來,按進小几前的扶手椅。
「這是你從廚房找來的嗎?每年我媽都會做聖誕布甸,但我從來都不吃,她做的很難吃……」
斐瑞抓起小銀匙舀了一口便塞進了愛德華嘴裏,讓他霎時噤了聲。
「嗯…呀……」他咀嚼着,發出意義不明的聲音,然後骨碌一聲吞下,睜大了眼睛。「這……好吃。」他看着斐瑞。
斐瑞笑了:「不是你媽做的味道吧?」
愛德華又回味無窮地吃了幾口:「是叫工人做的嗎?蓮達的手藝的確比媽媽強一點。」
「我做的。」
正在吞嚥的愛德華差點嗆倒。
斐瑞伸手揉着他的背部。「我就只會做這一道菜,今年沒有買禮物給你,就當這是聖誕禮物吧。」他親了呆住了的愛德華一口。「聖誕快樂!」
愛德華含着小銀匙良久,似在回味,又似捨不得把眼前的布甸吃掉,然後他小聲地咕嚕了一聲:「謝謝。」
斐瑞笑着擠身進了那張原本只供一人就坐的扶手椅,跟愛德華緊貼着,然後默然張開了口。愛德華有點臉紅,但仍舀了一口餵進了斐瑞嘴裏。二人就默默對望着,有一口沒一口地分享着一份甜品,直到一整份布甸都被他們吃光了。愛德華依舊意猶未盡地舔舐啜吮着小銀匙,邊斜睨着斐瑞,動作越發色情和挑逗,嘴裏還發出一些濕嗒嗒的聲響,看得斐瑞臉紅耳熱,心跳加速,一股熱流猛向下腹竄過來。
斐瑞終於抵受不住,奪去了愛德華手上的小道具,讓自己的嘴唇舌頭和牙齒取而代之攻進了那個壞傢伙的嘴裏。愛德華倒抽了一口氣,霎時被猛烈進擊的對手推倒在椅背,讓他胡亂搗攪着自己的口腔,失控地發出了嗚咽的聲音。他們嚐到了彼此口中的甜蜜,是聖誕的味道,戀愛的味道,情人為自己下廚的味道,為心愛的人獻上心意的味道,還有狂風暴雨稍歇乍晴時的喘息味道……
來回往返、難分難解的口舌交流,點燃了兩個純情男生的慾望,他們開始爭相脫掉對方身上的衣物,在掙扎與磕磕絆絆間,他們把阻隔物都除掉了,並來到了床邊雙雙倒在床上。他們四肢交纏的重量讓床架發出了怪聲,他們很想大笑,但馬上伸手掩住了對方的口,因為這個晚上他們不能被人發現,一切都要靜悄悄地進行。
他們不敢放開手,就將笑聲悶在對方掌心,光望着對方顫抖着忍耐着笑意,直到大家終於都平靜下來。他們可是首次在床上玉帛相見,目光都忍不住貪婪地在對方身上巡視,然後手掌移下來,撫摸過熟悉的臉龐、迷人的頸項、光滑的手臂、寛廣的胸膛、平實的小腹、修長的雙腿,輕吻舔舐,愛不釋手。他們一手輕撫着對方光滑的臀部,一手在腹股溝四周流連,都咬着唇以免在夜深人靜時洩出任何不恰當的聲音。
他們再次擁吻,為了隔絕聲音,愛德華把厚厚的兩張被子拉上來蓋住了他們,希望這能起到一定的隔音作用,在被子下斐瑞爬到了愛德華身上,讓二人交疊在一起,輕輕幌動磨擦着二人光裸的肌膚,感受着這個最親蜜的距離。敏感而腫脹的陰莖偶爾滑過了彼此,激起一陣快感的顫慄,但這不夠,遠遠不夠——愛德華圈抱着身上的美少年,漸漸加力把他拉下來,拉下來,直到他壓到自己身上,無縫地貼合在一起,胸膛抵着胸膛,兩根血氣方剛的勃起便可以磨擦着滑動,並在二人小腹間的壓迫感中尋求更大的快感。他們拼命吮啜着對方的唇,但求把對方的呻吟都吞下自己肚子,不讓別人聽見。
摸索間斐瑞觸碰到愛德華的會陰,又順着他那渾身一顫的反應摸上了他的屁股,愛德華呻吟着分開了雙腿,斐瑞乘機把他的腿拉得更開,讓自己擠身進去,讓他們的分身更緊密地貼合,湊合着馳騁起來。愛德華無法抵受這重衝擊,為免被震出去只有把雙腿圈到斐瑞身上並夾緊,這種刺激令兩人都目眩神迷,他們只有更落力地堵着對方的嘴,才不致大聲叫喊出來。
斐瑞捧着愛人的屁股,在他身上戳刺着,模擬着那最傳統的性交姿勢,但他仍忍不住伸手去摸索那個禁忌的入口——他摸到了身下人那個緊緻粉嫩的穴口,輕輕在那兒打着圈,偶爾輕輕一戳地試探一下,愛德華在刺激下夾得他更緊,手抓着他的背可能已留下了指甲痕或瘀青。
然後斐瑞感到愛德華輕輕推了推他的胸口,他馬上緊張起來,伸手支撐着床抬起了自己。
「Sorry……」斐瑞以為愛德華不喜歡這樣。
「不……」愛德華拉開了被子讓二人重見光明,然後他在床頭櫃的抽屜裏掏出了一盒軟膏,遞給斐瑞。「我想你需要它。」
「這……是什麼?」斐瑞一頭霧水。
愛德華紅了臉,湊近斐瑞耳邊小聲耳語:「這事我做過一點調查,假如你想……進來,要先用這個……做……準備。」說罷他連耳尖都紅透了。
「做……準備……」斐瑞也臉紅到脖子裏去了,結巴得差點忘了如何說話。「怎怎……怎麼做?」一想到愛德華願意讓自己進入他身體的最深處,斐瑞頭腦都蒸發掉了,頭頂還在冒煙。
愛德華無奈地盯着眼前這個性愛初哥,儘管兩人都沒有經驗,看起來還是他偷學回來的那些紙上談兵的技巧比較靠譜。於是愛德華擺擺手讓斐瑞坐到床尾去,空出地方好讓他四肢着地的跪在床上,光裸好看的屁股就在眼前令斐瑞大嚥了口口水。然後愛德華伸手分開了自己的臀瓣,把沾了軟膏的手指抵在自己的穴口,輕輕按揉,看得斐瑞又骨碌吞嚥了一下。然後斐瑞眼睛一眨不眨,看着那根修長美麗的手指,消失在那個粉嫩的皺摺之中,被完全吞噬,一會兒又被吐出,忽閃忽現。
紅暈從愛德華的臉龐、胸口一直漫延開去,他一晃一晃的軀體襯托着閃閃汗光顯得更加誘人,緊咬着下唇以免發出聲響的那個表情既挑逗又迷人,但最令人慾火焚身的還是那圈讓長手指消失的魔法地帶。斐瑞被深深吸引着,他湊近觀看,手想摸上去卻又不敢。
「來吧……」愛德華氣息不穩地說。
斐瑞依言上前,摸上了愛德華的臀瓣,自己滴着前液的勃起此刻離那個若隱若現的神奇小孔就只有兩寸。愛德華把手指抽了出來,把軟膏遞給斐瑞。於是斐瑞顫抖着的手沾上了軟膏,然後很溫柔地輕輕地愛撫着那個環形入口,待愛德華從緊繃變得放鬆,才緩緩將一隻手指放進去——那裏面很緊、很熱,吸啜着斐瑞的手指,感覺很神奇又讓人覺得親密得不可思議。
斐瑞保持着手指在愛德華體內輕柔按摩着,向前挪了挪,不管分身戳到身下的人,不管前液滴落在愛德華的臀瓣上,斐瑞只是急切想要拉近二人的距離,於是他從背後伸手環抱住愛德華的腰,輕吻他汗濕的背脊,末了又試着舔吮身下的肌膚,細味着那微鹹的味道。
愛德華輕喘着伏倒在床上,咬住了自己的拳頭以免叫喊出聲,他感覺到身後貼着自己的人也在忍耐着,並且極其溫柔地伸進了兩根手指,而按揉的步調逐漸摸索出一種節奏,慢慢變成了一種抽插的動作——這種感覺太強烈了,愛德華從來沒有讓人這麼對待過自己,這麼親密,這麼赤裸……讓人感到非常暴露,從而變得十分脆弱。
愛德華擺擺手讓斐瑞停下來,伏在床上喘着氣。
斐瑞爬上前,擔心地撫摸着他的背,問道:「你還好嗎?」
愛德華抬起頭,瞳孔放大着,整個人都渲染在一種情慾的氛圍裏,讓斐瑞感到自己正硬得發痛。愛德華看着斐瑞的眼神也流露出同一種渴望,天知道他是不是在斐瑞身上也看見了同一樣的景致。
「我……準備好了。」
斐瑞看着愛德華那堅定的目光,忍不住上前再一次堵住他的嘴,直到缺氧讓他們再一次分開。斐瑞再次望向愛德華,只見他微微點了點頭,於是斐瑞回到他身後,捏着他的臀瓣,扶正自己的陰莖向那小穴埋進去。
看着自己分身的頭部消失在眼前,那感覺太震撼了,令斐瑞忍不住馬上再做一次——他把分身拿出來,再一次埋進去,這次緩緩的一直推,感受着被另一個人的身體包裹着的感覺,那種緊迫感還有熱度,直到他的分身完全消失在眼前。
「還可以嗎?」斐瑞穩住不動。
「嗯。」愛德華把枕頭堆疊在跟前,把自己的臉埋進去。
斐瑞扶着愛德華的腰穩住自己,然後把分身退出來,再輕輕插入,直到二人慢慢適應,才逐漸加大力度和速度。斐瑞感到二人間節奏逐漸順暢,愛德華開始向後迎合着他,於是他伏下來抱住身下的人,讓自己的前胸緊貼着對方的背部,繼續戳刺進去。
這種二合為一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盡管過程有點狼狽,技巧並不純熟,但跟深愛的人以這種親密的方式連結在一起,就好像突然衝破了所有外在的阻隔,直達對方內心,彷彿所有不為世人所知的自己都被暴露出來,獻給了愛人。
事實上這活動很快便完結了,兩個經驗不足的新手,受不了這樣激烈的刺激,真正抽插的次數可能不過兩隻手的手指數目,便先後射了出來。斐瑞仍舊伏在愛德華身上,二人一起喘着氣。
「你……很重啊。」
「啊!對不起。」斐瑞靦腆地翻身下來,躺到愛德華身邊去。
愛德華瞇着眼睛盯着他,斐瑞尷尬地轉開視線但轉了一圈又忍不住轉回來,跟對方互望着——二人你眼望我眼,先裝着若無其事,然後都憋着一口氣,忍住那道從心底突然冒升上來的笑意,他們都知道對方快要爆笑出來,於是速速伸手掩着對方的嘴,然後看着對方忍笑忍得渾身顫抖。
等着,直到大家平靜下來。才放開手。
「你個白痴。」愛德華的手愛撫着斐瑞的臉,目光溫柔地看着他。
「你個自大狂。」斐瑞笑着摟住愛德華將他拉近,拉進自己懷裏去。
他們就這樣沐浴在性愛的餘韻裏,待了好一陣子。
直到覺得冷,愛德華伸手拿地上的衣服替二人大概清理了,再把被子拉上來蓋住他們。二人在被子下又往對方挪了挪,直到四肢交纏在一起,臉龐貼近得轉個頭便能親吻。
他們看着對方,只是笑。
「要睡了嗎?」斐瑞笑着問。
「嗯。」愛德華剛閉上眼,又睜開。「可是你不能睡在這兒啊。」
「對。」斐瑞也睜開了眼。「會被發現的,我一會兒要回去自己的房間。」
他們仍然誰也沒有動,不捨地待在一起。
「你睏了嗎?」斐瑞問。
「不。」
「那麼……」斐瑞突然把被子拉過頭,蓋住了他們,世界重歸一片漆黑。
「幹什麼你?」愛德華笑着伸手抵住他,一摸就是斐瑞的胸口。「那麼快又想來第二回?」
「不。」斐瑞卻是伸手把愛德華緊緊抱住,讓二人緊緊貼近。「我們趁這機會來聊聊天吧。」
「什麼?」
「我想多了解你一些。」
愛德華沉默了一會兒,只是把頭靠在斐瑞肩上。「......你想知道什麼?」
「關於你的一切。」在黑暗的被窩內,他們的交談接近耳語,顯得很私密。
「有什麼是你不知道的?」
「很多呀,譬如除了鋼琴你還會什麼特殊技能?是個語言天才、熱衷軍事政治還有什麼興趣?除了體育還討厭什麼學科?一直都不吃甜的嗎?還……還有……」斐瑞開始結巴起來。
愛德華感覺到斐瑞的手心開始出汗,肢體變得繃緊。「真正想問的你沒有問出來吧?」
「嗄?」
「為什麼我有時候會突然病發?是什麼病?我爸媽到底怎麼回事?我媽媽跟我又怎麼了?我妹妹的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禁錮恐嚇她的到底是什麼人?」
斐瑞聽見愛德華若無其事地說出他心裏的疑問,頓時緊張起來,擔心自己的關心會讓愛德華增加心理負擔,擔心他們的關係還沒有深入到讓他知道這些,擔心愛德華會拒絕回答並冷嘲熱諷他一頓。「你……不想說的話,不用告訴我。」他責怪自己怎麼那麼笨,要挑這個時候談這些大殺風景的事情。
愛德華又沉默了一會兒,但他沒有退開,仍然跟斐瑞相擁着,然後他嘆了口氣。「其實我早該告訴你,尤其現在把你也牽扯進來了。」
斐瑞很緊張又期待——愛德華要對他訴說自己最私密的秘密。這表示他真的對自己完全信任,毫無保留。這意味他們的關係又更進一步了。
「從小我媽家教很嚴,簡直到達吹毛求疵的地步,假如你覺得我是個強迫症或完美主義者,要不是從我媽處遺傳得來的,就是被她教育成這副樣子的。」愛德華說。「也可能因為我是長子,她又從來沒有當過媽媽,毫無經驗之下丈夫又常常不在家,她就把壓力都扛自己肩上,想把我教育成一個完美的小孩——就是一個不像小孩的小孩——她都按成年人的準則要求我,要求我做到最好,做到完美,希望把我教育成一個合乎社會標準的紳士。」
斐瑞輕撫愛德華的背脊,吻了吻他的前額。「你一定吃了很多苦頭。」
愛德華微微搖了搖頭。「她為了達成目的,制定了一套家規——要是我達不到她的要求,她就會將我鎖在閣樓那個古老大衣櫥裏面,讓我靜思己過。」
「所以你才那麼害怕上鎖的密室嗎?」斐瑞無法想像那對一個孩子來說,被媽媽鎖在閣樓衣櫥內會是多麼恐怖的童年陰影,他想像要是被困的人是自己,可能早嚇得屁滾尿流了。
愛德華又微微搖了搖頭。「她通常只會困我一個小時,往後她總會記得放我出來。所以起初我是有點害怕,但後來我也慢慢習慣了。」
斐瑞緊緊擁着愛德華,卻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迫令一個小孩面對恐懼,直到變成習慣,那簡直不人道。
「閣樓平常沒有人來,只是用來堆放雜物,所以很安靜,其實是個不錯的思考空間。」愛德華說。「有一天,我待在裏面,正在腦中練習着微積分運算,卻被一些怪聲打擾了。於是我從衣櫥門縫看出去,想看看是誰進來了並且在做什麼。」
「是誰?難道是雪莉?」
「不,那時候她還沒有出世呢。是我爸爸。」
「你爸爸?」
「是的,我那時也覺得很奇怪。我爸爸是個公務員,小時候我只知道他替政府工作,做些什麼卻好像很神秘,而且常常早出晚歸甚至離家數月不返——後來我才知道,爸爸原來替政府內部一個特務組織工作,負責研發配合他們工作的新科技用品。」
「嘩!這麼厲害!」
「噓......別吵醒了其他人。」
「對不起。」斐瑞小聲回答。
「這可是國家機密啊,你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我爸也沒有告訴過我們,只是我自己明查暗訪得來的資訊。」
「你也像個小特務呢,將來可以繼承你爸爸的衣缽。」
「嘿。」愛德華只是冷笑一聲。「總之那時我還對他的工作一無所知,只知他有個合作無間的同事,是個不拘小節的叔叔。那叔叔作風有點豪邁不羈,有空甚至會教我打架什麼的,跟溫文儒雅的爸爸個性可謂南轅北轍。有時他們會把工作帶回來家裏一起研究,有時也會跟我們一起吃飯說笑,就像家人一樣。那時候媽媽對這位叔叔也蠻客氣的,就只是對爸爸常常只顧工作不顧家有點怨言。」
「接着呢?」
「我在門縫裏看見了爸爸,以為他要進來找些什麼東西,卻發現他的表情很痛苦,還在呻吟。我嚇了一跳,才發現爸爸正被什麼人捉住,似乎正在粗暴地對待他,讓他痛苦受折磨。」
「是什麼人?」
「我看不見他的臉,但看背影就是那個叔叔。」
「嗄!」
「我就看着叔叔欺負我爸爸,心裏很害怕,但困在上鎖的衣櫥裏根本出不去,又怕大聲呼叫的話會打草驚蛇,連累爸爸受到更惡劣的對待,所以就只是眼睜睜地看着,聽着爸爸痛苦的叫喊和求饒,看着那個粗魯的叔叔半點沒有手下留情。然後情況一直持續,直到聽見他們各自慘叫了一聲,好像都筋疲力盡了,待了一會兒叔叔便押着爸爸離去。我嚇得滿頭大汗,混身濕透,連叫都叫不出來,但仍拼命用力去拉扯那道門,想打開門跑出去求救,結果抓得手指都流血了仍不得要領,最後掙扎得渾身乏力,就只是發軟地躺在那兒,那股被困的恐慌感和無助感一直縈繞不去,後來還全身抽搐起來。後來媽媽來找我時,發現我正在發高燒,已經失去知覺。」
「這就是你被鎖在密室就會病發的原因?」
「我想是的。還有遇到會讓我聯想起這情境的事情,都會病發。」
「哎……你爸爸和那叔叔到底怎麼了?」
「所以說我就是個大笨蛋。」愛德華自嘲道。「那年我九歲,看過許多書,以為自己懂得許多事,其實還只是個無知的孩子。我臥病在床時,看到爸爸和叔叔一起來看我,還看見他們暗地裏打眼色,以為爸爸仍被脅持住,以為爸爸一直都受那叔叔操控來做壞事,所以才會常常不在家。所以當他們走後,我就把我發現的大秘密偷偷告訴了媽媽,把看到的聽到的都一五一十形容給她聽。」
「難道說……」斐瑞滿腹疑惑。「他們……」
「對。」愛德華木無表情。「他們其實只是在做我們剛剛做過的事。」
「什麼?那……你媽……你……」斐瑞震驚得語無倫次起來。
「我父母原本就在冷戰,媽媽對爸爸跟叔叔比夫妻還親密的關係本就有怨言,料不到我把這一切都捅破了,她氣得馬上去找爸爸理論,結果是不歡而散。後來冷戰和爭執交錯發生了無數遍,爸爸搬離家裏的日子比以往更長了,媽媽才發現自己有了三個月身孕,但一切似乎已鬧得無法挽回,於是她就後悔了,就更加怨恨我把真相告訴了她——原本她可以欺騙自己,跟丈夫孩子一家人好好渡過餘生的。」
「這……這根本不是你的錯,你媽媽太橫蠻無理了!」
「真相不是人人受得了的,這是我從這件事學到的教訓。」愛德華說。「憎恨和討厭都是情感行為,並不能用理性去辯解,一般人就是喜歡一些甜蜜的假像,痛恨那些看穿假像的人。所以我明白雪莉為什麼交不到朋友,和她前面的路有多難走,因為我都走過了。」
「愛德華……」斐瑞抱住他,哽咽起來。
「說回雪莉的狗,是我帶牠去農舍讓牠接受人道毀滅的——因為早前牠被惡作劇的捕獸器弄致重傷,苟延殘喘只會增加痛苦。」愛德華淡然說道。「當然我告訴雪莉的是另一個故事,說牠被送往一個主人友善又有廣闊花田的農莊,過着比在莫法特家幸福得多的生活。」
「你也只是出於善意呀。」
「今天下午,爸爸打了電話給那位我懷疑工作是特務的叔叔,讓他去調查用惡劣手法禁錮恐嚇雪莉的人到底是誰。剛才晚飯後爸爸告訴我,那個阿各他懷疑是我們早年在蘇塞克斯居住時的鄰居,就是我送狗去人道毀滅那個農舍裏,那對農民夫婦收養的兒子——他們因為婚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子女,才在接近退休的年齡收養了一個男孩。」愛德華頓了頓。「可怕的是,那對夫婦後來被人虐殺了,連同整個農舍的牲畜都被大屠殺無一幸免,場面可怖到令當時調查的警員印象深刻。而那個只有八歲的養子卻像蒸氣般憑空消失了,連他在那兒居住過的痕跡都被消滅得一乾二淨。這件可怕的事件就發生在今年年初。後來據警方調查所得,那附近之前一直都有發生動物被虐待和殺害的惡作劇,懷疑都是同一兇手所為。那麼當年鐵鈎船長被捕獸器所傷,可能根本不是意外而是蓄意而為的,那個人早就盯上了雪莉。」
「那個叫阿各的小孩?他不是還是個孩子嗎?」
「在犯罪歷史檔案裏,不少變態殺手在少年甚至孩童時代就流露出兇殘嗜殺的傾向,他們許多時在兒童時期就會開始用動物做實驗,鑽研殺人方法,他養父母可能是他技術熟練以後的首次人類實驗品。」
他們霎時靜默下來,都為這個恐怖的孩童存在於世感到毛骨悚然。6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GpiOHWBQ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