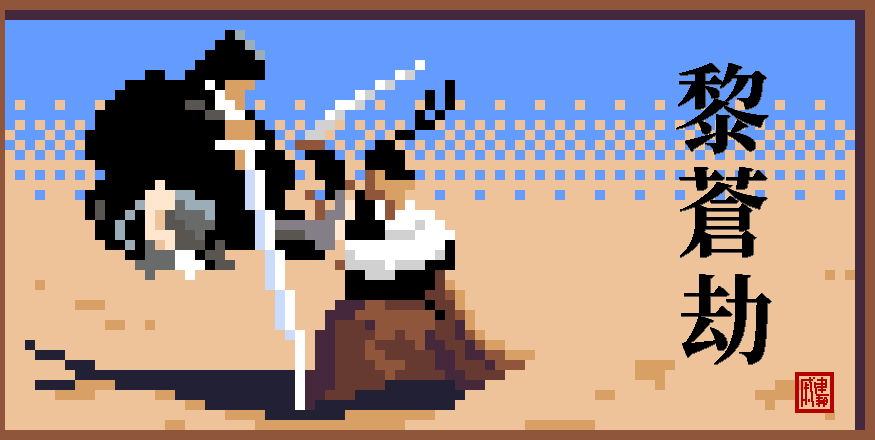調了數個月陰陽,鄭恆舟無論武功眼界都已達到全新境界。轉眼鄭恆舟入獄即將屆滿一年,這一日馮保與他拆解招數,突然之間使出一招從未使過的掌法。鄭恆舟但覺眼前一花,四面八方盡是馮保身影,掌風如同旋風般將他全身無數要害盡數籠罩。鄭恆舟大喝一聲,身形拔起,硬是自掌風間隙處翻了出去。落地之後雙掌一推,便聽「碰」地一聲,四掌交擊,兩人翻飛抖動的衣衫瞬間垂擺而下,紋風不動,便似兩人面對面坐著喝茶一般祥和寧靜。
遠處油燈火光突然一暗,隨即大放光明。鄭、馮二人相視一笑,緩緩放下雙臂。跟著馮保拉鄭恆舟來到囚門旁明亮處,招呼他面對面坐下,說道:「成了。你能擋下我這招八面埋伏,對付魏忠賢便有勝算。」
鄭恆舟喜不自勝,回想適才戰況,說道:「我也覺得如今動念之間隨意揮灑,武功已經練到超乎想像的地步。然而在我心中,魏忠賢似乎依然勝我一籌?」
馮保道:「從前你們強弱懸殊,他只須一招便能將你制服。這種積威恐懼根深蒂固,你總得要再度面對他才能化解。這兩天你好好調息內勁,然後就可以出去辦事了。」見鄭恆舟笑容一僵,笑問:「怎麼?捨不得我?」
鄭恆舟問道:「前輩,你在這黑牢中待了四十年,雖說遠離是非,與人無爭,三餐溫飽,沒有煩惱,但是……我怎麼想都覺得不對勁。總而言之,你這絕頂神功與淵博智慧就這麼埋沒在黑牢裡,豈不太浪費了?」
馮保笑道:「你不知道?真正的絕頂高手是不涉足江湖的,這叫不世出的高人。」
「有這麼說的嗎?」
「你看嘛,」馮保解釋道。「正因為有我這種不世出的高人,你才能在一切看似沒有希望的時候遇上我,進而嚐到這種絕處逢生的滋味,是不是?要是我們這種絕頂高手都死光了,你們這些武林人士不是通通讓魏忠賢給殺乾淨了嗎?」
「有這麼說的嗎?」
馮保哈哈大笑,說道:「這樣說吧,我躲在黑牢,龜縮不出,如此低調還能造就出一個危害天下的大魔頭,以及一個即將拯救天下的大英雄。你說說看,我要是出去了,天下豈有寧靜的一天?」
鄭恆舟嘆道:「我走了,誰來陪你說話?」
「這你就甭擔心了。」馮保道。「只要詔獄沒關,他們遲早會再送人下來。到時候可別讓我又得調教個徒弟出去打你啊。」
鄭恆舟弓身拜倒,說道:「晚輩絕對不會為非作歹,惹前輩操心。」
「起來吧。起來吧。」馮保受他一拜,隨即扶他起身。「我知道你很好。我是和你說笑呢。」跟著望向囚室外的大鐵門,說道:「看來咱們分別的時候提到來了。」
鄭恆舟也聽見黑牢外傳來沉悶的腳步聲,聽來起碼有五、六個人。「吃飯時間還沒到,來這麼多人做什麼?」
「找你吧?」
「說不定是來找前輩。」
馮保拍拍他的肩膀。「小兄弟,多保重。」
鄭恆舟神情感激:「希望有緣再見。」
馮保哈哈一笑:「等你下次給抓回來,咱們便又再見啦。」說完退入牢房角落,陰影之中。
黑牢鐵門開啓,當先兩名獄卒帶路,其後跟了四名錦衣衛官差。錦衣衛帶隊百戶從前是鄭恆舟下屬,此刻恭恭敬敬說道:「鄭大人,白大人有請。」獄卒取出鐐銬,過去要套鄭恆舟,錦衣衛百戶揮手道:「不必銬了。鄭大人真想走,我們攔不住。」
鄭恆舟在黑牢一年,練功夫也練修養,早將一切看得淡了。雖然答應馮保出去處置魏忠賢,但那也不過就是有待完成的一件事情。所放不下者,客婉清而已。他剛入獄時對白草之恨之入骨,如今卻也沒有多大感覺。若是有得選擇,他寧願當作從來不曾認識白草之。不過既然白草之找上門來,他也不得不謹慎面對。此人老謀深算,智計過人,加上心態失常,不能以常理臆度,在鄭恆舟眼中看來,白草之比魏忠賢還要危險。他一言不發,踏出牢房,錦衣衛百戶領著他沿石階離開黑牢。他們在詔獄中讓鄭恆舟沐浴更衣,綁頭髮,剃鬍鬚,換上一套錦衣衛官服,打理整齊後,這才帶離詔獄。
其時已近黃昏,鄭恆舟重見天日,恍如隔世,這才想起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
錦衣衛在詔獄之外安排一支百人隊,護送鄭恆舟前往錦衣衛指揮衙門。錦衣衛個個戰戰兢兢,如臨大敵,不過瞧他們神色,防得卻是外敵,而非鄭恆舟。鄭恆舟心下好奇,不知怎麼回事,不過也不願開口詢問。一路無話,眾人抵達指揮衙門,錦衣衛人人鬆了口氣。鄭恆舟舊地重遊,跟隨帶隊百戶,路過議事大堂,來到內堂之中。白草之於內堂設宴,坐在山珍海味之後,笑盈盈地望著鄭恆舟。
「鄭兄,別來無恙吧?」
「別……」鄭恆舟原以為自己心如止水,哪知道一聽白草之如此問話,火氣又冒了出來。他搖了搖頭,抑制怒火,說道:「別來無恙這四個字,你也好意思問出口?白同知的臉皮真是越來越厚了。」
「鄭兄說笑了。」白草之和藹可親,笑道:「托鄭兄之福,兄弟官運亨通,升任都指揮史已近一年。」他比向桌前座位:「鄭兄請坐。詔獄伙食不好,鄭兄這一年裡瘦了不少,先吃點東西吧?」
鄭恆舟眼望山珍海味,飢餓難耐,口水直流,不過還是搖頭道:「上回喝你一碗茶,此刻依然心有餘悸。你的東西,我不會再吃;正如你說的話,我通通當作放屁。客套的場面別再做了,有什麼屁,放一放。」
「皇上今日駕崩了。」白草之道。
鄭恆舟微微一愣,想起適才錦衣衛草木皆兵的模樣,問道:「怎麼會?」
「病逝。」白草之答。「皇上數月之前於遊玩時不慎落水,其後身體一直不適。兵部尚書霍維華進獻仙藥靈露飲,導致皇上渾身腫脹,臥病不起。皇上駕崩之前,召見信王,說道:『吾弟當為堯舜。』遺詔命信王繼位。」
鄭恆舟搖頭嘆息,心想光宗皇帝便是亂吃紅丸,暴斃而亡,想不到天啟帝竟然還來重蹈覆轍。他說:「那就恭喜你和王爺了。」
白草之微笑不語,舉杯一飲而盡。鄭恆舟見他又去斟酒,諷刺道:「我以為你已戒酒。」
「鄭兄啊,」白草之輕嘆一聲。「北京官場不是個戒酒的地方。這一年來,兄弟見識到官場無數爾虞我詐、背信忘義,思之甚是心寒。」
鄭恆舟道:「我只遇上過一件官場中的骯髒事,直到今日尚在付出代價。」
白草之冷冷道:「我沒殺你,不是嗎?」
鄭恆舟「哼」地一聲,不再答話。
「客氏有孕,懷胎三月。」白草之岔開話題。「如今皇上駕崩,那孩子是不是龍種已經無關緊要。然而十日之前,我們剛自太醫處得知此事時,你知道信王要我做什麼嗎?」
鄭恆舟揚眉不語。
「信王要我行刺客氏。」白草之道。「他不說客氏穢亂宮廷,也不說客氏已婚入宮,此子名份不正,他只是把我叫去,吩咐我殺了客氏。」他又乾了一杯,繼續說道:「什麼振興朝政、憂心百姓……到最後,他也只是想當皇帝而已。」
鄭恆舟冷笑一聲:「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憑什麼認為信王跟你有所不同?白大人,可別告訴我,你的良心突然又長回來了。」
「感慨一下。」白草之笑了笑。「皇上遺詔命信王繼位。他名正言順,我們作臣子的當然不會多說什麼。」
「那錦衣衛何以如此緊張?」鄭恆舟問。「你到底提我出來做什麼?總不可能是你跟信王心裡高興,想要來個大赦天下吧?」
「當然不是。」白草之道。「先王剛剛駕崩,朝廷一片混亂,遺詔依律送往司禮監,等待明日早朝發佈。今晚信王已經入宿乾清宮,安排先王後事。先王無子,王位理應由信王繼承,此乃滿朝文武百官共識。然則信王不喜閹黨,此事並非祕密。閹黨朝臣會往哪兒倒,此刻尚是未知之數。長夜漫漫,魏忠賢會採取什麼行動,誰也說不準。當年穆宗駕崩時,秉筆太監馮保便曾假傳遺詔,這種事情絕非沒有先例。我與禁衛軍指揮史商議妥當,此刻三大營加派侍衛,將乾清宮守得水瀉不通。魏忠賢不可能明刀明槍地不利信王,況且我量他也不會這麼做。魏忠賢向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他若想要採取行動,應當會自遺詔著手。」
鄭恆舟皺眉:「你都說了先王無子,他還能怎麼更改遺詔?難道將王位傳給外姓之人?」
「他可以分派顧命大臣,將王位傳給客氏之子。」
鄭恆舟立刻搖頭:「尚未出世的皇子,豈能繼承王位?何況既然尚未出世,如何肯定是男不是女?」
「照規矩說是不能繼承。」白草之道。「但是魏忠賢勢大,六部皆入閹黨手中。他若在百官支持下硬要這麼幹,也未必不能得逞。至於是男是女,那就不必擔心了。就算生下來是女的,他們也會弄個男嬰坐上龍椅。鄭兄,信王雖然不符咱們期望,畢竟還是名正言順的大明天子。做臣子的私相鬥爭,也還罷了。這種大關節處絕對不能含糊。」
鄭恆舟斜眼看他,不動聲色。這些言語冠冕堂皇,聽起來也像是當年白草之會說的話,只不過如今鄭恆舟壓根就不相信他的鬼話。他問:「你想要我怎麼樣?」
「信王的意思,如果魏忠賢沒有做到興兵造反的地步,咱們也不好主動出擊。以免落人口實,說信王不仁於臣,一登基就屠戮先皇臣子。閹黨勢力龐大,魏忠賢若願歸附,對於信王登基之初穩定政局會有很大的助益。」白草之說著搖了搖頭:「儘管我認為不太可能,但是信王希望我能想個辦法說服魏忠賢宣誓效忠。」
鄭恆舟道:「他也太看得起你了。」
白草之道:「所以兄弟才想找鄭兄幫忙。」
鄭恆舟道:「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鄭兄客氣。」白草之笑道。「你這一年來與馮公公朝夕相處,難道沒有學成一身絕世武功?」
鄭恆舟微感訝異,但想白草之雖然沒來詔獄找他,必定也在獄中派有眼線,隨時回報。他說:「我就算學了絕世武功,也沒有必要幫你。」
「白兄,難道你不了解兄弟苦心?」白草之語重心長。「當日陷你入獄,便是為了要你身入黑牢,搭上馮保,學來一身足以與魏忠賢匹敵的功夫啊。」
「放屁。」鄭恆舟冷冷地道。「你喪心病狂,賣友求榮,這種事情,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揭過的。」
「唉,」白草之道。「鄭兄不肯信我,也是人之常情。我們為了國家社稷著想,自當忍辱負重,承擔惡名……」
「說得比唱的還好聽。」鄭恆舟道。「你要是為國為民,當初怎麼不自己身陷大牢,去練絕世武功,讓我在外面承擔惡名?」
「鄭兄,」白草之滿臉無辜。「那是因為你剛正不婀,不肯賣友求榮啊。」
「算了算了算了!」鄭恆舟揮揮手。「你再怎麼說,我也不會信你。開門見山吧,到底要我幹嘛?」
「跟我去司禮監,逼魏忠賢交出遺詔,向信王效忠。」
鄭恆舟神色一凜:「你要和我聯手對付魏忠賢?」
白草之點頭:「仰賴鄭兄了。」
「東廠和錦衣衛都不會插手嗎?」
「東廠的人有三大營看著,錦衣衛今晚有要事待辦。」
「你們已經要開始肅清閹黨了?」
「看著。」白草之道。「暫時只是看著。」
鄭恆舟沉吟片刻,通盤思考。自己武功雖然有成,但是要找機會行刺魏忠賢依然困難重重。如今白草之支開東廠,兩人聯手對付魏忠賢,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只不過當前情勢都是聽白草之說的,實情如何難以求證。自己貿然出手,難保不會中人奸計。況且有白草之同去,直如芒刺在背,隨時還要防著他反咬一口。人心難測,想來就煩。他才剛出黑牢不到一個時辰,這便已經想要回去了。
「我幫你對付魏忠賢,然後呢?」
「然後?」白草之神色茫然,似乎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然後你報了血海深仇,我也完成了畢生志願。接下來要做什麼,咱們走著瞧。」
「我是說然後你要怎麼處置我?」
「鄭兄,倘若你打得過魏忠賢……」白草之笑道。「我哪裡還有能耐處置你?」
鄭恆舟緩緩點頭,站起身來。「走吧。」
***
兩人離開指揮衙門,前往紫禁城。錦衣衛白都指揮史位高權重,紫禁城中無人不識,無論守衛、朝臣、太監,遇上了通通低頭讓道。兩人進了午門,過太和門、太和殿,自乾清門旁轉入養心殿,來到司禮監秉筆值房外。養心殿位於乾清宮側,而乾清宮外此刻守衛森嚴。白草之特別交代,禁衛軍侍衛不必巡邏養心殿,若是聽見異聲,無須進來查訪。此刻養心殿中空無一人,秉筆值房燈火通明,魏忠賢於其中徹夜辦公。白草之一馬當先,穿越養心殿。來到半途,殿後走出來一名太監,乃是東廠首領太監沈在天。
「原來是白都指揮史。」沈在天道。「魏公公正在處理公文,請都指揮史明日早朝過後再來。」
白草之道:「我有緊急要事與魏公公參詳,請沈公公代為通報。」
沈在天臉色一沉:「魏公公說不見就是不見,白大人不要為難。」
白草之語氣不善:「滾開。」
沈在天勃然大怒:「白草之,你……」
白草之「噌」地一聲,拔劍在手,勢道凌厲地向沈在天劃了過去。沈在天想不到他說翻臉就翻臉,吃了一驚,身體齊膝後折,閃過此劍,跟著左手在地上一撐,右掌擊向白草之胸口。白草之感到寒氣撲面,知道此掌中運上培元內勁。他長劍急轉,劍勢絕妙,「唰」地一聲將沈在天的右掌齊腕斬斷。沈在天難以置信,張口大叫:「廠公!」這個「公」字方才出口,聲音卻已啞了,喉頭鮮血直噴,當場倒地斃命。
養心殿中一片死寂,便連燈火燃燒的啪啦聲響也清晰可聞。
鄭恆舟瞧著地上屍體,低聲道:「魏忠賢當真不帶東廠衛士,獨自在此辦公?」
「更改遺詔,自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白草之道。
「難道他不怕信王差人來對付他?」
「我本想他早已完事,原擬在路上攔截他。」白草之望著值房敞開的門。「不知道他在拖延什麼。」
白草之步入秉筆值房,鄭恆舟跟了進去。
秉筆值房中公文堆積如山,魏忠賢坐在靠牆的一張大書桌後,手持毛筆,專心瞧著癱在桌上的一封詔書。詔書旁印鑑、玉璽擺了一堆,顯見大明朝任何公文都能自這房間內發出,不管是真的公文還是假的公文。魏忠賢始終盯著詔書,眉頭深鎖,對於沈在天之死充耳不聞,似乎難以抉擇該如何更動遺詔。
白草之走到距離書桌五步之外,停下腳步,說道:「魏公公。」
魏忠賢也不抬頭,回道:「白都指揮史。」
白草之揚起長劍指向桌上,鮮血一滴一滴滴在地上,發出嗒嗒聲響,問道:「那便是天啟遺詔嗎?」
魏忠賢點頭:「正是。」
「你還沒改好?」
魏忠賢緩緩搖頭:「在想該怎麼改。」
「不如不要改?」
「你也說不要改得好嗎?」魏忠賢終於抬起頭來,望著白草之。「白大人,這些年來,你三番兩次壞我大事,現在又叫我不要更改遺詔。我魏忠賢到底哪裡得罪你了?」
白草之道:「你禍國殃民,用心不臣,凡是大明有血有淚的男兒都欲除你而後快。我只恨壞你的大事還不夠多,沒能阻止眾多弟兄命喪你手。」
「啊,你是指王恭廠爆炸案。」魏忠賢道。「老夫也真是佩服,死了兩萬多人都炸不死你。那日聽說你沒死,我就知道遇上了厲害對頭。後來我讓洪朝春去害你,想不到又給你給逃過一劫,而且還鹹魚翻身,連洪朝春都讓你鬥垮。」
白草之指節嘎嘎作響,眼中幾欲噴出火來,恨不得立刻揮劍撲上。他嚥下口氣,說道:「皇上要你交出遺詔,宣誓效忠,輔佐他接管朝廷。」
「就是說要我安撫閹黨朝臣,讓他重新任用東林黨人,將閣臣、六部尚書通通置換,順便再度起用袁崇煥,回山海關應付皇太極,等到我沒有利用價值之後,再把我一腳踢開,是吧?」
白草之道:「只要你肯擁立皇上,皇上准你將來告老還鄉。」
魏忠賢再度看回遺詔。「朱由檢這小子,倒也厲害得緊,老夫真是看走了眼。」
白草之道:「遺詔送來司禮監這麼久了,你到底改還是不改?」
魏忠賢放下毛筆,嘆道:「聽白大人口氣,似乎很想看我更改遺詔啊。」
白草之「哼」地一聲:「你表明立場,我便省事多了。」
「如此說來,朱由檢把遺詔送到司禮監,目的就是要我表明立場。」魏忠賢點點頭。「這小子深謀遠慮,比他哥哥強多了。有讀過書,畢竟不一樣啊。」他抬頭看向白草之,問道:「如果我改了遺詔,你又能怎麼樣?難道你以為單憑一己之力對付得了我嗎?」
鄭恆舟一直站在白草之身後,這時聽了此言,向前一步,與白草之並肩而立,說道:「魏忠賢,你還認得我嗎?」
魏忠賢打量片刻,認出他來,神色隨即大變,喝道:「是你!詔獄的人還跟我說你死了!好小子,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我不去找你,你竟然趕來找我送死?今日讓你離開養心殿,老夫不姓魏!」
鄭恆舟罵道:「魏忠賢!師仇不共戴天,今日是我來找你報仇雪恨!幹嘛說得好像我對不起你一樣?」
魏忠賢當真動怒,一掌將面前書桌擊成兩半,順手抄起遺詔,捲成一綑,說道:「你這淫賊,勾引我義女!害她茶不思飯不想,這一年來瘦得不成人樣。我……我……我……」他氣得說不出話,指著鄭恆舟的兩指抖得厲害,恨不得立刻宰了這個小子,偏偏想起客婉貞楚楚可憐的模樣,一時之間又想把鄭恆舟抓去見女兒。
白草之舉起長劍,說道:「魏忠賢,把遺詔交出來,跟我去見皇上輸誠。」
魏忠賢轉頭看他,語氣冰冷:「我計畫多年,眼看就要達到目的,偏偏那昏君在這個節骨眼上死了。你要我讓向朱由檢輸誠,將多年的基業毀於一旦?你要是我,會不會這麼做?」
「那你就改遺詔。」白草之道。「讓天啟遺腹子繼承王位。看看滿朝文武有沒有人服你!」
魏忠賢臉色陰沈,臉頰抖動,目光自白草之飄向鄭恆舟臉上,心中似乎十分掙扎。白草之問:「改呀,還等什麼?你不想向皇上俯首稱臣,就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大明朱氏剩下皇上一人,你想要另外找個小王爺來當傀儡還找不到呢。」
魏忠賢深吸一口氣,依然難以抉擇。白草之與鄭恆舟都深感奇怪,儘管這是性命交關的大事,但以魏忠賢之能,實在不該如此優柔寡斷。白草之突然靈光一現,斜嘴冷笑,緩緩說道:「客氏所懷,並非天啟之子,對吧?」
魏忠賢冷冷看他,並不置答。
白草之哈哈大笑:「想不到啊,魏忠賢,真是想不到啊。既然客氏懷得是你魏家的骨肉,你就更該將他推向王位才對。難道你為了孩子的性命著想,不願讓他尚未出世便淪為權力鬥爭中的棋子?看不出你魏公公還是有血有淚之人啊!」
魏忠賢望向鄭恆舟,依然不發一言。鄭恆舟想到客婉清以身相救,魏忠賢便饒了他,可見此人對家人確實十分看重。卻聽白草之又道:「老實跟你說了,客氏擾亂宮廷,害死張裕妃等數名賓妃與皇子,這些事情皇上都已經查得一清二楚。不管魏公公如何決定,客氏都已經下定浣衣局了。這個孩子,皇上是不會讓她生下來的。」
「白草之!」鄭恆舟喝道。他瞪向白草之,不知道他此時出言刺激魏忠賢究竟是何用意。
魏忠賢左手一揮,將遺詔拋到牆邊書架上,說道:「不管我改不改遺詔,你們兩人都已經知道太多了。」
白草之喝道:「今日要你葬身於此!」說完長劍疾刺,攻其心口。魏忠賢出指一點,盪開長劍。白草之翻身而起,化解魏忠賢的勁道,右腳跟著踢向魏忠賢面門。魏忠賢左掌一翻,擋在臉前,抓住白草之腳底,趁勢向前一推。白草之身如柳絮,隨風飄擺,輕輕落在鄭恆舟身邊。
「好功夫。」魏忠賢道。「夠資格給我提鞋。」說著踏前一步,右掌拍出。他這一掌來得緩慢,招式樸實,但是掌勁酷寒,如同刀鋒撲面,白草之長劍橫劈,當場斷成兩截。鄭恆舟以肩膀頂開白草之,大開大闔的拍出一掌。兩人雙掌交擊,同時後退一步。
魏忠賢臉色詫異,說道:「短短兩年,你如何練出這等功夫?」
鄭恆舟道:「馮老前輩要我問候你。」
魏忠賢難以置信:「那老不死的還沒死?」
「今日為馮老前輩清理門戶!」鄭恆舟說著運起狂沙掌搶攻而上。這套掌法說是狂沙掌,其實已與點蒼派狂沙掌大異其趣,可謂只得其意,卻無其形。魏忠賢曾多次遇上狂沙掌,對其招式變化早已了然於胸。然而眼前的狂沙掌法不但出手老練,妙到巔峰,而且新鮮招式層出不窮,每一掌都自難以想像的方位拍來。魏忠賢見招拆招,以繁御繁,憑藉高深的武學修為,隨意創出新招抵禦,絲毫沒有落入下風。兩人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佩服,都覺得對方屢出奇招,精妙絕倫,每一掌都難以抵擋,偏偏自己又擋了下來。
魏忠賢自從神功大成以來,縱橫江湖二十年,從未遇上如此高手。眼看鄭恆舟不過三十來歲年紀,內勁能夠強到如此荒謬境界,絕不可能自練,肯定另有奇遇,多半是馮保將一身功力過嫁給他,那也算不了什麼。真正讓他佩服之處在於鄭恆舟絲毫沒有辜負這一身內勁,武學上的見識不下於己,遠遠超越招式上的限制,動念之間都能開創新招,而且威力驚人。大凡武學的境界總是遇強則強,魏忠賢二十年來罕逢對手,儘管內力日漸深厚,在招式上早已停滯不前。直到今日一戰,他才又享受到施展渾身解數與人動手過招之樂。拆到兩百餘招之後,兩人在武學上的修為又俱深了一層。
魏忠賢打得渾然忘我,忽見眼角劍光一閃,卻是白草之手持斷劍,嚴陣以待。白草之武功雖精,內力不足,本來魏忠賢並不將他放在心上。然而此刻與鄭恆舟打得興起,若是讓他趁勢偷襲,倒也難以提防。為了不讓白草之以為自己不察外界動靜,他故作閒適,張嘴說道:「小子,你叫鄭恆舟,是吧?」
鄭恆舟眼見自己全力施為,對方竟然還有餘力說話,心中不免大吃一驚。他不願示弱,當下凝定心神,說道:「正是。」
魏忠賢雙掌做圓,連續化解來招,又道:「當年婉貞捨命為你求情,我才答應饒你。想不到你後來又來糾纏不清,惹她傷心。門不當戶不對,你們兩個是不會有結果的。」
鄭恆舟道:「我與客姑娘兩情相悅,不會因為小小挫折而抱憾終生。」
「哼!」魏忠賢斜裡一掌,又讓鄭恆舟提肘化開。「你去年入獄之後,婉貞傷心悲憤,曾三度行刺白草之。這件事情,白草之肯定沒跟你提過了?」
鄭恆舟眉頭一皺,正要發問,白草之已經答道:「鄭兄,我只是擒了客姑娘,把她送回去,可從來沒有傷過她一根寒毛。我明知她是你的心上人,怎麼會去動她?」
「廢話。」魏忠賢道。「你明知她是我義女,怎麼敢來動她?」
鄭恆舟想起白草之當時問他:「你怎麼可以為了一個女人離開我?」時的傷心模樣。這一年來,當天晚上的景象時常在他腦中浮現,但是其中有幾句話他都會刻意忽略。這時他也不知道能說什麼,只好問出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客姑娘……還好嗎?」
魏忠賢連環三掌,都讓鄭恆舟避過。他邊攻邊道:「婉貞以為你死了,整天喝酒,魂不守舍,看得真叫人難過。此間大事一了,我帶你去見見她吧。」
白草之叫道:「魏忠賢,今日拼個你死我活,你當是來攀親戚的嗎?」
「白草之,要攀親戚,你還不配。夠膽就上來,拼拼看誰死誰活!」
白草之眼看兩人聊開,出招都放緩了,深怕鄭恆舟顧念客婉清而手下留情,叫道:「鄭兄,不要忘了師門深仇!你師父讓魏忠賢害得半身不遂二十年,最後終究難逃一劫;你師弟天賦英才,大好前途都斷送在他手上!」
鄭恆舟想到當日柳氏父子捨身救己,心情激動,眼眶紅潤,大喝一聲,以蠻橫內力運起潛龍勿用。這一招威力本已奇大,如今在他驚世駭俗的內力摧動之下,直比當年龍有功與他合力擊爆巨石更加猛烈。魏忠賢不敢怠慢,施展培元神功中的萬元歸心訣,以絕頂內勁凝聚掌力。兩人四掌相交,運勁對峙,登時進入比拼內力的生死關頭。
白草之手持斷劍,一步一步自後方走向魏忠賢。
鄭恆舟眼見白草之舉起斷劍,轉眼便要了結魏忠賢的性命,突然間千頭萬緒,竟不知該不該就此殺了魏忠賢。白草之神色猙獰,手起劍落,叫道:「今日為眾弟兄報仇!」鄭恆舟心裡一急,張口叫聲:「白兄!」這麼著氣息一岔,內力不純,魏忠賢的培元勁如同排山倒海而來,當場將他震得離地飛起。魏忠賢側身跨步,終究躲避不及,讓白草之一劍插入右胸。他奮力反身,一口鮮血噴在白草之臉上,跟著左掌拍出。白草之出掌抵擋,身體如同斷線風箏般直飛而出,重重撞在牆上,緩緩滑落地面。魏忠賢反過左手握住劍柄,使勁拔出斷劍,隨即出手如風,連點前胸後背六大穴道。出血稍止之後,他拉過一張椅子,無力地癱坐其上。
三人接連受創,一時之間誰也爬不起來。
白草之咳出一口鮮血,揚起左手斷臂,卻見創口處滲出鮮血,竟然至今尚未完全癒合。他有氣無力地說道:「魏忠賢……你作惡多端……天底下人人都跟你有深仇大恨。皇上……盼你歸降。我白草之可不願見你……有朝一日……還能衣錦還鄉。」
鄭恆舟運轉內息,逼出一口淤血,緩緩爬起身來,走到白草之身旁。白草之眼看著他,比了比自己的斷臂,說道:「鄭兄……我在王恭廠受的傷,到現在還沒好……眼看這輩子都好不了了。」他兩眼一紅,淚水決堤,泣道:「我對不起你……對不起眾兄弟……對不起……所有相信過我的人。到頭來……我還是不能手刃魏忠賢……」
鄭恆舟跪倒在他身旁,將他扶在懷中。「白兄……」
白草之搖搖頭:「皇上……還有用得著他的地方。為了免除……朝廷一場殺戮……希望鄭兄不要殺他,將他……交給皇上處置。」
鄭恆舟看看他,又看看魏忠賢,一時難以應對。
「答應我。」白草之伸手抓他衣襟。「私怨事小……蒼生為重……答應我。」
鄭恆舟含淚點頭。「我答應你。」
「鄭兄,」白草之將鄭恆舟拉到臉前,擠出最後一絲笑容。「兄弟祝你和客姑娘……白頭偕老。」說完掌心一鬆,就此死去。
鄭恆舟抱著屍首,愣在原地,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反應。片刻之前,他還對白草之恨之入骨,如今陳年往事一幕一幕浮現心頭,一年前那場背叛似乎都變得無關緊要。他長嘆一聲,滴了兩滴眼淚在白草之臉上,慢慢伸出手掌,闔上他的雙眼。
正哀傷著,聽見魏忠賢說道:「婉貞是我親生女兒。」
鄭恆舟抬頭看他,只見魏忠賢胸口一片血紅,不過講話氣息不亂,受傷雖重,多半不會致命。他繼續道:「希望你能好好待她。」
鄭恆舟放下白草之,站起身來,問道:「你打算去向信王輸誠?」
魏忠賢撫著傷口:「天啟駕崩,我便大勢已去,這場仗原來就打不贏。客印月腹中之子究竟是我的還是天啟皇帝的,其實誰也不知。」他仰頭遙想,繼續道:「天傲反我,婉貞也反我,究其原因,還是我多行不義。繼續這條路走下去,即便成就霸業,將來這孩子……只怕一樣要反我。」
鄭恆舟見他老態龍鍾,忍不住想要說什麼話來勸勸他,可是一想到此人做過些什麼事情,嘴裡便半句話也吐不出來。魏忠賢又道:「萬曆怠政、泰昌縱慾、天啟又寄情工藝,渾不將大明江山當一回事。朱家子孫個個昏庸無道,亂七八糟,你說這朱由檢……當真能夠改革圖新,富裕民生嗎?」
鄭恆舟搖頭:「我不知道。」
「就當他能吧。」魏忠賢提氣起身,拿起遺詔。「我要去乾清宮了。你一起來嗎?」
鄭恆舟見他傷勢沉重,絕不可能在禁衛軍守衛之前行刺信王,於是搖頭道:「我要去找客姑娘。」
魏忠賢點點頭:「帶她遠走高飛,離開京城。不要讓她回來找我。」說完步出秉筆值房,穿越養心殿而去。
鄭恆舟在白草之屍首前拜了三拜,隨即離開。
ns 15.158.61.4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