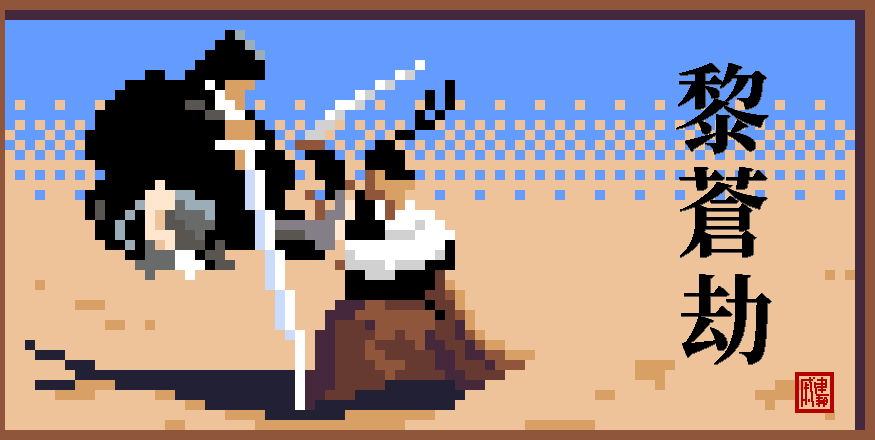追隨白草之而來的錦衣衛高手於王恭廠大爆炸中盡數喪生。鄭恆舟與毛篤信將白草之交給城門守軍照顧,隨即分頭趕往錦衣衛與信王府。信王府不在爆炸範圍內,不過依然受創嚴重。所幸信王爺上朝未歸,打聽後得知其安然無恙。錦衣衛接報後立刻前往城門守軍處迎接白草之僉事,經大夫急救性命無礙。鄭恆舟與毛篤信回歸錦衣衛,全力參與救災。
這一場災,足足救了兩個多月。東廠、錦衣衛、禁衛軍三大營等京師部隊難得攜手合作,軍民一心,共度難關。寧遠錦衣衛鄭千仇百戶(白草之安插鄭恆舟入錦衣衛時所用化名)軍功顯赫,聲名遠播,白草之京師舊部都願跟隨他奔走救災,搬石運屍。到得七月中旬,京城中的屍首清理完畢,坍塌廢墟逐漸理出頭緒,原先的街道也清出來供人行走。儘管百廢待舉,需要重建經年方能盡復舊觀,但至少救災工作終於告一段落了。
每日傍晚,鄭恆舟與毛篤信總會前往白府探視白草之。白草之始終拒而不見。白府下人都說主上重傷未癒,卻終日意志消沉,借酒澆愁,大家想勸都不知如何勸好。一日,鄭恆舟忍耐不住,闖入白府內堂,來到臥房門口,呼喚白草之開門。白草之始終沒有吭聲。鄭恆舟於門外等待片刻,聽見屋內隱約傳出哭聲。鄭恆舟心下惻然,說道:「白兄請多保重。」輕聲離開白府。
罹難的錦衣衛眾弟兄與鄭恆舟師兄弟相處一年有餘,儘管他兩不像白草之那般傷心欲絕,畢竟心中還是蒙上一層難以言喻的陰霾。頭兩個月忙著救災,他們還能不去多想此事。救災工作告一段落後,當日的淒慘景象開始浮現心頭,鄭恆舟連續幾個夜晚於噩夢中驚醒。他也很想借酒澆愁,但總覺得自己必須為白草之保持堅強。白草之總有一天會開門見他,到時候總不成是兩個酒鬼湊在一起「將進酒」。
轉眼已至八月中旬。這一日鄭恆舟與毛篤信在錦衣衛營房中用早膳。兩人自顧自地吃飯,偶爾講上幾句話,也是言語無味,有一搭沒一搭,誰也沒當真在聽對方說些什麼。救災結束後,兩人就一直覺得沒什麼話好講。經歷過這等災變,他們彷彿自人間地獄走過一遭,再也提不起勁兒去管世間俗務。東廠、魏忠賢、努爾哈赤、東林黨,一切都像是上輩子的事。說什麼師門血海深仇,走過王恭廠災變現場,血海也不怎麼血海了。
「大師兄。」毛篤信喚道,見鄭恆舟愣愣地看著粥碗,便又喚了一聲:「大師兄?」
鄭恆舟一回神:「怎麼?」
毛篤信瞧他片刻,說道:「大師兄……要是最近沒什麼事,我想去鳳陽府瞧瞧二師兄的孩子。」
鄭恆舟「嗯」地一聲,緩緩點頭,說道:「也好。這段日子辛苦你了。去透透氣也好。咱們都需要透透氣。」
「那個……大師兄……」毛篤信吞吞吐吐。「我是想……照你之前說的,接了孩子,回點蒼山。我不想再回來了。」
鄭恆舟放下碗筷,擠個笑容。「你既已決定,那就回去吧。這個世道也沒什麼好闖的。見過世面,可以回家了。」
「白兄這個樣子,我實在放心不下。只是……」毛篤信低下頭去。「只是我覺得再不離開這裡,我受不了。」
「白兄有我看著,你不必擔心。」鄭恆舟道。「其實白兄之前和我提過,他也不想你再涉朝廷恩怨。」
毛篤信愣了愣,說道:「那是之前的事了。白兄把咱們三十幾個弟兄個個當作親兄弟看待……當年咱們失去二師兄,尚且如此難受,白兄一下子失去了三十幾個兄弟……我真怕他再也站不起來。」
「此乃心結,站不站得起來,得看他自己。」鄭恆舟道。「你去吧。去了就不要再回來了。白兄有我看著便是。」
毛篤信點頭。「我待會兒去向白兄辭行。」
鄭恆舟揚眉:「今日就走?」
「我一日也待不下。」
鄭恆舟拍他肩膀。「點蒼派交給你了。」
毛篤信站起身來,說道:「大師兄,我在點蒼山等你回來。」說完回房收拾行李。
***
鄭恆舟獨自吃了點粥,讓士兵上來收拾碗筷。正打算再往災區走走,突然有兵來報:「百戶大人,洪都指揮史有請。」
鄭恆舟一愣:「洪大人來指揮衙門嗎?」
那兵回道:「是,都指揮史大人在內堂等候。」
鄭恆舟穿戴整齊,隨即走向內堂。錦衣衛都指揮史洪朝春掌管全國錦衣衛,乃是京城中有權有勢的大人物,平日都在他的侯爵府中應酬滿朝權貴,鮮少前來錦衣衛指揮衙門。上個月全城救災,他曾到過衙門幾次,聽取救災報告。鄭恆舟除了向他彙報外,沒有與他說過半句閒話。他不認為洪朝春知道他是誰,自也沒想到他會一大早跑來指揮衙門找自己。鄭恆舟滿心狐疑,讓內堂守衛進去通報。
卻見洪朝春笑容滿面,迎到門口:「鄭百戶,快進來坐。」鄭恆舟恭敬行禮,跟了進去。一看內堂裡已經擺出一桌酒菜,洪朝春讓他坐在自己身旁,親自幫他斟酒。鄭恆舟受寵若驚,陪他喝了幾杯,問道:「不知都指揮史大人召見,有何指示?」
洪朝春笑道:「聽說鄭百戶跟著白僉事在寧遠當差,立功無數,乃是白僉事最得力的手下。咱們大明最重軍功,但是寧遠戰後,鄭百戶卻沒有封賞。我聽說袁崇煥將軍曾想幫你報功,結果讓白僉事壓下來了。不知道這事是怎麼回事?」
鄭恆舟道:「卑職只知盡心當差,完成上面交付的使命。升官封賞的事情,並非下官可以置喙。白僉事既然沒報,自當是因為下官功勞不顯之故。這是小事,大人不必掛心。」
洪朝春道:「鄭百戶不願爭功,自是美德。但是白僉事知功不報,倒也有違朝廷栽培人才的美意。你看會不會是白僉事……唯恐你的鋒芒蓋過了他,所以才……」
「大人明鑒,決無此事。」鄭恆舟連忙道。「白僉事照顧下屬,那是沒話說的。咱們一班弟兄跟著他出生入死,便是為他丟了性命,誰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白僉事絕對不會存有私心,隱功不報。」
洪朝春笑道:「鄭百戶赤膽忠心,令人佩服。說起你們那班弟兄,聽說他們都在白僉事的指揮下,盡數喪身於王恭廠爆炸案中……」
「大人……」鄭恆舟聽洪朝春語氣,似乎是將錦衣衛弟兄身亡之事怪罪於白草之身上,心裡一急,忍不住插口說道。「大人,當日白僉事率領下屬匆忙入京,便是為了阻止王恭廠爆炸案。此事經過,下官早已呈報上去。大人怎麼……?」
「你那份文我看了。」洪朝春道。「白草之讓下屬先走,自己留在後面。部隊帶兵,應當身先士卒。你說他是留下來交付任務,但是旁人不明就裡,難免會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
「決無此事!決無此事!」鄭恆舟忙道。他這段日子心情低落,平日敏銳的心思都擱下了。如今接連讓洪朝春嚇了幾次,終於有點回過神來。他看著洪朝春,凝神問道:「洪大人,你我皆知實情並非如此。白僉事忠心護國,絕非貪生怕死之徒。大人這些言語,究竟是何用意?卑職愚蠢,還請大人明言告知。」
洪朝春又在兩人酒杯中斟滿了酒,向鄭恆舟敬酒。鄭恆舟無奈,又陪了他一杯。放下酒杯後,洪朝春才道:「鄭百戶是聰明人,本官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恭廠災死傷慘重,損失財物無可計數,不論天災或人禍,它都是大明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災變。錦衣衛得知朝中有少部份官員已經在聯合研擬奏摺,要將此次事件歸罪於當權無道,是以老天降下災難,藉機警告朝廷。不管這種說法有無根據,皇上都不希望有人說此閒話。簡單來說,皇上要人出來扛起責任。」
鄭恆舟難以置信,說道:「白千戶已經失去三十幾名弟兄,又斷了一條胳臂,傷心欲絕,了無生趣……大人竟然還想把王恭廠的事情怪到他的頭上?」
「你看過他那個樣子沒有?咱們帶兵打仗,死幾個弟兄算得了什麼?犯得著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嗎?」洪朝春道:「白草之已經玩完了。你道他還能東山再起?」
鄭恆舟搖頭:「此事乃是後金奸細所為。若要歸咎責任,咱們該派兵去打後金。」
「你打得起嗎?」洪朝春道。「要是打得過後金,咱們會不打嗎?」他搖了搖頭,自懷中取出一份公文,遞給鄭恆舟。「寧遠傳來消息,你們抓到的那個後金奸細事後又再招供,王恭廠地圖是他故意帶在身上洩露給你們看的,目地就是要讓白草之率兵趕往王恭廠。黑龍門炸王恭廠,除了要切斷前線軍火供應,部份原因也是要對付寧遠錦衣衛。這根本是請君入甕的陷阱。你們弟兄之所以會死,完全是因為白草之庸碌糊塗所致。」
鄭恆舟打開公文,仔細閱讀。這份軍情公文屬於錦衣衛密件,不須經過袁崇煥蓋印批示,有可能是他們為了誣陷白草之而捏造出來。然而此事合情合理,就連白草之當日也曾懷疑,是以鄭恆舟也不多加爭辯。他將公文交還洪朝春,認命問道:「洪大人親自來訪,究竟想要下官怎麼做?」
洪朝春道:「我要你更改報告,坐足白草之失職罪名。」
「辦不到。」鄭恆舟直言拒絕。他也不管洪朝春臉色有多難看,只道:「白僉事對我有恩,我絕對不會出賣他的。」
洪朝春誘之以利:「白草之已是廢人,留著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你助我辦成此事,我保薦你升任僉事。」
鄭恆舟道:「我並非貪圖功名之人。就算把洪大人的位子讓給我也不幹。」
洪朝春皺起眉頭,神色不悅,說道:「此事不但皇上要管,魏公公也在施加壓力。」
鄭恆舟心中一凜,問道:「洪大人此言是什麼意思?難道鏟除寧遠錦衣衛,魏忠賢也有一份?」
「鄭百戶,聽我勸,在這京師之地,不要隨便直呼魏公公的名諱。」洪朝春道。「魏公公有無參與此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魏公公想要除掉的人,從來沒有除不掉的。白草之惹上魏公公,已經是個死人了。」
鄭恆舟心下盤算,緩緩說道:「洪大人,這些年來卑職每每聽人提起大人,總說錦衣衛洪都指揮史城府深沉,動向不明,就連魏忠賢也對你忌憚三分。想不到皇上要你陷害白草之,你就幹了;魏忠賢對你施加壓力,你就怕了。我看你根本就是見風使舵的牆頭草。」
「年輕人,作官的一大要訣,就是不要得罪人。」洪朝春語氣冰冷,喜怒不形於色。「只要你能做到『城府深沉,動向不明』這八個字,那麼除了你去討好人家,人家也得來討好你。咱們當官的樂趣就在這裡。」
鄭恆舟冷冷一笑:「白草之不到三十歲,便已官拜錦衣衛指揮僉事,洪大人以為他沒有後台嗎?」
洪朝春笑容一僵,無言以對。白草之迅速竄起,行事神祕,洪朝春早就知道他有後台。特別是上回寧遠軍功,他竟能跳過鎮撫連升兩級,更是洪朝春入錦衣衛以來從未見過的事情。洪朝春身為錦衣衛都指揮史,朝庭之中眼線滿布,竟然查不出白草之的後台是誰,此事一直讓他耿耿於懷。如今鄭恆舟提起此事,正好說到他所憂心之處。他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於是又來斟酒。
這一回,鄭恆舟卻沒有舉杯回敬。他瞧著洪朝春喝酒,緩緩說道:「洪大人,白僉事的後台,絕不是大人願意招惹之人。這個燙手山芋,我勸你還是盡快丟了吧。」
洪朝春嘴硬:「再硬的後台,也硬不過皇上。鄭百戶忠心耿耿,佩服佩服。不過人生在世,除了對友盡忠,也該為自己的前途打算打算。我給你幾天時間考慮此事。你回去好好想想,改天給我答覆。」
鄭恆舟送他到門口,跟著又回內堂,長嘆一聲,自顧自地喝了幾杯悶酒。
***
鄭恆舟步出衙門,往災區而去。才走出兩條街,迎面過來一名男子,攔在鄭恆舟面前,低聲道:「鄭百戶,我們家主人在百花樓擺下筵席,邀你一聚,有要事相談。」鄭恆舟心想還沒到中午,已經吃了兩頓飯,再來一桌豈不撐死?他問:「請問主上是誰?有何要事?」對方道:「鄭百戶到了便知。」鄭恆舟心情不佳,不願招惹閒事,說道:「那就是不到便不須知了。」說完舉步就走。
那人心急,追上去道:「此事與白僉事有關,我家主人請鄭百戶務必前去。」
鄭恆舟嘆了口氣,隨對方前往百花樓。那百花樓位於城東,裝潢菜色在京城裡都算不上是第一流的酒樓。對方相約在此處見面,多半是想要保持低調。此時尚未正午,酒樓中酒客不多。鄭恆舟隨對方上了二樓,來到蓮花廳門外。男子打開廳門,請鄭恆舟進去,隨即關上廳門,留在門外守候。
廳內裝擺設為雅致,靠窗牆邊一整排桌上放了各式盆栽,花香陣陣,清新怡人。正對廳門的牆上掛著幾幅字畫,增添一絲文人雅士的氣息。廳中一大圓桌,擺滿山珍海味。桌旁便只一人,年紀輕輕,氣宇不凡,衝著鄭恆舟一抱拳,打起江湖口吻說道:「兄弟魯莽邀約,打擾鄭兄作息,還望莫怪。」
鄭恆舟心下有底,依然抱拳回禮道:「好說。敢問閣下是誰,有何見教?」
「兄弟朱由檢。」對方往身旁一比,又道:「鄭兄請坐。」
「原來是信王爺。」鄭恆舟來到信王面前,也比了個請。兩人同時就座。
鄭恆舟開門見山:「王爺宴請卑職,可是為了白僉事之事?」
「正是。」信王道。「白僉事忠肝義膽,功在社稷,無論膽識武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如今落魄至此,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鄭恆舟問:「王爺可曾前去探望過他?」
信王道:「本王身份敏感,不便親身探望。我遣了家丁前往,白僉事沒有接見。我遣御醫去給他看手,御醫說他終日飲酒,意志消沉,導致傷口一直無法痊癒。唉,大好男兒,卻讓奸人所害。實在是……」說著搖頭嘆氣。
鄭恆舟道:「白僉事剛毅堅強,終有一天會振作起來。」
信王點頭:「我也希望他能早日振作。然而朝中形勢,瞬息萬變,我有多少大事待辦,不能如此空等下去。」
鄭恆舟問:「王爺有什麼事,或許卑職可以代勞。」
信王道:「我皇兄自從對朝臣結黨鬥爭失望之後,一心縱情工藝,不願理會朝政,將國家大事交到乳母與宦官手裡,弄到如今朝政不修,奸邪當道。我們家裡的人想盡辦法規勸,皇兄始終聽不進去。這次王恭廠爆炸案,實在是前所未見的重大災變。我與朝中僅存的忠義之士商議,都認為應該趁此機會規勸皇兄,將王恭廠災歸於天譴,好讓皇兄反省己身,或許便能精力圖強。」
鄭恆舟懷疑:「如此作法,當真能有什麼效嗎?」
「只要天子力圖振作,便不怕小人弄權。」信王說道。「這一年多來,白僉事與我魚雁往返,對於鄭兄讚譽有加。他說鄭兄武功見識都不在他之下,若是他有不測,叫本王可以信任鄭兄。」
鄭恆舟點頭:「白僉事過譽了。卑職在各方面都及不上白僉事,不過王爺有什麼吩咐,卑職便是拚了性命不要,也必當代白僉事完成使命。」
「有鄭兄這句話,本王就放心了。」信王道。「前日我已讓湖廣道御史江城南打頭陣,上了一道勸王疏。當晚魏忠賢便將他誣陷為東林黨人,逮捕下獄。此刻我計畫讓手下官員上疏聲援江城南,不過其中有些朝臣深怕此事會演變成當年左光斗聲援楊漣案那般,導致無數官員遭受牽連。除非我能保證他們安全,不然他們不敢上疏。」
鄭恆舟沉思半响,說道:「王爺,憑我一己之力,不可能保得眾官安全。」
信王點頭:「是。本來此事由白僉事出面是最好不過。我竭力保薦他升任指揮僉事,便是要他取得足以在此類事務上出力的權位。東廠與錦衣衛雖然存在主從關係,但是錦衣衛指揮僉事畢竟不是小官,東廠首領太監都得要看他面子。只可惜白僉事深受打擊,重傷未癒,實在不適合處理此事。」
鄭恆舟問:「王爺希望卑職怎麼做?」
信王道:「聽說我皇兄打算讓白僉事揹黑鍋,扛下王恭廠爆炸案的責任。」
鄭恆舟點頭:「適才洪都指揮史已來找我提過此事。」
信王道:「我想將計就計,便讓白僉事揹了這個黑鍋。到時候革了他的官職,錦衣衛指揮僉事出缺。以鄭兄在寧遠的戰功,加上這次王恭廠指揮救災得力,本王有把握可以保你出任指揮僉事。」
鄭恆舟心下冰涼,難以置信:「王爺,你這是過河拆橋,打算犧牲白僉事了?」
信王搖頭:「此事有利社稷,白僉事一心為國,不會反對的。鄭兄放心,本王必將極力斡旋,洪都指揮史只能說白僉事見事不明,領導失職,最多就是革職丟官,入獄三年。等他出來之後,本王不會虧待他的。」
鄭恆舟大搖其頭:「王爺,白兄對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你叫我把他賣給洪都指揮史,跟著又來謀他的官職。我鄭某豈不成為忘恩負義的小人?」
「鄭兄,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信王勸道。「個人名聲事小,國家社稷為重。本王在此為天下蒼生請命,希望鄭兄能夠答允。」
鄭恆舟靠向椅背,眼望信王,不知道能說什麼。
信王見他不語,繼續勸道:「保定巡撫劉敬先說只要鄭兄肯出面,他就願意聲援。鄭兄,今日的你,舉足輕重,國家大事都在你一念之間。」
鄭恆舟想了一想,說道:「洪都指揮史給我幾天時間考慮……」
「好。」信王當即說道。「此事事關重大,鄭兄自然不能立即答覆。便請鄭兄考慮兩天,就兩天,不能再拖延了。」
鄭恆舟點頭:「兩天。」
信王起身。「你我見面之事,本王不想洩露出去。我先離開。鄭兄吃點東西再走。」說完推門出去,帶領隨從離開。
***
鄭恆舟隨意吃了幾口菜,便又開始喝起悶酒。一個早上兩度密談,北京官場已經讓他倒盡胃口。洪朝春權謀算計,也還罷了;信王薄情寡義,當真令他心寒。或許信王說得不錯,白草之顧全大局,多半會毫無怨言地揹下黑鍋。但是說到底,有些事情不該做就是不該做,不管有多崇高的理由,還是不該去做。他很想立刻前去白府,將一切通通告訴白草之。但想白草之本已意志消沉,無謂再提這種事情讓他徒增煩惱。只不過……自己夾在中間,根本無力解決,到最後,不管他如何決定,這件事情總是得讓白草之知道。
鄭恆舟心下煩惱,便想來個一醉解千仇愁。他拿起空酒壺,打開廳門,四下尋找跑堂的蹤影,結果目光停留在左首一桌的姑娘臉上,再也移不開去。此女二十歲出頭,瓜子臉,鳳眼薄唇,右眼下有顆美人痣,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客婉清。鄭恆舟只覺心頭一震,當即僵在原地,動彈不得。
客婉清認出他來,亦是目瞪口呆。接著她緩緩起身,離開座位,一步一步朝向鄭恆舟走去。鄭恆舟手足無措,不由自主地退回蓮花廳中。客婉清跟了進去,反手關上廳門,與鄭恆舟倆倆相對。
客婉清心情激動,嘴唇微顫,上前一步。鄭恆舟不再後退,站在原地。客婉清輕輕將額頭靠上鄭恆舟胸膛,哽咽說道:「鄭大哥。小妹天天記掛著你。」
鄭恆舟彷彿置身夢中,緩緩伸起雙手,搭在客婉清背上,說道:「我也是。」
客婉清淚水決堤,背心起伏,輕聲道:「見到你,好像一切煩惱都消失了。」
鄭恆舟輕輕拍她幾下,跟著心中一陣激動,將她擁入懷中。「我也是……」
ns 15.158.61.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