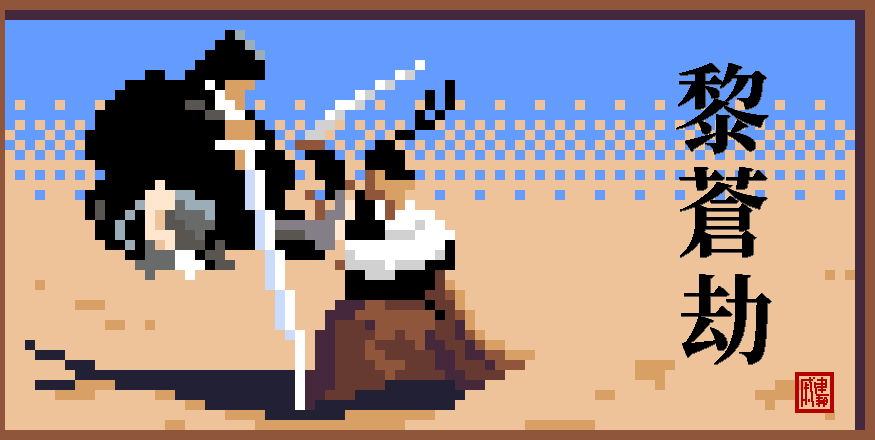鄭恆舟醒來之時,手腳給上了鐐銬,身上衣衫化為布條,全身皮開肉綻,無處不痛。他雙眼讓血塊糊住,須得以手撥眼方能睜開。他身處陰暗囚室,骯髒汙穢,臭氣熏天。眼前站著兩名獄卒,其中一人見他睜眼,一腳踹在他的臉上,啐道:「無恥漢奸,害死這許多人。若非上面吩咐,老子早就把你打死!」
鄭恆舟道:「我不是……漢奸……」
另一名獄卒蹲下身去,一拳捶落,打得鄭恆舟門牙鬆動,滿嘴鮮血。「罪證確鑿,還想狡辯?你勾引後金奸細,陰謀爆破王恭廠火藥庫,炸死京城兩萬餘人,還說自己不是漢奸?」
鄭恆舟叫道:「我沒有!」
「沒有?」獄卒拉起他的衣襟,惡狠狠地道:「錦衣衛已經查出你本名叫作鄭恆舟,曾經殘殺軍官、劫持欽犯,乃是點蒼派的亂黨。你若不是奸細,何以化名混入錦衣衛,於前線戰事吃緊處蟄伏一年有餘?」
鄭恆舟說:「我是亂黨!不是奸細!」
獄卒又是一拳。鄭恆舟噹啷一聲,架開此拳,隨即一腳使勁,將另外一名獄卒踢出牢房。先前的獄卒連忙後退,反手拔刀,鄭恆舟一撲而上,意欲奪刀。無奈腳鐐釘死在牆上,他撲到中途便即倒地。獄卒揮刀砍下,鄭恆舟以手上的鎖鏈招架。獄卒連砍三刀,都讓鄭恆舟架開,砍到第四刀時,鄭恆舟運起內勁,獄卒拿捏不住,大刀脫手而出,竄出囚室,撞在牆上。那獄卒見他厲害,連滾帶爬衝出囚室,取鑰匙緊鎖囚門。鄭恆舟掙扎向前,鎖鏈噹啷作響,叫道:「我是冤枉的!叫白草之過來見我!白草之!你不是人!給我過來!」
那獄卒站在門外,驚魂未定,罵道:「好漢奸,果然厲害,別以為老子治不了你。」
鄭恆舟只是叫道:「叫白草之來見我!我是冤枉的!叫白草之來見我!」
另一名獄卒這時已經帶了五、六個人下來,人人手持粗大棍棒。眾獄卒打開囚門,擠了進去,同時舉起棍棒往鄭恆舟身上招呼。囚室狹窄,鄭恆舟又行動受限,當場給打個頭破血流。
眾獄卒圍毆片刻,見鄭恆舟躺在地上,氣息微弱,怕把犯人打死了,於是住手。眾人離開囚室,原先那獄卒鎖上囚門,說道:「漢奸,你道這裡是哪裡?京城詔獄啊!冤枉?這裡人人都說自己冤枉,還有半數犯人確實冤枉,我可從來沒見有人放出去過。你慢慢叫吧。」
鄭恆舟神智不清,嘴裡兀自有氣無力地道:「白草之……過來……見我……」
此後數日,眾獄卒照三餐毆打鄭恆舟。鄭恆舟皮開肉綻,樣貌恐怖,不過都是皮外傷,沒有傷到筋骨。一連打了五天,這才稍微收斂。到第六天上,獄卒將他提入刑房,架上刑架,隨即恭恭敬敬地讓道兩旁。刑房門開,走入一名官員。鄭恆舟睜眼細看,認得是錦衣衛洪都指揮史。
洪朝春上下打量鄭恆舟,向獄卒道:「怎麼把犯人打成這個樣子?」
獄卒惶恐道:「回大人,此人傷天害理,弟兄們氣不過,這才動手教訓他。」
洪朝春道:「弟兄生氣也是人之常情。這人我還有用,別把他給打死了。你們先出去吧。」
「是,大人。」兩名獄卒離開刑房。
洪朝春站在鄭恆舟面前,皮笑肉不笑地道:「鄭百戶,這詔獄裡還住得慣嗎?」
鄭恆舟「呸」地一聲,說道:「洪朝春,你明知我是冤枉的。快點放我出去。」
洪朝春道:「鄭百戶,你是皇上欽點的漢奸,冤枉兩字,可是沒人敢隨便說的。」
鄭恆舟問:「你待怎地?」
洪朝春道:「我要知道是誰在給白草之撐腰。」
「不知道。」
洪朝春瞇起雙眼,冷冷說道:「鄭百戶有情有義,洪某深感佩服。然而那白草之忘恩負義,賣友求榮,你又何必跟他講什麼義氣?」
鄭恆舟道:「你有求於我,這才讓我活命。我要是把人供了出來,還有性命在嗎?」
洪朝春道:「只要你供出來,我便代你向皇上求情。」
「求情?」鄭恆舟不信。「你將王恭廠兩萬餘條人命誣在我的身上,求情?我倒要看看你怎生求法。你錦衣衛偽造證據,誣賴好人,想要隻手遮天,沒有那麼容易。炸王恭廠可是大明開國以來最重大的刑案,待得三法司會審的時候,我把你們通通抖出來!」
「哈!」洪朝春大笑。「三法司會審?錦衣衛承辦的案子什麼時候輪到三法司會審了?我洪朝春說一句話,管他刑部、都察院還是大理寺,誰敢跟我來吭一聲?況且此案還是皇上親自交辦。鄭恆舟,搞清楚,就算我現在就把你一刀殺了,也不會有人來問我一句。」
「來啊,有種一刀殺我了啊!」鄭恆舟挑釁道。「這回白草之偵破王恭廠案,上面如何封賞?加封爵位嗎?還是直升指揮同知?」一看洪朝春臉色難看,他也來個哈哈大笑。「看來白草之已經爬到錦衣衛第二把交椅啦!洪大人,你當年升同知的時候,貴庚啊?吏部有沒有人告訴你他這官職是誰升的?你不盡快找出白草之的靠山,他遲早會爬到你的頭上。」
洪朝春右掌直劈,將鄭恆舟的左臂骨劈斷。鄭恆舟劇痛難耐,但卻咬緊牙關,不肯叫出聲來。洪朝春抓起他的下顎,狠狠說道:「是誰在幫白草之撐腰?給我說!」
鄭恆舟額頭冒滿汗珠,喘息道:「放我出去,我就告訴你。」
洪朝春搖頭:「我就跟你直說了。皇上已經詔告天下,指名道姓地說王恭廠案是你幹的!聖旨既出,再也沒有更改的餘地。你就算不被處死,這輩子也不必妄想離開詔獄。」
鄭恆舟經歷這一番權謀背叛,心思已比之前明白。儘管滿腹冤屈,忿忿不平,夜深人靜時還是仔細思量。他早知道洪朝春為了查出信王身份,遲早會來找他,也早已想好該如何應對。他道:「湖廣道御史江城南早已上了勸王疏。白草之既然得勢,一干非閹黨的朝臣此刻必已紛紛上疏聲援。皇上栽贓一個錦衣衛便想草草了結王恭廠案,哼哼,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洪朝春問:「那又怎樣?」
「只要皇上被迫下達罪己詔,你就可以幫我趁機翻案。」
所謂罪己詔乃是皇帝在朝政動蕩、政權不穩或是天災嚴重的時候為了反省自責所下達的詔書。通常在罪己之後,臣子便會趁著皇帝痛定思痛的機會提出改革建議,而皇帝也會為了呼應罪己詔所宣告的意義而廣納建言。洪朝春大搖其頭,說道:「你是叛國之罪,罪無可恕。即便皇上下詔罪己,也輪不到你來翻案。」
「那就是你的問題了。」鄭恆舟道。「你能捏造證據關我進來,自然也能捏造證據幫我翻案。你可要想清楚,白草之此人厲害得緊。他這次連我這麼親近的弟兄都給賣了,明白宣告他要全心投入北京官場的決心。你千萬不要心存僥倖,以為他還有絲毫良知。他已經六親不認了。你玩不過他的。」
洪朝春冷冷凝望他片刻,最後說道:「你把人供出來。我保你活命。」
「活命?在這詔獄裡渡過殘生?」
「我最多只能做到這樣。」
「那就等著讓白草之鬥垮吧。」
洪朝春深吸口氣,緩緩道:「我三天後再來看你。」說著走出刑房,對門口的獄卒道:「給我打。」說完便即離開。
***
此後每隔三天,洪朝春便來詔獄提審鄭恆舟一次。每次總是問一樣的問題,得到一樣的答案。獄卒還是會毆打鄭恆舟,不過既然知道是洪大人要問話的人,他們也不敢把他給打壞了。鄭恆舟的左臂讓洪朝春打斷,他們也立刻找大夫進來醫治。到得後來,眾獄卒也只有在洪朝春來前打個幾下,添點新傷痕交差了事。如此過了近一個月,鄭恆舟已漸漸習慣住在詔獄中的日子。
開始幾天,他恨極了白草之,每天心裡想的就是出去之後要如何報仇。後來洪朝春來了,他又把心思放在利用此人逃離詔獄之上。過了二十來天後,心境逐漸冷靜下來,客婉清的容顏開始浮現他的心頭。他不知道白草之會不會去對付她,也不知道魏忠賢能不能夠保護她。想到自己竟然期待大仇人魏忠賢去保護自己心愛的女人,鄭恆舟就覺得整個世界天翻地覆,再也沒有道理可言。
這一天被提到刑房,洪朝春關緊房門,朝鄭恆舟走來。鄭恆舟冷眼看他,只覺得此人老態畢露,竟連頭髮都比第一次見面時要白了不少。他哈哈一笑,說道:「洪大人,近來煩惱不少啊。」
洪朝春竟然沒有反唇相譏,只是拉把椅子,在鄭恆舟面前坐下。
「有什麼事情不能在侯爵府裡想,一定要跑到牢裡來想?」
洪朝春抬頭瞪他一眼,站起身來,嘆了一聲,說道:「當初你要是接受本官提議,出面誣陷白草之,今日我們兩人都不會走到這個地步。」
鄭恆舟倒感訝異:「你這麼快就讓他逼上絕路了?」
「此人真乃官場奇葩,天賦英才。」洪朝春道。「他為了聲援勸王疏的事情暗中與東廠較勁。皇上於日前下詔罪己,他竟然馬上又能聯合魏忠賢與禁衛軍三大營指揮史來對付我。我現在已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要一步踏錯,立刻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洪朝春揚眉瞧他,說道:「我死了,你便再也別想出去。」
「那咱們是命運與共了。」鄭恆舟道。「放我出去,我或許能夠救你性命。」
「如今就算知道白草之的後台是誰,我也未必能夠逃過一劫。」洪朝春無奈嘆息。「想我多年經營官場,結交無數權貴,如今有難,竟然沒有一個人膽敢出面幫忙。」
鄭恆舟冷笑一聲。「你等太久,手腳太慢。朝廷都已落入魏忠賢手中,你還在跟人家城府深沉,動向不明。這不是自作自受嗎?」
洪朝春緩緩點頭,似乎認為鄭恆舟所言很有道理。片刻過後,他回過神來,壓低聲音說道:「唯今之計,只有助你逃獄了。」他不待鄭恆舟驚訝,揮揮手繼續說道:「明日會有人來提你,押往刑部大牢密審,評估有無三法司會審的必要。我安排了一批手下劫持囚車。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逃出來後,立刻供出幕後靠山。大家的性命都擲在這一把上了,你要是再給人抓回來,連我都死定了。」
鄭恆舟問:「我怎麼知道供出來後,你的手下不會殺我滅口?」
「你只好相信我。」洪朝春道。「不然就相信自己能夠殺光我的手下逃走。」
「洪大人倒很坦白。」
「我要是你,也不會相信我。」洪朝春道。「只能說在這個節骨眼上,我不打算節外生枝,自找麻煩。明日午後。養足精神。」說完開門離開,吩咐獄卒直接將鄭恆舟帶回牢房,不必毆打。
這一夜,鄭恆舟養精蓄銳,一夜好眠。夢中,他與客婉清攜手出城,從此遠離是非,開心度日。
第二天,刑部的人沒有出現。
第三天也沒有。
第四天,洪朝春沒有按照慣例來找鄭恆舟。鄭恆舟心下冰涼,知道洪朝春多半出事了。他說服自己懷抱一絲希望,說不定洪朝春只是一時未能安排妥當,再過幾日就會等到消息。
等到第七天上,獄卒又將他帶往刑房。鄭恆舟滿心期待可以看見洪朝春,結果卻見兩名獄卒將自己綁上刑架,關上房門,隨即一人拿起一把刑鞭,神色猙獰地走了過來。
鄭恆舟給獄卒打熟了,知道左邊那個姓毛,右邊那個姓鄧。就看那姓毛的獄卒扯扯刑鞭,奸笑道:「姓鄭的,在等洪大人嗎?」姓鄧的道:「苦等哇,苦等。」姓毛的道:「改天你去跟閻羅王打探打探洪大人的消息吧。」姓鄧的道:「代我們向他問候一聲。」
鄭恆舟心裡涼了半截,問道:「你們想怎麼樣?」
「怎麼樣?」姓毛的說著將刑鞭一扔,順手抄出懷中一把短刀,獰笑道:「東廠長官要我送你去見洪大人!」說著舉起短刀,順勢砍落。
姓鄧的連忙撲上,一把攔下姓毛的,急道:「毛大哥快住手!」他壓下姓毛的短刀,將他拉到一旁,問道:「怎麼東廠要殺姓鄭的嗎?」
姓毛的說:「是呀,怎麼樣?」
「這不對吧?」姓鄧的道:「錦衣衛要咱們留活口啊。」
「有這種事?」姓毛的道:「這不成吧?錦衣衛誰說的?」
「是白大人下的命令。」
「白大人?」姓毛的皺眉。「白大人鬥垮了洪大人,多半將會接任錦衣衛都指揮史。這個人,咱們可得罪不起啊。」
姓鄧的問:「東廠又是誰下的命令?」
「沈在天公公,說是奉了魏公公之命。」
「魏公公咱們也惹不起呀!」
兩人面面相噓,一時沒有主意。片刻過後,同時轉頭看向鄭恆舟。姓毛的道:「這傢伙什麼本事,能夠得罪這麼多人?」姓鄧的道:「白大人當初就是拿了他才開始得勢的。毛大哥,其實依照咱們當差的經驗,這人擺明是冤枉進來的。照說白大人冤他入獄,應該急欲除掉此人,有什麼理由留他活口呢?」
「是了!」姓毛的恍然大悟,一拍手掌說道:「這你就有所不知啦。我之前就聽說傳聞,原來那白大人性好男色,姓鄭的乃是他的相好。這是感情糾紛啊。錦衣衛的弟兄都說,白大人為了出賣這姓鄭的哭了好幾天呢!」
「胡說八道!」鄭恆舟大怒。「我跟白草之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是了,是了。」姓鄧的大點其頭。「情人翻臉,原是世上最深刻的仇恨。這姓鄭的相貌堂堂,體格精壯,白大人會喜歡上他也是人之常情。」
「放屁!」鄭恆舟怒不可抑。「我跟白草之清清白白,你們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姓毛的說:「好了,別說了。這話要是傳到白大人耳裡,咱們兩人吃不完兜著走。」他瞧向鄭恆舟,喃喃說道:「魏公公固然得罪不起……要是殺了白大人的相好,咱們日後也別想在京城裡混了。」
「殺,還是不殺?」姓鄧的問。「就是這個問……」
「我看只有一個辦法了。」姓毛的道。「把他丟入黑牢吧。東廠的人問起,就說已經殺了。白大人要問起,咱們再帶他去會老情人。」
姓鄧的大驚失色,顫聲道:「毛大哥,黑牢……你下去過嗎?我聽說……聽說那老怪物專吃獄友啊?」
「不要人云亦云。」姓毛的道。「人家只吃過一次而已。那是新來的伙房不知道要給黑牢送飯,馮老爺子餓得慌了才吃獄友。況且他也不是殺人來吃,是人家先餓死了才撕來吃的。」
「毛大哥,」姓鄧的道。「你這麼說我還是很怕啊。」
***
兩名獄卒壓了鄭恆舟,走到牢房深處,打開一扇鐵門,點起兩根火把,沿石階而下,直到空氣又悶又熱,瀰漫濃厚土味,這才來到石階底端。兩人取出鑰匙,又打開一道厚重鐵門,步入另外一間牢房。此地深入地底,暗無天日,全憑火把照明。姓毛的插好火把,在門口油燈裡添了燃油,這才壓著鄭恆舟來到一扇囚門之前。
「馮老爺子,」姓毛的說道。「我帶了個獄友來陪你解悶。」
黑牢中一個中氣十足的蒼老聲音說道:「這麼客氣?」
「是呀。」
「放進來吧。」
姓毛的打開囚門,將鄭恆舟推了進去。「姓鄭的,能見到馮老爺子是你的福氣。要懂得敬老尊賢,不要得罪人家啦。」說完帶著姓鄧的匆匆離開。
鄭恆舟站在牢房油燈旁,戰戰兢兢地望著深邃陰影。陰影中彷彿有人影晃動,但是鄭恆舟說什麼也看不清楚。他突然看見一條腿步入火光中,心裡一驚,當即後退一步。
對方見他受驚,便也不再逼近,說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呀?」
鄭恆舟不答,只是一直盯著那條腿看。
對方將腿縮回火光外,又說:「說句話嘛。不是說要敬老尊賢?」
鄭恆舟冷冷道:「痛痛快快把我殺了便是。不要再耍奸計害我。」
「可憐啊,又是一個給人害到不再信任他人的孩子。」那人說。「這黑牢裡便只你我兩人。想要找人聊天,開口就好了。」說完退回陰影之中,不再發出任何聲響。
鄭恆舟等待片刻,見他不再說話,便也不去理他。他走到牢門旁,打量那盞油燈,適才添的燃油不多,只怕燒不了多久。他就著燈火瞧著牢門牢欄,黑黝黝地觸手冰涼,看不出是何金屬所鑄。他深吸一口氣,暗運內勁,雙手向外一分,當即扯斷手上鎖鏈。他拍拍牢門,看準位置,紮穩馬步,一招潛龍勿用推了出去。牢門晃了一晃,牢欄絲毫沒有彎曲。
鄭恆舟跟著又在附近的石牆上拍了幾掌,都是實心牆壁,沒有拍出半點石屑。他沉吟片刻,認定還是牢欄脆弱,於是走回門旁,運起掌力,一掌一掌地拍了下去。這一拍,直拍到燈火熄滅,伸手不見五指為止。鄭恆舟又拍了幾掌,休息片刻,正待再拍,黑暗中突然感到一片死寂,除了自己的喘息聲外,再也聽不見任何聲息。剛剛那名老者彷彿憑空消失了般。
鄭恆舟頭皮發麻,毛骨悚然,忍不住便要出聲相詢。
「小兄弟,不要怕黑。黑暗傷不了你;恐懼卻能讓人發狂。」
鄭恆舟一聽這聲音還是發自適才的位置,暗自鬆了口氣,原地坐下來休息。對方見他不答腔,也就不再言語。兩人就這麼在黑暗中一言不發地坐著。
不知過了多久,鐵門外傳來沉悶的腳步聲。鄭恆舟靠向內牆,遠離囚門。便聽見鐵門開啓,走入一名老者。對方插好火把,在地上放下一個餐籃,於油燈裡添了點燃油,隔著牢欄將餐籃裡的兩大碗飯菜放入囚室,拾起地上用過的餐具,隨即拔出火把,關門離開。鄭恆舟緩緩走過去,拿起一副碗筷,其中青菜豆腐,還摻了幾條肉絲,聞起來倒也挺香。他腹中一陣飢餓,正要開動之時,想起地上還有一副碗筷。
鄭恆舟走到燈火邊緣,將手中碗筷往前一遞。黑暗中伸出一條皺紋滿布的蒼白手臂,輕輕接過碗筷。鄭恆舟一言不發,走回囚門旁邊,開始吃飯。
黑暗中傳來一聲輕笑。「小兄弟嘴裡挺硬,其實心底還是敬老尊賢嘛。」
鄭恆舟矇著頭吃飯,沒有心情理他。其實瞧起來,這老頭多半是在此囚禁多年的人犯,不會是獄方安排折磨他的人。只不過他總覺得去跟這人交談,彷彿就表示他這輩子也要在此暗無天日的黑牢裡耗下去般。他還不打算放棄希望。
吃完飯後,他上前去檢視適才掌拍的囚門牢欄,一點讓降龍神掌轟過的痕跡都沒有。他抓起兩根牢欄往外一扯,那囚門還是絲毫沒有反應。這情況就跟當年練潛龍勿用掌拍大石一樣,他也不灰心,運起掌力又拍了幾十掌。眼看油燈漸暗,他回過頭去找個舒服的地方躺下去窩著。
日復一日,他就在這般吃飯練功的情況下過日子。自從身入黑牢之後,再也沒有獄卒提他去打,彷彿他從此遭受世間遺忘了般。鄭恆舟心無旁騖,專心練功,每日來來去去就是那六式降龍神掌,一掌一掌拍在囚門欄杆或是石壁上。那老者偶爾跟他閒聊幾句,鄭恆舟始終沒去理他。黑牢中不分日夜,只能憑藉每日兩餐送飯的次數來計算時日。約莫過了一個月餘,一日鄭恆舟擊出一招雙龍出海,兩掌分別將兩根欄杆拍得嗡嗡作響,不住共鳴。鄭恆舟自覺功力大進,低頭看著雙掌,嘴角不禁露出罕見的微笑。
卻聽那老者說道:「小兄弟,你這降龍十八掌當真練得亂七八糟,便是再練個十年也無法脫離這玄鐵牢籠。」
這些日子以來,老者總是客客氣氣地逗他說話,從未如此澆他冷水。鄭恆舟心中不忿,起心反唇相譏,跟著突然想到這老者如何知道自己使得是什麼功夫?他終於開口:「我這降龍神掌乃是丐幫幫主親傳,怎麼會練的亂七八糟?」
老者「嘖嘖」兩聲,說道:「怎麼這套掌法改名叫作降龍神掌了嗎?是了,定是嫌它不足十八掌,打起來不夠氣派。小兄弟,你說這掌法是丐幫幫主親傳,只怕有點不盡不實。你這六招降龍掌中,便只一招潛龍勿用使得有模有樣,深得名師傳授。其他五招,得其意而無其形,似乎只學會了內功口訣,招式卻未獲得名師指點。我這麼說,沒冤枉你吧?」
鄭恆舟心中驚訝,忍不住道:「前輩這麼說,難道練過降龍神掌?」
「那哪需要練,用看的就知道了。」老者說著走出陰影,步入燈火之下。相處月餘,這是鄭恆舟第一次得見此人模樣。只見他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皮膚白到彷彿沒有半點血色,鄭恆舟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年邁之人。然而年邁歸年邁,此人目光銳利,氣勢逼人,散發一種老而不衰的感覺。光看外表,怕沒有一百幾十歲了,但是加上這份氣度,彷彿是個正值壯年的前輩高人。他來到鄭恆舟面前,比劃了他剛剛雙龍出海的模樣,說道:「你這雙龍出海,力分雙掌,功力聚而不散,很是難得,可見你內力運勁的法門學得十分到家。問題是你這兩手肘都擺得太高了點,一推出去力道便少了三分,掌法上的威力可打了折扣啊。」
鄭恆舟道:「我也知道放低手肘威力更強,但是我出掌之時,掌勁自手臂傳自掌心,硬是會牽引手肘姿勢。要是刻意壓低,出招便不夠快捷。我與現任丐幫幫主參研此招,對於這個環節始終百思不得其解。」
「喔,那沒什麼,就是你們筋骨沒有特別練過。上任幫主沒傳你們易筋之術,就讓你們在那瞎摸。這麼說來,這位幫主是臨危傳功,托你將丐幫神功代傳給繼任幫主了?」
「是。」
老者點點頭。「潛龍勿用威力奇大。他悉心調教你這一招,多半是因為你們兩個被困在這種地方,需要憑藉蠻力離開。」
鄭恆舟心下佩服,說道:「前輩料事如神,如同親見一般。」
老者笑呵呵道:「什麼料事如神?料事如鬼罷啦。」
鄭恆舟好奇問道:「前輩對降龍神掌如此熟悉,難道是丐幫高人?」
「不是。」老者搖頭。「我只是曾經和丐幫幫主打過幾架而已。」
「是龍幫主嗎?」
「誰?」
「龍有功,龍幫主?」
「不是。」老者道。「老夫入獄乃是萬曆十一年的事情。算算也快四十年了。萬曆皇帝還在嗎?」
鄭恆舟搖頭:「當今皇上年號天啟,如今是天啟六年。」
「是囉,古來天子,很少能在位這麼久的。」老者側頭想想。「我當年倒是聽過龍有功這號人物。那時候啊,他還是丐幫五袋弟子。現在他是幫主了嗎?」
「是前任幫主。龍幫主逝世至今也已快要兩年了。」
「世道混亂,人生苦短啊。」老者感慨道。「總要待在這種地方,才能像老夫一樣長命百歲。」
鄭恆舟一拱手:「晚輩點蒼派鄭恆舟,拜見前輩。這些日子以來,晚輩多有無禮,還請前輩莫怪。」
「在這黑牢裡,客套什麼勁兒?」老者哈哈一笑。「原來你是點蒼派的?這一個月來,可沒見你練過半點點蒼派的功夫啊?」
鄭恆舟深感慚愧。「晚輩點蒼功夫練不到家,降龍神掌反而……」
老者道:「丐幫降龍神掌威力雖強,你點蒼派的勁蒼訣練到深處,也未必輸給它了。」
鄭恆舟心裡惶恐,忙道:「還望前輩指點。」
「指點?」老者問。「在黑牢之中,指點你功夫做什麼?難道你還想要出去嗎?」
鄭恆舟心下一沉,轉頭看向玄鐵牢欄,嘆道:「難道真的出不去了嗎?」
老者走到牢欄前,雙手各握一根,使勁一拉,牢欄應力而彎,當場露出一條足以供人通過的大縫。鄭恆舟目瞪口呆,卻聽老者說道:「要出去當然可以。問題是你出去要做什麼?外面人心險惡,風風雨雨,不如待在黑牢裡消遙自在,也不必擔心有人陷害。」
鄭恆舟愣愣看著凹彎的牢欄,跟著轉向老者,問道:「前輩,你究竟是什麼人?受到什麼冤屈,讓人給關在黑牢四十年?」
老者笑著說道:「老夫姓馮名保,乃是萬曆初年的提督東廠。一生壞事做盡,罪大惡極,被人關在這裡,實在恰當之極,誰也沒有冤枉我了。」
鄭恆舟大吃一驚,跳起身來,問道:「你……前輩便是……顧命太監馮保公公?東廠的培元神功就是前輩所創?」
「是吧?罪大惡極。」馮保笑道。「這麼多年了,老夫自報姓名,一樣嚇得你跳起來。」
「但是……」鄭恆舟道:「他們說你老早便已死在獄中啦。」
「喔?小兄弟,你不知道?」馮保道。「你也已經死在獄中一個多月啦。」
鄭恆舟雙腳一軟,坐倒在地,瞧瞧身處環境,知道他說所言不虛。自己被關在這個暗無天日的黑牢裡,詔獄的人必定向外宣稱他已死去。不知道客婉清聽說自己死訊的時候會怎麼樣?想到客婉清傷心欲絕的模樣,鄭恆舟不禁一陣心痛,目光隨即轉向牢欄大縫上。
馮保道:「這縫是我拉的。你想出去,自己拉條縫。」
鄭恆舟心中激動,說道:「前輩……」
馮保道:「憑你現在功夫,就算出得了黑牢,也闖不出詔獄。就算出了詔獄,陷害你的人還在外面,你又要怎麼對付他們?」
鄭恆舟心下無力,只道:「我只想要帶著意中人遠走高飛,從此不問世事。」
「喔,原來你在外面有個意中人,那又另當別論了。」馮保笑道。「既然為了意中人,你更不應該現在出去。現在的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怎麼帶人家遠走高飛?」
鄭恆舟著地拜倒,說道:「還請前輩指點!」
馮保順手一揮,鄭恆舟只感一股大力襲體而來,整個人當場站起。馮保道:「指點你功夫,不過就是打發時間,犯不著這麼拜來拜去。」他側頭沉思,片刻後道:「降龍十八掌乃是至剛至陽的功夫,練到深處,當可無敵於天下。只不過你才學了六掌,再怎麼練也就是半調子了,經我調教,循序漸進地練下去,五年之後當可離開黑牢。」
鄭恆舟道:「五年啊?」
「嫌短是不是?」馮保搖頭:「練功夫想要速成,便會入了魔道。」
「是,這話晚輩聽說過。」
「不過說起來,你們點蒼派的勁蒼訣源自道教一流,與老夫的功夫殊途同歸。咱們自這方面著手,說不定更有練頭。」
鄭恆舟眼睛一亮,連連點頭,當下將勁蒼訣中他所想不明白的疑點提出來請教。勁蒼訣由毛篤信轉交給他自修,並未經過師父指點,有些地方練起來總是不大對勁。其後他雖與毛篤信相處一年有餘,但是一來錦衣衛事務繁忙,二來他把時間都花在苦練降龍神掌上面,是以勁蒼訣始終沒有弄熟。馮保博學多聞,武功精湛,儘管沒有學過勁蒼訣,卻也解釋得頭頭是道,彷彿已經教授此功數十年般。此後他為鄭恆舟闡釋武學之道,教了他許多聞所未聞的門道。鄭恆舟學武天資本已極高,如今遇上名師,開了眼界,進境只能以飛快形容。馮保見他學得快,心裡高興,教得也很起勁。如此匆匆數月,兩人專心練功,日子倒也不怎麼難過。
閒暇之餘,馮保也會講點武林逸事,鄭恆舟便跟他說些朝廷近況。馮保聽說魏忠賢權傾天下,只聽得搖頭嘆氣。「當年我任提督東廠,便讓人說過宦官禍國。想不到跟魏忠賢比起來……差得遠了。」鄭恆舟問:「前輩識得魏忠賢?」馮保點了點頭,不再多說,鄭恆舟也就沒有多問。
這一天送飯老者在油燈裡換了新的燈芯,光線明亮了些,鄭恆舟練功練到一半,在一面牆上看見一個掌印。那掌印入壁三分,端得是威猛無比,鄭恆舟伸掌比了比,肯定那掌印不會是馮保留下的。他向馮保問道:「前輩,這黑牢中還關過其他武林高手嗎?」
「四十年間,關過不少啊。」馮保走到他身旁,欣賞牆上掌印。「這一掌是少林大力金鋼掌,乃是三十年前達摩堂首座恒真和尚留下的。少林功夫博大精深,當真厲害。像這一掌,我培元神功便打不出來。」
鄭恆舟轉頭瞧他,問道:「前輩,有個問題我早就想問了。前輩的功夫出神入化,於天下武學無所不包,為什麼會創出培元神功如此陰毒的功夫傳世?」
「唉,你誤會了。培元神功並不陰毒,掌力其實可剛可柔。只是練的人多半功夫不到家,所以才會產生這種誤解。」
鄭恆舟道:「可是這功夫……要……要……」
「要是太監才能練?」
鄭恆舟點頭。
馮保嘆了口氣。「這其實不能怪我啊。我自小入宮,起始練功的時候就已經沒了寶貝。我怎麼知道我創出的功夫有寶貝的人不能練?」
「這麼說還真有道理。」鄭恆舟道。「那恒真和尚後來怎麼了?」
「讓我吃了。」
鄭恆舟想起當日兩名獄卒關他進來前所說的話,倒也沒有如何驚訝。兩人站在牆前,望著掌印,心中都有所感。片刻過後,鄭恆舟問:「前輩,四十年來,可有人曾活著離開黑牢?」
「只有一人。」
鄭恆舟心生嚮往,問道:「那必定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前輩高人了?」
「有名得很。」馮保道。「此人盡得我培元神功真傳,出去之後叱嗟風雲,權傾天下,近年來更掌司禮監,任提督東廠,集黨結社,消滅政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端得是前輩高人。」
鄭恆舟目瞪口呆,問道:「魏忠賢?」
馮保點頭說道:「二十年前,東廠培元祕笈遭竊,魏忠賢奉命追回,結果任務失敗,讓提督東廠關入大牢。當年他也跟你一樣,有人要殺他滅口,有人要保他性命,弄到最後糊裡糊塗,終於來到黑牢,與我為伴。我見他遭遇可憐,又是東廠一脈,且已練過培元神功,算得上是我徒子徒孫。於是便在這黑牢之中指點他功夫。此人不但聰明絕頂,而且機緣巧合,得天獨厚,正是習練培元神功的絕佳人選。單以培元神功而論,此人功力比我還深。」
鄭恆舟瞪大眼睛:「有這等事?」
「不過這也不表示他打得過我,畢竟我會的功夫比他多多了。」馮保繼續道。「其實自從聽你提起他後,我心裡就一直惶恐不安。當年他花言巧語,騙得我傾囊相授,而我竟還一直以為他是正直之人,一心只想改革東廠,輔佐天子。想不到此人狼子野心,竟然連勾結胡虜,謀朝篡位之事都幹得出來。萬一大明因他而亡,老夫罪過可就大了。」
鄭恆舟道:「既然如此,前輩何不出去教訓他?」
馮保瞪他一眼,搖頭道:「我一百幾十歲的人了,你竟然好意思叫我去跟人打架?小兄弟,你的責任不可推到我的身上。魏忠賢殺了你師父、師弟,而你又想娶他女兒做老婆,這筆恩怨,你總是得要跟他算清楚的。」
鄭恆舟道:「前輩,晚輩這半年來雖然武功大進,但是要對付魏忠賢只怕還差了一點。」
「還差多了。」馮保道。「天下武功,往往偏陰偏陽,東廠的培元神功至陰,丐幫的降龍神掌至陽,這兩門功夫練到深處,原是不相上下。然而降龍神掌少了七掌,缺憾甚多;培元神功原來便不該是極陰的功夫,實在是讓練功之人把它給練小了。其實真正的絕頂神功,應該道走中庸,陰陽調和,不陰不陽,同時既陰且陽,如此才能一法通,萬法通,天下武學,盡為所用。」
鄭恆舟深以為然,緩緩點頭。
「你啊,根本聽不懂,點什麼頭?」
「前輩這麼說就不對了。」鄭恆舟辯道。「我聽得懂,只是做不到而已。」
「那倒也是。」馮保接著說道。「我說魏忠賢機緣巧合,得天獨厚,重點便在於此。培元神功正常人練了會燥火攻心,慾火焚身,熱血沸騰,剛烈難耐;讓太監練起來卻又變得至陰至寒,怪裡怪氣。真正陰陽調和,適合習練此功的人……」他伸出右手,比出一根食指。「乃是閹了一顆之人。」
鄭恆舟雙眼瞪得老大,驚訝到說不出話來。
馮保笑問:「這樣講很有道理吧?」
鄭恆舟想說:「確實很有道理。」同時也想大叫:「簡直狗屁不通!」
馮保瞧他臉色,哈哈大笑,說道:「總之,不管是不是因為魏忠賢只閹一顆的關係,他的培元神功都已突破往日藩籬,進入深不可測的境界。要打贏他,可不容易啊。」
鄭恆舟堅定神色,說道:「那我可得要加緊練功才行。」
馮保點頭:「加緊練功,當然需要。不過我近來一直在想,魏忠賢既然有此圖謀,如今也已大權在握,而你進來之時,他又已經聯合新人除掉錦衣衛都指揮史,接下來多半就會一步一步對付禁衛軍三大營。距離他發難之日,只怕不遠了。想要及時對付他,我們或許該走些速成的法門。」
鄭恆舟皺眉:「前輩說過速成會入魔道的。」
「我只說會入魔道,可沒說不能速成。」馮保道。「入魔道這種事情,其實很見仁見智。再說,只要我按部就班地給你速成,也不會真有什麼危害。」
鄭恆舟問:「前輩打算怎麼做?」
馮保嚴肅:「我給你調陰陽。」
鄭恆舟一身冷汗:「入魔道啦!」
馮保哈哈大笑:「放心,不會閹你的。」他笑了一陣,側過身來,說道:「運足十成功力,與我對掌。」
鄭恆舟氣沉丹田,奮力出掌。他此刻內功已經隨心所欲,降龍神掌與勁蒼訣內勁不分彼此,隨手揮出都是威力驚人。馮保右掌一提,與其掌心相對。霎時之間,鄭恆舟彷彿又進入了當年龍有功試他功力時的無際汪洋,不過這一回整片汪洋卻是風平浪靜,波紋不生,渾不似龍有功那種排山倒海,驚濤駭浪,反而令他心中一片寧靜和諧。便在此時,水面彷彿向下一沉,鄭恆舟先是感到丹田空虛,跟著又有一股綿力散入其中,一點一滴填補他的空洞。
鄭恆舟張開雙眼,神色驚訝,眼前卻不見了馮保。他轉身張望,發現馮保坐在牢門口,已將不知何時送來的飯菜吃個精光。鄭恆舟愣愣地走了過去,坐在馮保身旁。馮保將他的那碗飯菜遞給他,說道:「累了,吃吧。」
鄭恆舟吃了兩口,心緒不寧,問道:「前輩,你剛剛……是將自身功力傳到晚輩身上嗎?」
「是調陰陽。」馮保笑道。「小子,你江湖傳說聽太多啦。」
鄭恆舟點了點頭,繼續吃飯。
ns 15.158.61.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