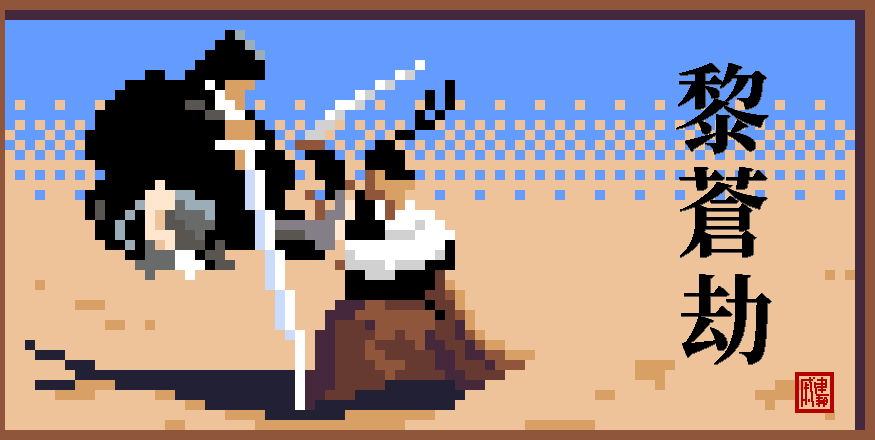寒風刺骨,肅殺陰沈。
已時,日頭高掛,保定巡撫衙門外本是喧囂鼎沸,卻在突然之間了無人聲。宋師爺等在門內,心中奇怪,跨出衙門口察看,只見滿街販夫走卒待立原地,默不作聲。宋師爺順著眾人目光瞧向街尾,心下登時了然。原來有十名身穿金黃飛魚官服,腰配繡春寶刀的冷面官差,死氣沉沉地穿街而來。這隊人馬行進無聲,氣燄內斂,表面看來並不如何可怕,卻能將眾百姓嚇得噤若寒蟬。宋師爺身著公服,站在衙門口目送官差路過,十名官差卻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眼。整條街的人就這麼戰戰兢兢地瞧著他們離開,直到連一點腳步聲也聽不到後,這才開始議論紛紛。
站在衙門口左邊姓方的衙役低聲說道:「師爺,錦衣衛的人跑到這兒來做什麼?」
宋師爺沉吟半响,搖頭嘆道:「瞧這模樣,多半是去城南萬安客棧。昨晚聽說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大人的夫人下榻萬安客棧,這會兒多半還沒啓程。」
「錦衣衛要拿左夫人?左大人都已經入獄,魏公公還要趕盡殺絕?」右邊姓李的衙役忿忿說道。「聽說魏公公誣賴左大人和楊漣楊大人接受熊廷弼大將軍的賄賂,五日一審,嚴刑逼供,想把眾大人屈打成招。」
「這些話咱們自己說著便是,可別到外面張揚。」宋師爺提醒道。
方姓衙役又問:「左大人究竟為何入獄?近日錦衣衛四處拿人,看來此案牽連不小啊?」
宋師爺再次搖頭。「為何入獄?還不是為了彈劾魏忠賢?先是楊漣楊大人上書揭發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皇上不聞不問。接著左光斗大人又上奏三十二條大罪,皇上還是不理。宦官亂政,奸臣當道,眼看大明江山......」
李姓衙役連連揮手,急道:「師爺,小聲,莫在衙門口說這等言語......」
宋師爺長長吁了口氣,壓低聲音說道:「聽說左大人上奏之前,早已吩咐左夫人先行南下。只可惜魏忠賢手腳太快,左夫人還沒出保定府,這就已經派人來拿。唉......上什麼書?彈什麼劾?想那九千歲魏忠賢位居司禮監次輔,任秉筆太監,朝臣的奏章都要經過他那一關,近年來甚至傳言有些奏章根本沒能上達天聽,就讓他給直接批了。左大人他們上這種書,不是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嗎?況且魏忠賢還任提督東廠,錦衣衛南北鎮撫司都聽他號令。左大人他們自己性命不保也就罷了,只怕一家老小都難逃一劫。」他轉向方姓衙役,說道:「你說此案牽連不小,只怕沒有說錯。魏忠賢閹黨策劃許久,多半會藉此事件大舉行動,徹底鏟除東林黨人......」
方姓衙役雖在巡撫衙門辦事,然而職司卑微,對於朝中情形不甚了了,問道:「那咱們巡撫大人……是不是東林黨的?」
宋師爺瞧他一眼,無奈說道:「劉大人潔身自愛,明哲保身,本不欲結黨議政。只可惜當今世道,非黑即白,容不得人置身事外。莫說魏忠賢要他表態,左大人何嘗不是三番四次來向劉大人示好?此事會不會牽連巡撫大人,眼下沒人說得準。只能靜觀其變。」
正說著,兩名補快自街尾快步走來。其中一人遠遠望見師爺,舉起一手:「宋師爺。」宋師爺大步迎上:「鄭捕頭。」三人並肩步入衙門。那姓鄭的捕頭約莫三十歲上下,相貌堂堂,不怒自威,乃是保定巡撫衙門的總捕頭。他邊走邊問:「師爺派人找我過來,可是衙門人手不足?何捕頭分派案文了沒有?」
「派過了。當班捕快都已出門辦事。」宋師爺使個眼色,將鄭捕頭拉到一旁。「恆舟兄,我知今日你沒當差,不過劉大人吩咐下來,有件案子勞煩你跑一趟。」
鄭恆舟點頭:「師爺請說。」
宋師爺取出一張案文,問道:「城東張大鵬,恆舟兄知道這人嗎?」鄭恆舟點頭:「賣天津包子的張老兒?他的包子皮薄餡多,做生意一向老實。」宋師爺道:「他昨兒夜裡讓人殺了。」
鄭恆舟一愣。「可知兇手是誰?」
「不知。」宋師爺說。一看鄭恆舟蹙起眉頭,他跟著又道:「今日一早,張老兒家隔壁的林在春來報的案。他說昨兒夜裡就聽見張老兒家中傳出異聲,是以他今早一起床就去拍門詢問,沒想到張老兒已經陳屍家中。我找了仵作過去,這會兒應該到了。」
「報案的有說人是怎麼死的?」鄭恆舟問。
「沒瞧見外傷。」宋師爺翻看案文。「口鼻流血,應是給人毆打致死。」他將案文交予鄭恆舟,說道:「劉大人交代,要你立刻趕去查辦。我聽他的意思,似乎是想盡快將了結此案。」
「既然如此,我這就去。」鄭恆舟瀏覽案文,順手收起,轉身往衙門外走。宋師爺在他身後叫住。「恆舟兄,若是遇上麻煩,大人要你盡力周旋。」
鄭恆舟愣了一愣,點頭道:「知道了。」揮手招呼適才同來的捕快,快步朝向城東而去。
***
不一會兒功夫來到張大鵬的住所,鄭恆舟方才轉過街角,立刻知道已經來遲。只見兇宅門口站有兩名官差,飛魚公服,卻是錦衣衛。鄭恆舟與手下捕快對看一眼,雙雙皺眉。捕快陳遠志低聲問道:「死個賣包子的關他錦衣衛什麼事?」鄭恆舟心下卻想:「劉大人怎麼知道會有麻煩?」
走到近處,一人苦哈哈地迎了上來,原來是仵作。「捕爺,你來了就好。錦衣衛的大人不放我進門啊。」
「我來。」鄭恆舟說著走向凶宅。門口一名錦衣衛官差揚手阻攔。鄭恆舟停下腳步,衝著錦衣衛抱拳道:「兩位大人,卑職鄭恆舟,保定巡撫衙門捕頭。今奉巡撫大人之命,前來查訪張大棚命案。」說著解下表明身份的腰牌,捧在手心,恭恭敬敬地呈上。
錦衣衛不看他的腰牌,只是點頭說道:「你回去稟告巡撫大人,就說此案已由錦衣衛接手,不必派人來查了。」
「卑職遵命。」鄭恆舟收起腰牌,卻不離去。錦衣衛眉頭一皺,問道:「怎麼?」鄭恆舟說:「啓稟大人,這張大鵬乃一介良民,從不作姦犯科,靠賣包子維生,如今無端喪命,案該地方衙門所管。不知何故驚動錦衣衛各位大人?」
錦衣衛不耐煩道:「錦衣衛辦事,還要跟你衙門捕快解釋嗎?」
「卑職不敢。」
這時凶宅內走出另外一人。門口兩名錦衣衛立刻轉身行禮,同聲道:「千戶大人。」鄭恆舟等人一聽,連忙跟著低頭行禮。那千戶「嗯」了一聲,低頭打量鄭恆舟的腰牌。「大家都在公門裡辦事,何必鬧僵?」他跨出門檻,朝鄭恆舟笑道:「久聞保定巡撫衙門鄭總捕頭劍法了得,曾在蘇州府力壓楊氏三雄,捍衛官府顏面。今日得見尊駕,白某深感榮幸。」
鄭恆舟忙道:「千戶大人謬讚了。雕蟲小技,不足掛齒。」
「鄭捕頭不必過謙。」白千戶道。「聽說鄭捕頭是點蒼神劍柳成風柳老英雄的大弟子,一手蒼松劍法造詣非凡,就連現任點蒼掌門柳乾真都是閣下師弟。柳掌門近年來在江湖上可是大大的露臉啊。」
鄭恆舟不知白千戶這番場面話是何用意,拱手說道:「千戶大人明鑒,卑職曾得恩師傳授幾年功夫,不過沒學到家。從前在江湖上行走,等閒也不敢抬出點蒼名號,以免有辱師門。敝派掌門雖為卑職師弟,武功可比卑職要高明多了。」
白千戶笑容滿意面:「鄭兄何必客氣。貴派勁蒼訣內勁天下聞名,令師弟三掌震斃丐幫長老神拳連天山,內功修為在武林中已是一流高手。」
鄭恆舟道:「回千戶大人,敝派內功確有獨到之處,然則師門規矩,勁蒼訣唯有掌門人方能修習。卑職雖為大弟子,卻未蒙恩師傳授。」白千戶沈吟:「是這樣啊……」鄭恆舟又道:「大人……」
白千戶揮手打斷他,說道:「鄭兄,你我雖然身在公門,實則都是武林同道。這官場職稱掛在嘴邊,聽了總不是味兒。咱們還是打著江湖口吻自在點。小弟姓白,名叫草之。」
白草之語氣甚誠,然而鄭恆舟仍心下仍然犯疑。他在衙門之中打滾多年,深知錦衣衛的話不能盡信。錦衣衛乃明太祖所創立之軍事衛所,負責監視朝臣,權力甚大。他們直接聽命皇上,有權緝拿任何人,並可私下審問,直接用刑。他們是皇帝統治朝臣的恐怖手段,滿朝文武聞風變色,沒人膽敢絲毫得罪。明成祖設立東廠之後,監視朝臣的大權落入宦官手中,錦衣衛名義上是獨立軍旅,實際上須聽東廠號令。
明熹宗登基後,寵信宦官魏忠賢,將一切朝政交其處置。魏忠賢大權在握,自稱九千歲,後更進一步稱九千九百歲,僅比皇帝的萬歲少一百歲。他掌控東廠與錦衣衛勢力,聯合朝中所有與東林黨不睦的朝臣一起對抗政敵,是為閹黨。
時為明熹宗天啟四年,過去數年間,魏忠賢指使錦衣衛處處為難東林諸臣,鬧得朝廷烏煙瘴氣,人人自危。鄭恆舟聽說太多錦衣衛假裝示好,贏取官員信任,隨即反咬一口之事。他非蠢人,自然不會相信堂堂錦衣衛千戶會毫無由來地仰慕自己俠名,不恥下交。或許此人意圖透過他去揭露劉大人的瘡疤。不管對方意欲何為,自己都須小心應對。「既然白兄這麼說,在下就不拘束了。」鄭恆舟拱手道,「不知道這張大鵬案......」
「在下也是奉命行事。」白草之沒讓他說完。「上面交代下來,我們也不好多問。鄭兄當差多年,應該了解此中難處?」
「這個自然。」鄭恆舟點頭。「然則巡撫大人派我查案,我總得要有個交代。白兄若不方便透露......」
「這樣吧,」白草之又打斷他。「就當是錦衣衛和巡撫衙門聯手辦案。待我的人看完之後,鄭兄盡管進去察看。不過屍體我得先領回去。仵作驗屍結果,我再差人送往巡撫衙門。」
鄭恆舟心想等你看完,我還有得看嗎?然而白草之已經讓步,他也不好繼續堅持。「那就有勞白兄費心了。」
「舉手之勞。」白草之領著鄭恆舟走向一旁,問道:「鄭兄在衙門當差幾年了?」鄭恆舟照實回答:「五年。」白草之嘆道:「以鄭兄人材武功,待在巡撫衙門,未免太委屈了點。」
鄭恆舟搖頭:「白兄取笑了。」
白草之正色道:「衙門捕頭雖受百姓敬重,畢竟還是衙役。沒有品級,不算官職,薪俸少,事情又多。同樣是為朝庭辦事,鄭兄怎麼沒想過要投軍嗎?」
鄭恆舟笑道:「在下胸無大志,不好功名。只想憑一己所長,抓賊辦案,也算為百姓盡點心力。」
白草之勸道:「從軍報國,一樣是為百姓盡力。鄭兄如果不喜行軍打仗,在下可以代為保薦,入咱們錦衣衛當差。小弟在洪都指揮史面前還算說得上話,只要鄭兄點頭,憑你當差經歷,當可直任百戶,為正六品職。這光是每月俸祿就跟你現在天差地遠了。」
鄭恆舟瞪大眼睛看他,實不知該如何應答。「白兄,」他謹慎以對,「請恕在下直言。你我素未謀面,何以......」
白草之哈哈大笑。「不知何故,我一見到鄭兄,就感到十分投緣。在下行事魯莽,不意交淺言深。想我錦衣衛聲名在外,也難怪鄭兄見疑。剛剛那些話,就當我沒說了。鄭兄若不嫌棄,改天出來喝茶?」
鄭恆舟連忙做揖道:「白兄待友至誠,在下豈有嫌棄之理?不知白兄是暫駐保定府軍衛,還是要趕回順天府覆命?」
白草之道:「小弟這次為辦此案而來,明日就得回京覆命。過幾天我當專程前來拜會鄭兄,為今日搶案之事賠罪。」
「賠什麼罪,白兄太客氣了。」
「這次事出突然,沒有知會巡撫衙門,自當賠罪。」白草之說著朝向鄭恆舟一抱拳。「鄭兄先請回吧。等我們查完,在下再派人通知鄭兄來查。」
鄭恆舟拱手告別,帶著捕快仵作離開。
***
三人轉過街口,遠離錦衣衛監視範圍,鄭恆舟遣走仵作,這才對捕快說道:「遠志,去年保定知府衙門遭竊一案,錦衣衛王總旗欠下的人情,可還了沒有?」
「還沒。」陳遠志回道。
「嗯......」鄭恆舟沈吟半响,道:「去向他探探白草之白千戶是什麼來頭,該管何等事務,他的長官是誰,又是奉什麼人的命令來查張大鵬一案。」他邊走邊想。「最好弄清楚張大鵬案何以牽涉錦衣衛。」
陳遠志問:「總捕頭,咱們在錦衣衛就只王總旗這條人脈。此案當真重要到要動用這個人情?」
「時機敏感。」鄭恆舟道。「以左光斗御史大人為首的東林六君子已讓魏公公拿入東廠,閹黨近日肯定要大張旗鼓對付東林黨人。時局如此關鍵,錦衣衛與東廠理應不會浪費人力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張大鵬一案要是就此了結也就算了,萬一日後牽扯不清,惹回咱們地方官府,到時候怎麼讓人誅連的都不知道,豈不是冤枉至極?這件案子一定要調查清楚,否則後患無窮。」
陳遠志皺眉道:「我看那白千戶說話客氣,倒似誠心要與總捕頭結交?」
鄭恆舟一言不發,走出一段路後,這才開口問道:「遠志,你我共事四年,交情匪淺,可知道我是點蒼派大弟子?」
陳遠志搖頭:「不知。總捕頭從來沒有提過師承門戶。我見你出手數次,一直以為你是少林派。」
「我也不是刻意隱瞞,只是當年恩師對我決意投身官府之事不大諒解,是以我身入公門後,便盡量少用師門武功,也不敢自稱點蒼弟子。」他心下遺憾,仰頭長嘆,片刻後道:「我的師承來歷雖算不上是什麼秘密,但總也要費上一番功夫查訪方知。姑且不論白千戶如何得知我是點蒼弟子,想我點蒼一派,人丁單薄,向來不是武林大派。他堂堂錦衣衛千戶,何故刻意與我結交?」
「總捕頭俠義為懷,聲名遠播,就連錦衣衛的千戶……」
「少拍馬屁。」鄭恆舟打斷他。「你這就去保定軍衛走走。過西大街時,順便讓王老丐下去放話,瞧瞧有沒有人聽說張大鵬的出身。」
陳遠志皺眉:「總捕頭,丐幫雖然人脈寬廣,消息靈通,但畢竟是武林一脈,對官府有所顧忌。宋師爺也吩咐了,叫我們別跟丐幫走得太近。」
「宋師爺不想我們花錢買消息而已。」鄭恆舟笑道。「然而有些案子總是要有武林人脈才方便查辦。總之時機敏感,你就問問去吧。」
陳遠志得令而去。鄭恆舟信步來到城東市集,於張大鵬空蕩蕩的包子攤前駐足片刻,搖頭輕嘆,隨即趕回巡撫衙門覆命。
ns 15.158.61.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