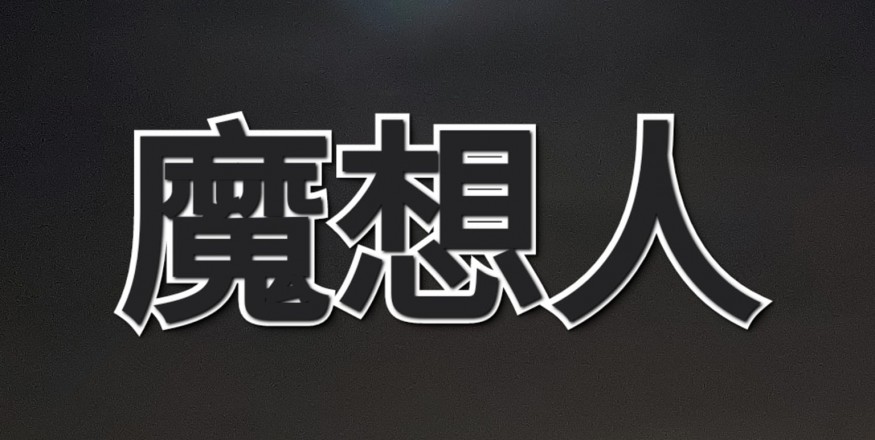第三章 掐
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8T6QX3yYr
一早,我起了床,洗了把臉,輕摸著昨天留下的傷口,內心感到一陣難過。我很想哭,卻逼著把自己眼淚收回去。一想到換上運動服後,又要去面對那些讓人感到無力的學校、班級,甚至是那討人厭的『異類』同學,頓時整個人心情大受影響,更不用說那個讓人一見就心寒不已的班導。我想這日子應該會持續到我畢業的最後一天。或許,但我不敢保證會有什麼變數,只是我想會得憂鬱症是真的。
我起了個大早,拿著浴巾到浴室裡沖冷水澡,讓自己思緒冷靜一會。
此刻爸爸在門外喊著。「阿德,等等出來吃早餐。」
「好。」
早在我起床前,老爸已經在廚房打理我的早餐。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因為我總覺得他的臉似乎要跟我談些什麼事,而我昨天那番狼狽模樣,似乎無法騙過他的直覺。有可能,他明白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沒辦法,誰叫我是他兒子。我想我的眼神無法騙過他,我想我昨晚回到家,想必破綻百出。
在洗完澡,換上運動服後,我坐在廚房的餐桌上吃早餐。比起這更尷尬的,老爸坐在我對面共渡著早餐時刻。只不過,他嘴裡咀嚼著東西,而喉頭像是咽著什麼東西出不來,不時輕咳,雙腳不安地在椅邊騷動著。
他將最後一口吐司吃完,輕啜了一口牛奶後,眼神專注地盯著我。「阿德。」
即使我不想面對他,但仍看在他是爸爸的份上,勉強盯著他看。「怎麼了?」想想沒有電視機的聲音,這氛圍特別讓人不習慣。
「你昨天是不是被霸凌?」他摸著我臉上的瘀青說道。
「爸~」我假裝生氣,然後把他的言行舉止詮釋成怪異的舉動,像是他完全在胡思亂想,只是我單純跌到大水溝罷了。「我不是跟你說過我跌到大水溝嗎?」
老爸一臉不安地望著,感覺他在分析我臉上的傷口走向,像個名偵探一樣眼巴在我臉上不放。「好!希望是這樣。」他接著語重心長地把手掌壓在我頭頂上。「阿德,我希望你有什麼事情別隱瞞,我就只有你和姐姐兩個最親的家人,我不奢望你們成績要好到哪去,但至少,你們要過得平安快樂。」
老爸的這番話,不禁使我倒吸一口氣。
沒錯!我的確被這番話給深深嚇到了。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身上的傷口,突然讓爸爸變得那麼感性。但我內心感受到的,卻是一種許久未見的暖活,是一種比起打電動看電視,還要讓人長久性的快樂。
「爸,我知道啦!」
我背起書包,或許這是一天之中,最值得讓人覺得開心的事情吧?
我緊握著拳頭忍耐著,穿好鞋子,在關起家門的那剎那,眼淚不自覺的從眼角流下。我開心又自責。我開心的是,我獲得了老爸這分關懷;我自責的是,我說了謊欺騙老爸。我自責自己為何辜負了他的關心。但是,唯有這麼做,我才能安安穩穩地在學校順利畢業,儘管對我來說那間學校爛的跟餿水一樣,某些師資爛、人品爛、同學爛,到處都是爛。我想轉學,但這對我來說,可能只是一種輪迴罷了。也許從現在開始,至少至少,義成會是我另一個照應。
走在半路上,我其實希望眼前不遠處的那棟建築,是我到不了的地方。我希望路可以再更長更長,建築可以漸漸地變小,甚至倒掉都沒關係。
到了學校,整個氣氛壟罩在一片烏雲之下。也許是對我來說。對於別人,可能是片晴朗無雲的好天氣,值得去期待別的事,甚至不用擔心被針對霸凌的問題,更不用提心吊膽地設法躲過那些傷害。但更有可能,有人正與我站在這片烏雲下,正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希望霸凌的那些人不得善終,此刻、往後,甚至他們更晚年,終將獲得因果報應。也許他們未來回想起這件事情,會有所懊悔,但到時那候,一切都來不及,一切都會從他們霸凌別人的那一刻起計算,然後時刻一到,霎那性的回報於他們。他們沒有彌補的餘地,全身上下只有被痛苦償還的價值。
走到班級前,我望著正在吃早餐的霸凌者。他們無憂無慮地笑著,言語中仍然在調侃著我們,把我們當成茶餘飯後的『笑話』。
此刻,義成跟伊凡同個步調尾隨在我身後,嘆了口氣。「怎麼?不敢進去嗎?」
「我正在做心理準備。」
義成一副得意的樣子。「哧!今天準備讓他們吃一頓粗飽。」
「義成,你不要這麼做吧?」伊凡在一旁勸道。
「你最好別管我,這種學校生活我已經受不了。得讓他們嚐嚐教訓。」
我好奇傾向前問道:「你帶了什麼傢伙?」
「是時候也該讓你知道,只不過不是現在。」他自信滿滿地走進教室。一進去,立刻被包圍,然後像玩具一樣被那群吃完早餐的人渣圍成一圈,再次一頓的拳打腳踢,直到有眼線提醒老師來了,那群人才甘心地收回手,裝做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和伊凡分次進到教室,因為我不希望他們會認為我跟伊凡有什麼關聯。首先是伊凡,他先進去。隔了半分鐘,我才假裝走上樓梯巧遇老師,跟在老師旁邊,順利安全地回到座位上。
右後方的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欸~很會唷,很會討救兵喔。」
後面分佈著暗自的竊笑聲。
「我沒有。」
「還沒有勒,反正下課你也一樣完蛋啦,最好有種別給我跑。」
我倒吸了一口氣。
「我跟你自我介紹嘿!我叫楊加洋,我想你也知道啦,同個班級那麼久了,以後我們就是天天見面的『好』同學。」
「好了,同學,上課不要講話了,把書翻開。」老師在講台說道。
即便把書翻開,我的心思仍舊徘徊在剛剛的出言恐嚇之中。我不敢往回看,甚至看後頭的公佈欄一眼,都像是被萬隻眼睛給注視著。我仔細萬分聽著後頭一絲一毫的動靜,卻連書本及老師的課堂內容都無心在上下去。他們就像一組軍隊監視著我的行動,或許是我多想,但我的第六感就是這麼告訴我的,任何一舉一動都可能成為他們再度霸凌我的媒介。
直到第六節課,我們到室外上體育課。今天這節課剛好是凱盛老師的課,那些人全擁在凱盛老師的周圍,假裝是好學生般遞上飲料,和凱盛老師打好交情,為感謝昨日他拿球讓他們霸凌我們。但我在想,他可能還不太清楚,自己的舉動已經深深的傷害到我跟義成了吧?
凱盛老師將大家集合在網球場上,今天上的是網球課,他開始講解網球的分析動作。所有人坐在地上仔細地聆聽著,尤其是那些人聽的特別專心,跟他們以往上課睡覺的作風有著天差地遠的區別,直到老師開始實際示範網球的連貫動作。就在上課上到一半,老師的手機響了,這一響打斷了原本課程的教學。
老師接起手機。「喂,你好……」
只見老師頓了一會,似乎有什麼緊急的事情找上他。
「對,沒錯。現在嗎?好!那我知道了。」他放下電話,吐了一口氣,神情看起來有些糟糕。「各位同學,你們先拿著網球拍來練習,老師家裡臨時有事,我會請其他老師來幫你們代課。」老師急忙忙地離開網球場,朝著川堂的方向跑去。
大家開始拿起網球拍各自地練習,我從沒想過會遇到這種狀況。
此時我到一旁的籃內拿起網球拍,就在抽起的那瞬間,一隻手把我緊握的網球拍給拍掉。我往旁邊看,是楊加洋。他一語不發,露出難以解讀的微笑神情,然後身後跟了一群好『霸』友,其餘與此事無關的同學則是退到了一旁,暫停了練習的活動,絲毫不敢吭半點聲。
神不知鬼不覺,頓時間網球場地的周圍全都被淨空,我毫無反駁餘地的被抓到牆壁前,旁邊還跟著義成,兩個人被硬貼在充滿球印的牆邊。「欸!你們兩個,給我站好!」
他做好開球預備姿勢,準備拋球。
砰!的一聲,一顆球削過我的耳邊,要是這個力道打中眼睛,後果將會不堪設想。但我想他們應該也不會太在乎自己的言行舉止。
後面他們那夥的掃興地數落楊加洋。
「遜欸!加洋,再準一點好嗎?」
「加洋,我覺得右邊的其實還不錯,可以換打右邊的看看。」
「技巧有待加強,看在我們都還是新手的份上,打肚子應該算簡單吧?」
「加洋,加油!等凱盛老師回來,他一定會對你另眼相看。」
此時陳叡文走到加洋旁邊,他奪走加洋手中的網球拍。「兄弟!我來試試看。」
「好吧!看你的囉!」
他開始瞄準,身體前後擺動著,然後準備拋球。
這時他猛力一揮,那飛快的球體瞬間砸中我的嘴鼻。他們在另一端歡呼,此刻我感覺到一股溫熱順著鼻孔流下來,這味道嚐起來鹹鹹的。我摸向嘴巴,一片鮮紅染在我的掌心上。接著我的頭似乎有點暈暈的,然後跪在地上,只見我的血一直在滴。
義成跑到我身邊攙扶著我。「德瑪,你還好嗎?別暈過去。」
伊凡跑向我。「尹德瑪,我帶你去保健室。」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針對我?」
「德瑪,你先別想這個問題,那群人渣欺負人不需要理由。」義成咬牙切齒的說道。「他們都是看你不爽。」
我稍稍抬起頭來,遠處的他們見狀情況似乎不對勁,立刻散開,然後若無其事的在假裝自由活動,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切都像是我自己自作自受惹出來的意外。
「這太過份了!」
我顫抖著,感覺眼前的地板開始在旋轉,拼命喘息。「我…我要去保健室。」
伊凡在旁邊把我攙扶起來。「走!我現在就帶你去保健室。」
義成對著我說:「德瑪,你放心!這裡就交給我處理。」
就這樣,我在模模糊糊的意識下,步履蹣跚地走到保健室,再來,我就毫無知覺地睡著了。實際來說,是暈倒。
我睜開眼,發現我躺在保健室的床上。伊凡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玩手機。「伊凡。」我發出鬆散的氣音,像個老人一樣連發出聲音都需要一些力氣。
「德瑪!你還好嗎?」伊凡在旁邊問道。
我點點頭。「好多了,現在。對了,義成呢?」
他吱吱嗚嗚地說:「被…..被叫到訓導處了。」
我驚訝地爬起身。「訓導處?為什麼?」
他似乎很不情願地嘆了口氣,彷彿有什麼事情不想說出口。「好吧!我想這件事情,最後可能也會讓你見證到。嚴格來說…我們是見習巫師。」
「你是說……會魔法的那種巫師嗎?」
「不算是魔法吧,但就是一種巫術。」
「所以他被抓去訓導處就是因為使用巫術?」
「實際上是這樣沒錯,因為人渣口徑一致……不過主任他們根本無法對我們採取有力的證據,所以也只能對義成採口頭談話。然後,基本上主任是不可能對他過問關於巫術的問題,因為那群人…..渣發瘋了。另外,主任完全不信這種東西。」
「發瘋!」我敲了敲頭。「我在作夢嗎?」我百思不得其解地望向他。
「沒有,他們現在變得很怕義成,在網球場上哇哇大叫,你沒看到實在太可惜了。」伊凡接著說:「我原本想說適可而止,但想想他們帶給你的傷害,我和義成兩個人都討論過了,這點小巫術還不夠他們償清。你知道那時候其他同班同學都竊喜的多開心啊!」
「這樣真的好嗎?」我有點擔憂的說著。
「那你現在這樣真的好嗎?」伊凡說:「他們不是小孩子了,霸凌的案例和觀念心態也該從社會上攝取到了。如今是他們執意這麼做,他們所造出的因,要由果來收。」
想了想,確實是這樣沒錯。如果我對他們多出同理心,是不是到時候我死了,那些人只會設法把原因歸咎於『我』自己的問題。應該這麼說,這是我的選擇,如果照剛才伊凡說的話,我將我的心軟變成因,我收到的將會是他們弄死我的果。而我,吃了這個果實會有比較好嗎?想想也未必是一種解脫。
此時保健室的護士小姐走了過來。「同學,你還好嗎?情況有沒有好一點?」
我點點頭。「好很多了,謝謝護士小姐。」
伊凡站起身,然後獨自離開。在他打開門前,回過頭看著我。「你自己回班級吧,我不希望接下來的事情會跟你有什麼關聯。不過沒關係的,放學我們仍然可以一起,到時候你就可以見證到一切了,事情可能會鬧的有點大,請你習慣。」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伊凡跟我之前遇到的那個他看起來截然不同。包括個性、談吐,甚至是整個人散發出來的特質,彷彿被一片烏雲給籠罩著,有著難以捉摸的神祕朦朧感,卻又在外表的包裝下,顯得平凡無奇。
我起身,鼻子被貼了一塊紗布,在鏡子的反射下看起來有點可笑。我帶著害羞的心理離開保健室,然後趁在下課前盡速回到教室,以免有更多人看到我這滑稽的模樣。
上課時走廊安靜一片,我掩著鼻子假裝咳嗽,避免其它教室內上課的同學看見這副模樣。好在這一切都很順利,我回到自己的班級。我在後門外駐足了一會,腦海裡正跑著等等其他同學看我的反應跟表情。
做好了心理準備後,我接著踏進教室。果不其然,大家全都望著我愣住,一副不可置信的呆滯模樣。就連正在講課的老師也停下來,整間教室全靜默成一片。有好多雙眼睛盯著我看,但我內心知道,他們都沒有惡意,也和曾經那些人的眼神差很多…對!我是指座位上空蕩蕩的那些人。我望向那堆空椅,包括我身後的,他們全都被叫到訓導處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我入座後他們整批人回到了教室。
只見他們的眼神從先前的霸道轉為冷靜。想當然陳叡文跟楊加洋這兩位霸凌頭頭,他們似乎為了鞏固自己帶頭的氣勢,仍舊一臉毫無所謂的入座,在經過我時,還不忘瞪了一眼,看來這些人好像也沒到發瘋的程度。也許他們只要一離開義成的視線外,彷彿那些暴戾之氣的靈魂又再度回到他們身上。
只不過看來看去,似乎找不到義成的身影。
「老師,不好意思,我晚了一步,剛剛去上廁所。」此時義成最後一個進來。
他一進門,第一眼看著我露出一抹微笑,接著將目光轉向那些霸凌者。瞬間,一陣桌子的嘎拉聲從右後方傳來,彷彿把椅子往後推了一下,也許我能夠分析出這些聲音的舉動,是『害怕』。
義成經過我時,輕輕的拍了拍我的肩,掠過了一句話。「你沒事就好。」
就這樣,難得上課期間到下課,直到放學了,那些人都沒有來找我麻煩。下課鐘聲響起,大家背著書包一溜煙就飛快地鳥獸散。
就在此時,義成迅速地站了起來,將那些人喊住。「等等!你們這些霸凌的人,放學全部給我留下來,我們走廊上好好談談。」
他們絲毫不敢輕舉妄動,然後將書包揹著,直到人潮散去後,才開始在走廊上談話。
我想他們倆並不是有意要和善地談判。只見陳叡文和楊加洋整顆頭裸露在五層樓高的半空中。和伊凡、義成兩人掐著他們的脖子,抵住的脖子不停發出掙扎時摩擦的中空聲響。
「說!你為甚麼要欺負他?」眼前兩張質問的口氣,宛如我的守護神。
陳叡文死命搖頭。「我沒有。我只是不小心的…是那群女生叫我做的。」
「不小心?」義成哭笑不得地回道:「那我現在也是不小心掐著你的脖子嗎?雖然女生也必須付出責任,但你這樣會不會太鱉了啊?」
叡文哭了出來。「對對…對不起。」
「陳叡文,我警告你,腦袋是個非常好使的東西,不是別人叫你去做什麼,你就像個奴隸一樣的去做。對不起這句話你可以留著跟你原本的良知道歉,但在做出這種要不得的事情之前,你也應該早要知道,其實你不用說這句對不起,也不用承受現在這樣的場面。」
「對不起…我我我不知道你是巫師嘛!」陳叡文持續哭道。
「重點不是我是不是巫師,看來你的腦子也生鏽的不輕。今天不管我是不是巫師,你覺得這樣霸凌欺負人是對的嗎?還是你拿這些無辜的生命來排除消遣你無聊的生活?手癢可以跟我說,」義成接著轉向那些女生。「妳們也是,我可以讓你們體會沒有手的生活。」
「我以後不敢了。」
「別老拿著別人的地位、身分、能力就對誰臣服,因為那樣的面容是最骯髒的。」義成仍然掐著,似乎無意放手。「聽懂沒?」
陳叡文頻頻點頭。
「算了,我想你還是不懂。」
「難道…和伊凡…….你你你也是巫師?」楊加洋面露驚恐地說著。
「這還要你說,比起我是巫師,我才需要擔心你們這些人,比起巫師要恐怖好幾百倍。你還有資格害怕嗎?沒有~」
傍晚,校內早已人去樓空。
就在此刻,女生的後頭突然站著一群藍領黑色衣褲的男子,彷彿一縷煙憑空出現。那群女生的手互攀在一塊,害怕的模樣不時往後看。
「你們知道這樣子…是在自討苦吃嗎?」和伊凡平淡地說著。
某個綁著馬尾的女生提起勇氣走向前。「並不是我們,我們只是…只是…以為有趣,附和開個玩笑。真正先出頭的,是陳叡文,對不對,尹德瑪?」他雙眼懇求著我能接受她的話。
我只是冷漠地看著她,我的傷痕早已縱容不了他們。
「不對!」我冷漠地搖搖頭。
那位馬尾女孩被後頭的黑衣男子掐住,指頭掐入她脖子邊的肌肉,她不經發出一聲哀響,眼神猙獰。「對…對不起。」
陳叡文受不了被掐住的怒氣,用力反駁。「你…你們這豈不是也在霸凌嗎?你們都不會好好反省自己嗎?你們有想過嗎?」他邊說邊掙扎,但仍抵不過一隻手的制伏。
「這問題很好!你們有資格欺負別人,為什麼別人沒資格反擊你們?你們的目的就是要讓自己內心獲得一份成就、慾望,希望別人臣服於你們,而我們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維護自己的生命,維護自己生活中該受到的尊重跟安全。當你們在霸凌別人時,你們有想過別人的感受嗎?」義成說著:「人總是在吃虧時講著對自己有利的話。但當自我佔上風時,囂張立馬蓋掉所謂的狗屁道理。你說是不是阿?陳叡文,你好意思說這句話?我敢講都不敢聽了。」
一抹陰沉的微笑,他們倆順帶拎著叡文和加洋的領子,帶到女生的旁邊。「你們這堆狗屁人,只懂得欺負人,被欺負時,恨不得當個縮頭烏龜,互推責任。你們終於看清楚彼此的面貌了吧?有嗎?有看清楚嗎?虛偽懂嗎?彼此在利用彼此當擋箭牌你懂嗎?好笑。」伊凡說著。「你們現在全都給我跪下。」
他們循著和伊凡的指令一個個跪了下來,後頭幾個藍領男子從褲頭抽出一支支甩棍,如行刑式的場面,將甩棍抵在脖子上。和伊凡一派輕鬆的看著我。「最後這個指令給你下,你的機會。」
那群女生苦苦求饒,男生則是滿臉瘀傷,卻無任何反抗。
「限你十秒,如果你沒下指令就換我來。」他看著我。「五…四…三…二…一…」
「好夠了。」我吐了一口長氣。「放過他們..」
那群黑衣男子收起甩棍。和伊凡說:「你說的是。但我不想放過。」
此時有個老師從對面走來。她的聲音很激烈,很大聲。「你們在幹嘛!霸凌嗎?」那些黑衣男子在老師大聲喝斥前,剎那間,消失無蹤。
現場只剩我們幾個。「沒錯!老師,他們霸凌我們。」那些女生恢復囂張的表情。男子滿臉瘀青,撫著那紫色的傷口。「他們三個。」
義成、伊凡、我,三個人站在校長面前。沉重的氣氛,三對眼睛和一雙凝重的視線面面相覷。左邊那群是我們的仇人,正在一旁對校長吐訴我們的種種暴行。老師在旁護著他們。
此時義成跳出來據理力爭。「校長,你知道這幾個女的,還有叡文、加洋同學,在下課的時候言語、動作霸凌德瑪同學嗎?還將德瑪同學的百科全書撥到地上,體育課私下拿他練球。我和伊凡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
「好了,不管,你們都把人打成這樣,有打人就是不對。」校長反駁。他肅穆的神情像是想把這件事情快點解決掉,並且打發掉這些麻煩的事情。「我將會對你們進行懲處。」
「那他們呢?」
老師走過來一旁插道:「你們無證無據不能這樣誣賴別人。況且我都看到你們三個讓他們跪在地上,叡文同學也被你們弄成這副德性。剛剛宇琪的媽媽說要找記者來。待會叡文要去驗傷,準備提告。」
「總之你們這次慘了,會要你們好看的。」叡文說。
第一次這麼緊張。心臟毫不規律的跳動,彷彿隨時都會停止。不是因為上台,不是因為表現,而是那種即將被審視的壓力不斷的在累積。一旁的兩位則是神態自然,一副不因為這件事情而屈服的模樣。反倒義成正在替我打抱不平;伊凡則是感到不耐煩,對他們大翻了白眼。兩個人的立場態度說明白就是槓上了校方及同學。
他們忿恨校長和老師的一知半解,更不用說那群正在暗中掌控竊笑的同班同學們,他們利用校長的權勢、媒體,家長護子心切的心態,使得這些人在家長不知情的情況下扮演無辜和被害者的身份反咬我們。
最後他們盡力的解釋仍舊被打了回票。校長對於我們的解釋不感興趣,一手擋掉我們奮力爭取的決心。因為我知道,校長他需要結果。他要的是立馬能定罪的一方,將事情立刻解決掉,並且恢復學校原本該有的狀態。然而,他仍選擇有明確傷害證據的那方,而我們可能會成為被隱瞞的受害者。
此時我和伊凡他們的家人都來了。聽聲音或許不止這麼少,連對方的家長都來了。
一群人擠在校長室外的門口。原本安靜的走廊也隨著腳步聲靠近變得吵雜。放學時間,單純寧靜的校園染上雜亂的囂聲。「出來!竟然敢打我的小孩,出來,你這沒有家教的小孩。你們知道這叫霸凌嗎?」
我還想問你們的小孩。你知道你們的小孩在教室對我做出了怎樣的事情嗎?
此刻我只能在心裡徘徊這樣的問題,卻不敢真實地說出口。他們兩個在盡力為我爭取平反的機會,而我卻無能為力像個廢人站在這悶不吭聲。
頻繁的拍門聲宛如要把門擠破,外頭家長的怒火像是點燃了一道火牆,正在侵蝕焚燒校長室的門。「快開門。」碰撞聲一次次傳進空蕩整齊的校長室,幾個人則是不敢輕易動手轉開那道門把。
老師彷彿不耐煩吵雜的聲音瘋狂地在後頭騷擾,連忙將門打開,家長像從瘋人院暴衝而出的狂者劈頭朝著我們罵,然後賞了我一巴掌。「你們憑甚麼打我兒子。」她睜大的眼睛恨不得將我給折成兩半,那勃然大怒的模樣已經讓她的眼白佈滿血絲。
其他家長站在後面悶不吭聲,但眼神全部聚焦在我身上。是那種就算求饒也無可原諒的絕境,納悶又不解的眼神。
「調監視器。」後面有個低沉的聲音,冷靜沉著。我知道是誰了。
「爸爸。」我暗自喃喃的說出,卻絲毫不敢回頭。
他冷靜的口吻,然後呼吸聲彷彿正在調節他無法克制的怒氣。「那樓的監視器,我需要知道。這樣也可以給大家一個交代,不是嗎?」他上前將我拎起。「這筆帳回家後再跟你慢慢算。」
其他家長同聲附和,唯獨那個帶頭出來的女家長似乎不服。「傷口都看的出來了,還得去看監視器嗎?有這個必要嗎?」她看著其他家長,旁邊也有人在安撫著那位正在氣頭上,叡文的母親。
另外一名女同學屏住氣,仍無法克制的上前賞了我一巴掌。「行刑式的懲罰,很好玩是吧?」
有位家長立刻拉開自己的小孩。「你在幹嘛….我有教你這樣打人嗎?有嗎?」
「他們還叫了好幾個人抵住我們。要拿甩棍攻擊我們。」
那位家長納悶地看著那些『受害』同學。「校外的嗎?」
「對。」他們異口同聲的點頭並說道。
「校長,你們警衛是不是有失職的疑慮?」家長走到辦公桌前冷冷地說著:「竟然連他們帶一群人進來警衛都不知道嗎?還是你們這裡算是開放性的空間,隨意閒雜人等進到校園滋事?」
「我相信我們學校的警衛是不可能疏忽這塊的。」校長站了起來。「我們對學生的安全一向是很在乎的。」
「在乎?」那位家長充斥著戲謔的笑聲,宛如電視上的大反派,顯得不太真實。「哈哈哈哈…校長,別跟我說你很在乎。今天在乎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爸爸說:「校長,請你調監視器。監視器是最有力的證據。今天不是說我站在我兒子他們這裡的立場,但凡事得講求證據。如果是我兒子不對,我會讓他負責這一切,連同我這個做爸爸的一起。」
「好!」
我們二話不說,一群人到了警衛室裡。警衛一臉尷尬的開始調起監視器,畢竟這件事情與他也有關。
警衛將五樓二班旁的監視器倒回當初事發的時間,以及更之前的時間。伊凡和義成則是很淡定的看著這一切,表現出來的模樣完全無關緊要。家長們正屏息以待著結果出現。
「我可以確定,很確定我沒有放行外人進來。」警衛額頭已經冒出冷汗。他想證明自己有做好警衛的義務。他不停吱吱嗚嗚的說著,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他脈搏正快速跳動,血液中正排斥著與麻煩(後頭的家長)區隔。我的雙耳像是被朦住,心臟跳動的頻率正從汗水中激發出來。我與警衛處在同一塊頻率上,心情正在結冰當中。「我可以發誓,校長。」
「好,你的事情等等再說。」校長專注地對警衛說:「先把當時的情況給調出來。」
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snXHSILf4
日期:2019/4/25
地點:五樓.二年二班走廊 (4號監視器)
時間:17:30-18:02
警衛按下確認。
義成與伊凡不約而同隱隱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zcDfY21J3
只見一排女學生跪在走廊,後頭完全沒有任何人。義成與伊凡和我站在一塊,眼睜睜看著叡文和加洋自顧自抵在欄杆上發瘋、自毆,看起來像是在排演一場獨角戲。不!那群女生正眼睜睜地陪著他們共同演出。一舉一動,真實流露。淚水、激憤、緊張。
時間前移,我們三個從走廊走了出來正準備放學。接著叡文他們將我們團團圍住。在螢幕上叡文拎著我的領子顯露出一絲霸氣,質問著我,譏諷著我。那群女學生正在觀看著好戲,學著我的獨特語調,附和譏諷。「哈哈!外星人阿~」
家長看著監視器一臉訝然,摀著嘴不可置信地觀賞著孩子的行徑。後面那群霸凌者的書包有的都掉了。那副理所當然的無辜、面具被拆穿了,流露著的是希望被原諒的虧欠、悔過。在自己家人面前可不能再更霸道。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現在」並沒有更大的本事在外闖蕩生活,亂來。說直點,還沒有勇氣。
校長似乎鬆了口氣,然後對著家長說:「監視器已證明沒有外在人士,並且,你們孩子還霸凌了他們。證據已經出來了,各位家長,是否能還給這些同學一個道歉。」校長喜歡當個模棱兩可的人。他認為對他有利的那邊,先給他偏了再說。這次家長理虧,證據會說話,記者可不是連個監視器問題都不會查的人。還好校長聰明…哦不!還好老爸救了校長,否則校長會在記者面前丟大了臉,然後拉下臉皮道歉。
義成說:「我們….完完全全沒有找人。」
伊凡接道:「可以證明我們是無辜了吧?」
叡文的家長自顧自地說著:「我的小孩該不會瘋了吧…?」她擔憂的看著,叡文無言以對,只有尷尬相對。
不只是家長,連我也完全無法理解這一切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群穿著黑衣藍領的男子到底從何而來?為何聽從著伊凡及義成的話?卻又在螢監上毫無他們的蹤跡。
這件事情落幕,我們獲得了道歉,卻無法為我解開內心納悶的謎題。義成他們一向挺我,也為我默默做了很多。那群同學最終獲得了懲罰,很可惜只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記過處分。
只不過他們這一掐掐出了我的憤怒,我的爽快。雖然我沒親自動手,但看著當時他們恐懼的反應,我的眼眸正在濃聚著一股無法解釋的力量,甚至愉悅的心情。我不知道那是甚麼,只覺得負面的能量讓我更強大,他們倆的所作所為正讓我茁壯當中,宛如我的雙手正幫我處理著一切。我似乎懂了什麼,我似乎離黑暗的距離更近。
1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JuTjgZ2wg
放學後與他們各自先行回家….
父親因公司臨時有事自先離去。「不要在外惹事生非了,回家等我,我得好好質問你一些事情。」他這麼對我說。
至少我現在是半個麻煩。
回家路上,恰巧遇見了一件臨時車禍。
那位肇事騎士將一個懷孕婦人給撞倒後駕車離去。婦人疼痛的倒坐在地上,身上冒著濃厚的血。我吸收了那份痛覺,頓時感覺難耐。「孩子….撐著。」我在無意識下講出了這句話,同時也是婦人的感受與擔憂。
「撐著…」
聲音迴盪在我的耳邊。
那股能量使我雙眼開始聚集負面的意識,肇事者慌張的情緒,吸收了無可救藥的罪惡,然後駕著車良心不安,甚至帶著僥倖。
當我望向徜徉而去的肇事者,雙眼突如其來釋放出了憤怒。我能深深感受到毛細孔冒出一道道黑色細煙正在飄渺著,快速地朝著肇事者飛去。
肇事者像是無法克制般加快油門,自撞電線杆當場倒地不醒。
我的身體獲得了釋懷,雙眼恢復了正常,不再沉重。「我怎麼了?」此刻的心情仍處在當時警衛所處的狀態當中。我吞下了一顆藥,心情緩和了下來。
事後婦人已送上救護車,我在角落只能當起旁觀者。因為我知道,我不能把身上的負能量傳給那位婦人。我只能吸收,我不能害人。也許這是當掃把星的宿命,但我已經為婦人報了仇。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