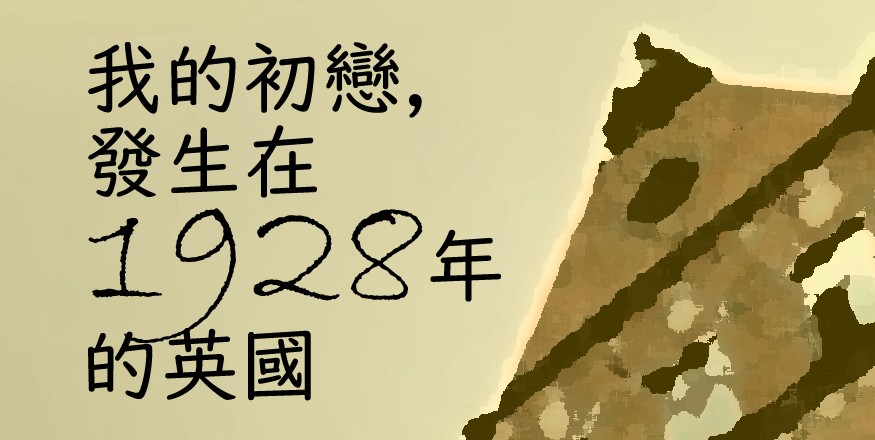下午又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雪,以至現在走在雪地上都會一步一腳印,在身後造成一個又一個的小雪坑。原本愛德華跟斐瑞還可以走快些,就因為拿着觀星望遠鏡和毛毯在雪地上磕磕絆絆的,才到現在還耽擱在後山。然後嘭嘭嘭的,他們背上頭上連吃了幾記雪球,不問可知是從屋子裏追出來的雪莉在背後向他們投擲的。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RHZxZXhhq
「要不要……」斐瑞回頭,正想邀請雪莉一起上山觀星,口鼻便馬上吃了一記狠狠的雪彈攻擊,弄得鼻子都發紅了,還一頭的雪渣。
「笨蛋愛德華!」雪莉又投了兩記雪彈。
愛德華一一避過,回頭冷笑。「是誰連地球是繞着太陽轉的都不知道?」
「知道來幹什麼?沒用!」雪莉大喊。
「那你就回去看你的顯微鏡好了,我們去觀星你又沒興趣的。」愛德華說。
「哼!誰稀罕?最討厭天文學!」雪莉又氣沖沖地胡亂投了幾球發洩,才轉身向大宅方向走回去。
「不用理會你妹妹嗎?她一個人回去會不會有危險,這裏入夜會不會有什麼狼呀野狗什麼的出沒?」斐瑞看着雪莉獨自回去的小小身影,覺得她怪可憐的。
「這裏離家裏有多遠?她可是在這兒大的。」愛德華頭也不回,就拉着斐瑞的手繼續向山上走去。
只有兩個人,在月夜下的荒山裏走着,周圍是樹林,這情境似曾相識。那時候,仍然是夏天,他們邊跑向溪邊邊脫掉衣服,為的是泡進水裏去消暑;現在已是冬天,他們包裹着厚實嚴密的衣服,手拉着手,默默地走着。那一天,可能就是斐瑞發覺自己對愛德華「不止室友」的那一天;而這一天,他們真的「不止室友」了……斐瑞突然覺得一點也不冷了,耳尖還熱得發燙。
為了打破尷尬的寂靜,斐瑞清了清喉嚨。「還以為你跟你妹妹感情很好?」斐瑞邊走邊問。「你銀包內還放着她的照片呀!」
「她還未學會說話,就學會拿晚餐扔我臉上了。」愛德華無奈地翻了翻白眼。
「什麼?不是吧?」斐瑞想像當時餐桌上,嬰兒雪莉扔食物到小學生愛德華臉上的情境,直笑得肚子痛。
「她呀,就是愛耍小性子,霸道又情緒化,還很喜歡搞些戲劇化的場面,像擲雪球什麼的。」愛德華說。「要是再亂慣她,我怕她會長大成一個混世魔王!」
「你們還真是親兄妹。」斐瑞笑不攏嘴。「你不知道自己也很戲劇化吧?」
愛德華再度翻了翻白眼,嘆了口氣。
事實上剛剛那頓晚餐,氣氛絕不比被妹妹拿飯菜扔臉上這回憶好太多。不理莫法特夫人怎樣威迫利誘,雪莉都不肯吃下半口食物,只是拿着那隻樣子猙獰名叫曲奇的玩偶在自言自語——準確點說,是練習俄語。聞說雪莉已學會了英、法、德、意四國語言,正在學習俄語。她整頓飯除了不給好臉色愛德華看,就是無視其他人的存在,只是跟她的「朋友」曲奇(即那隻怪玩偶)用俄語聊天。
為了逃開雪莉那怨恨的目光,愛德華才叫斐瑞飯後出來散步,並提議拿上他爸爸的觀星望遠鏡,因為幸運的話,這兒晚間可以看見很美的星空。
而這晚他們很幸運,因為現在萬里無雲,天上的星星都出來了。
這時愛德華已選了一塊較大的空地,把毛毯舖到就近一塊又大又平滑的大石上,以供他們等會兒躺臥在上面看星星。他把望遠鏡設置在前面,正在調整觀看的角度。
「那隻叫曲奇的玩偶到底怎麼回事?」斐瑞問。「怪嚇人的。」
「它是雪莉的朋友。」愛德華說。「唯一的朋友。」
「什麼?」斐瑞駭然。「沒有別的朋友嗎?別的小孩?」
「你覺得她會跟小丑魚玩嗎?她只會嘲諷人家是沒有腦袋的生物。」愛德華頓了頓,望着地面。「其實她以前有隻寵物犬,他們一起長大的,感情很要好,她還替牠改了個海盜名字叫鐵鈎船長,常常一起玩冒險遊戲什麼的……那時候的她倒還像個孩子。」
「那隻狗呢?」
「死了。」
「噢。」
「自此之後,她就更野蠻了。」愛德華說。
「她太寂寞了吧?」斐瑞說。「唯一的哥哥也離開家裏進了寄宿學校,可以說話的就只有曲奇。」
「她早晚也要學會一個人的,人出生時獨個兒來,死時也是獨個兒走。」愛德華透過望遠鏡觀測着遙遠的星雲。
「愛德華,她才只有六歲……」斐瑞感嘆。
「她生來就太感情用事,不是大吵大鬧就是大哭大叫,對極微小的事情也會反應過敏。」愛德華轉頭看着斐瑞。「她還要有一個比一般人更聰明的腦袋,想想看,她的吸收能力比人強,反應又比人大,這輩子會是多麼的折騰?放任她下去,她會比一般人更脆弱更易受到傷害。」
「所以就要加倍嚴苛對待她?」
「只是想她學會冷靜理性,隔絕感情的不良影響。」愛德華解釋。「擁有特殊頭腦的人,跟身邊的小丑魚根本無法溝通,即使身處人群,她其實也只是獨自一個。」
斐瑞想到擁有傑出頭腦的愛德華童年可能也是這般的孤獨,頓時覺得很難過,拉住愛德華的手摩挲着。「我也只是條小丑魚,我們也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在一起呀。」他把愛德華的手貼上自己的臉龐暖着。
愛德華注視着斐瑞,手輕輕撫摸他的臉。「這可能是我犯過的最大的錯誤。」
「錯誤?」
愛德華雙手捧着斐瑞的臉,看了又看。「你說我們這樣子可以長久嗎?」
「你是什麼意思?」斐瑞茫然看着愛德華。
「這是違法的。社會不容許的。」愛德華呢喃着,嘴唇離斐瑞只有兩寸。「我們的關係會影響到我們的名譽地位、事業前途。要是你將來要當警察,你能容許自己私底下犯法嗎?你不會害怕被別人揭發、被上級發現嗎?」
斐瑞根本無法想到那麼遠,愛德華就在眼前,那雙清澈的眼珠子就那樣專注地看着自己的嘴唇。他只能湊上前吻下去,緊緊擁抱住眼前的人。
他們的擁吻茫然又絕望,在荒涼的夜色裏掙扎着拼命的擠近對方,激情忘我間拉扯着彼此的衣料,磕磕碰碰撞上了身後的大石塊,最終躺倒在毛毯上。斐瑞把愛德華拉向自己,抱緊他,在他唇上呢喃:「我們會想到辦法的……」他不停地吻他,並在喘息之際輕訴:「我們可以一直這樣開心……我們一定可以的……」
愛德華看見斐瑞意亂情迷地望着自己,這麼近,近得他也快要迷失在對方的瞳孔之中。他覺得不確定,但抗拒不了這誘惑,被眼前這甜蜜的漩渦扯了進去,只得不停地從斐瑞口中吸取氧氣,只得不停從他身上撫摸出溫度。
「你這麼聰明……」斐瑞在零碎的親吻間發出迷亂的聲音,他捧着愛德華的臉。「會想到讓我們永遠在一起的辦法……對不對?」
愛德華緊抱住斐瑞,聲音悶在對方口裏,只能發出一些咕嚕聲。他們抱緊對方,濕潤的唇舌深入對方口腔搗攪着,那感覺親密又怡人。身體在對方身上磨蹭着,胸膛緊貼着胸膛,胯襠緊貼着胯襠,嚴密無縫地緊貼着對方,讓二人融成一體。但不夠,這樣不夠,他們解開了對方大衣的鈕扣,伸手進去把對方的衣擺拉出來,好讓脫掉手套的雙手能探進去,撫摸裏面的肌膚。但不夠,仍然不夠。他們拉開了彼此的皮帶,拉下了褲鏈,把手探進那片禁地——那片他們曾在黑暗中誤闖的禁地。
呻吟和喘息成為了寂靜夜晚的唯一配樂,他們在月光下看着彼此,摸索着對方的私密之處。
不夠,這還是不夠。
在激烈的心跳和上升的體溫中,他們褪下了一截褲子和內褲,讓彼此的分身在密友眼前露面,讓它們在月色下互相追逐起舞。
外面很冷,他們仍然穿着大衣,斐瑞爬到了愛德華身上去,讓自己的大衣遮蓋着二人裸露於空氣中的部位,像蓋上了一張溫暖的被子。衣料下,他們讓彼此的硬挺滑動在一起,前液滋潤着它們,磨蹭製造了快感,他們發出了羞澀的聲音,但那股讓人顫抖的瘋狂的快感讓人欲罷不能。
「你好美。」斐瑞低頭看着潮紅着臉、氣喘吁吁的愛德華,忍不住又去吻他。
愛德華發出了更多讓自己羞憤難耐的聲音,卻是斐瑞聽過最動聽的聲音。他伸手握住二人的分身,讓二人戳刺進他的拳頭;愛德華有力的手握了上來,握住了斐瑞的手和他們的硬挺,一起上下擼動。
「呃~」斐瑞感到自己呼吸不了,即使在空曠的野外依然嚴重缺氧。
愛德華空出來的一隻手撫上了斐瑞的臉,看着他漲得通紅的臉。「你也好美……哦……」忍不住洩出一聲呻吟。
他們又在半途陷進了一個熱吻,然後下半身加快加強衝刺着,帶他們去到一個從未到達的境界,一個透着白光的懸浮世界。在那裏,周遭一切顛倒着,地心吸力失去效力,只有他們變成了磁鐵,緊緊地吸附着彼此。
在令人眩暈的快感中,他們輕呼一聲,射進了他們的拳頭,然後喘着氣癱倒在一起,良久。之後愛德華掏出手帕,抹掉了二人手上黏糊糊的液體,然後看向斐瑞。斐瑞撥開愛德華汗濕的劉海,親了他一口,二人默契地相視一笑。
「我們做了。」斐瑞的聲音帶着驚奇和滿足。
「我們做了。」愛德華以平淡掩飾着一絲羞澀。「……你之前有做過嗎?」
「沒有。」斐瑞想起愛德華曾向那男生承認是處子。「你也沒有做過?」
「沒有。」
「但你差點給了那個男生。」斐瑞想掩飾住他的妒嫉,但不成功。
「你跟伊莉莎白也不遑多讓。」
「你妒忌?」斐瑞忽然笑了。
愛德華翻了翻白眼,然後兇巴巴地睨着斐瑞。斐瑞仍然在笑。於是愛德華翻身壓了上去,狠狠地咬上了斐瑞的嘴唇。
一隻松鼠在林間竄過,定睛地望了一會,不明白這兩個人類怎麼好像在扭打,但又發出了一陣陣的嬉笑聲。
# # #
愛德華沒想過,在家門後等着自己的,是來自莫法特夫人的一個火辣辣的巴掌。斐瑞看着愛德華的臉霍的一聲燒紅起來一個掌印,他也跟自己一樣呆住了。
「夜半三更的,你把妹妹帶到哪兒去?」莫法特夫人兇悍的樣子把斐瑞嚇住了。
「雪莉還沒有回來?」愛德華這刻真的墮進了最深的恐懼之中。
# # #
那夜凌晨,莫法特家上下總動員,提着照明工具四出尋找雪莉的下落。斐瑞跟着愛德華搜索過了矮樹叢一帶後,便跑到了湖的那邊。愛德華握緊拳頭,盯着月光下湖面那剛凝結的薄薄一片冰面,嘴唇發白,神情茫然憂懼。
「她不會掉進去的,她會看見警告的嘛。」斐瑞指着湖邊豎着的那個「危險勿近」的警告牌,撫了撫愛德華的肩膀。「她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不是嗎?愛德華?」卻發現愛德華正在微微發抖。
愛德華沒有回應斐瑞半句,便轉身離開了,繼續沿着湖邊山路找下去。斐瑞只能擔心地跟着他,看着他搖搖晃晃差點絆倒的腳步,卻連伸出去攙扶對方的手都被甩開了。斐瑞心知肚明雪莉不見了是他們的疏忽導致,因為他們當時被戀情沖昏了頭腦;他深知道疼愛妹妹的愛德華這刻肯定悔疚不已,而內疚會令他對他們的戀情產生罪惡感、甚至條件反射地對斐瑞產生厭惡。斐瑞心裏祈禱着但願雪莉能平安無事,那麼可愛的一個孩子千萬別要出意外,否則他的餘生良心都不會好過,而且愛德華以後恐怕連看斐瑞一眼都未必想了。但現在胡思亂想於事無補,他們只能加把勁更仔細地搜尋。
然後斐瑞嚇了一跳,因為愛德華突然在一所廢棄農舍前跪倒地上。他伏在地上俯視着眼前一隻鞋子,然後他顫抖的雙手拾起鞋子,湊到眼前仔細地觀察——那好像是雪莉剛才穿着的鞋子,的確是雪莉的!
斐瑞把激動得發抖的愛德華扶起,二人提起照明工具一起向農舍門前看去,那兒有些像是血跡的東西,而大門被粗重的鎖鏈一圈圈圍住緊緊鎖上了。
愛德華發狂似地衝上前,從口袋裏掏出鉗子想把鎖鏈剪開,但鉗子太小,鎖鏈太粗,他手指頭都被鉗開來的金屬破口割得流血不止,仍然在不斷地邊鉗邊拉開那條粗鏈子。斐瑞看不過眼,把鉗子從他手上奪過來,接着用力去剪斷那條粗鐵鏈。愛德華無法站着不動,繼續伸手去拉扯那條鐵鏈,最終在二人合力下把鎖鏈弄開。
當他們把大門推開,月光從外面照進來,畫面令人驚駭——地上血污處處,牆上歪歪斜斜的小孩字跡寫着"Merry Xmas!",但書寫顏料看上去卻像是血的東西,而雪莉正蜷伏在一角,躺在一灘血泊當中,似是不省人事。
「雪莉!」愛德華跑上去抱住她,發現她尚微有知覺,而且渾身發燙。「雪莉!」他已經慌亂得不知所以。
倒是斐瑞能強作鎮靜,上前仔細檢查一遍雪莉的身體。「她沒有受傷,血不是她的!」
愛德華茫然無措地把雪莉抱起,跌跌撞撞想要走出去,卻在門邊的陰影處絆倒了什麼東西。斐瑞上前穩住他們,並把照明往陰暗處照過去,駭然發現那是一隻死狗。
# # #
愛德華完全想不起來自己是如何回到家中的,只是抱着昏迷的妹妹盲目地向前走,一直走,一直走。到他回過神來時,雪莉已被管家和傭人接走,莫法特夫人正忙着指揮他們捧來急救藥箱和熱開水——這時愛德華突然雙腿發軟,身後的斐瑞趕緊上前扶住他。
「雪莉會沒事的。」斐瑞柔聲安慰道,溫暖的掌心撫揉着愛德華酸痛的肩膀。
莫法特夫人發號施令完畢才轉頭望着愛德華,接着咬牙切齒地走過來,瞪着她的長子說:「你想連雪莉也弄走嗎?你就恨不得我們家四分五裂?」然後她一把推開愛德華,神情極之厭惡。
斐瑞被她的兇相嚇呆,瞥向愛德華只見他臉色慘白。然後家裏又是一陣騷動,原來是緊急電召過來出診的醫生趕過來了,傭人馬上招呼他進來,莫法特夫人也急急忙忙跑過去,臨行前卻不忘警告愛德華:「待回你自己的房間,別再接近你妹妹!」說罷便跟醫生進了雪莉的房間並關上門。
斐瑞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這兩母子怎麼了,跟之前人前一副母慈子孝的畫面完全是兩回事。正要發問,斐瑞卻感到跟前的愛德華渾身發軟和顫抖,臉色鐵青狀似呼吸困難。
「愛德華?」斐瑞把他扶到椅子上去,但愛德華手足開始發抖抽搐,不管斐瑞如何替他按摩,他也喘着氣一副快要昏倒的樣子——愛德華病發了,斐瑞明白是儲物室那天的事件重演了!
「藥呢?」斐瑞大驚,但摸遍了愛德華身上的口袋都不見有藥。
眼看愛德華嘴唇顫抖着,斐瑞把耳朵湊過去,聽見他氣若游絲的說:「在……房中……」
斐瑞眼看四周一個人也沒有,大家都聚集到雪莉的房間去了,於是他不顧一切把愛德華抱了起來,就這樣抱着他走過了這所大宅,把他抱回到他自己的房間,放在床上。斐瑞發現愛德華已然不省人事,只好焦急地翻找他的桌面、抽屜,幸好終於找到了那些藥,急忙搖醒愛德華逼迫他吞了下去,然後兩個人儘管在冬天也渾身被汗水濕透了,都累得筋疲力竭動彈不得。
待了一會兒,斐瑞便趕忙爬起來,但愛德華乏力的手一把拉住他。「去哪裏?」
「去找你媽媽告訴她你的狀況,叫你的家庭醫生也上來看看你啊。」
「不要。」
看見愛德華說得那麼辛苦,但眼神堅決,斐瑞只好作罷。他轉為前去關上了房門,然後回到愛德華身邊,把他的衣服一件件脫了。愛德華全身無力,只能瞇着眼任由他擺佈。
「你……在幹什麼?」
「會着涼的。」斐瑞拿脫下來的髒衣服替愛德華把汗水抹乾,再拿新衣服來替他穿上,然後再拿棉被給他蓋好,蓋得嚴嚴密密的。
愛德華朝他虛弱地笑了笑。
斐瑞忍不住伸手撫着他的臉龐,嘆息這樣的一個天才,心疼怎麼會有那麼多糟糕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但現在不是發問的好時機。「閉上眼,歇一歇吧。」他只能輕輕吻一吻那雙嘴唇,取代當初那個「人工呼吸」的儀式,然後希望愛德華快點好起來。
# # #
斐瑞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伏在床邊睡着了,然而一陣嘈吵聲驚醒了他,他睜開眼發現眼前的被窩空了,愛德華的外套正披在自己身上。斐瑞連忙起來,看看掛鐘,現在是凌晨三點多。
他在門外不遠處找到了愛德華的蹤影,他正站在轉角處似在窺探着什麼,正在爭吵的人在走廊的另一邊,聽聲音是一男一女——女的是莫法特夫人,男的是個陌生的中年男人。
「這裏不歡迎你,你回來幹什麼?」
「讓我看看雪莉吧。」
「她要不是發生意外,你會回來看她嗎?」
「我每年的聖誕都想回來看看孩子們,是你叫我別回來的。」
「是啊,分配得真好,聖誕在這兒過,新年在那邊過,多和諧多高興啊!你倒想得美!」
「夜半三更,你要把屋裏人都吵醒嗎?」
「你還知道丟臉嗎?知道的話怎麼會幹出那麼傷風敗俗的事情來?」
斐瑞來到愛德華身邊,愛德華向他做了個別作聲的手勢,二人一起偷偷看出去,可見莫法特夫人很生氣和激動,那男人則臉色蒼白,一副欲語還休的樣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麼骯髒,我們的關係是建基於……」
啪的一聲,莫法特夫人在那男人臉上留下火燒似的掌印,然後指着走廊盡頭對他說:「滾!你還要替那個破壞別人家庭幸福的敗類說話,你就馬上滾回那邊去!」
「讓我瞧雪莉一眼吧?聽說她的高燒還沒有退?」那男人一臉擔心。「求求你……」
莫法特夫人再摑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然後忿然瞪着他。
他低下了頭。「求你。」
又一記耳光。
他躬了身。「求你了。」
莫法特夫人咬了咬唇,一言不發的拂袖離去。之後那男人進了雪莉的房間,不久裏面的傭人捧着面盆和水瓶出來了。愛德華跟着那男人走進了妹妹的房間,斐瑞站在走廊不知如何是好,也就跟着他進去了。
那男人正憐愛地看着睡在床上臉蛋紅通通的雪莉,並替她弄好蓋在額上的濕毛巾。
「爸爸。」愛德華來到了他身旁。
莫法特先生轉過身來,慈愛地摸摸愛德華的頭髮。「愛德華,你長這麼高了。」
他們互相擁抱了一陣子。
然後愛德華蹲下來撫了撫妹妹的臉頰,仍然很燙。他爸爸的大手撫上他的肩膀,慰解他的擔憂。
「我跟勞倫醫生談過了,他已經開了退燒藥給雪莉服過,現在我們要想辦法給她降溫。」
這時傭人捧着新換的清水進來,站在門口的斐瑞便順手把它接過來,遞給愛德華。
「這是我的同學斐瑞.德桑。」愛德華介紹說。
「你好,歡迎你來過聖誕。」莫法特先生向斐瑞展露和藹的笑容。
然後這個夜晚,他們就守在雪莉身邊輪流替她換毛巾。終於在天亮以前,雪莉的額頭不再火燙,體溫回復到正常程度。
當三人舒了口氣的時候,愛德華才發現妹妹房間裏有些異乎尋常的東西,就跟雪莉換下來那堆沾上了血跡的衣物堆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從口袋裏掉出來,還是他們回來時無意中一併帶回來的——就一個狗項圈和一張賀卡。
「那是什麼?」斐瑞問。
「這項圈上面繡着鐵鈎船長的名字,是屬於雪莉那隻死了的寵物狗的,為什麼會在這裏出現?」愛德華看着他爸爸。
「讓我看看。」
他爸爸說着打開了那張沾了血的聖誕賀卡,發現裏面是小孩子的手筆,畫有鐵鈎船長遭人道毀滅場景的蠟筆兒童畫,還歪歪斜斜地寫着「雪莉,來玩吧!阿各 X」,稚嫩的筆跡卻令人看得毛骨悚然。
「誰是阿各?」
「雪莉她不知道……」愛德華臉色發白地搖了搖頭,全因他回憶起剛才農舍裏那隻死狗還有滿室的狗血,想像得出他妹妹經受了何種程度的驚嚇。「她根本不知道鐵鈎船長被殺死了,我只是告訴她鐵鈎船長離開她是去了一個快樂的地方,她也相信了。」愛德華眼神驚恐地握緊那個項圈,攥得指節發白。「是誰仍留着鐵鈎船長的遺物?還給雪莉看一隻死狗?他一定告訴了雪莉……」
「冷靜一點。」莫法特先生按着愛德華的肩膀。斐瑞能從莫法特先生沉穩的嗓音中感受到那股安定人心的龐大力量。
「讓我們一起去調查這個謎團。」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UqGo8pE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