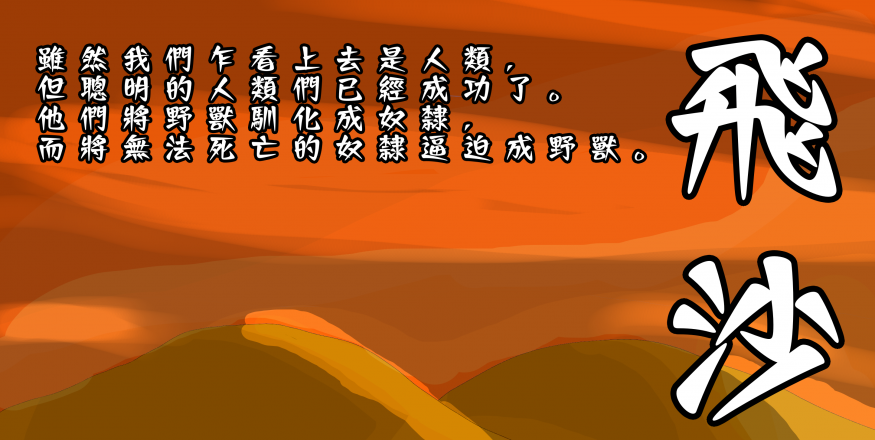當早晨第一道的曙光穿越沙丘的縫隙,順道帶著溫柔的微風將那成片的野獸給從睡夢中喚醒,睜開那豎起的金黃且銳利的瞳孔,戈多爾大軍再次開始了進攻。
血染的紅色沙塵取代了藍天,野獸身上染血的鱗甲將搖搖欲墜的磚瓦徹底的稀碎,利爪與刀劍再次交鋒,此時已經沒人分得清楚那戰場上的聲響是來自何方,是人類的嘶吼又或者是野獸的吼叫,只知道戰鬥開始了。
「打也打不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放棄嗎?」
「小心!十點鐘方向有火球,所有人各自找掩護。」
數量倍數增長的魔法,就連時刻盯著戰場天空的貝爾莉特都來不及應對,火球、土石以及閃電就迅速打在戰場中央,就連最前排的戈多爾也被一同的轟飛,掀起的陣陣煙塵遮蔽了大半的視野。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戈多爾的薩滿數量比起昨天增加了許多,不斷低語的奇怪語言穿插在戰場的喧囂聲之間,肆意的飄盪在所有人的耳邊。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在碎念什麼,但是那些話語絕對都不是些好東西,那些詞語之中甚至能夠激發出人的恐懼,好在現在還活著人早就已經沒那個力氣去思考恐懼為何物,勉強算是一種應對策略。
然而不管是甚麼策略,在面對數量比自己多出數百倍的的野獸面前,還是如同砂礫般渺小。
「啊!」
又倒下了一人,剩餘十人。
人類依然是人類,就算是習慣了戰場上的戰士,體力、精神都到達了極限,什麼時候會有人倒下都不會覺得奇怪。
「大家……我先走了一步了。」
拖著已經無法止住鮮血的腹部,四肢已經幾乎被撕咬得不成樣子,但那殘破的身軀毅然決然的跳進野獸之中,到全身四分五裂之前雙手雙腳始終沒有停下過。
死亡的潮流已經無法避免,那沒有理由的憤怒的尖牙,乘著黑色的潮水湧來,一次又一次的拍打在搖搖欲墜的堡壘上。
「好像是時候了……」
鱗口中呢喃著的同時,身處戈多爾大軍中心的漢娜突然高聲喊叫,只是並非是受傷或者遇到無法解決得敵人,而是看見了不得了的景象。
順著漢娜喊叫的方向,許多人也都看見了,那從地平線下湧現出的軍隊。
金屬的盔甲在陽光下顯得波光粼粼,鐵甲與武器的碰撞聲響參雜進本就混亂的戰場,戈多爾們的注意力很快就通通都被吸引,黑色的潮流隨即改變方向。
「那是支援?」
人類的士兵與戈多爾展開混戰,讓原本就滿是煙塵的戰場顯得更加昏暗和混亂,然而接下來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那些士兵本應該腳踩著鮮血與屍體,如同丟進煉爐中的金屬一樣,被戈多爾給輕易地融化,但現實卻是,穿著鐵甲的士兵訓練有素的維持著戰線,靠著騎兵的側翼攻擊,不斷的讓戈多爾向後退縮。
就算天空飛來強力的魔法,將身邊的戰友詐得血肉模糊也絲毫沒有畏懼的向前,每當有缺口出現時後方的士兵就會立刻補上,儼然就像是一隻訓練有素的軍隊。
沒有旗幟、沒有標誌,就連身上的盔甲都是來自各地東拼西湊起來的,實在無法判斷這是來自何處的軍隊。
神秘又強大的人類軍隊,總讓人感覺有些奇怪。
恐怕就連野獸們也沒想過這樣的結局,他們將兵敗如山的讓綿延整條地平線上的大軍中被切出一道裂口。
「鱗……」
貝爾莉特緊張的來到鱗的身旁說道,並用著右手抓住她手臂上那明顯的傷疤。那並非是來自與野獸的戰鬥造成的傷疤,反而身上的大多數傷疤與病症都不是來自野獸,而是在成為奴隸士兵前,由人類親手造成的。
「我知道,讓孔茲去接應就好,跟其他人說保持距離,特別是漢娜。我想索耶不會想再次看到她受到傷害,還有戰鬥可還沒結束喔!」
「嗯,知道了。」
鱗看出貝爾莉特的恐懼,那位平常天不怕地不怕,就算是遇見野獸也絲毫沒有畏懼的她,此時還是被勾起了記憶深處的回憶。
出生於妓院的女孩,經歷過一連串無人可以想像的童年,毒品、暴力都無時無刻伴隨在左右,直到她因為病症失去作用而被拋棄在掩埋場時,她才第一次的看見外面寬闊的世界。
很快的戈多爾大軍不知道是找到新的目標還是發現損失過大,主動的退了開來,雖然哨塔上還是能見到大軍行進的煙塵依然滾滾揚起在遠方,但至少牠們停止了對堡壘的進攻,這算是好事吧?
那支神秘的軍隊沒有想要追擊戈多爾的意思,很自然地聚集到了堡壘底下,踩著那成百上千的野獸屍體靠近。
「請問貴部隊是哪位率領的?」
孔茲率先從掩體後方走出,扯開嗓門大聲地問道。
或許是被孔茲的面容給嚇到了,最前排的士兵仰望著孔茲停下了腳步,畢竟現在孔茲是背著陽光,因此那如同被紅色油漆潑灑過全身的樣子,包含手中拿著的殘破盾牌和長劍,簡直就像是個剛從墳墓中爬出的活死人。
緊接著跟在孔茲的身後,鱗和漢娜為了清理身上沾染的屍塊,慢了幾步出來,身上也同樣的血跡斑斑。
漢娜用著被黏稠血液取代淚水的乾涸雙眼,看見到那人類軍隊一字排開在底下,如此壯觀的場面少女還是第一次見到。
「你好,我可以先詢問你們是奴隸還是士兵嗎?」
看上去像是指揮官的人物走上前,他身上的制服只有少許飛濺上去的血漬,從那生硬的腳步和委婉的手部動作,大概是哪個地方的貴族。
孔茲和鱗快速地互相交換了眼神後,孔茲便上前說:
「我是駐守於此的第一軍團奴隸士兵,十分感謝大人您的軍隊替我們解圍,但現在堡壘的狀況實在不如樂觀,恐怕沒辦法讓您的軍隊休憩。」
「第一軍團……是柴爾斯家的奴隸嗎?後面的把東西搬上來!」
在鱗和孔茲還沒理解指揮官的意思前,就有兩名士兵抬著木箱上前,箱子裡裝著許多細小的玻璃罐子,裡面裝著的全是深黑色的液體。
比起亞克的黑暗料理,那液體給人的感覺顯得更加詭異,莫名有種噁心的感覺。
「請問大人這是?」
「你們先喝下這些東西,你們奴隸不是想要自由嗎?這就是二皇子殿下要給予的自由道路。」
「二皇子殿下?柴爾斯公爵並沒有給我們下達新的指示,能先請問現在的狀況嗎?」
看著孔茲並沒有想要喝下藥水後,那名指揮官的臉色有了變化,他緊接著說: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不打算喝下嗎?抱歉我們的時間真的所剩不多了,希望來世能夠跟你們道歉。」
這瞬間的三人都沒能理解眼前的指揮官所說的話語,剛經歷過與死亡擦身而過的大戰,好不容易看見了那貌似是希望的光芒,然而他們錯了,那不是希望、也不是救贖,而是另一個深淵。
疲憊的戰鬥使他們的神經麻木,就連體力與反應力最好的漢娜也同樣比起平日裡還要遲緩許多。面對從毫無戒備的人類士兵裡飛出的箭矢,以及弱小的人類用著與野獸戰鬥的力量捅出的長槍,三人都慢了不到一秒的時間才分別舉起手中的武器做出回應。
在絕大多數奴隸的淺意識裡早就習慣了來自人類的攻擊,那種無法反抗的意志已經扎根於心中,哪怕是面對這種毫無理由的攻擊,也同樣不會有任何的抵抗,即使堅固的防禦都會下意識地露出細微的空隙,因為奴隸的主人若沒有成功,他們只會更加的憤怒而已。
那就放棄抵抗吧!
「漢娜、孔茲退後!」
鱗今天沒有參與太多的戰鬥,因此反應比較迅速些,很快的一手抓住漢娜,將她向後拉開閃過攻擊,並用著另一隻握著長劍的手擋下飛來的箭矢。如果再慢個半秒漢娜就會被飛來的箭矢射成蜂窩,然而救下一個人就已經是鱗的極限了。
少女怒吼著,憤怒、悲傷的眼淚無法控制的從眼角流出,身軀被鱗用出全力的托拽著,才壓抑住那股來自殺氣的衝動。
又要離開了……
又要失去了……
孔茲就算舉起了雙手上的盾牌和長劍,但仍然被數十把銳利的長槍給刺穿身軀,緊跟著一名士兵便揮刀斬下了他的腦袋。
「孔茲!」
鱗抓著怒吼的漢娜沒有回頭的跑回堡壘中,同時在高處觀望的貝爾莉特拉緊弓弦,將追上來的士兵點名般的逐一殲滅,女人不安的直覺成真了,果然人類依然是最該消失的存在。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