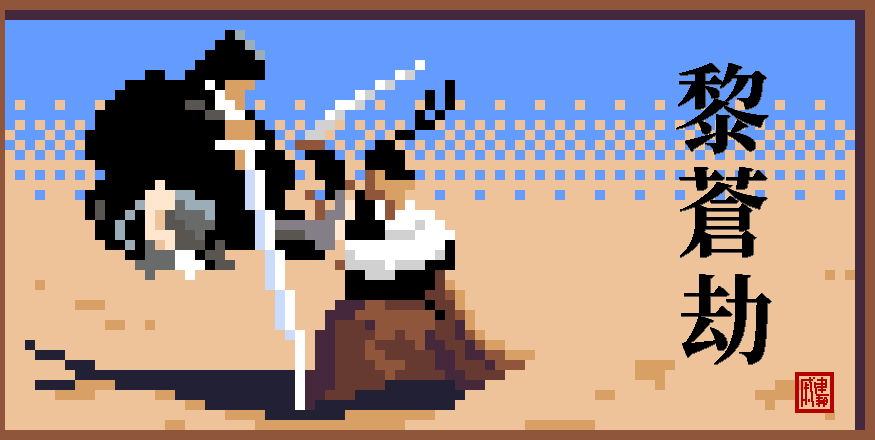客婉清與鄭恆舟擁抱片刻,便即分開。他兩當年相處,雖然交心,始終相待以禮。後來情素暗生,卻是誰也沒有機會說出口。客婉清取得降龍神掌圖譜後,女兒家心思,總覺得一旦將圖譜交與義父,自己與鄭恆舟便再無相見之日。況且她去丐幫做奸細便已有違本願,是以才會終日與酒為伍。她原先帶著圖譜回歸北京,不過臨到河間府卻又裹足不前,最後易容改裝,折返應天府,默默跟著鄭恆舟。
其後鄭恆舟趕往武昌府捉拿蒲察泰,參加武林大會,她都一直尾隨在後。本來孤帆莊一役,東廠若是其他人帶隊,她早就跳出來解圍。然則魏忠賢親自出馬,她便不知該如何是好。鄭恆舟雖是她的心上人,畢竟情話也不曾說過一句,義父卻是自小便待她極好。這兩人與她之間的親疏不言自明,她實在不該為了鄭恆舟去忤逆義父。只是當魏忠賢欲殺鄭恆舟時,她畢竟還是跳了下去。她心知這麼做會傷透義父的心,但是為了鄭恆舟,她什麼也不顧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出於一時激動還是當真對鄭恆舟刻骨銘心。或許內心深處,她也和客天傲一樣,早就想反魏忠賢。然而之後隨同義父回歸北京,住在富麗堂皇的深閨之中,出入都有東廠衛士跟隨,她對鄭恆舟的思念只有與日俱增,酒癮也越養越大了。每當微醺之際,她便幻想著鄭恆舟會突然出現,私定終身後花園,然後帶她遠走高飛。
而今,鄭恆舟真的出現了。
兩人心中歡喜,互訴別來之情。鄭恆舟鬱悶許久,直到今日才感到世上尚有開心之事。他真想一把抱住客婉清,說什麼也不再讓她離開。不過他至今不曾近過女色,此等真情流露的親密舉止,在他做來頗不自然。他輕輕握起客婉清的小手,客婉清也就讓他握著。適才相擁,出於激動,如今只是牽牽小手,客婉清都羞得低下頭去。
「清……貞妹……」鄭恆舟想叫點親密的,這才覺得自己實在不習慣客婉貞這個名字。
「鄭大哥,你愛叫我婉清,便叫我婉清吧。」客婉清道。「我這輩子,還是當客婉清那兩年逍遙快活點。」
「清妹,清妹。」鄭恆舟輕喚兩聲,覺得這個稱呼自在多了。其實他在想起客婉清時,心裡也是這般叫她。不過這話倒是不忙讓她知道。他問:「妳說有東廠衛士跟著妳?」
客婉清點頭:「我讓他們在樓下吃喝。這些日子,我常常一個人出來喝酒。他們習以為常,不會上來找我的。」
「妳在京裡,過得還好嗎?」
「義父待我很好,只是這些年沒時間多陪著我。」客婉清低頭偷看鄭恆舟握著自己的大手,輕聲道:「我本來一直覺得苦悶。今日見到你,一切都好了。鄭大哥,日後我還能時刻見到你嗎?」
鄭恆舟凝望著她一雙大眼,一時答不出來。他當然想說:「可以,我時時刻刻都跟妳在一起。」然而此事顯然不是說得那麼簡單。光是如何擺脫東廠眼線,不讓魏忠賢發現就已經困難重重。況且此刻他身陷北京官場的一場政治風暴中,只要一步踏錯,誰也說不準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嘆了口氣,說道:「清妹,妳我相處,聚少離多,接下來的考驗,只怕也不會少了。但是我心裡只有妳一個人,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客婉清笑中帶淚,輕輕將頭靠上他的肩膀。「大哥……」她說。「我好歡喜。」
兩人在蓮花廳裡說了一下午情話,直到再待下去東廠衛士必將起疑這才依依不捨地作別,相約明日再來相會。鄭恆舟待客婉清走後,打開窗戶瞧著她的背影夾在兩名東廠衛士之間遠去。客婉清走了一會兒,突然回頭,與他遠遠相望,露出甜蜜的笑容。一時之間,鄭恆舟只想拋下一切,帶她私奔。
***
第二天一早,鄭恆舟收到關外緊急公文,努爾哈赤身染惡疾,已於八月十一日暴斃身亡。鄭恆舟見報大喜,連忙趕往白府,要將這天大的喜訊告訴白草之。
來到白府,他不等下人通報,直接入內,走到白草之臥房外,揚聲道:「白兄!大喜!努爾哈赤死了!」
片刻過後,白草之終於推開房門,讓鄭恆舟進去。鄭恆舟一見到他,心情當場沉了下來。只見白草之渾身消瘦,臉色慘白,眼眶坍陷,神情頹靡,端得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與他印象中那個頂天立地的男兒判若兩人。
「白……白兄……」鄭恆舟難過說道。「你何苦如此呢。」
白草之瞧他片刻,一言不發,走回房內。鄭恆舟連忙跟了進去。房內酒氣沖天,要是不喝酒的人只怕一進去便要醉倒。地上堆了許多酒罈,桌上擺著幾盤小菜,一大罈酒,還有一個大酒碗。白草之以其獨臂在地上的空罈間翻找片刻,撿出了另外一個酒碗來,擺到桌上,倒了兩大碗酒,揮手讓鄭恆舟在他對面坐下。
鄭恆舟愣愣坐在他面前。就看白草之也不敬酒,也不說話,端起酒碗便喝,彷彿鄭恆舟根本不存在般。鄭恆舟看了一會兒,心裡難過,說道:「白兄,振作啊。」
白草之重重放下酒碗,狠狠瞪他,似乎滿心怨氣都要發在他身上。鄭恆舟見他如此,反而高興,心想有點反應至少也是好事。白草之瞪他片刻,搖了搖頭,又拿酒罈倒酒。倒完之後,他沒有拿起來喝,只是兩眼無神地望著酒碗,聲音沙啞地說道:「篤信昨日來向我辭別。」
鄭恆舟道:「是。那日之後,咱們師兄弟倆一直在錦衣衛幫忙救災。他看了太多慘狀,終於難以承受。我讓他回點蒼山去了。就像我們之前講好的那樣。」
白草之不置可否,端起酒碗又喝起來。
鄭恆舟實在看不下去,只想一把搶過他的酒碗,把房中酒罈通通砸爛。不過他沒這麼做,只因不管願不願意承認,眼前這個酒鬼依然是他最敬重的白草之。近三個月來,白草之避不見面,自是不想讓他看見自己這副德性。或許他真的不應該來,看到白草之這樣,對誰都沒有好處。
「白兄,」鄭恆舟語重心長。「外面的人不會因為你萎靡不振而放過你。北京官場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再不振作,他們會將你生吞活剝。洪都指揮史要我更改報告,讓你一肩扛下王恭廠爆炸案的責任;信王爺要我取代你的地位,繼續幫他辦事。」說著將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白草之默默聽著,始終面無表情。鄭恆舟說完,見他毫無反應,只是喝酒,說道:「白兄,你倒是說句話啊。」
白草之冷冷地道:「隨便他們怎麼搞,我不在乎。」
「怎麼可以不在乎?」鄭恆舟大聲道。「我絕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如此對你!也不能眼睜睜看著你自暴自棄!今天就是因為你變成這個樣子,他們才都會想來欺負你。如果你肯振作,如果你還是從前的白草之,洪朝春根本不敢動你,朱由檢也會再度重用你。人生在世,不管多麼消沉,起碼的尊嚴還是要有。我們不能讓人欺到頭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白草之看他一眼,說道:「一場功名擺在眼前,你不拿就笨了。」
「你說什麼?」鄭恆舟大怒,站起身來一把抓起他的衣襟。白草之毫不反抗,任由他抓起自己。鄭恆舟瞪視著他,卻在他的眼角看見淚光。鄭恆舟心裡一酸,輕輕將他放回椅子上,跟著坐回原位,終於拿起面前的酒碗來,張嘴喝了一大口。
白草之理理衣襟,斜眼看著他喝酒,等他放下酒碗之後,說道:「沒什麼事,你回去吧。」
「我昨日遇到客姑娘了。」鄭恆舟突然說道。
白草之一愣。
「見到她,我覺得人生的輕重緩急都變得大不相同。」鄭恆舟說。「前一刻我還在煩惱該怎麼應付洪朝春,要如何說服朱由檢。見到她之後,那些事情彷彿都不太重要了,就連魏忠賢似乎都不再是我的仇人。」他拿起酒罈,幫白草之倒了一碗酒,自己那碗卻不再添滿。「信王給我兩天時間考慮。白兄不必擔心,我會想辦法解決此事。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繼續這樣下去。寧遠衛的弟兄,不會喜歡看到你這個樣子。」
白草之將一碗酒潑到他的臉上,跟著把酒碗摔在地下。「滾!」他道。「你給我滾!」他臉頰流下兩道淚痕。「弟兄們喜歡不歡看我什麼樣子,輪不你來多嘴……」
鄭恆舟退出房外,關上房門,隨即轉身離去。他不願意再聽到白草之的哭聲。
***
來到百花樓,見到客婉清,鄭恆舟心裡煩悶,把白草之的事情說了。客婉清勸道:「大哥,白僉事打擊太大,需要時間平復傷口。這種事情急不得的。」
鄭恆舟道:「我也知道急不得。但是身為朋友,看在眼裡,實在難受。怎生想個法子,幫他振作起來。」
客婉清想了想:「他受到這麼大打擊,都是因為失去眾多朋友的關係。難道他沒有其他朋友嗎?」
「我啊,篤信啊。」
「我是說錦衣衛以外的朋友。」
鄭恆舟道:「武當山的師兄弟吧。我曾聽他說過,等到天下太平之後,他便會拋下功名,回歸武當。」
「武當山裡有什麼人在等他呢?」客婉清問。「好比說小師妹什麼的?」
鄭恆舟搖頭:「武當派不收女弟子。」
客婉清微笑:「大哥,我如今覺得,人啊,總要有個伴侶才完整。不管遇上了多大的困難,我知道,只要有你在,我都可以勇敢面對。」
鄭恆舟握握她的手,兩人相視一笑。「總不成叫我現在去找個媒婆幫他說媒?」
客婉清搖了搖頭,話鋒一轉:「信王要你明日答覆,大哥打算怎麼做?」
「不幹。」鄭恆舟道。「沒什麼好說,我不會賣友求榮,就算為了天下蒼生也不賣。」
「我當然知道大哥不會賣友求榮。問題在該如何應付信王及洪都指揮史。」客婉清說。她此刻雖然沉迷愛情,有了情郎,什麼都可以不顧,畢竟素有機智,而且自小便在北京官場外冷眼相看,對於權謀之術,還是有點心得。「就怕你拒絕了他們,他們另外還有對策。到時候會不會對你不利,就很難說了。」
鄭恆舟問:「我不過是個錦衣衛小小百戶,從來不曾對他們造成威脅。他們何必對我不利?」
「大哥,在官場上,知就是權。你知道的事情越多,談判的籌碼就越多,人家對付你的理由也越多。信王還只是個少年,照說不會是厲害角色,但是他能隱身幕後,操弄朝政,若非聽你說起,我真不敢相信。今天他能夠擁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關鍵就在於其他勢力都不知道是他在幕後搞鬼。」客婉清語氣嚴肅。「對信王而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大哥若是拒絕了他,立刻就會變成一個知道太多內情的人。他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鄭恆舟只聽得一股涼意上心頭,問道:「那洪朝春呢?」
「皇上要他找人揹黑鍋,白草之自然是最適當的人選,但沒人說一定得是白草之。要知道,當日寧遠錦衣衛趕來京城的人馬,除了白草之外,還有兩名活口。大哥若不願意陷害白草之,洪朝春大可以把罪名安在你的頭上。錦衣衛的公文都是密件,他愛怎麼捏造隨他高興。就算他說你是後金奸細,你也百口莫辯。他要你答允更改報告,只是為了封你的口而已。 」
鄭恆舟冷汗直流。「錦衣衛當真如此無法無天嗎?」
客婉清嘆氣:「大哥,錦衣衛就是如此無法無天。難道你今日方知嗎?」
鄭恆舟癱坐在椅子上,無奈道:「從前我在巡撫衙門當差,整天聽劉大人批評時事,自以為已經看透官場嘴臉。想不到當真置身其中,也不過是隻井底之蛙。」
客婉清道:「北京官場是天底下最骯髒的地方。正直之人絕不可能在此生存。白僉事能在這裡打滾這麼多年,自然有其為官之道。但憑大哥的能耐……」客婉清搖了搖頭:「不太樂觀。」
鄭恆舟道:「清妹,依妳說,我能怎麼做?」
客婉清道:「大哥勢孤力單,便只能接受安排。如果執意不肯出賣白僉事,大哥就得要找個靠山。」
「靠山?」
「本來嘛,最恰當的靠山便是信王,但信王偏偏又要逼你去做你不願做的事情。既然你註定要跟信王作對,不如就把他給賣了。朝廷中各方勢力都想找出這個幕後人物,大哥知道他的身份,那便奇貨可居。錦衣衛、禁衛軍、或者是我義父,隨便出賣給一方勢力,大哥都可以就此脫身。」
鄭恆舟搖頭:「找他們當靠山只會讓我越陷越深。再說信王雖然不仁不義,卻也是在為國家社稷著想。我抖了他出來,白兄不會高興。」
客婉清點頭:「這麼說也是。但是大哥如果不找靠山,那便只剩下一條路可走。」
鄭恆舟原也只想得到一條路可走。他問:「逃?」
客婉清道:「大哥便算過了這一關,日後還是麻煩不斷。所謂朝中無人莫做官,想要闖蕩官場,你遲早得要集黨結社。不想找靠山,還是趁早走吧。」
鄭恆舟嘆口氣,說道:「我根本不想闖蕩官場。我只想看著白兄振作起來。王恭廠一場爆炸,弄得我滿腔熱血都冷卻下來。救災的時候,我看過好多……理應讓人永生難忘的畫面,但是到後來都麻木了。人永遠不該對某些事情麻木,因為那不叫麻木,那叫心死。心一旦死了,就會對一切失去感覺。我師弟就是因為這樣,才決定退隱江湖。清妹,妳不知道在這種時候遇上妳,對我而言有多大的意義。因為妳,我的心又活過來了。」
客婉清輕輕靠著他。
「我總說為國為民,要擊退後金,扳倒奸邪。事實上,我一路走來,心裡總不踏實。東林黨人我一個不識,東廠的人除了妳義父之外跟我也無怨無仇,那一切都是高調,都是口號,都是俠義道該做的事情,於是我就去做了。我沒有一個珍貴的東西需要守護。就算失敗,充其量不過賠上我一條性命,那也沒什麼。即便天下蒼生都因為我的失敗而慘遭危難,似乎也不怎麼關我的事。但如今有了妳,一切大不相同。」
他伸手輕撫客婉清的髮絲,繼續說道:「白兄這些年來,一直以救國為己任,但是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卻是那班弟兄的性命。珍貴的事物一旦消失,原先追求的目標就失去意義。白兄心死了,我不知該如何讓他的心活過來,但我絕不能讓他就此倒下。我要救他,並不是因為那是俠義道該做的事情。我要救他,是因為他也是我必須不惜一切守護的人。」
客婉清問:「你要帶他一起離開?」
鄭恆舟點頭。「就算我必須點了他的穴道,揹他出城,我也一定要帶他一起走。」
客婉清道:「他終究會了解你一番苦心的。」
鄭恆舟輕輕將她推開一點,正色說道:「清妹,跟我一起走吧。」
客婉清愣愣瞧著他。
鄭恆舟道:「我知道,我無權要求妳在義父和我之間做選擇。但我實在不想繼續和妳相隔兩地。妳跟著我不能富貴榮華,但我答應妳,我會全心全意照顧妳一輩子,盡我所能不讓妳吃苦。」
客婉清淚中帶笑:「傻哥哥,我早就打定主意跟著你了。只怕你不想要我呢。」
兩人相擁片刻,甜蜜溫馨。接著分別離開百花樓,回家收拾行囊,相約傍晚在永定門見。
***
鄭恆舟回到錦衣衛指揮衙門,正要回房收拾,又有親兵來報。「百戶大人,白草之僉事有請。」鄭恆舟大喜,東西也不收了,連忙趕往白府。
到了白府,白家下人歡天喜地地迎他進去,之前愁雲慘霧的氣息一掃而空。來到內堂,只見白草之穿戴整齊,臉色比早上紅潤許多,儘管整個人依舊消瘦,總算恢復了些許往日風采。他將斷臂綁在袖中,揚起右手迎了上來,說道:「鄭兄,早上兄弟多喝了幾杯,出言不遜,頂撞鄭兄,好生過意不去。這就給你賠罪來了。」
鄭恆舟見他如此,心裡開心,連忙說道:「白兄哪兒的話?自己兄弟,賠什麼罪?看到你……現在這樣,我心裡不知道有多開心呢。」
白草之拉著他的手,來到堂前椅子上坐下,吩咐下人上茶,說道:「這幾個月來,承蒙鄭兄不棄,日日前來探望。兄弟心裡想不開,始終回絕鄭兄好意,實在是……唉……」
鄭恆舟道:「人總有心裡想不開的時候,白兄不需要放在心上。我日日夜夜盼望著白兄能夠重新振作,終於讓我等到了。」
下人送上上好香片。白草之親自倒茶,隨即舉起茶杯,說道:「兄弟暫時是不敢再碰酒了。此刻以茶代酒,敬鄭兄一杯。」
鄭恆舟當即和他乾了一杯茶。熱茶燙口,兩人也不在意。白草之放下茶杯,繼續說道:「多虧鄭兄今早跑來點醒我,不然我還不知道要醉生夢死到什麼時候。在北京這個地方,真是一刻都不能放鬆,一刻都不能示弱,一旦讓人逮到機會,真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鄭恆舟晃晃腦袋,看著茶杯,眨眨雙眼,困惑問道:「白兄,這茶……?」
白草之道:「茶中參了咱們錦衣衛獨門迷藥醉千罈,鄭兄沒嘗過嗎?」
鄭恆舟四肢無力,頭重腳輕,只說:「什麼?」
白草之解釋道:「洪朝春要誣陷我,信王又打定主意要放棄我。我白草之一輩子行得正、坐得直,沒有理由落得這等下場,鄭兄說是吧?別人欺到我頭上來,我絕對不能坐以待斃。」
鄭恆舟道:「我……我絕對不會讓他們這樣對你。我不會出賣你的。」
「鄭兄剛正不婀,我當然知道你不會出賣我。」白草之道。「但我同時也知道你不是官場鬥爭的料子,讓你去跟信王和洪朝春周旋,我一樣是死定了的。想要保住我這條命,只好犧牲你了。」
「你待怎地?」
「把你賣給洪朝春,然後重新取得信王重用。」
鄭恆舟撐不開眼皮,閉著眼睛道:「我……沒有出賣你……」
「你背棄我!」白草之吼道。「你們全部背棄我!我為了你們,做了多少犧牲,結果你們一個一個離我而去!」他深吸一口氣,放穩語氣道:「我做這麼多到底是為了什麼,嗯?還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讓我們幾十個兄弟好好享受享受辛苦換來的太平盛世?他們走,我不怪他們;我怪我自己。因為我的無能……害他們枉送性命。那是我的錯。但是在我傷心欲絕的時候,篤信居然說走就走?好吧,他走也就算了,這麼多年的交情,幾次出生入死,他不放在心上,沒有關係,就當他沒血沒淚。」他看著鄭恆舟,心寒地道:「但是你……你怎麼可以棄我不顧?」
「我沒有棄你不顧。」
「你要跟那個女人走!」白草之大吼,神色淒厲,眼泛血絲。
鄭恆舟難以回答。他確實打算跟客婉清遠走高飛,但是他沒有要棄白草之不顧。
「難道我不曾捨身救你嗎?難道我沒有處處看照著你嗎?難道我對你不夠好嗎?」白草之傷心地道。「你怎麼可以為了一個女人離開我?」
鄭恆舟從來不曾如此難以回答任何問題過。他擠出全身的力氣,試圖起身,結果雙膝一軟,癱倒在地。
「不重要了。」白草之哽咽道。「你們都不重要了。從今而後,我就只為我自己。富貴於我,不再如浮雲。我要貪圖。我要貪圖一切。即使要踏著你們的屍體往上爬,我也甘之如飴。」
鄭恆舟伸手抓住他的腳踝。「白……兄……」
白草之將他一腳踢開。「我永遠不想再見到你。」
ns 15.158.61.4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