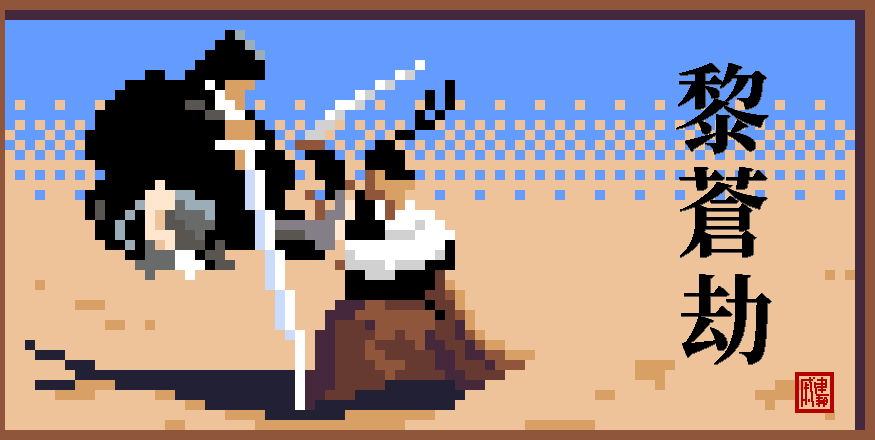白草之走後,劉敬先吩咐道:「遠志,出去門外看著,別讓人任何人進來。」陳遠志道:「是,大人。我先讓人搬走屍首。」劉敬先揚手。「一會兒再說。」跟著又向宋師爺道:「師爺,你先去打理打理。」二人得令而去。
鄭恆舟拱手道:「給大人添上這等麻煩,卑職好生過意不去。這些年承蒙大人照顧,今日特來向大人辭別。」說著伏身拜倒。「恆舟感謝大人知遇之恩。」
「快別多禮。」劉敬先連忙將他扶起。站定之後,問道:「你打算上哪兒去?」鄭恆舟答:「先離開北直隸。想辦法與我師弟會合,瞧瞧有無幫得上手的地方。接下來何去何從,到時再做打算。天下之大,總有我容身之處。」
劉敬先感慨道:「眼看朝政混亂,有才幹的人不是被捕入獄,就是被迫遠走它方。這樣下去......」他長嘆一聲,又道:「回想萬曆年間,皇上不肯上朝,朝政不修,缺員不補,奏摺不批,臣子連告老求去都不可得。好不容易盼到光宗皇帝繼位,朝政終有起色,想不到在位不過一月有餘,光宗皇帝就縱慾駕崩。當今聖上本來該有一番作為,卻因為朝臣結黨內鬥,而對朝政失去耐心,重用宦官,讓魏忠賢這等小人得勢。如今閹黨醞釀許久,勢力龐大,只待他們部署完畢,證據做足,那就萬事休矣......」說著搖了搖頭。
鄭恆舟勸道:「大人,大勢如此,咱們勢孤力單,只好隱忍一時。」
「你忍一時,我忍一時,如此隱忍下去,天下都讓魏忠賢拿去了。」劉敬拉先走到茶几旁,翻開兩個茶杯,提起茶壺來倒茶。他意示鄭恆舟過來坐下,推了杯茶給他。自己吹了吹早已冷掉的茶,喝了一口,問道:「恆舟,我一直以來就只在你們面前出一張嘴,評論朝政,卻始終毫無作為,只想明哲保身。其實你心裡很不以為然,是吧?」
鄭恆舟道:「不在其位,不掌其事。大人擔任保定巡撫,勤政愛民,份內之事毫不懈怠。朝廷中央的事情,那也不是大人管得了的。」
劉敬先搖頭道:「左、楊兩位大人數次欲舉薦我進入兵部任職,是我一直推辭不就。我甘於當個地方官,就是為了不要去淌那些混水。我整天嘴裡大放厥詞,但在有機會時,卻又不敢下去改變什麼。我自許清流,其實懦弱得緊。」
鄭恆舟不知能說什麼,只道:「大人......」
劉敬先搖手,說道:「平心而論,東林黨中當然有不少高風亮節之士。但是朝中數十年來紛紛擾擾,東林黨人也須付很大的責任。」
所謂東林黨,起源於萬曆三十二年,因得罪神宗遭到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於無錫重修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人開課講學,評擊時政,主張開放言路,實施改革,獲得廣大的支持,同時也遭到部分朝臣與宦官的反對。反對朝臣依地緣關係又組成浙黨、宣黨、昆黨等黨派,聯合起來與東林黨對立,自此開啟長達數十年的結黨鬥爭,史稱東林黨爭。
各黨朝臣每每利用主持京察的機會鏟除異己。京察便是官員考察制度。浙黨之人主持京察,就會趁機開革東林黨人,反之亦然。萬曆年間,各黨朝臣就這樣革來革去,鬥得不亦樂乎。加上神宗為了欲冊封鄭貴妃之子為太子遭到群臣阻擾之事,憤而怠政,竟然三十年不肯上朝,有些朝臣甚至從來不曾見過皇上一面,中央地方官員出缺也不補人,邊疆戰事吃緊也不增援,導致萬曆年間朝庭空虛,無人主事,就此種下明朝滅亡的禍根。
光宗繼位後,對內重用東林黨人振興朝政,對外啟用熊廷弼紓緩戰情,終於讓明室的困境稍得疏解。可惜光宗一生活在其父陰影之下,三十九歲方得登基。身獲自由後,立即收下八名美女,縱慾發泄,不久便即病倒。之後又吃了太監的瀉藥、朝臣的紅丸,終於暴斃而亡。
天啟帝初登大寶,力圖振作,同樣重用東林黨人。然而東林黨人卻不自愛,持續惡鬥他黨,爭奪官位,弄到天啟心生不耐,懶得處理政務,導致魏忠賢趁機干政。他聯合浙黨等所有與東林黨不合的朝臣組成閹黨,處處打壓東林黨人。如今楊漣與左光斗因彈劾魏忠賢被捕入獄,東林黨人人自危,紛紛收起之前的氣燄,上朝時安靜無聲。說什麼高風亮節,只怕都在結黨鬥爭中化為烏有。
劉敬先繼續說道:「我一直排斥結黨議政,是因為這些年來,朝臣們結黨根本不是為了議政,而是為了爭奪權力與官位。要說閹黨可恨,其實有不少人是讓東林黨鬥得走投無路這才投靠魏忠賢。好比說阮大鋮,本來還親東林黨,要不是去年趙南星在京察中阻他升遷,他又何必去跟閹黨的人混在一塊兒?真說起來,若非閹黨諸臣與宦官掛鉤,惹人反感,其實東林黨與閹黨也沒有多大差別。」
鄭恆舟皺眉道:「大人這麼說雖然有理,然而縱觀時事,過去這些年裡,只要皇上重用東林黨人,朝政便有起色。我想東林黨還是有其長處的。」
劉敬先點頭:「東林黨人長於問政,這點毋庸置疑。想要救國,得靠他們。只不過他們在權力鬥爭中打滾太久,不少人已經忘卻士大夫應有的氣節。政治黑暗至此,就算沒有黨爭,只怕也要多年時間才有起色。然而無論如何,朝臣之間集黨結社,明爭暗鬥是一回事。魏忠賢動用東廠威權,巧立罪名,栽贓嫁禍,私刑處置,屈打成招,如此迫害東林黨人,總不是個道理。」
「大人所言甚是。」鄭恆舟道。
劉敬先眼看著他,緩緩說道:「我得到消息,此刻魏忠賢正著令閹黨諸臣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本,偽造一部東林黨點將錄,藉以抹黑東林諸臣。待得此錄一成,他定將上呈天子,惡意毀謗,到時候黑的給他說成白的,東林黨人在劫難逃。」
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並稱明宮三大案。萬曆四十三年,有人手持木棍闖入太子寢宮行兇傷人,事後查出乃神宗寵妃鄭貴妃主使,是為梃擊案。光宗縱慾過度,罹患腹瀉之疾。服用鄭貴妃親信太監所獻藥物,病情加重。之後又服用朝臣所上的紅丸,暴斃而亡,是為紅丸案。光宗駕崩後,李康妃霸佔乾清宮,夥同魏忠賢挾持皇太子,要朝臣奏章先呈李康妃,後呈皇太子,導致朝臣反彈,聯合要求李康妃移出乾清宮。李康妃被迫移宮,天啟皇帝順利登基,此為移宮案。明宮三大案中,東林黨人出力甚多,奠定他們在朝廷中的地位。魏忠賢意欲藉機翻案,顛倒是非,徹底抹黑東林黨賴以發跡的三大案。這一步走下去,東林黨終將難以翻身。
鄭恆舟恨恨地道:「這奸賊如此惡毒,難道天底下就沒人治得了他嗎?」
「他得皇上寵信,滿朝文武鬥都束手無策。」劉敬先道。「這幾年來武林中陸續有人出手行刺,卻連他一根寒毛都沒傷到。」
鄭恆舟無奈搖頭:「傳說魏忠賢武功之高,深不可測。就算沒有東廠護衛,武林之中只怕也沒多少人是他的對手。要行刺他,難如登天。」
劉敬先嘆道:「單憑你我二人,對付魏忠賢直如痴人說夢。然而當此浩劫將至之時,咱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殘害忠良。萬一魏忠賢真把東林黨給滅了,到時候他隻手遮天,說不定還想在那九千九百歲上多加一百歲。」
鄭恆舟聞言駭然,問道:「魏忠賢當真如此大逆不道?」
劉敬先搖頭:「誰說得準?我只知道此人權勢滔天,慾望無窮,兼之武功天下無敵。在他眼中,謀朝篡位也未必是什麼不可為的事。」見鄭恆舟心中驚訝,一時說不出話來,緩緩說道:「恆舟,我有件事想托你去辦。」
鄭恆舟一聽,知道劉大人終於進入正題,當即收拾心神,正色道:「大人請吩咐。」
「張大鵬案,可有頭緒?」劉敬先問。
「有。原來他是少林弟子,不知為何還俗前來保定定居。我聽見白千戶與其屬下談話,京師附近似乎還有其他像他這般的武林人士隱居市井,伺機圖謀。錦衣衛今日奉命收拾殘局,動手行兇的乃是東廠高手。」他見劉敬先不動聲色,問道:「大人早知錦衣衛會插手此案?」
「我也只是猜測。」劉敬先道。「張大鵬遭人擊斃,自是身份敗露之故。不論動手之人為誰,總之不會有我們巡撫衙門插手的餘地。」
鄭恆舟又問:「大人知道張大鵬的身份?」
劉敬先點頭:「似張大鵬這種人物,保定府內尚有四人,北直隸約莫有三十人,都是名門大派的高徒。」
鄭恆舟疑惑:「他們隱居市井,所為何事?」
劉敬先道:「三年多前,魏忠賢出掌東廠,左光斗大人就擔心他有朝一日會頃東廠之力誅殺東林黨人。於是他藉病告假,四下奔走,聯絡武林之中有志之士,暗中保護東林黨人。這件事情,少林、峨眉等名門正派都有參與,就連令師點蒼神劍也居中調節。幾年下來,倒也暗地裡解救過不少危難。」
鄭恆舟點頭:「此事我也略有所聞。武林中人本就常與東廠為敵,經左大人奔走請援,各大派掌門人幾番商議,從而畫分地緣,互通聲息,彼此照應,大大妨礙了東廠在地方上的執法力。魏忠賢處心積慮想要鏟除武林人士,主要原因就是各大派暗中相助東林黨的緣故。」
「然而南北直隸始終都是東廠的天下,尤其北直隸乃東廠根據地。武林人士保護地方官員得心應手,想要混入京師辦事卻是困難重重,偏偏中央官員才是最容易遭受東廠打壓之人。」劉敬先緩緩喝口茶,繼而言道:「為此,各大掌門數度密會,集合各派少數精英成立了一個保黨同盟,各自從派中挑選幾名武功精湛,但卻默默無聞的弟子或宿老,改名換姓潛入直隸,隱身市井之中。三年來,他們掩藏身份,從不顯示武功,也不出手管事,為得就是等待魏忠賢終於決定一舉鏟除東林黨人。」
「保黨同盟嚴守機密,此事就連各派的首腦人物也未必知曉。東廠雖然得知此事,但卻無法查出所有人的身份。眼下東林六君子遭擒,閹黨蠢蠢欲動,保黨同盟認定時機已至,下令潛伏在南北直隸境內的武林人士採取行動,伺機救援東林黨人。保定府內保黨人士所勾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協助左夫人脫困。」
鄭恆舟「啊」地一聲,說道:「張大鵬讓東廠先下手為強。」
劉敬先點頭:「我想東廠只有查出張大鵬的身份,所以保定府其餘四名保黨人士才能逃過一劫。然而張大鵬是保定府保黨同盟之首,他一死,保黨人士亂了方寸,左夫人便讓錦衣衛給拿走了。」
「錦衣衛回報,劫走左夫人的亂黨共有五人,其中之一擅使點蒼劍法。」鄭恆舟邊想邊道。「這麼說,我師弟是臨時趕來主持大局的?」他對於毛篤信參與保黨同盟之事毫不意外。他的恩師柳成風吩咐弟子對東廠敬而遠之,是因為擔心弟子傷在東廠手下,其實他本人極為痛恨東廠。只不過毛篤信參與這等大事究竟是奉了師命,還是自己做主?這點日後倒要弄個明白。
「你師弟?書生劍毛篤信來到保定府了?」劉敬先語帶訝異,顯然並不知情。「原來王公公並非信口誣賴,劫走左夫人之事,確實是點蒼派領頭幹的?」
鄭恆舟將毛篤信下午來訪之事說了。劉敬先聽完笑道:「原來如此。恆舟,王公公找上門來之時,我還真以為左夫人是你帶人劫走的。似你這等人才甘於屈就巡撫衙門擔任捕頭,怎麼看都像是保黨同盟的人呀。」
「大人說笑了。」鄭恆舟說,繼而又道:「大人,卑職有一事不明。」
劉敬先微笑:「你想問我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鄭恆舟點頭:「正是。大人心腹之人都在巡撫衙門當差。這些事情既非咱們幫你查出來的……」
劉敬先道:「我並非刻意瞞你,然而此等朝廷鬥爭之事本就十分機密,一不留神就會惹來殺生之禍,我不想牽扯衙門中人,是以沒讓你們知道,也不派你們留意這類事情。」他停了一停,眼看鄭恆舟仍是眉頭緊蹙,繼續說道:「其實朝廷之中還是有些像我這種不願牽涉黨爭的官員,像是刑部郎中謝哲道大人、兵部主事何再興大人。我們不像各黨那般招搖聚會,只是私下互通聲息。王公公說得不錯,朝廷是個大染缸,進來了就別想置身事外。似我們這些沒有靠山之人更需時刻留意當朝情勢,不但要洞悉閹黨一舉一動,更要掌握東林黨的動向。」他向前一湊,正色道:「所謂脣亡齒寒,我們不能坐視魏忠賢鏟除東林黨人。當情勢一發不可收拾之時,我們得要知道能夠做些什麼。」
鄭恆舟思前想後,心知光靠幾名無黨無派的官員難成這等氣候,劉大人的黨羽裡必定還包括一股專司打探機密的勢力。單就保黨同盟一事,劉大人所掌握的內情甚至多過東廠。放眼京師,也只有錦衣衛有此實力。他問道:「那錦衣衛白千戶......」
劉敬先接過來道:「我也是今日初識。這白草之行事難測,動向不明。儘管今晚看來,此人是友非敵,然而他說話不清不楚,令人難以盡信。錦衣衛雖有同情朝廷命官之人,畢竟人數稀少,而且不敢張揚。像他今晚這般率領手下殘殺東廠,不要說我不曾見過,根本聞所未聞。我猜測他背後必定有人指使,一個膽敢暗地衝撞魏忠賢之人。或許是洪都指揮使,不過我看不出他這麼做有何好處。日後我得持續留意白草之的動向才行......」
鄭恆舟心想此事內情太多,一時三刻也問不明白。雖說天色已晚,東廠方面理應不會為了拿他一個小小捕頭加派人馬,然而畢竟身處險地,不宜久留。他問道:「大人說有事要我去辦?」
劉敬先道:「不錯。左大人有個學生,名叫史可法,於前日午後疏通獄卒,進入大牢探監,讓左大人趕了出來。據我們在刑部大牢裡的人所見,左大人曾趁亂偷傳一張字條讓史可法帶出大牢。」
鄭恆舟問:「那是什麼?」
「不知。」劉敬先搖頭。「史可法是左大人的得意門生,此刻尚無功名,是以東廠並未留心。左大人在獄中對其言道:『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足見對史可法極為看重。我們認為左大人交給他的,必定是極為要緊的事物,其上多半記載了東廠一直逼左大人交出的保黨同盟名冊所在。」
鄭恆舟訝異道:「還有這種名冊?」
劉敬先點頭:「保黨人士身份機密,由各派分別造冊,交與左大人統籌,是以完整的名冊只有左大人保有一份。一般相信名冊被藏在蘇州無錫東林書院裡。東廠曾數度派人夜探書院,始終找不到這份名冊。東林書院乃是東林黨人根據地,除非有明確證據,魏忠賢也不好直接派人進去搜刮。恆舟,這份名冊事關重大,要是讓東廠得去,一來潛伏京師的保黨人士難以倖免,二來也等於是抓住了武林人士勾結東林黨人的證據。一旦坐足東林黨人的罪名,魏忠賢便可以勾結亂黨為由,名正言順地發兵攻打各大門派。到時候武林腥風血雨,死的人可多了。」
鄭恆舟聽得直冒冷汗,說道:「卑職必當竭盡所能,不讓名冊落入東廠手中。」
劉敬先道:「東廠對此名冊志在必得,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史可法平安離開刑部大牢,難保不是東廠欲擒故縱之策。眼下他還在沒離開順天府,你遭受東廠追緝,可不能北上前去找他。今晚你出南門離開保定,先到河間府盤旋幾日,待得史可法抵達後,再設法跟上,若是見他遇上危難,你便出手代為料理。即便他此行不是為了取回名冊,你也當是守護忠良。如今政治黑暗,當朝的臣子鮮少出淤泥而不染。想要振興大明王朝,只好寄託在你們年輕一輩的手裡。」他愣愣地看著茶碗片刻,跟著抬起頭來,說道:「此刻宋師爺已經打點好南城門的守衛,你寄在我這裡的糧餉,也給你備好了。你這就出城吧。」
鄭恆舟站起身來,恭恭敬敬作了個揖。「大人請保重。」說完退出書房,離開當差五年的巡撫衙門。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