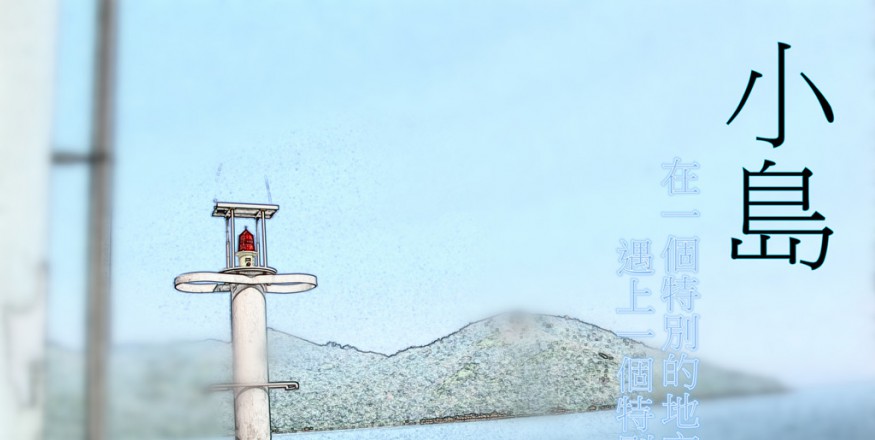於是不知怎的,我一見到他就在講、講、講;他只有一個反應就是微笑,沒叫我住口,也沒什麼表示。
我不知他心裏有否想叫停的時候,但他沒說,我就不理。
每次講完,我又會覺得心頭輕了一點。如果連體重也可以隨之輕一點就好了。
跟他講話是很過癮的,因為他只會微笑。我通常選他雙手都沒空的時候來講,例如在做飯、洗廁所、或是澆水、抹窗、洗地板,那他連寫這個回應也做不到,被迫聽我說。
大概我是欺負…不,是看准他是啞巴,講完可以很放心,就像跟屋外那棵椰子樹講話那樣。即使我講到不開心,口水鼻涕流到一臉,也只有他知道。
雖然他也是個人,會寫字,但我感覺到,他不會洩露出去,一來他還得靠我的薪水過活,二來—他不會。
有時我講了一整天,很累、很隨意地在沙發或沙灘椅上睡著,他會替我蓋毯子,或是抱我回房間。
講多了,他簡直成了我的垃圾筒,有什麼想說,找他就好。講完克里斯、合作的出版社和工作,我就講去旅行的經歷、讀書時代的事等等。每次講得像機關槍那樣停不了口,我覺得不亦樂乎。每天我就是找他講話、講到肚子餓他就會給我弄點吃的、再講到累就睡覺。
有天他沒有在,只留下花、紙條和早餐。原來他今天放例假。沒有人聽我講,我頓感空虛…
四周都相當清靜,只有海浪聲和風聲。
我在屋內又踱又坐,又看電視又看書什麼的,好不容易地才捱過一個早上。麥可不在,島上就只得我一個,想到這個我的心頭便很冷。
我是不是該出去走走?但我怕又見到克里斯,或是其他我不想見到的東西,而且我不知該去哪。這裏吃的用的什麼都有,只是沒有別人罷了。
我午飯做了一大盤炒飯,卻沒有人跟我分享。我獨自啃完,過了一會便肚子痛。
我發短訊給麥可,問他在哪裏,什麼時候回來。他答我在忙。我告訴他肚子痛。他問我發生什麼事。我回他吃炒飯,吃了很多,所以現在肚才撐得很難過。
他問我吃了多少。「七碗。」因為我炒了七碗,用料十足,而且吃著老覺得不夠,一碗光了又一碗。
ns 15.158.61.1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