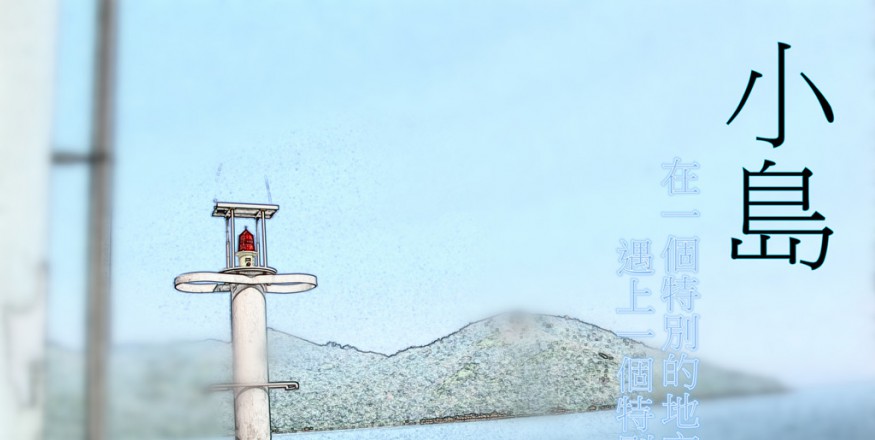x
x
這個人很高大,看上去也挺健碩,皮膚是小麥色,像烤得很漂亮的雞翅膀。說是傭工,看來也像,只見他穿普通的T恤短褲,頭髮有點淩亂,腳踏殘殘爛爛的拖鞋,扛著像是用來耕作的用具回來。
雖然說是傭工,但我對這麼一個粗獷男人有點抗拒,尤其買下來只得我一個女人住。我想業主要挑客人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男僕,所有人包括我,買下之後一定會換掉他。
經紀告訴我,除非這男僕自己離開,否則最好不要辭掉:「他在這島出生,父母替這裏以前的主人工作。這算是他的故鄉。」除了求學時期去過市區,其餘的時間都在這裏當男僕。
經紀看我跟其他客人一樣,很在意這男僕,便非常落力地讚賞和推介他,比起推銷這島和別墅時差十萬八千里:「妳看他多健碩!搬啊、抬啊,什麼體力勞動都交給他就好。他可以替妳出去購物,完成所有家務,妳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還包辦所有維修、園藝整理,妳不必操心。妳自己一個人住,總要有個人照應,起碼發生了什麼意外,也有個人替妳打電話求救。晚上也有個護衛。薪水才幾千元,簡直物有所值!」
這個男僕向我咧起嘴巴笑,彷彿也在給我好印象,希望我會聘用他。
但就是晚上孤男寡女共處一島才叫我不安。
經紀見我還猶疑,悄悄對我說:「還有最大的一個特點,他是個啞巴,保證不會頂撞妳;就算妳有什麼秘密也不會說出去;而且看他多戇直,無事絕對不會來騷擾妳的。」
雖然經紀是「悄悄」地告訴我,但男僕還是聽得見。他黯然地垂下頭,拿著清潔工具從大門走出去。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傷害了他。
其實來看過盤的人,以及這個經紀,也傷害了他。一個傷殘人士想在自己的出生地自力更新而已,但「我們」卻自私地,因為自己的喜惡而想趕走他。其實說起來,他才是這裏的「原居民」,「我們」是「外來人」;可是我們卻在搶他的地方、搶他的生存空間。
我問經紀他住在哪裏,別墅裏沒看見傭人房間。
他帶我走到別墅後面,走了五分鐘,穿過一個花叢,有個小石屋和小小的前院,打理得很整齊。男僕坐在小木櫈上,洗木盤裏的衣服。
男僕聽到聲音抬頭,看到是我們勉強拉起了一個笑容,然後又低頭繼續洗。我想他仍為剛才的事不太開心。我明白他的心情。如果有人向別人「介紹」我的缺憾,我也不能接受。他還能對我們勉強一笑已算大量。
ns3.137.148.22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