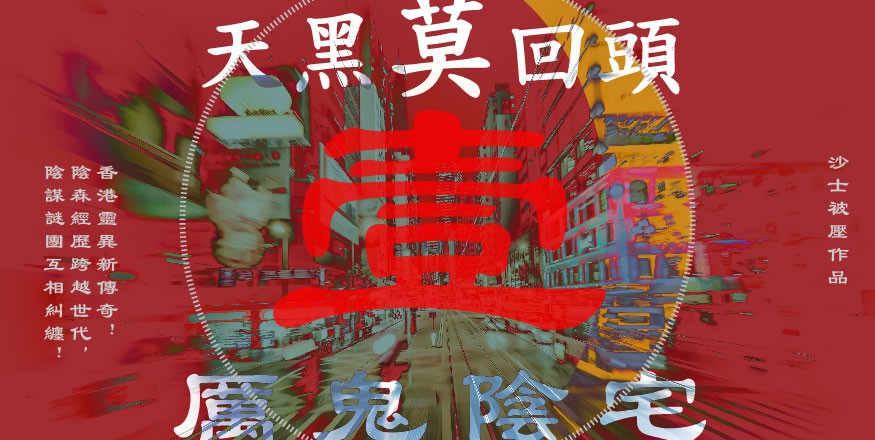這一回的事主是由小葉介紹給我們的,名字叫啊成,是小葉的大學同班同學。最近他好像被什麼東西給纏住了,聽說小葉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於是就求她幫幫自己,小葉見他面色的確很差於是馬上把他轉介給我們。
我跟大叔還是老樣子約了啊成在咖啡廳裡見面,在他出現時我被他那幅憔悴的模樣給嚇到了,那黑眼圈真的已經可以媲美熊貓。啊成坐下後簡單的作了一番自我介紹,然後就開始跟我們講述自己所遇到的問題。
「我已經三天沒有睡過覺了。」啊成看上去好像快要支持不住的樣子。
「能說一下不睡覺的原因嗎?」我小心翼翼地問。
「現在我每次入夢都會夢見一個懸浮在半空的女人頭,在夢裡她張着半開的眼睛不斷的追着我,每當我從夢中驚醒時都會發現全身無法動彈,而且耳邊還會傳來一把女人的笑聲,聽起來感覺好像是在嘲笑我。」啊成閉上眼睛努力逼使自己去回想那段可怕的回憶。
鬼壓床嗎?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呢,確實是挺可怕的。
「後來我發現只要不睡覺就不會作那種恐怖的夢了,一開始我是靠喝咖啡來提神的,效果還算不錯,但是在第二天晚上時咖啡因對我來講已經沒什麼用了,現在的我是全憑着意志力來支撐自己不去睡覺,可是我覺得自己已經快要到極限了,尚師傅,求求你幫幫我,我不想再發那種可怕的夢了。」啊成苦苦哀求大叔幫忙。
大叔一聽就知道他撞邪了,於是就問他最近有沒有招惹過什麼東西。
啊成想了想就說:「有,內地最近發生了一單殺人分屍事件,我嘲笑過那個女死者,說她死得活該。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夢中的那顆人頭跟互聯網上刊登的女死者照片十分相似。」
「人家都已經被人殺害了,你幹嘛還跑去嘲笑人家?死者為大,這道理還用別人教你嗎?」大叔聽到後馬上訓斥他,啊成聽到後知道自己理虧所以垂頭不語。
大叔在訓斥後就讓他把事情的前後經過全都如實報上,啊成只好灰溜溜的把前幾天上網的事慢慢說了出來。
那是一宗內地的新聞,女死者名字叫啊花,是一間小賣店的女老闆,啊花人不比花嬌但卻水性楊花,經常蒙着丈夫外出與其他男人鬼混,而且一走就是好幾天,啊花的老公呂先生生性懦弱,雖然知道自己綠帽子已經從頭頂套到腳底了,但仍然不敢對她有任何微言。
有一天,有個流浪漢發現在河邊的橋底下有一根用報紙包着,約有棒球棍那樣長度的物體,好奇心驅使下流浪漢走了過去把報紙拆開,結果卻發現是一條人腿!在他向警方報案後,市裡開始陸陸續續在不同的地方有人體的殘肢被發現,有的是在江裡被撈上來,有的則是被棄置於垃圾站中,殘肢經過鑑定後發現是屬於同一個人,而且是一名女性的,可是不管怎麼找也好死者的頭就是沒被發現。
過了幾天,有個老人去登山時發現有一個旅行包被人扔了路邊,老人見裡面鼓鼓的就以為是有人不小心把它遺留在這裡了,於是他就把拉鏈拉開想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沒想到打開後發現裡面裝的居然是一個死不瞑目的人頭!老人差點沒被當場嚇死。
內地公安在調查其DNA後確定這人頭就是那些殘肢的主人,在經過其他鑑定後就確定女死者的身分就是開小賣店的啊花。很快的公安就來到了呂先生的家裡並把他拘捕起來。
呂先生被捕時沈默不語,什麼話都沒有說,就好像根本不關自己事似的,而現場環境雖然被他清理拭擦過,但是經魯米諾測試後證實了小賣店就是第一現場同時也是肢解女死者的地方,而住在附近的居民都說過小賣店曾經有幾天突然無緣無故的不開門做生意。
鐵証如山,呂先生被警方以謀殺罪起訴並判處死刑。
根據呂先生的自白,妻子長年累月的給自己戴綠帽子讓他覺得自己一點尊嚴都沒有,有一天妻子又準備出去跟別的男人鬼混,呂先生終於忍受不住,他攔在門口不讓妻子出門,而女死者當然不依於是就跟他吵了起來,在跟女死者爭執過程中呂先生以往積累的怨氣一下子爆發了,他拿刀子把妻子活活的插死,然後把她肢解掉再分批埋在深山裡。
到這時問題就出現了,如果真如呂先生說他把屍體全埋了在深山裡的話這宗案子永遠都不會被揭發,因為啊花經常會因為跟男人鬼混而失蹤,要是啊花突然不見了大家都只會說她跟別的男人跑了,而不會懷疑她已經被呂先生殺害並埋掉。
然而屍體卻突然在市內不同的地方出現,從而揭露了這宗案件,而把屍體扔到市區的不是別人,正正就是呂先生他自己本人!他說不知道為什麼腦袋裡一直有把聲音跟他說一定要把屍體扔到市裡才會安全。
有人說呂先生在長時間受壓下得了精神病,而有些人則說是女死者的鬼魂在作祟,她不甘自己被殺於是就迷了呂先生的心竅讓他把自己的屍體扔到市區從而讓警方注意到自己的失蹤。
新聞到了這裡就結束了,啊成說他在看完這篇報道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覺得女死者水性楊花給綠帽子自己丈夫戴,死了活該。而怪事就是在他說完以後就開始發生了。
大叔聽完後就覺得啊成應該是被那女死者的冤靈給纏上了,至於原因大概就是因為啊成嘲笑自己所以來報復他了。從他被鬼壓床時會聽到笑聲來判斷,那女鬼是以看到啊成恐懼的樣子為樂並同時嘲笑他以達到報復的目的。
一般來說由於距離太遠,這一類的靈體大多數都只能小打小鬧而已,不會對人造成什麼大傷害。不過那叫啊花的女鬼生前所做的事的確是不怎麼光采,但充其量也只是道德問題,罪也不至死,啊成說她死的活該的確是有點過分了,難怪人家從大老遠的地方也要過來整你。
「尚師傳……那我現在該怎麼辦啊?」啊成苦惱地說。
「惹惱了別人當然是要道歉啊!這還用教。」
大叔讓啊成帶我們回去他的家,這樣大叔才可以替他進行儀式他把女鬼請走,啊成聽到後就明白大叔這是答應幫他的意思了,他那憔悴的臉上終於頭一回出現笑容。
在到達啊成家門前時,一個菲藉的女傭打開門迎接我們,我進去後往四周打量了一下,他家的面積少說也有一千多呎左右而且還請得起傭人,家底看起來算是不錯的樣子,相信他給大叔的酬金也不會少吧?大叔從蔡先生手上得到的賣符錢已經快用得七七八八了,前幾次的工作他根本都沒有收到什麼錢,現在也該是時候賺點小錢來用了。
我們在脫了鞋子後就直接走進啊成的房間裡,大叔讓那菲傭待會兒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開門打擾他,那菲傭雖然不明就裡但仍然點頭答應了。大叔說完後就關門並順手鎖上了。
「那麼尚師傳,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啊成坐到自己床上問到。
大叔想也不想就說:「很簡單,睡覺就行了。」
「睡……睡覺?」啊成驚呆了,過了一會他才緩回神來說:「我們三個人睡這張床恐怕有點擠吧?」
我聽到後大驚,馬上就轉過頭去問大叔:「尚大哥,你這是要鬧那樣啊?我為什麼也要睡?這是要桃園結義嗎?」
大叔白了我一眼說:「他理解錯也算了,倒是你發什麼神經?我什麼時候說要三個人一起睡了?都睡了誰幹活?」大叔用食指指着啊成後又說:「要睡的人只有你。」
大叔說完後就讓我在房間的四角安置紅蠟燭,而他則用紅線圍着門把繞了幾圈,然而啊成還是不解地問:「為什麼非要睡覺不可?如果又夢到那女鬼我真的以後都不敢再睡覺了。」
大叔解釋說:「因為那女鬼只會在你入夢時作祟,所以為了方便把她請出來只能讓你睡覺咯。」
啊成聽到後疲累地點了點,然後說了一句「那就拜託你們了」就蓋上被子準備入夢了。可能是因為三天沒有睡覺的關係,他躺下來後還沒兩分鐘就傳來了陣陣呼嚕聲。
大叔在房間中央又點了根長紅燭然後就把左眼上的眼罩給解了下來,在所有準備都完成後他就把房間裡的燈關上,「啪」的一聲後整個房間馬上變得昏暗下來,現在這裡就只有四角以及中間的蠟燭為我們提供着視野。
房間裡除了我跟大叔的呼吸聲外就只剩下啊成的呼嚕聲了,在他入夢沒多久後他就突然在床上掙扎起來,看來是在作惡夢了,與此同時四角的燭光亦「嚓」的一下全滅了,視野頓時變差。
「來了。」大叔手裡抓着黃符說,而我聽到後全身的神經都繃緊起來。
到底會從那裡出現……那懸浮在半空的人頭。
但是等了一會兒都不見有什麼動靜,於是我就壓低聲音問大叔:「不是說來了嗎?怎麼沒反應?」
大叔把手放在嘴邊比了一個安靜的手勢又說:「四角的燭光滅了就說明它來了,安靜一點。」
我只好回到自己崗位上等着,房間裡還是只有我跟大叔的呼吸聲,還有……
慢着,啊成的呼嚕聲怎麼沒了?
我看了啊成的床鋪一下,發現原本呼呼大睡的氣居然不見了!我急忙向四周張望想把他找出來,可他房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躲人啊?唯一一個看上去可以收納一個成年人的衣櫃就在大叔的旁邊,但是這跟床鋪起碼有四步左右的距離,要是他跑到那裡的話大叔一定會發現的。
大叔彷彿看穿了我的憂慮,他用眼神瞄了床鋪一眼示意讓我再看清楚一點,我只好把目光再次放到啊成的床鋪上。
是不見了啊……被子的被翻了起來,裡面確實是空無一人,我再次望向大叔尋求指點,沒想到大叔剛剛讓我看的原來並不是床鋪的上面,而是……下面。
我這才留意到床鋪底下是空的,要說啊成剛才是趁着燭光滅掉的那一刻竄進了床鋪底下也並非不可能。
床鋪底下啊……我又想起了老爸在小時候給我講的鬼故事,床鋪底下總是各種可怕的妖怪躲藏的地方,要我選一個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我肯定是選床鋪底下。
現在那裡有起碼大半張的被子把底下給遮住了,我沒法看清楚啊成是不是躲了在裡面,而大叔又用眼神示意讓我把被子挪走,好看看裡面的狀況,我明白他的意思後就拚命搖頭。
我不幹!打死我也不幹!
但在被大叔數次怒目而視後我終於屈服了,被他那異色的眼睛盯着時會讓人有種混身不舒服的感覺。
唉……只能硬着頭皮上了。
我戰戰兢兢的走到了床鋪前,正當我準備把被子拉開的時候床底下突然冒出了一雙手抓住了我的腳!我還沒來得及反應就被那雙手扯得摔倒在地上,而那手沒有想放開的意思,而且還不斷的想把我拉進床底下!
在我摔倒後我終於看到那手的主人,果然是啊成!他現在雙眼發着綠光,面目猙獰地想把我拉進去,我雙手用盡全力的頂在床鋪上才不至於立刻被拉走,但是他的力氣之大我根本撐不了多久,我只好大聲呼叫大叔讓他趕緊來幫忙。
而大叔看到出狀況後也三步拼作兩步走到我身邊把黃符貼在啊成的手上,啊成慘叫了一聲後雙手馬上就鬆開了,不過那聲音聽起來根本不是屬於啊成的,因為那是把女聲……
我感覺到施在腳上的力量減少後就立刻手腳並用的亂撐着,務求讓自己盡快離開那該死的床鋪。而大叔沒有鬆懈,一下就把啊成的手抓着並將他從床底下拽了出來,當啊成曝露在燭光時他不但顯得相當痛苦,而且更胡亂揮動手腳想要掙脫大叔躲回去。
而大叔的手像是個鉗子似的緊緊的抓着了他的手不放,他一邊唸咒一邊把紅線繞到啊成的身上,而現在一身怪力的啊成被這根細細的紅線纏住後居然沒能掙脫。大叔愈是唸咒啊成就叫得愈厲害。
這時候那菲藉女傭好像在外面聽到有怪聲,於是就敲了敲門問有沒有什麼事要幫忙。大叔見狀就叫我把門給堵住別讓她進來另外趕快女傭打發走。我就只好對着門外的她胡亂應了幾句,還好大叔事前有吩咐過,所以那女傭也不敢貿然把門打開,所以很快就走了。
要是讓她看到啊成現在這幅模樣不把她嚇死才怪……
過了沒多久大叔終於制服了啊成,他如今跪了在地上動彈不得,大叔把一張白符貼到他的額頭上時,他突然發出一聲怪叫,接着便兩眼反白後就暈死過去。
「呼……好了。」大叔用衣袖拭擦着額上的汗。
「好了?那靈體呢?送走了?」我癱坐在地上問到。
「不。」大叔晃了晃手上的白符說:「在這裡。」
大叔讓我扶起啊成然後自己用拇指用力地按壓着啊成的人中,在他醒來前的這段空檔時間,我抱怨大叔一開始明明講過這種靈體只會小打小鬧,結果我卻差點沒被它嚇死。大叔就解釋是因為我們的存在不多不少會惹怒那些靈體,因為它很清楚我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明知道它會發怒還讓我去掀被子!」我不滿地說。
「哎喲,你就別在抱怨了,你怎麼不想想若果是我被它撲倒了那誰來制服他?頂多我待會兒請你吃飯就是了。」
我想了想大叔所說的也不無道理,換作是我的話肯定沒法把啊成從底下扯出來。
過了一會啊成終於醒來,慢慢的張開眼睛的他以錯愕的眼神望着我道:「你抱着我幹什麼?我不是睡在床上的嗎?」
我白了他一眼後就把剛才發生的事全都告訴他,在聽完後大叔點了三炷香遞給了啊成讓他向白符裡的靈體道歉,啊成聞言後一一照做,在儀式完畢時大叔把白符燒掉並讓啊成向靈體的家鄉方向叩了三個響頭。
在這一切全都做完後,四角的蠟燭才重新的着了起來。
事情完結後,啊成十分高興的打電話告訴我們他睡覺時再也沒有被任何東西騷擾了,現在他每晚終於可以安心入睡,大叔告誡啊成讓他以後不要再亂說話,就算開玩笑也要有個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讓你開玩笑的。
電話另一邊的啊成不斷稱是,在掛線前他還告訴大叔說自己已經把酬金打進了他的銀行帳戶裡,讓他查收一下。
第二天我跟大叔去銀行打簿的時候偷偷瞄了他的存摺一眼……果然富家子弟出手就是大方,裡面的錢都夠我繳好幾個月的房租了。
157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HwOqFQh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