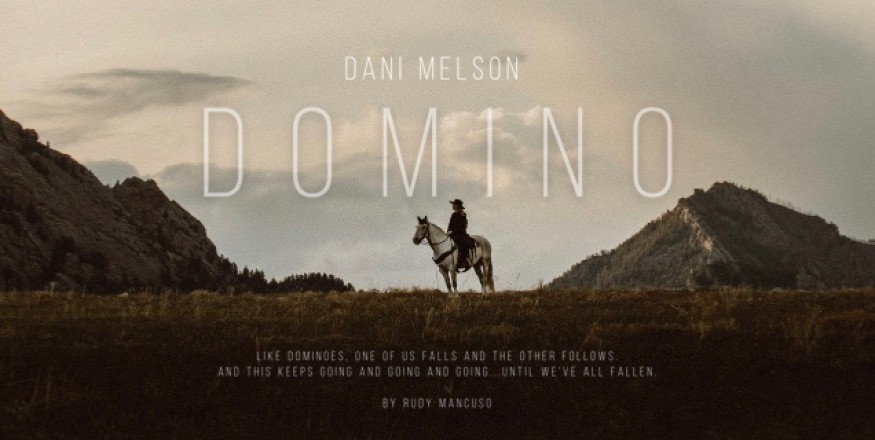x
x
他足足昏睡了好幾天左右,卻恍若失去了一整年。
醒來之時,映入眼簾的竟是滿天星斗。甦醒那刻他還沒意識到自己的狀況,只是隨著寧靜回想起受盡苦頭的那天,他也是這樣負傷看著夜空。
那晚如今一樣——絕美的星辰就像銀幣的微光,廣闊的天空告訴他世界最珍貴的寶藏一直以來就在身邊,望著那些肅然起敬且屹立不搖的指標,他的目標也從意識到時而不再動搖。
去往東部,獲得合法工作,過上安逸的生活。
而如今看著同樣場景卻覺得這是奢侈的享受,只差臨門一腳,命運卻安插了各種意外,彷彿在測試他的決心。
傷口裹著似乎是乾淨的布條,傷口上有著新鮮換過的藥草,他不清楚為何露辛達會知道哪些草藥可以療傷。隨後他才察覺自己獨自一人的躺在一棵樹下,對於周圍的情景困惑不已。這裏並非他所認知的瀑布湖邊,極為相似的森林風貌且黑夜也讓他搞不清楚是否還在瀑布附近。
在他找尋不到人影卻又不敢冒然呼喊後,保羅坐立難安的硬逼自己站起身,手想移向手槍卻想起槍枝在落水時也一同遺失了。無奈之下,他只能拿起營火火炬,往其中一個方向前進。
尋覓的時候他也一邊擔憂後續。他不清楚自己位於何處,他的隊伍跟其中一批貨物大概充公或遺失了,不知道回到瀑布處是否能找回一些。雖然狄弗洛那批仍有斯里蘭卡寶石跟一半的酒,但遺失一些重要資產還是讓他挫敗。
但話說回來,那些人是誰?
跨越草叢,他皺眉一邊尋找那頭如同火焰的紅髮女人。保羅本來信誓旦旦也堅信自己的路線鮮少人通行,而且沿路上他都沒有放鬆警戒,也確認不可能有人跟蹤。那是誰洩漏了他的行蹤?或是他真的沒發現他們的隨行?
氣惱的感受令他臉頰因咬牙而緊繃,傷口在他撥開垂枝時為此疼痛。神經牽連的疼痛如雷電迅速,往上竄的霎那令他整個左臉都痛痲。咒罵一聲,他嘶聲的頓足。
他無法確認那些人是誰,手忙腳亂也使他忘記觀察他們。槍法算好,子彈因角度才擊中肩膀,不然原本可以將他當場擊斃。他不確定記憶中那些人拿著那種槍枝,只記得似乎有溫徹斯特步槍,但這種槍枝說實話也算常見。
可他們的目標如果是貨物,為什麼在攔截馬車後還要趕盡殺絕?而且其中的手法也很奇怪。保羅扶著大樹從刺痛中找回意識,再繼續深入森林後,他不免在規律的蟲鳴鳥叫中又回想起來。
他的記憶就像翻騰的河水一樣,混濁而急速,使他看不清到底遺漏了什麼關鍵。
走了沒多久,他突然感覺到附近鳥鳴消失。站直身子,他感覺頸部汗毛因隨之而來的恐懼而豎起。立即踩熄火炬試圖隱藏自己的位置,他屏息以待的躲在附近一棵大樹後。濕潤的氣息他已經很久沒有聞過,而如今生氣蓬勃的森林可能將是他的葬身之地。
在他摸索到乾凅樹枝後,他仔細聆聽周圍聲響。如蜻蜓點水般的聲音穿越葉地,雖然發現有東西靠近,但令人頭皮發麻且心跳加速的是,聲響來自四面八方,就像逐漸湧起的巨浪準備將他吞噬。
它們清楚他的位置。
狗屎。保羅站起身往剛才的方向拔腿狂奔,打算回到營火旁。聲響也撲擊而來,隨著他傖惶逃竄而緊跟在後。該死該死該死!他不確定西部森林藏有什麼野獸,但棕熊、灰狼或山獅種種獵食者的模樣都在腦內閃過。
在好不容易看見微小火光在眼前閃爍,他卻發現一個熟悉不過的身影站在旁邊。望著自己將帶著危險靠近她,保羅更是忽視疼痛的奔跑。
「露辛達!」他大喊,紅髮女人應聲回頭。「快——」
話還沒說完,一個東西突如其來的捆住他的雙腳,他在震驚之餘也因重心而往前摔倒。刺痛加上露辛達的呼喊,他心急如焚的將自己恐懼拉出,喘氣的爬起想要拆掉腿上的東西。
「保羅!」聽見露辛達的叫聲那刻他也好不容易拉開纏住雙腳的繩石索。在他掙扎起身時,幾個高大黑影已竄到眼前。在石斧抵住他脖子時,他大氣都不敢一喘的僵在原地。
後方突然有火炬帶來的光芒,在照亮眼前有著圖騰刺青綁著辮子的兇惡臉孔後,他驚恐的想要露辛達快走,卻因斧頭而無法發聲。
可出乎意料的是,露辛達來到他身旁對高大的印第安男人用著急且懇求的語氣說了話,用的還是印第安語。他們是哪族的人?他知道某些印第安人像切羅基、莫霍克已經受到同化,但他們一看就知道不是。
如此野性的裝扮和武器,甚至連英語都不會說,他們可能匿藏在這很久,那這樣露辛達是怎麼敢判定他們會放過他們?
可這個女人總是令他訝異,印第安男人在聽完露辛達的話後頓了一下,接著才鬆開石斧。保羅退後好幾步,仍然不理解露辛達是用了什麼方式才讓這些人放過自己。
看見他狼狽的模樣,四個印第安男人不禁嘲笑出聲,還對彼此揶揄他。他們向露辛達說了幾句,在她點頭後也對他用警告的態度說了些話,然後轉身消失在森林裡。
她回頭難掩笑意的說:「他們沒有惡意。」
他皺眉。「妳怎麼會說印第安語?」
她聳肩與他一同走回營火處。「我小時候的保姆是印第安女人,她偷偷教會我很多印第安部落的語言。我也是很幸運他們懂我的意思。」
「那他們剛說了什麼?為什麼要追我?」
綠眸充滿笑意的看向他。「他們只是要提醒我們不要亂跑,這片森林是他們的家,有人在你家亂走你難道不會想要趕跑嗎?」
「我昏睡了幾天?」
「意識模糊的話大約四天半。」
他不發一語的坐下,在放鬆下來之後,肩膀的疼痛又開始揮發。見他臉容扭曲,她走過來主動的拉開他的衣服要檢查傷勢。
在她去附近樹下拿出用葉子和陶罐裝著的藥物回來後,他忍不住問:「這些是他們給妳的嗎?」
「對。」她答道一邊幫他更換藥物,一邊拿出口袋乾淨的布條。「我們在瀑布時被他們發現,我在清醒後稍微跟他們解釋我們的狀況後,他們願意給我們吃的和藥物,但我們好了之後就一定要離開這裡。」
「我以為妳會留在他們的部落。」
「他們有這個想法,但也有些人依舊很怕我們——也就是殖民者。所以為了避免爭端我還是決定帶你來這休養,但他們固定會與我碰面給我藥物和食物。」
在包紮好後,露辛達也去收拾藥物並遞給他牛皮水壺。他沒有拒絕,反倒像是快要渴死一樣暢飲。在最後她遞給他肉乾時,他也是順從的吃下。
在她坐到他身旁後,他才說:「謝謝妳在這幾天照顧我。」
她似乎感到吃驚,彷彿他不會是個輕易道謝的人。保羅也沒打算挖苦,畢竟知恩圖報這件事,他也不是很常做,他的道路一直以來都是自己開拓,自然沒有什麼需要感謝的對象。
「你救了我,這是應該的。」
聞言,他與她四目相對一會看出她的真心而點頭。
「我們明天就可以離開森林了,但我想先回到瀑布那看起來有沒有殘留的貨物。」
她的表情變得難看,讓他相信了她知道了什麼,而結果並非好事。躊躇片刻,她還是坦承。「基本上沒有了。我跟著部落裡的人回去過,但大部分的酒瓶都已破損,所剩無幾的幾瓶我也以善意回贈給他們了。」
明知道會是這樣的結局,保羅還是感到憤怒。一方面是自己又將失去一筆開拓的資金和勞力而感到的無力和挫折,另一方面卻是認同她的作法,畢竟成為朋友總比做敵人還好。
他遲遲沒有回話,露辛達的表情也陷入糾結之中,兩人似乎都忘記了先前的爭執。他靠著樹幹看著天空,望著星辰他不禁感嘆至少還活著,闔上眼他閉目養神。既然受到了治療,他之後還能繼續上路,馬列奇那場不確定的交易和那狄弗洛那些貨物還是有機會討到不錯的價錢。
他還有機會,這次不是走投無路。
「那就算了,當作他們救我們的禮物。不過之後我們還是要前往泉石鎮,我需要錢去到東部。」良久後,他打破沈默。
睜開眼他看向回頭看他的露辛達。「我知道,你之前提過。」
他撇開眼神,良久後自顧的坦承。「妳之前問過我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賺錢……我一開始也沒想過。」
她頓了一下接著問道。
「為何要解釋這些給我聽?我以為你不喜歡講這些私人話題。」
保羅聽得出她是真心困惑,為此他聳肩。
「我想我現在也沒什麼事好做。」
她啞然失笑。「可我也說過我不會因你講這些而放過你啊。」
他聽到反倒也笑出聲,彷彿不屬於自己的笑聲隨著胸膛震盪而竄出。「那就當我說個故事好了。」
她的眼神變得跟營火一樣溫暖,與他一同靠著樹幹並問:「你之前做過什麼?」
「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牛仔、農業工人,雜貨店打雜的等等,基本上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從小就生長在窮苦人家,我沒什麼機會讀書,識字還是在長大之後請人教我的。但隨著我母親的病情加重,我必須要更多錢,但經濟動盪,裁員和薪水調漲,物資昂貴到我無法負荷。在我……」
他不自覺的愣了一下後,才發現自己是如何硬生生的扒開過往。那些乞求的羞辱、拒絕下的心灰意冷,看見床上咳血的母親時的絕望感。保羅彷彿在述說的當下一一回憶那時候的刻骨銘心。
「……在我最好的朋友投資失敗,被人打死丟在礦坑後,我也在沒多久因經濟不景氣被開除,在最絕望的時刻我也認清了像我們這種人做的工作永遠無法逃離窮困的枷鎖。窮困潦倒無法保全我的朋友,如今更不可能治癒我的家人……在聽聞東部的繁華跟進步,我不可能不奢望。上帝並不眷顧我,露辛達,祂從來沒有。」
露辛達沒有馬上說話,他也拿起水飲用順便沉澱複雜心情。半晌後,她突然輕語,聲音帶著少許的哀嘆。「他是誰?你的朋友。」
不自覺地,腦袋自動挖出更多想要埋藏的記憶,隨著眉頭深鎖與遲疑一下,他告訴了一個近乎陌生的女人,關於那個摯友的故事。
「……他叫橡樹,我跟他是在做煤礦工人時認識的。他從沒告訴我他的全名,不過他人很好,也做了比我還久的工人。他告訴了我許多賺錢的方法,還教我不少歌謠跟處世道理。甚至有一次他還帶著我去酒館,他調戲女孩的方式——妳不知道有多荒謬——」他邊想邊笑出聲,橡樹滑稽的演技和模仿歐洲人的口音都讓他難以忘懷。
看見他發笑,露辛達也在沒多久嘴角失守。
這是他難得有機會放聲大笑,在橡樹死後他基本上沒在這麼快樂過。或許橡樹對他的影響比他想像中還大,失去他之後回憶起還是能開懷大笑。
在笑意逐漸平復之後,他又多講了幾個橡樹的荒謬事蹟,使得她也一同捧腹大笑。
「他聽起來真的是個有趣的人。」
保羅點頭。「他是我見過最奇葩的人。但因為他,那段時光是我最開心的時候。」他的笑容隨著之後的事也消失在了嘴角。「或許我們各自的問題都很大。但我還太幼稚不懂的隱藏或觀察,也太心浮氣躁的沒有察覺到身旁的變化……我不知道他的兒子欠了債,事後用了他的名義去投資,可想而知結果是注定的。橡樹在死的前一晚找過我,說要跟我借錢,我以為——」
他咬緊牙關,彷彿不願將那些事公諸於世,那也等於在宣判自己的罪孽。
在閉眼深呼吸幾次後他吐氣道:「他是打算拿錢去喝酒,因為那陣子他喝的很兇。那時候我母親的病情使我焦頭爛耳,我沒辦法三心二意。於是我就拒絕他,他卻開始死纏爛打……所以我不聽他解釋只怒罵他一頓就將他趕走了……隔天,我才得知他的屍首在礦坑的事情。」
腦中橡樹的屍體是如此歷歷在目,他甚至感覺到當時自己的絕望和深沈的愧疚。用手摩挲面容,他裝作若無其事的繼續。
「在得知他的死因後,我後悔莫及卻也意識到自己就像他一樣。總是以為懷抱樂觀就能總有一天過上好日子,社會不可能善待我這種窮人。於是我走上妳認為可恥的道路,儘管如此我也不會販毒給窮人。我將第一筆錢拿去還了橡樹的債,把他們的家贖了回來,儘管這樣我也還是教訓了他的兒子。如今現在我存的每一分錢都是為了讓我母親受到良好的治療。」
望著露辛達五味雜陳的表情,保羅並沒有動容,只是拿出頸部一直不怎麼打開的項鍊遞給露辛達,讓她看見匣子中兩面陳舊的照片,自己反而看向營火。
「那是橡樹和我母親。」
在她歸還後他看都不看的收起。「我都沒有意識到你帶著這個。」
「有時候我也希望我忘記戴上它,但他們是提醒我為什麼走上這條路的原因。」
她沈默了一會,使得保羅看向她。發現她難受且欲言又止時,他才認定這個女人是真的善良到沒什麼壞心腸,或許他先前對她的批判都有點太過了。事到如今,他也不是為了得到安慰或是寬恕。
「什麼都不必說,警長的女兒。」
見她瞪大眼感到疑惑時,他說:「就像我說的,這只是個故事。而如今它結束了。」
ns 15.158.61.3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