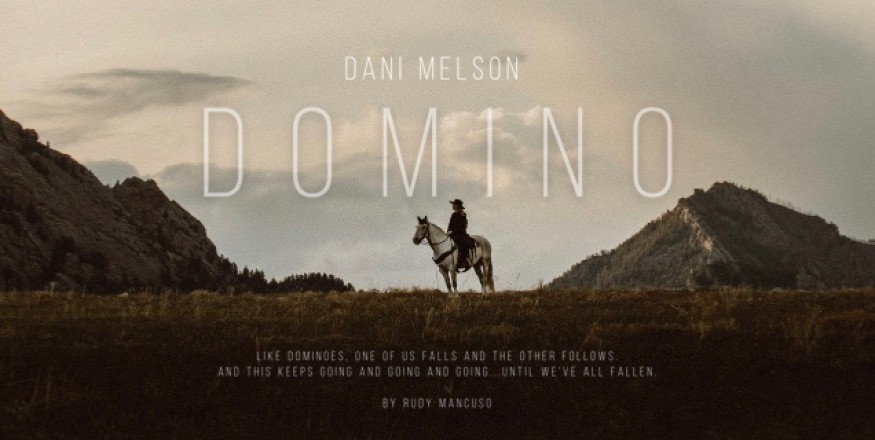x
x
死亡谷的路比她想像中還要折磨人,前幾夜的暴雨更拖累他們的行動,雖然威廉·鄧普西找到一個勉強臨時的山洞,但那次幸運卻沒有延續到之後幾天。
躲雨後就趕路,還得小心馬匹不會因地滑而跌倒導致受傷,一開始的旅途就讓貝絲的信心受創不少,只能仰賴威廉熟悉路線的敏感。
之後的幾天雷陣雨就像鬼魂一樣消失無蹤,陣陣熱浪撲面而來,乾燥的氣息奪取了身上的水分,萬里無雲的天空讓他們毫無防備的曝曬於艷陽之下。
四周山谷就像死人的牙齒般崎嶇而灰白枯竭,散發著寸草不生的氣息,雖然前幾天經過某個山丘時看過些許綠葉草原,但接下來的景色卻都是一成不變的乾枯褐黃土地,只有少許風滾草出沒。
按照威廉前一晚所說的時間,那他們要穿越死亡谷還需要大概兩到三天,但那也只是運氣好的話。
如果不是內心信念支持,貝絲或許早已支撐不住。少量的休息和不正常的飲食模式讓她的外表反應了極大的壓力。雙唇因氣候而破裂,眼窩凹陷導致面容無精打采,口乾舌燥下氣息沈重的像是要窒息。一整天的路程幾乎讓她體力透支卻只能硬逼自己繼續,即便已經頭暈腦脹到無法思考。
「貝絲?妳還好嗎?」似乎注意到她的騎速減緩,威廉也放慢速度來到她身旁關心道。
她搖搖頭,試著露出有精神的一面。
「我沒事。」
「死亡谷的天氣就是這樣變化多端,妳需要水的話儘管跟我說,不要讓自己真的脫水了。」
「我還有一些水。」她艱難的說,然後拿起水壺抿了一口。儘管水的滋味甜如蜜,但為了之後行程她必須節省。
威廉見狀反而沈默,他的氣色雖也沒好到哪,但模樣和精神卻比她還要好。貝絲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眼下她也無暇顧及他人。
他一手扶著氈帽一邊仰頭查看太陽位置接著說:「已經接近黃昏了,我們在走一段路就可以準備紮營。我們可以開始尋找適合的休息處了,貝絲妳能再撐一下嗎?」
她硬是擠出一抹微笑點點頭。
之後的路程她幾乎都是無意識的在騎行,偶爾臀部的疼痛才會稍微換回她的專注,但很快乾燥昏熱的天氣就使她意識渙散,連眼前威廉的身影都像熱浪一樣模糊不清。
斜陽很快就出現,橘紅色的天空在他們左側出現,延伸過去使蒼穹形成粉藍色。她吞嚥濃稠的口水,鼻息終於不再像是吸取熱氣。稍早從死亡谷離開後兩旁巍峨的山脈就逐漸包圍道路,深褐色的乾凅紅土就像分裂的海洋,隨時都能吞沒他們。
由於天色漸漸昏暗,威廉讓他們的速度減緩,並下馬拿了兩隻粗壯乾凅的樹枝用酒點燃。等到四周一片漆黑時,火把就成了最完美的保命工具兼武器。
「鄧普西先生。我們現在在哪?」沒多久貝絲騎到他身旁問道。
威廉一手攤開地圖指著一個樣子如迷宮的山脈區。「德洛斯山脈,前幾天在死亡谷我都沒看見有傑克·歐森的跡象。所以我在猜測他可能會從這去到肯塔基的小鎮。」
「德洛斯山脈?」她驚呼。
她聽過鎮民談論過這個山脈。它既崎嶇如迷宮詭譎又是罪犯最愛偷襲商團的地點,畢竟不搭乘火車的話用馬車沿著德洛斯山脈最能聯同兩座城鎮。要不是因為德洛斯山脈時常有季節性大雨導致土石流,東部與西部政府本想打通這裡。
而如今這是她第一次踏入這座人人畏懼的山脈,她不禁臉色發白感到擔憂。威廉·鄧普西見她侷促不安的神情便露出安慰的笑容。
「放心,貝絲,我走這一帶已經很久了。我大概知道走哪裡能夠很快出山脈。」他語氣肯定的說,於是她選擇相信。
望著四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遠處還傳來令人頭皮分麻的郊狼嗥叫,她暗自祈禱威廉的地圖和他的記憶力不會出差錯。
沒多久他們就找到一塊特別凹陷的山壁休息,升起營火後,威廉拿出鐵鍋加熱剩餘的葡萄酒並讓她沾麵包吃。原本又硬又無味的麵包在攝取了酒香之後變得鬆軟好吃,以至於在吃完後她感覺體力回來一些而昏昏欲睡。
「妳不如休息一下,明天還有一段路要趕。」他坐在對面石頭上說道。
貝絲本想拒絕但卻耐不住睡意,一整天的操勞和氣候的變化無常,夜晚氣溫下降的過快讓她難以適應。她道謝後將氈布繞緊身驅就靠著山壁,在火光和威廉守候帶來的安心感陷入夢鄉。
————
之後的接連兩天都像在原地打轉,同樣高聳紅褐色高土,動物骷髏與半死不活的樹木。偶爾會看見蠍子、沙蛇或蜥蜴攀爬山壁出來覓食,天空中也會閃過禿鷹群的蹤跡,彷彿是在觀察他們何時死去。
隨著時間的拉長,食物也隨之寥寥無幾,她知道威廉會找到出口,由於山脈極大花點時間趕路是難免的,以至於她從未過問他是否迷路。
直到她感覺自己的身體漸漸無法負荷麵包和酒的味道,儘管威廉用自己一點的水跟從埃及人那學來的技巧用麵包製作發酵酒,仰賴發酵後的酒根本難以吞嚥。而且她開始時常頭暈目眩,貧血造成的眼花撩亂更是讓她體力透支。
在第二天夜晚看著月光,聆聽著威廉說著他第一次當賞金獵人的經驗時,她的意識已經不再能穩定下來。她很不甘心自己的虛弱,既沒有還家人一個公道還得不到殺人犯的解釋,貝絲痛恨自己這麼懦弱無能。
看著滔滔不絕的威廉·鄧普西,她很訝異他居然還可以有力氣使她從疲累中分心。經歷了痛苦漫長的兩天他的氣色也變差很多,卻看起來仍舊比她好。她不清楚賞金獵人曾讓他有多麼恐怖的經歷才會使他在這種環境下依然游刃有餘。
嘆口氣,她抵擋不了沈重的眼皮,在闔上眼的那刻他的聲音就像塵土一樣飄渺。
夢中貝絲回憶起母親的懷抱,小的時候母親都會帶著她去雞舍看新鮮的雞蛋,接著餵養豬和羊後就帶著她去廚房做菜,晚餐前母親會編織著要給他們的衣服,而貝絲則會蹲在家門外的樓梯等候趕牛回來的父親與哥哥們。
雙胞胎湯米和雷夫和最小布萊德都會趁父親跟母親聊天的時候,在夕陽真正落下前帶著她去山坡上騎馬,並俯視山丘另一頭的山脈和山丘下的墨菲威爾小鎮,黑幕降臨而霎那燈火通明的絢麗畫面不管幾次都讓她為之震撼。
儘管那些回憶都在母親染病去世後封陳於內心深處,貝絲卻感到溫暖又懷念,那時候的她依然可以是無憂無慮的女孩,被愛包圍,不必下葬任何所愛之人。
夢中浮現每一個家人死亡的面容,一次次的帶走她僅剩的愛。她開始哭泣,哀求、懇請卻依然失去,時間不願停留她的家人也同樣如此。
她墜入深淵,卻像被落石擊中般猛然驚醒。
貝絲立即睜開眼,一清醒就看見一個大塊頭的黑影壓在自己身上,衣料已經被扯開而自己的裙子被拉到腰上,他背對火光使她看不見他的面容,但他粗糙的手撫摸自己身體的那刻意圖就十分明顯。
那些觸覺告知她這不是在做夢,她驚恐的尖叫呼喊威廉的名字,但卻只被壓在身上的男人打了一巴掌。衝擊力讓她眼冒金星,鐵鏽味在她口中散發,她死命掙扎,淚水不爭氣的落下。
威廉呢?威廉去哪了?他被殺了嗎?傑克·歐森是不是察覺他們在追蹤他而埋伏於此,並趁他們毫無毫無戒備時攻擊?
救命!她在被這人摀住嘴巴時大喊,他壓著她的口鼻讓她呼吸混亂不已,另一手持續粗暴的要扯下她的內褲。
憤怒、恐懼還有絕望的包夾下,貝絲發狂的扭動身體,一手成功擊中他的面頰卻被對方用拳頭攻擊腦袋,太陽穴遭受的重擊讓她頓時眼冒金星,反抗的力量頓時喪失一些。
在鼻血滑落臉頰到塵土時,她的內褲被硬是扯下,骯髒的手觸碰了她的下體,無法言喻的噁心感受讓她回神,她在意識快要失去的那刻伸出另一手快速抓住他腰間槍套裡的左輪手槍,趁對方被性慾干擾而沒察覺時轉動保險。
在對方聽見聲音時已經來不及制止了,好幾發子彈貫穿他想抵擋的手射穿了他的頭顱與面容。溫熱的鮮血噴灑在她的臉上,她卻沒有任何猶豫,怒火壓下了悲慘帶來的惶恐,貝絲直到那人倒下的那刻才停止射擊。
推開沈重的屍體並用裙子用力拭擦下體,在穿回衣物前她都保持近乎歇斯底里的冷靜。雙腳穩定的走向營火並拿起其中一隻火棒,她看向四周卻沒看見威廉的屍體,他們的馬依然在附近因剛才槍聲而有些急躁不安。
貝絲依然毫無感覺,彷彿被人操縱的木偶轉身走回陰影下躺在血泊中的屍體,她用腳翻開屍體卻遲遲不敢把火棒往下照亮他的面容。
也許她早有預感,在那雙手觸碰她的身體那刻她就有意識到。
在這刻她咬緊下唇直到出血,無法抑制的怒火吞沒了她破碎的心靈,她掏出手槍往已經了無生氣的屍體再次連開數槍。
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之中,她的槍鳴就像死神的鐮刀劃下休止符。
貝絲喘著粗氣並丟開手槍,接著連看都沒看就將火把丟向她到現在都不願去看的屍體,火開始燃燒、蔓延,吞噬令她心碎、憤恨的一切。
轉身帶上自己的衣物,她走到馬匹處並翻開威廉·鄧普西的側袋。望向裡頭的東西她嘲弄一笑,這狼心狗肺的男人居然一直暗藏好三瓶酒與水、一些黑麵包和真正的地圖和錢袋,他恐怕一直在等待她毫無還手之力時才行動。
掛著賞金獵人的名號他做了多少汙穢不堪的事情?虧她是如此的信任他,而他耗費幾日假扮的好人形象只不過是為了達成強姦她並棄屍的意圖。
貝絲怒火中燒的握緊拳頭,傑克·歐森或許根本沒來過德洛斯山脈。去到德洛斯山脈八成也是因為這裡警察難尋屍體和兇手去向,而基本上根本不會有人冒險來這。
她對自己付出不必要的信任感到羞恥又可悲。迅速的拿起一支火把,拿走有用的東西後她跨上自己的馬並釋放威廉的,頭也不回的騎向地圖與指南針所指的方向前進。
直到遠離了營地她才拿起麵包開始啃食,即便乾燥的令她喉嚨疼痛,她也依然不停嘴。淚水很快流下面頰,讓她嚐盡苦澀和背叛的滋味。少了指引馬兒很快停下腳步,於是她索性趴在牠的鬃毛上無聲哭泣好幾分鐘。
隨後一小時她都不允許自己去回憶那段恐怖的經歷,現在她只有一個目標,先去肯塔基的小鎮買足糧食用品,然後拿去傑克·歐森的懸賞單就去找那個該死的殺人犯。
儘管第一次殺人的恐懼很快就影響了她的內心,貝絲的雙手開始顫抖,反胃的感覺就像囤積已久準備爆發。她忘不了那雙手在自己身上游移、碰觸下體的觸感,更無法忘懷他溫熱的鮮血染盡衣料和皮膚的感受。
一連串憤怒與失望湧現讓她決心今後不再隨意輕信他人。
破曉時分她已經騎了不知道多久,身上的血跡也已乾凅在皮膚與衣物上,她看向地圖發現沒意外的話這附近會有一個難得的綠山丘和池塘。
於是花費了一點時間她趕到山丘附近,綠意盎然的景象差點讓她誤以為是海市蜃樓。但在馬兒開始吃起嫩葉後她才會意過來這是真的,儘管草不像小鎮附近的山丘一樣翠綠但也足以點綴一成不變的德洛斯山脈。
把馬安置在山丘附近一顆吃得到草的樹附近後,她步履蹣跚的走向另一頭池塘的所在地。
池塘水因近期從死亡谷處蔓延的暴雨變得豐沛,她既感激又感概的脫下衣服,把替換衣物和手槍放在草叢旁。確認水底沒有水蛇後就踏入池塘中,粼粼波光在陽光下閃露,她很快飲了一些解渴並洗去臉上血跡。
刺眼的白金色陽光漸漸籠罩她,貝絲卻從沒感覺如此生氣勃勃,彷彿疾病已經離去,她不禁呼口氣再度流下淚水。
在此之後她不想哭泣了。不管是為了誰。
穿上乾淨的衣服,她看著水面並將雜亂的頭髮綁成辮子。突然之間附近草叢有微小的聲音出現,但此刻無風那聲音也不像單純的動物,於是她蹲下身假意繼續整理頭髮,實則一手伸向槍套裡的手槍。
隨著心跳聲變得明顯,她感覺有人朝她走近。握住槍柄她悄聲滑開保險。在腳步聲離她不遠那刻,她掏槍瞬間轉身對準來者。
在轉身時她就想過,右手拿槍使她的姿態在蹲著時傾斜於左,用右肩和膝蓋保護了心臟處。也因此除了開槍要瞄準快速且冷靜之外,她的死亡機率只有頭部較為危險。
但意外的是兩人都沒開槍。
不外乎彼此的面容都震撼著對方,兩人的槍枝也因此懸在空中。
貝絲瞠目結舌的望著在馬多仕酒館遇見的那個年輕男人,而他也吃驚的瞪大眼看著她。
ns 15.158.61.3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