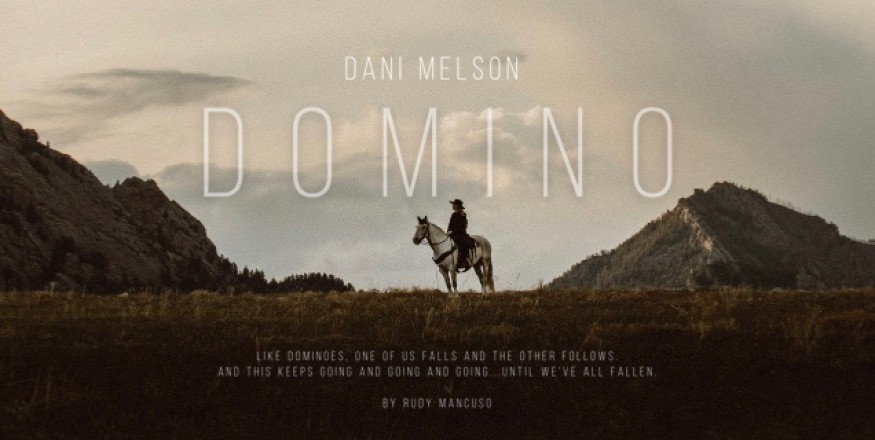x
x
儘管知道一切都像在重蹈覆徹,她還是替這個叫安賽爾的陌生男子看顧了一整晚。再做完緊急包紮並確認血已停流而子彈沒有造成感染後,她便埋葬了另一個似乎是他同夥的男人。
兩人起內鬨的過程貝絲並不清楚,在她趕來之前他們就已劍拔弩張,而兩人意氣用事且不假思索的後果,就是讓她又被困在原地,被時間嘲笑處境。
忙碌的過程之後便是另一場空虛的開始,那晚她在綠洲上紮營。望著營火燃燒,夜空的星斗似乎也跟她一樣羞於見人,遼闊的山丘與峽谷平地上,僅有迸裂的柴聲與安賽爾痛苦的呻吟。
藉由池塘的水來驅散他的高溫,他冒著的汗卻像一點一滴流失的體力,使得蒼白的面容逐漸憔悴。偶爾她會聽見男人喊著一個含糊的詞語,一開始她以為只是呢喃中的碎語,但在幾次下來,她確信這個賞金獵人喊道一個叫柏沙的人。
是男是女她不確定,但他的聲音中飽含了另一個情緒——愧疚而有的罪惡。
對此而言,貝絲再清楚不過那種感受,也無法再冷靜的面對。她很了解那種苦痛:愧疚於他人卻無能為力的感受時時刻刻侵蝕著她,她的軟弱無力、她的性別帶來的枷鎖與危機,她從沒如此痛恨生活在這個年代。
為此她才沒有拋下安賽爾,或許他也曾跟她一樣家破人亡。
內心深處她明白自己不該同情任何陌生人,尤其在被背叛過之後。也因此同理心的產生讓她五味雜陳。
隔天醒來時,安賽爾的高燒已經退下,但看起來依然面色鐵青。她清楚在這此人的傷口不可能會好,所以在確認他的傷口沒有再滲血之後,貝絲費盡全力將他扶到不遠處的馬匹旁邊。
她不能冒險讓他自己待在馬上,所以斟酌思考後,只能利用他馬鞍皮袋中裝有的牛鞭將他們兩人綁在一起,確認安賽爾靠好她的背後,她帶著剩餘東西一同往威廉·鄧普西地圖上最近的城鎮前往。
她的運氣不再如以往,不到下午就開始下陣雨,只好險她已經離開峽谷與綠洲,不然周圍的土地有可能化為泥濘使他們難行。她戴上安賽爾的氈帽遮雨,並確認他的狀況還能撐到他們抵達城鎮。
雨勢忽大忽小,偶爾劇烈到需要她找到樹下遮雨確認變小才繼續上路,途中他們的水也快要消耗殆盡。一路上這個男人的理智從沒正常過,偶爾會對她餵水的行為嚇到卻也無法反抗。
這種神智不清的人她不是第一次見識,她的母親就是最好的案例。她不可能遺忘那一兩年照顧重病的她,令她痛苦的不是那段時光,而是不管如何看照、愛護,母親的性命依舊逝去。
望著安賽爾痛苦的表情,貝絲唯一能做的就是拿僅有的乾布擦拭他臉上的水珠。
最終她的努力有了成果,經過積雨雲地區後沒多久太陽很快烘乾了他們的衣裳,她也能快馬加鞭的前往小鎮。
直到黃昏她也抵達地圖上標示的小鎮,威廉並沒有在上頭寫上名稱,但鎮子規模不大路上也沒什麼人在,她不敢奢望這裡會有良好的醫療設備,只希望會有家庭醫生或護士之類的。
她很快就找到鎮上僅有的旅館,破舊又小完全比不上墨菲威爾的,但眼下只希望房間還算乾淨不會感染他的傷口。一開始她扶著沒什麼意識的安賽爾進去時,一樓只有三人待著。
一個正在打掃並收拾桌椅的顯然是服務生,另一個在櫃檯的就是老闆,最後一個是坐在樓梯旁牆壁附近椅子上的男人。
他們原本正在聊天,直到她闖入打斷了相談甚歡的情景。服務生看起來是個比她年輕的男孩,看見安賽爾的狀況就二話不說熱心的過來攙扶。
她道謝後就看向應該是老闆的人。
「還有空房嗎?」
「有是有。」老闆是個矮大個,濃密的絡腮鬍和粗眉讓他看起來更像稍微高且壯碩的侏儒。他頓了一下然後問:「他怎麼了?需要醫生嗎?」
貝絲雙眼為之一亮,嘴角終於浮現微笑。「這裡有嗎?他受了槍傷,我們在路途上遇到了搶匪。」
「噢,那可真是不走運。」這時坐在椅子上抽著雪茄的斯文男人答道,語氣卻不帶一絲情緒。
她沒有特別理會他的感嘆,只是在老闆點頭後鬆口氣的說:「那太好了,如果可以能幫我請他來嗎?我的同伴已經撐太久快要體力透支了。我先帶他上樓,等一下會下來付錢的。」
沒等老闆回應,她就去將癱坐在椅子上的安賽爾扶起來,原本瘦弱的男孩想要幫忙,卻被走過來的男人打發走。
他對男孩說:「湯米,你太瘦了,爬這種樓梯不到多久你就會連同他們一起摔下樓。我來幫她就好,你趕快去幫你爸的忙吧。」
瘦弱的湯米扁了扁嘴卻沒說什麼,只是點頭拿著掃把離開。眼下她也沒辦法顧及他的感受,誰比較健壯能幫她那就誰來。
貝絲望著男人搭起安賽爾另一隻手臂與她走上樓梯,她沒有拒絕他的好意,畢竟他說的是真的。在到二樓後,她感覺自己的體力也快盡失,連之前幫父親處理穀物都沒這麼辛苦。
再把安賽爾放到床上後,她立即解開他的衣服,將如何會壓迫到傷口的衣物卸下,一路上她已經用完了乾淨布料,好險傷口似乎沒在大量滲血。
她撫摸他的額頭,令她憂心的是,經過大雨和豔陽洗禮,他開始冒冷汗並發燒了。
「他可能有點脫水。」一個聲音傳來她才想起不只有他們在房間。她困惑的看向倚著門的男人,他交叉雙手用眼神示意。
「我看過這種症狀。嘴唇乾澀,雙眼凹陷。他意識是不是到這都不清楚?」
她雖然不解卻點頭。
男人表情像是明白了一樣,走過來時還捲起襯衫袖子。「去跟傑克——就是妳看到的那個虎背熊腰的男人要一些檸檬水吧,我還需要乾淨毛巾和我的東西,妳去跟湯米說他會清楚我指什麼。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會需要妳的幫忙。」
這下她恍然大悟,驚愕的雙眼圓睜。
「你是醫生?」
聞言男人聳肩露出笑容。「不算是,我不喜歡這樣定義自己,只是有點經驗。我可以幫他,快去吧,現在分秒必爭。」
在之後的手術裡,男人要對醫療一竅不通的她充當助手,在慌亂狀態中他卻耐心的指點她在何時給予正確的東西。
他替安賽爾打了一劑名為嗎啡的藥劑,在沒多久安賽爾的身子也稍微癱軟一些,確認意識不清後男人就開始執行。他做了關於消毒、檢查傷勢後縫合等等一連串動作,一旁的貝絲只能霧裡看花般看著男人用神乎其技的方式安置好安賽爾的傷勢。
在結束後時間也過了兩個時辰,但看見安賽爾的漸漸穩定下來的狀態她還是忍不住鬆口氣。男人在結束手術後站起身放下捲起的衣袖,拿著一袋不起眼卻裝有醫療用品的手提箱準備離開。
她連忙起身。「謝謝,呃……」
男人微笑。「戴斯蒙·傑佛遜。」
「謝謝你,傑佛遜先生。」她拿起腰帶上的錢包。戴斯蒙見狀只是搖頭制止。
「我今天心情不錯,就當舉手之勞。」
即便是好心,這也讓她過意不去。在墨菲威爾她早就見識到醫療在西部的匱乏,如今治療了她卻沒給予任何回饋感覺就是不對勁。「但我們花費了你昂貴的醫療資源。」
對她的歉疚他只是表露好奇的問。
「妳是他的誰?」
她困惑的眨眼,不理解醫生的用意。「……說實話我不認識這個人,但我也沒辦法拋下受傷的他。」
她沒提起安賽爾的身分,更不用說她事實上救他更深一層的含義是為了自己的死亡。少了安賽爾的話,她找到傑克·歐森和事後落網的目的都會功虧一簣。
戴斯蒙只是莞爾一笑,棕眸閃過一絲認同的光芒。他只是戴上氈帽說道:「那就跟我救人的想法如出一撤。如果妳過意不去,等一下可以下樓請我喝一杯,或許妳可以跟我聊聊妳怎麼到這個小鎮的。」
望著戴斯蒙·傑佛遜離去的背影,貝絲啞口無言的坐到床邊椅子上,但望著床上稍微有了血色的男人,她仍舊對危機的解除感到如釋重負。
ns 15.158.61.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