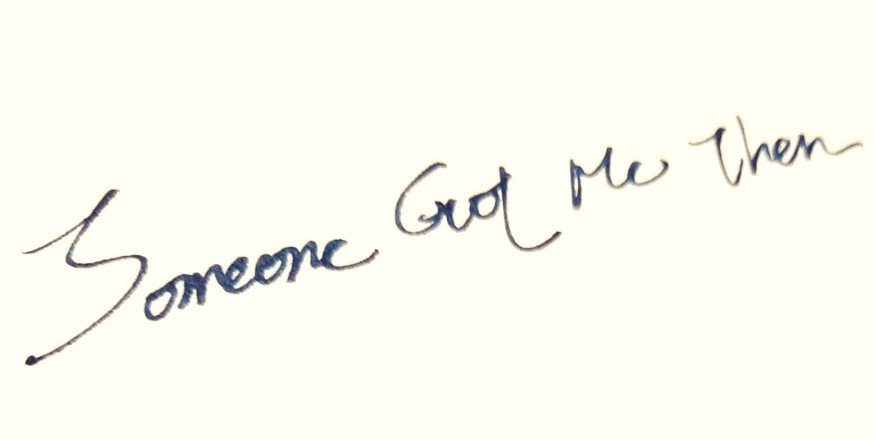|2022年阿納托利・奧爾洛夫生日賀文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mbKSrySmI
|BGM:Bastille〈Pompeii〉
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n7ebL6Gbu
收到生命賜予的二十七歲生日禮物時,阿納托利先是挑眉低嘆一句「喔豁」,接著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反手拍了張照片傳給伊利安。
果不其然,不消兩分鐘,他聽見自樓梯傳來離得極近的倉惶跫音,最後止於大得驚人的拍門聲,似要生生把那扇木門拍破。
「托利亞,如果你⋯⋯如果你告訴我這是惡作劇,我發誓,老子絕對會把你的腦子從屁股踹出來。」即便一門之隔,阿納托利也能輕易想見摯友那張素來冷淡的面容多麼氣急敗壞、心焦與憂慮——他常說伊利安太容易擔心了,但對方和他一樣,很少把彼此的話放在心上,這點他倆算是半斤八兩——便是使用幾乎與情感脫勾的母語,他也能聽出其中的緊繃,唯獨沒有責難。「嘿,那你現在還好嗎?我晚點煮點熱湯還是什麼的,跟感冒藥一起放在你房門。」
「謝了,我的免費Ubereats司機。」阿納托利沒有拒絕對方的好意,有意以輕快的語調緩和氣氛,「頭痛、喉嚨痛、全身痠痛,可能還有點低燒,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算哪門子的沒什麼大不了?!」如果伊利安的心理狀態能以動畫呈現,阿納托利覺得,肯定是動物星球頻道裡草木皆兵的狐獴,或在荒野尖叫的土撥鼠迷因。「算了,閉嘴,我先提兩桶水和熱水壺給你。等下敲門來領。」
搞得我好像在房間裡迷航還是遇難似的——
還不待他回應,就聽外頭腳步聲離開了,阿納托利無謂地聳聳肩,盯著桌上手指寬的檢體,兩條鮮豔的紫紅色橫槓昭示著不令人樂見的結果。嚥下唾液時,咽喉傳來陣陣針砭似的刺痛,讓他蹙起劍眉,厭煩高於體感的難受,就像乘機時總要忍受大得惱人、讓人無法成眠的引擎聲。
老實說,在歐盟各國口罩令紛紛鬆綁後,他對此並不特別放在心上,畢竟隨疫苗普及率提高,中重症的病例也大幅下降,遑論他過往接觸的人不乏確診者,大抵能從經驗法則裡判定自己就算染疫也不會太嚴重。
不過這個時間點真他媽會選。粗魯地揉揉因濕氣發癢的鼻頭,直到有禮的敲門聲響起,他下意識揚起一貫的輕慢笑容,近乎是種反射動作。「叩叩。」
「謝啦,伊留沙。我等等去拿,你可不能再跟我有更多接觸了。」說到這,阿納托利平時帶有一股狂妄之氣的聲線因語速慢下來,而聽來沉穩許多,像是個真正的二十七歲人。「嘿,雖然我昨晚下車後直接就洗洗睡了,但你和亞瑟也該找時間驗一下,如果不幸這成了伴手禮,我只能說,我很抱歉——」
「托利亞,生病不是一件需要道歉的事。」門外傳來一道相較於伊利安醇厚的男音,以英文打斷了他的喋喋不休。
阿納托利不知道對方聽懂多少,一時只得四兩撥千金地揭過:「喔,嘿,早安,亞瑟。我以為是伊利安拿水來了。」
「我拿過來了,五公升的水和消毒過後的熱水壺。稍後我會煮一壺薑茶,連同和早點放在你的門外,希望你不挑食,需要或想要什麼隨時告訴我。伊利安先出門採買其他日用品了,我想,暫時轉移注意力對他現在的心理狀態會有明顯的改善,希望你不介意我偷聽到年輕人的悄悄話。」亞瑟慢條斯理道,雖然隔著門版的聲音略帶朦朧,他仍能輕易感覺到對方身上那種令人安心的氣質。在簡短解釋後,年長的英國男子話鋒一轉:「但我想讓你知道,我們都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你絕不是會刻意染疫的那種人。你大概連怎麼確診的都不知道吧?機上?機場?計程車司機?誰知道呢?因此,你完全不需要為此致歉,生病不是一個錯誤,你也不是。」
說不上是否隱隱作痛的喉頭作祟,阿納托利沒有接話,拿起筆電旁的茶杯,低頭抿了一口冷水。
「而就算發生了這個小插曲,也絲毫沒有消減我們對你的歡迎。實際上,很慶幸你是在我們家裡發現的。我們無法想像,也不願意去想,你若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異域遭遇這些事,又該如何是好。」說到這裡,亞瑟頓了頓,在阿納托利懷疑那是一段嘆息的長度後,才繼續道:「說句無關的,你和伊利安讓我有同樣的感覺。我不禁想,相對於我這個年紀的人,你們那個時代高唱的個人主義,似乎反倒助長了羞愧與自卑情結,讓你們習慣把所有的過錯——包括那些發生在你們根本沒活過的時代的歷史共業、你們根本沒有造訪過的地方的戰事、你們根本不可控的天災人禍、你們不認識的人的生死等等——與責任扛在自己肩上。儘管毫無憑依,我卻覺得,你們這個世代要比父輩溫柔多了。」
從小受父親出入的場合耳濡目染,阿納托利一向長袖善舞,在一眾各有盤算的成年人面前亦能表現得像個得體的孩子,但對這席話,他不知道怎樣才能更適切地回應。
當然,他能將這些「情緒反常」歸罪於免疫系統耗弱而生的多愁善感,不過他也是最知道,哪些不是的人。
公平地說,他的親長從不吝於給予愛情。
然而,就與大多數孩子的成長經歷相去不遠,父母總是用著自己想要被愛的方式,或者,他們唯一能想到的方式愛他,吝於考慮那是不是他渴望的。這讓他數度以為,他的一生只需用上刪去法與拒絕的藝術,因而當最接近理想的選項出現時,熟絡的人際交旋完全派不上用場,他彷彿重返青黃不接的青少年時代,在他年少到對視線所及一切都充滿憤怒的時候。
如亞瑟說的,他們一代的所見教導了孩子們如何控訴與反抗社會的不公,但對如何恰如其分地接受善意,知道的少得可笑、可憐、可悲。他們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卻沒有人具足夠的自信能看見未來。
「謝了。」最終,阿納托利啞聲道,有意提高的音量聽來還是缺乏底氣。
只怪這詭譎的病毒來得太不湊巧了。
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0JHQyRbUh
惦記著病患得先墊胃才能服藥,亞瑟沒讓沉悶的氣氛停滯太久,確認他沒病到無法動彈,吩咐一句「客房的窗戶對著廚房外的空地,不會有人經過,可以打開來通風」後,轉而前去準備餐食。
經一遭大起大落的情緒起伏,阿納托利往椅背一躺,任慣性與椅座的滾輪將自己帶到床畔,然後面部朝下、隨意地趴了上去。
彈簧床磕得鼻樑滿是壓迫感,就著這個消極姿勢,在面龐與床鋪間的狹隘空間間攫取空氣,稀薄的氣體使他偏高的體溫又添高幾分,床單上殘存與霧都城市形象相距甚遠的太陽的氣味,若呼吸節奏加快,便可能窒息。但他此時不欲移動,鬆懈下來後的痠軟感雖遲仍到,霎時順著四肢蜿蜒而上,無力感如無形的枝蔓蜿蜒全身,就是結實的背肌與骨幹也沾染上了那份懶散,只得鬆散地癱在原處。
不合時宜地(也可能沒有什麼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阿納托利懶洋洋地忖道),他想到一個在社交媒體上流傳極廣的新冠病毒冷笑話:「告訴你們我是怎麼無意間發現自己的表演型人格的:起初我是沒感覺的,但在收到PCR陽性報告當天,身體就自動配合那兩條線開始喉嚨痛了。你們遇到就知道了。」
誠如亞瑟所言,他對這疾病的來源全無頭緒。即使他的個人立場傾向疫苗無用論,考量到職業與長途行旅所需,他從不迴避全面的防疫措施,在疫情初期,不乏有人笑他是神經質過度,直到時間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雖然現在看起來,也不過是早晚的問題罷了。他自嘲,不是不到,而是未到。
蹬開質地綿軟的室內拖,阿納托利弓起身子以右膝施力,慢吞吞地翻身坐起,將先前隨手拋上棉被的手機拾起。赤色標示的未讀訊息、閃爍的系統通知、藍光與爆炸性的資訊,爭先搶奪他淺薄的注意力,對鈍痛的前額無異於雪上加霜。
「有夠垃圾(Xуй на блюде)。」腰墊枕頭,阿納托利將上背靠上床頭板,讓他感覺自己活似個酒精中毒的八十歲老頭,沒有特殊意涵地低咒了幾句,復而斂下眼,打開通訊軟體。
應用軟體頂端的訊息,停留在他傳給伊利安的那句「驚喜(SURPRISE)」。其他幾名置頂聯絡人的對話紀錄,停留在兩天到數月之前不等,唯獨他母親終日鍥而不捨地分享抖音影片與長輩圖,未讀標籤已多達十則,堪比聲稱低息小額借貸的罐頭簡訊。所以就算是搪塞,他也分毫不樂意點開。
以預覽模式瀏覽一回其他訊息,忽略千篇一律的生日祝賀,他僅簡略回覆了編輯丹尼爾森。在近三年的疫情與國際角力影響下,百業蕭條,以「人流」為指標的旅遊業自然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就是總被認為樂觀得無可救藥的美國人,也不得不為旅遊禁令與高通膨率垂首頓足,在這些自由作家的僱傭契約上,限縮了與財務掛鉤的相關條例。
這使丹尼爾森興致勃勃地想將他過往的專欄文章統整成冊,發行成電子書,趁勢打入新媒體外的圈子。同是行動派,阿納托利不排拒他另闢蹊徑的思路,只是偶爾不免感慨,深根於歐陸的格局到底是沒有新大陸的拓荒者來得大膽。
父親常道他缺乏定性、恣意妄為,自詡為「現代主義者」,實則是拒絕對未來許下承諾的冠冕堂皇之詞,短視近利,渾然不覺所有的「現在」都構築了通往「未來」的道路,他的逃避亦然。
「像隻追著自己尾巴瞎跑的狗」,來自他父親的原話。
在常年的爭論中,這些已是老調重彈,因此多數時候,阿納托利習慣充耳不聞;可是有時,他內心還是會無端升起一股火氣,想直勾勾看進父親與他相仿的眼睛問:「如果我不接觸更多人、不走過更多未知的地方、不嘗試更多的東西、不見過更多的文化,怎麼會知道,我最適合在哪裡呢?你是最知道我們是多麽不同的人了,那何必勉強把我變成,跟你一模一樣的人呢?難道你對幸福的理解只有一種?難道你已經老到無法動彈,老到不能接受新事物了?或者更糟,難道你從未長成一個能理解他人的『大人』?」
「智者能屈能伸(Der Klügere gibt nach)。」冷不防地,一道介於冷淡、鎮靜與漫不經心的女聲自他以為已經遺忘的記憶裡浮現,以及下一句:「既然要用別人的愚蠢懲罰自己,那何必當個聰明人呢?」
如果非得要有人不痛快,怎樣也是對方吧。或許不常,但在兩人獨處時,莫桑並不避諱表達出對事真實的看法,而狀似被她劃入狹窄的、排外的、獨一無二的圈子內的暗示,總能讓阿納托利心情大快。
誠實地說,隻身在外時,他不常想起莫桑。
實際上,他很少想到任何人,大學同學曾在聚會上將其歸因於他的任性妄為與獨裁,笑說他連做小組報告都能企及「目中無人」的境界,簡直喪失人性。後來,伊利安不以為意地評論:「不過那也不代表不在乎吧?你只是把自己的每一分精力都在『現在』全力以赴了。那就是你啊,托利亞。」
這讓阿納托利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莫桑從未與他談論未來,好像彼此都默認,在他們之間的「發生」,無需增添自作聰明的衍生解釋。人們夢裡建構的未來,於他、於她,以及他們,無非是可能永遠蓋不成的巴別塔,她不欲受未知的、不可靠的、泡沫幻影般的臆想綁架,只要他傾注一切的「現在」,就足夠了。
「但是為什麼?」在一次「古蹟/古物維護的正當性」課堂激辯後,伊利安這般問他,語調不是惶惶不安,似是單純的好奇。「你追求的不是每一個『現在』都表現出最好嗎?那為什麼反對(維護)呢?明明那讓我們有機會,最大程度的了解那個『現在』是什麼樣子吧。」
他忘記自己具體答了什麼,依稀記得大意不脫「自然風化、蓄意破壞與疏於照顧,也代表著部落遷徙、新文化侵襲、政權轉移、社會觀念轉變等歷史意涵,這些都是歷史的痕跡,某些人存在過或不存在的痕跡」云云,結尾他說:「這時代誰都在追求『真實性(authenticity)』,但最純粹的『真實』只存在於事件發生的當下,就算是創作者完成作品後,也可能隨時間、他人評價、心境轉變,無意識地為其作出更多『原本沒有的解讀』,遑論被視為永恆辯證的歷史。而在歷史中,如果真有什麼必須『真實』,歷史本身自然會有辦法將那個樣貌留存下來。」
「舉例呢?」伊利安不置可否,不忘保有學者該有的懷疑論精神。
「龐貝吧。剎那即永恆,不是嗎?」他聳聳肩,得來對方「那算是神的領域了呢」的感嘆。那天晚上,他們不知怎地又提起這件事,然後一起哼了巴士底樂團的同名歌曲。
時值今日,阿納托利仍抱持著固執的偏見,認定那側面證明了天長地久的荒謬。
——假如有什麼非得凍結於此刻,也只能、只可能是災厄吧?
盯著逐漸暗去的螢幕光度,他的動作先於思考,直覺性地以輕點喚醒手機。這也讓他登時清醒過來,意會到思緒走到了一個未曾抵達的遠方,暗自解嘲他怕不是和《Lucy 露西》一樣,因高燒而覺醒了什麼。
病毒肆虐的悶痛感依舊,卻讓他分外清晰地感知到「現在」。
躍動的心跳、微熱的肌膚、溫熱的吐息,與忽然而至的,讓他無法抵抗的思念。
低下頭,阿納托利見指尖輕觸的那欄暱稱,頓生一種鼻稍縈繞著煙霧的錯覺,溫柔得不可思議地笑了起來。
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KZyzBPjC0
他知道二十七歲第一天的「現在」要獻給誰了。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JUl3aCBMc
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gmNEnXijZ
23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Evwd552Dz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