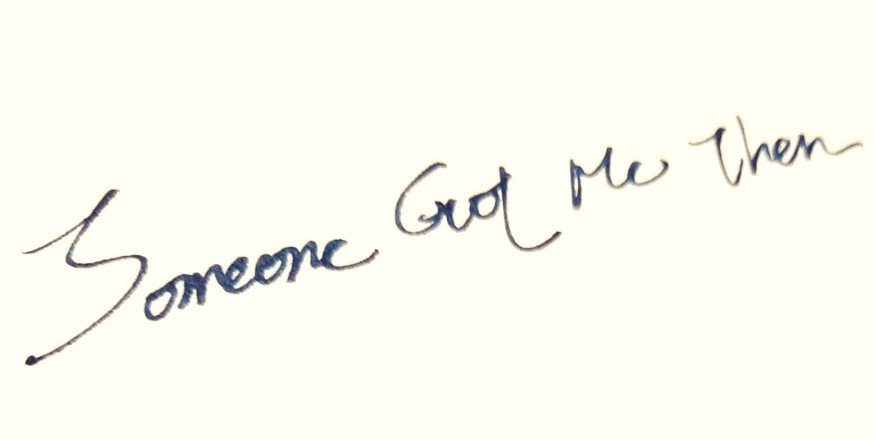- 設定於2012~2013年的北倫敦(North London)和諾丁罕(Nottingham)
- 亞瑟・安斯提/珊曼莎・歐蘇利文 Arthur Anstey/Samantha O’Sullivan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ZIzQrQvQv
#Side A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zPrc6XnG5
珊曼莎難得排到假,本欲拉著同居男友出門散心,便被對方一句輕飄飄的「我們約好的,週三的午後時光屬於好音樂」否決。
她未嘗沒有和亞瑟商量是否可以「彈性一點」,但在多數時間通情達理的他,獨獨對此毫不退讓。認真地說,那態度稱不上強硬,只是像見到性格溫馴的人偶爾情緒潰堤一般,讓人時會對那些邊界的界定感到好奇——
是的,好奇。在同一張床上迎接過不可計數的早晨(大概有兩千、或三千個?她想),觸碰過彼此每一寸肌膚,她最喜歡的那件薑黃色開襟洋裝、都染上了他衣櫥裡的鼠尾草芳香劑氣味,而他也總會備好熱騰騰的厚壓吐司、讓她帶著趕上七點十分發車的地鐵⋯⋯可便是相處那麽久,珊曼莎還是時常感覺,自己好像不了解他在想什麼。
有時候,單單是他的目光落在一個較遠的地方,她就覺得好像要失去他了。
這個猜臆毫無根據,日久月深,好友也從方始義憤填膺地齊聲指責「難道他劈腿」,轉為一面促狹裡帶點羨慕地感嘆「大概是七年之⋯⋯喔不,十年之癢的倦怠期吧」,一面暗示她該珍惜這段比許多婚姻經營得要來得長久的穩定關係。
結婚嗎?珊曼莎幾乎是在產生這個念頭時,就立刻掐滅了那點不存在的火花。
理由有很多,在英國同居人的法律權益近乎於合法伴侶、婚禮是耗時費力且無投資報酬率的沉沒成本、他倆都是對在聖堂前許下終生不抱想像的無神論者⋯⋯當然,最直截了當的原因不脫意願,而她未曾從亞瑟的任何言行舉止裡觀察到,他具任何想要步入禮堂的意圖。相處越久,珊曼莎益發區分不出來,是婚姻這件事的意義不再重大,或者她只是害怕問出口後、會得來對方為難的婉拒之詞。
亞瑟暗灰色的眼睛保有黑白之間的餘裕,但不過分強調立場同樣預示著,不會輕言許下承諾的游離態度。
經過多年,那種流離感依舊似他們邂逅時,滿身狼藉飽受宿醉之苦、骨子裡充滿悲傷仍對遞來杯裝水的她竭力報以微笑的年輕人。
那是她最鍾愛也最無法割捨的部分。
見亞瑟從電視櫃挑出一塊唱片,俯身準備打開播放器與藍芽音響,珊曼莎也打消出行的打算,索性挽起袖子、打算整理對兩個人的生活恰恰剛好的小套房。
平素在超市輪班的作息,使她在輪休日與一般人一樣,多半在休憩與無所事事間度過;作為勞動強度較低的居家工作者,他大多時間會肩負起家務,幸而經濟基礎的提升也使這一切變得不那麼惱人,如他二十歲時、沒幾個月就要重新置裝,汰換那些被揉洗得鬆垮的衣褲。
大掃除讓珊曼莎活力四射。
不是她熱愛打掃,只是藉清掃的機械性動作,平時在工作場合應對突發情況的緊繃情緒也能緩解些許,像是盯著四個半拍往返的節拍器、你總能找到一個安放自己的節奏。
因此,當座機響起,見在沙發上捧著《刺鳥》[1]精裝本、指節隨樂音輕點書封的亞瑟無意起身(他總會在這種氣氛裡兀自陷入個人的暢想,好似置身外太空或某種無法被涉及的時空間隙,她分辨不出來那是沉思或單純在發呆),她也不抱怨,愉快地就著一個滑步、靠上進門一側的壁掛電話。珊曼莎以結帳時能讓最刁難的客人緩下久待的怒容的燦爛笑容拾起話筒,語氣明亮澄澈,直到對頭傳來特瑞莎異常沉鬱的聲線,那抹笑瞬時如散盡夜空的煙火,湮滅於灰濛濛的餘燼。
自她的轉述獲知瑪莉姑姑心肌梗塞的死訊時,亞瑟還沉浸於《悲喜交響樂》[2]的漫長前奏裡,彷彿自己就是影帶裡剛站定位,待主歌一下便要橫越馬路、眼神陰鷙的反骨青年,就算整個世界的吶喊咆哮都無從停止他前行的步伐。
只惜他不是李察・艾希克羅[3],他倆也不是邦妮和克萊德[4],無法對他人的死亡置若罔聞,尤其是至親之人。
登時像從夢裡醒來的亞瑟沉默關上了音響,戴上腕錶的舉動是外出的前置準備,珊曼莎下意識道:「我跟你一起過去吧。」
這句話似乎讓那雙灰眼睛鬆動了一些。她覺得。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HloH7KTnv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eQCdD4jny
時近年末,市景逐漸染上節日氣息,每個街區都佈置起了紅白綠金色調的飾品,十足應了車上廣播的《聖誕就在不遠處》[5]。
支著臉,見駕駛座的亞瑟唇抿成一直線,珊曼莎不禁感覺,歡快的背景音樂在此刻都是種戲劇性諷刺。她無來由地感到難受,明知不合理還是想指責那些人的快樂是種殘忍,明明他們毫不知情,也毋須承擔陌生人的哀慟,世上每分每秒都有生命在凋零,甚且遭逢比死去更悲慘的命運,不是只有死亡令人傷感。
然而,巨大的傷感拉扯著她的理性,讓她懷念起關上房門後、就能將世俗侵擾阻擋在外、盡情嚎啕大哭的少女時期。
「你覺得,溫蒂成為人母後對彼得・潘的溫柔,是出於一種社會化的偽裝,抑或是童年的召喚呢?」剛認識不久時——差不多是他們第二、三次約會的時候吧?珊曼莎隱約記得那天她戴著一條銀色的手鍊——得知她對迪士尼電影[6]情有獨鍾,亞瑟冷不防問道。
「溫蒂離開夢幻島後,還有與彼得・潘再會嗎?」當時二十歲的珊曼莎對孩提時代的印象已記不精確,不掩驚訝地反問。
聞言,亞瑟不失禮貌地微笑點頭,沒再解釋或提及先前的問題,視線卻無端隨這舉動飄離,似自她身上飄落的雪花,最終消融於半空中,徒留人一身悵然若失的冷意。
說來是少年心性的荒唐也罷,珊曼莎望著那張削瘦的側臉,天真地想,自己或許能溫暖這個人。
後見之明,說不清是長大成人的她漸漸意識到,那種冷淡的距離感才是人世間的常態,又或者亞瑟本就不需要她的溫暖,因為那種微冷的溫度已是他認定的溫暖。
一如此時緊盯著路況的灰色眼珠,沉穩冷靜得、狀似在無聲拒絕她欲言又止的關心。
「妳還好嗎?」待思緒回籠,珊曼莎才發現亞瑟不知何時將車靠道停了下來,不再專注於車前交通的眼凝重看她。
平日總含幾分敦厚笑意,偶一為之的面無表情使他看來格外嚴肅。
見她目光閃爍、神色惶惑,亞瑟也反應過來,抿唇似要緩和氣氛,又道:「我沒別的意思,只是意外《女孩只想玩樂》[7]竟然是首這麼悲傷的歌嗎?妳看起來很⋯⋯難過。還是路程顛簸,頭暈了?我們可以下車透透氣。」
這話讓珊曼莎留意到背景音樂,辛蒂・羅波帶點神經質的標誌性嗓音在封閉的車廂裡迴盪,來自八〇年代晚期的流行樂符使整個空間擁擠起來,讓她胸口發悶、意欲逃離這個矛盾的場合;但是,她也明白,亞瑟知道她沒有暈車的毛病,順應這種體貼反倒是種將自身軟弱當作武器的任性。她是不喜歡那種難耐,但她更不希望他的耐性被消磨,畢竟連她都不知道這種情緒化的表現所由為何。
「不是的,我喜歡她,尤其是《一次又一次》[8]。」深吸口氣,她眨了眨眼,有意識地往雙頰施力,彎起唇線,想要露出一個讓人安心的微笑。
職場上多少會歷經必須強迫自己露出職業笑容的壞日子,她以為自己做得夠好,但亞瑟僅是不發一語,背光的眼睛看不出是什麼神情。
良久——可能實際上不到十秒鐘吧,但珊曼莎只覺長得像是一輩子——之後,他紓了口氣,在她聽來就像嘆息,將排檔打回停車檔、俯身解開安全帶的扣環。金屬撞擊的清脆聲響敲擊她敏感的神經,無法名狀的窒息感又像鬼魂一般回過頭來糾纏⋯⋯
在她忍不住要尖叫著推門而出前,就聽亞瑟用比往常更低沉的聲線道:「我從剛剛就想說了,我可以給妳一個擁抱嗎?或者相反,妳可以給我一個擁抱嗎?我現在最需要的,大概就是這個。」
只是這個。
幾乎是在語落的那一刻,珊曼莎立刻將大半個身子探向駕駛座,彷彿落水之人抓緊浮木似地,重重抱住了對方,不顧安全帶因這劇烈動作將她肩頭勒得發疼、直要發揮功能性將她拉離他。
初始的驚訝使亞瑟繃直身子,隨後卸下緊繃,回應了這個來得急促的擁抱,在她倚上自己肩頭的髮頂落下輕得簡直感覺不到的吻。
不知有無察覺這細節,肌膚相觸的溫情讓珊曼莎泛紅眼眶,別過臉避免浸濕他肩上的襯衫布料。
從前她以為,人對於事物的冷漠與傲慢是最糟糕的,因為那代表他對除了自身之外的世間毫無敬意;虛長幾歲後,她才慢慢意識到,亞瑟・安斯提這個人最令人絕望的從不在這兩者,而是就連在這種時候,都溫暖得讓人難受。
珊曼莎第一次發現,原來連一個人的溫暖都能讓人如此受傷、如此痛恨、如此無能為力。
他分明才是此刻需要撫慰的人,她卻得到了一個擁抱。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tMoTuanja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FakQIjNRU
抵達諾丁罕時已是日暮時分。
後半段的旅途不如起先沉悶緊繃,他們就著電台輪播的七八〇年代金曲在休息站簡單帶了兩個三明治,最後在《我想要出逃》[9]的鼓點中,驅車滑入瑪莉姑姑那幢獨棟平房前的空地。
下車時,亞瑟見車道旁一小欉大花耬斗菜被某個糊塗司機生生軋扁,不在花期的枝枒稚嫩,巴掌狀的細葉經車輪洗禮後蔫萎於地,讓他皺起了眉。盯著那殘景瞧了好一會兒,他才在珊曼莎的叫喚聲中別過目光,徑直往大門走去。
除長年旅居海外的幽靈人口,遠近的親屬都到了——羅德尼當然也是,他們抵達時站在門樑旁抽捲菸的不是他,還能是誰?——因此,當亞瑟的德比鞋踏上玄關那張瑪莉姑姑珍愛的土耳其地毯時,房中頓時陷入詭異的靜謐,只有未掩實的門外的羅德尼一聲嗤笑分外突兀。
初次來此,走在前頭的珊曼莎腳步侷促、下意識回頭看他,見他面無慍色時鬆了一口氣,卻又因而憂慮,只得遲疑地朝房中的熟面孔道好,試圖緩解僵硬的氣氛。
「嘿,你們來了。」聽見她的聲音,特瑞莎從廚房探出頭,揚了揚手上的熱水壺,招呼他倆要不要喝點熱茶咖啡或吃點什麼。
「水⋯⋯白水就可以了,謝謝。」珊曼莎彎起嘴角,想要擠出一個笑容,打散這個他們像誤闖不受邀請的舞會的怪誕錯覺。
亞瑟一個大步跨前越過她,緩聲說了句「我不用,謝謝」後,朝廳堂裡說笑的安斯提家人——包括他的父母——點頭道聲「下午好」,便直往二樓走去,像是熟絡於通往秘密基地路徑的孩子,背影有種堅毅的孤獨,與義無反顧。
面對一室陌生人無端逼仄,珊曼莎原想跟上,舉步時便被特瑞莎自後頭拍了拍手臂,隨之得到了一杯冷開水。
「給他一點獨處空間吧,他沒事的。」與那雙鉛色眼瞳相仿的淡灰眼珠看向僅留殘響的階梯,特瑞莎捧起手上散著伯爵茶香氣的馬克杯,一面咕嚕咕嚕喝著,一面模糊地說:「沒事的。」
珊曼莎欲言又止,分不清她說話的對象是自己,還是她自己。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aWIKkTNwu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LojSUxKC0
#Side B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iEWT9biYj
自十八歲赴布里斯托(Bristol)求學後,亞瑟就不像少年時代那麼頻繁地造訪瑪莉姑姑。
然而,爬上滋戛作響的老舊樓梯後,身體記憶先於他的所有邏輯推理,直接右轉朝走廊靠底那個房間走去。那房間的門沒關上,因此還未走到定位,他就能見到落在門口的那塊長方形狀的羊毛地毯上、躡手躡腳闖入房子的陽光,讓人能輕易想見赤足踩在上頭會有多麽快活。
在全球暖化成為共識的當代,瑪莉姑姑是他所知的所有人中,唯一將主臥室設在酷暑夜晚也熱得難耐的西曬房的。
房間格局不大——想來最初的設計者也沒料到有人將這當作寢室——加大單人床上頭罩著老太太喜好的小碎花式棉布,尺寸與使用年限不一的櫃櫥沿牆置放,此間食譜與文學小說按字首交錯排列,櫃子頂部零散擺著滋潤得茁壯的多肉植物;入門處左側的梳妝台上堆著亞瑟看不出差異的瓶狀乳霜、形狀各異的木梳、人的一生需要用上的所有鏡子、幾張寫著隻字片語的紙片、兩支輪流戴的老花眼鏡,與角落被特意放在陰影處的、去年亞瑟準備的聖誕禮物:一支迪奧的淡香水。
透明香水瓶裡頭餘有三分之二,可見物主多珍惜用之。
亞瑟垂首凝望,淺紫色液體在玻璃瓶裡像是靜止的歲月,他拾起巴掌大的方形玻璃瓶,往空中隨意摁了一下,香氛如同茉莉花在冬日不開暖氣也被日光照得生暖的室內舒展,末調有另一種花的香氣,他不知道是什麼,感覺像是在森林漫遊時會遇到的那些無名小花。
感覺像是他未曾見過、卻無比篤定的,二十歲的瑪莉・安斯提。
背靠著碎花布的床沿坐在地板上,暖冬的房裡讓他大衣內的肌膚生出一層薄汗,卻無意褪下外衣,只若對火柴光火懷有期望的小女孩,在空氣間的香氣餘韻散盡後,不厭其煩地、好似對疲憊渾然不覺地摁下香水瓶。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kA6rL0FqK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7LqT2H6dnO
亞瑟下樓時,素來社交手腕高超的珊曼莎已融入了一群年齡相仿的遠房親戚——裡頭的領頭者好像在市區的診所執業,他記得——凝神傾聽著其他人說話,看來話題足夠有趣,因為她眼睛閃爍著好奇的光。他沒有上前打擾,見跟自己父母坐在餐桌的特瑞莎朝自己擺擺手,他打了個手勢,表示要先去倒杯茶。
瑪莉姑姑一輩子單身,雖然整室人已是這世界上法理上、基因上與她最接近的人,但亞瑟難能斷言,那是不是她臨終時最掛在心上的人,而至今無人提及這點,彷彿自然而然,或說理所當然地,在這種時刻帶入了「可憐獨居中年人的家屬」的角色。他不想作為打破「這個」的人,只是這念頭就像喉頭的一根刺,饒是他可以避而不談,也不想故做無謂地、在她不在的此時,偽作他們親密無間。
儘管,是的,他們曾親密無間。
走入廚房時,亞瑟彷彿還能嗅到這房子的女主人拿手的瑪德蓮香氣,一陣情緒連帶鼻酸湧上心頭,可坐在裡頭的人讓他頓下腳步,迅速收拾好心情與打亂的步伐。
相對來說,羅德尼更不擅長(或樂於)應付親戚,因此他今日出現已是不易,不料還帶著七年級的養女,他過往可從未讓亞瑟在內的任何家人與泰利有過多接觸,遑論出席這種指向性明確的場合。想見也是考慮到這點,早熟的女孩雖無選擇在外吸羅德尼的二手菸,也有意識地獨自待在角落戴耳機用iPod Nano聽音樂,避免節外生枝。
見他來了,泰利禮貌性地摘下一側耳機,打了聲招呼:「嗨,亞瑟。」
「在聽古典樂?」在動輒進勒戒所或警局的兄長比對之下,亞瑟無意指摘這種頂多造成聽力衰退的小興趣,或自詡為道德高點,控訴年輕人科技冷漠云云,只是一邊給自己倒杯水,一邊問道:「我記得妳是吹小號的。」
「新秩序樂團[10],是羅德灌的歌。」少女不置可否地聳聳肩,金髮像是散落的陽光,隨動作自肩上滑落。
亞瑟一時語塞,不好在孩子面前提到監護人的壞話,只能乾巴巴地說:「但我以為,這個年紀會著迷於強納斯兄弟[11]或麥莉·希拉[12]。」
「太美式了吧。」泰利以一種比凡常十歲孩子更成熟的口吻笑著說。
「我不確定小賈斯汀[13]或一世代[14]是不是比較好的選擇,而且這個年紀就有文化偏見可不是什麼好事。」這話讓亞瑟鬆弛許多,玩笑道。
「有次羅德的同事聽到我的歌單內容,說我有個『老靈魂』,但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是稱讚嗎?」女孩雙手支著臉看他,稚嫩的臉龐被手掌托得圓潤,可靈動的眼睛與輪廓線已預示未來將出落成怎樣的美人。「如果是稱讚的話,為什麼大家還那麼怕『變老』?」
因為老去時常讓缺乏想像力或深度思考的悲觀者聯想到死亡、凋零,或者腐敗。用吞下一口水的時間斟酌說詞,可最終亞瑟仍找不出什麼合乎心意的推諉之詞,只是淡淡地說:「可能有的人的好與不好,跟年紀沒有實際關聯吧。然後,嗯,那是稱讚沒錯。」
得到滿意的答案,泰利點點頭,又戴上了摘下的耳機,沉浸於那些多半比她年歲更長的樂曲。
靠著流理台喝水,亞瑟不再發話,也不急著離開,為這種恰逢其時的安靜感到慶幸,想起了一些舊事。
彼時,搭紅眼班機抵達科克機場(ORK)的他們租了車,直奔珊曼莎在愛爾蘭的老家過復活節假期。車內廣播是當地電台,正輪播八九〇年代的英國單曲排行榜(UK Singles Chart),主持人的口音濃厚,讓珊曼莎為亞瑟只能聽懂七成的串場詞頻頻發笑。
然而,在聽到「年幼的身軀裝著老靈魂」一句時,她難得尖銳地諷笑出聲,惹得亞瑟挑眉看她。
「我不懂為什麼人們會自豪於此。我的意思是,喜歡聽『某個時代的流行歌』算是什麼靈魂的驗證?我真的很受不了那些只聽過一張專輯——有的甚至只聽廣播輪播到爛的那幾首歌——或買了幾張演唱會們票,就自詡為『忠實粉絲』的人。」她不以為然道。
「為什麼?」
「他們多半是憑一點追趕流行的熱情加入,對這個人、這樂團或這種音樂型態一無所知,在這熱度之前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也毫無頭緒,就說是『喜歡』也太可笑了吧?」
亞瑟沉吟片刻,復而又道:「如果人凡事都需要足夠了解背後的深意,才具有『喜歡』什麼的資格,或許許多人的終其一生都不該、也不會在一起吧。」
珊曼莎張了張口,像要說什麼,好一會兒後還是歸於沉默,任車廂中那首《說我愛你卻詞不達意》[15]像是窗外的夜色,一點一點覆沒他們。
直到此刻,亞瑟還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無意間攪擾了他們之間的什麼,讓她覺得還是什麼都不說更好。甚至說,他是不是為這種什麼都不說感到僥倖。許多長年相處的伴侶會以一種「這種事我看很多了」的口吻說,那種磨合的產物會成為一種默契,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該對此保持盲目的樂觀——
愛情,或說愛的真義是否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呢?難道愛勢必歷經人所知、已知、未知的辛苦呢?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lupuK5W6D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QhdTYEwMP
他們那天沒見著瑪莉姑姑的遺體,因為當急診室醫師正式作出死亡宣告後,大體便被直接送往殯儀館,因是除了住家離得最近的查爾斯叔叔一家先去認屍,獲知這消息的親屬約好在她的住所集合、整理遺物,一道籌備悼念會。
事隔數日,未能見上瑪莉姑姑最後一面,亞瑟倒是見著了她的律師。跟在場多數人一樣。
眾人驚異的先是保守——不拘泥於她的政治立場,還有打毛線、善於烹飪的那些特質——的瑪莉姑姑竟會留下遺囑,還安排了遺囑宣讀這麼戲劇化的橋段;其次則是,她將自己所剩且僅剩的一切獻給了慈善,還有,亞瑟。
「請容我引述安斯提女士的原話:『銀行戶頭裡的流動資金捐給無國界醫生協會,退休基金給世界展望會,其他動產與不動產交給世上最愛我做的糕點的人。』幸運的是,最後那個人經我們詢問當事人後,恰巧是她的姪子。」
半途才到的羅德尼聽完這段,毫不在意場中凝重且困惑的氣氛,大笑起來,見其他人望了過來也不羞愧,反倒挑釁似地看回去,目光炯炯,叫人一口氣堵在胸口,進退維谷。
可就連一朝獲得這幢宅邸所有權的亞瑟也措手不及,呆坐在原地好半晌,才抬起頭。他想問些什麼,可見周遭探究的目光,又將那些注定沒能得到最佳解的問題吞進腹中,端起禮貌的微笑承接親戚好奇(與好事)的試探。
離開之前,律師建議亞瑟近日整理一下瑪莉姑姑的遺物,看有沒有不列在已知帳冊上的條目,待他拿到死亡證明後,可以到事務所討論要如何申報這些細項。對方話說得婉轉,但亞瑟的工作時常需經手避稅文件,因此他明白這話背後真實的意義,沒有戳破,只是面不改色地點頭。
送走律師後,親戚們知這結果其來有自,商量好了下葬的時間也沒多糾纏,相繼道別,羅德尼更是一句話都沒說就走、只留下重機轟隆隆的引擎聲和一車屁股廢氣。
特瑞莎、珊曼莎和亞瑟的父母平日有工作,因此只有他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感受人來人去平添的一股寂寥感。
斂下眼,他拿出手機打開通訊軟體,摁下珊曼莎的頭貼輸入一段文字,想想又刪掉大半,長話短說,終以一句「我晚上不回倫敦了」發了過去。她值班時很少將手機帶在身上,因此他沒有等到她的回應,又將手機收了起來,轉而上樓走進瑪莉姑姑的房間。
亞瑟是會在此度過一宿,但沒打算在這房間入睡,裡頭的樣貌還保留了原屋主印象中最好的模樣,以它們慣常的姿態等待著陷入永眠的主人歸來。不管未來如何,此刻的他捨不得打亂這一切,因為就連他自己,都不確定是否接受了那個事實。
沿牆而設的矮櫃上陳列華茲渥斯[16]及蘭姆姐弟[17]一眾湖畔詩人的作品,邊上擺著幾本手札大小的素面筆記本,其中兩本封面寫著「食譜」的沾染些許污漬,餘下的精裝本如出一徹,外封都有著燙銀的「日記」字樣,右下角簽著「瑪莉・安斯提」。他猶豫片刻,終是把那些札記簿悉數拿了出來,靠著書櫃席地而坐,翻起其中一本,確認內文確實是日記,便從寫入日期最早、字跡最青澀的那本開始閱讀。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1Kpj8qL9MW
#Side C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Ey1IH3tyC
抱著整沓札記,亞瑟一直讀到深夜也不覺飢餓。
瞟見窗外月上樹梢,積雨雲般濕悶厚重的寂寥溢滿胸膛,教他發不出聲,也不知可以向誰傾訴,只是將簿子整齊地疊在地板上,然後,在一旁的地毯上躺了下來,不管不顧襯衫會因此發皺,像個孩子蜷起身子。彷彿瑪莉姑姑還在的時候。
將那些厚實的筆記本籠統稱為日記言過其實了,裡頭的日期斷斷續續,間隔次序不一,內文不全是生活點滴,即使偶有幾頁寫著麵包店學徒的待辦事項,主軸仍圍繞著一個人,精確地說,是一段起於一九六八年、長達九年的秘密戀情。亞瑟無從分辨那些敘述裡有多少是美化過後的兒女情長,可一筆一畫勾勒出的喜悅、懵懂、不自覺的渴望,甚至是末了曲終人散的黯然,讓他無法置若罔聞,無法忽視一個人身處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所生的光芒,以及愛。
那才真是少女時代的瑪莉・安斯提活過的痕跡。
昏黃燈光在夜色裡溫軟地覆蓋上他的面容,他輕輕地闔上眼,任那些文字捲起的情感浪潮隨呼吸與思緒,在身體裡流淌。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NUcYrLPn2
#Side D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kvSDnt6ON
安斯提家稱不上富裕,祖輩在工業革命後投入了鐵路事業的文職工作,所幸家族在二次大戰並無帶來太多影響,只是母親開始在附近的報社上班了,也鼓勵瑪莉去上學。
起先,雖然終日坐在桌子前聽老師滔滔不絕很惱人,但同齡孩子間聚在一起還是很好玩——尤其她家裡只有兩個吵鬧不休的兄弟,襁褓中的妹妹又小到不適合聊些女孩的話題——她也喜歡裙裝的制服,所以瑪莉一意想在現代中學(Secondary modern schools)學個一技之長後,再申請進入護士學校。不料在她進入中學那年,重點中學(Grammar schools)的學制逐步併入其中,加之六〇年代去文法教育的潮流當道,讓比起理論更擅長實務的瑪莉更加吃力,只得說服父母讓自己休學,轉而到親戚的引介的麵包店打工。
老實說,她原本只打算藉此累積一些經驗而已,畢竟儘管她喜歡跟母親一道窩在小小的廚房裡烤派,喜歡追逐把蛋清和奶油打發的時效,喜歡店主夫婦的笑容,也喜歡小麥粉的氣味,但那麵包店離家極遠,她每天得要五點出門,在公車與東密德爾幹線往來奔波,十六歲的她壓根兒沒想過要將此作為一生的事業。
然而,自從店主夫婦偶然吃到瑪莉當午飯裹腹的法式鹹派[18],便將跑腿的雜務轉由收銀的伙計承接,誠懇地問她想不想跟同是麵包師的店主一同烘焙。她沒有多想,純粹因為上漲的工資應諾,比起在櫃檯交際,她也更喜歡見證發酵麵團在烤爐裡逐漸膨脹成形的過程、感覺那就像魔法一般,遂肩負起塔類、鹹食和糖漿餡餅[19]在內的製作。
不若東海岸主線停靠的城鎮繁華,周遭小鎮的人們因豐富多樣的小點心聞香而來,生意興隆,店主夫婦忙得腳不沾地,卻也笑得合不攏嘴。在這種忙碌之中,他們也迎來了年末的旺季:特殊甜品最多的聖誕假期。店主不是正規廚藝學校畢業的學生,在南方城市的糕點專賣店當了多年學徒,有一些工作歷練後便返鄉開了這個小小麵包坊,因此沒能接觸到樹幹蛋糕[20]諸類技術需求更高的精緻甜點,那對任何對烹飪懷有熱忱的人都是種遺憾,幸而瑪莉的分勞解憂、使他有時間鑽研食譜,也放心地放手讓她負責更多的品項。
縱使在廚房的時間增加,親和近人的瑪莉仍是很快與鎮上的居民打成了一片,偶爾碰上幫父母跑腿的孩子,總會讓她想起弟弟,她都會偷偷塞給他們自己做來當零嘴的薑汁蕾絲小脆餅[21],換得孩子們大大的笑臉。即便如此,欠缺行銷的好產品吸引到的客群終是有限,在沒有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她終日面對烤箱與糖霜,認識的人事物彷彿已成定局,視野日復一日所見的景色讓少女不免為自己的青春感到悵惘,難道她的人生就是這樣、只是這樣嗎?
那名青年是這種一成不變中最好的意外。
她們在初冬相遇。那天飄著雨,氣溫很低,青年恰恰在打烊前進門,見他渾身打哆嗦,店主夫婦也不計較他面生,連忙招呼他到壁爐前暖暖身子;正在清點甜點餘數的瑪莉也沖了杯熱茶給他,順帶附上兩塊剛出爐的百果餡餅[22]試作品。
年約二十的青年怯聲道謝,解釋自己是來買麵包的,他聽說這裡的千層酥[23]很好吃。店主見他如此驚慌也覺好笑,連聲安撫他慢慢享用,就隨妻子到後場打掃,留兩個年輕人在爐前待著。拉開隔板,隔著爐柵,瑪莉用火鉗翻動木柴——不是他們在火車都在電氣化的時代還追求舊時代的浪漫,而是窯烤麵包主要仍是以柴火導熱,因此伐木也是他們的例行公事——木屑燃燒的滋滋聲、身旁陌生人咬開餡餅的甜美氣味,一切種種都輕易讓她想到那個讓無數家庭齊聚一堂的節日。
哇。忽然,那名素昧平生的青年發出了讚嘆聲,她望過去,與之四目交接。
青年有一雙榛子色的眼睛,看著人時有種莫名的誠懇,好似情感也是透明的。當他問她是誰做出這些餡餅的,見她司空見慣地用手指朝自己比了比,面上的驚艷立刻成了震驚,趁得嘴角的塔皮碎屑格外孩子氣。
「你讓我想起一個女孩,她有兩個——還是三個?——孩子,現在應該差不是三十多歲了⋯⋯」見到瑪莉的神情,那男子立刻發現自己的措辭多不恰當,放下手上的甜點,連忙解釋:「噢,見鬼的,我不是那個意思,請相信我。那個女孩——咳恩,那位女士是我以前常去的餐酒館的服務生,手很小,膚色很深,襯得一排牙齒很白、非常漂亮。她老喜歡塞一堆好吃的東西給我,我每次都吃不完,但她人真的很好。總之,嗯,讓我想起妳。」
「你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她輕聲說了聲謝,又為一個陌生人說自己像是三十歲人致謝感到好笑,忍不住笑出來。
見她不惱,青年也笑了起來,接著說:「她每天都會烤新鮮的派⋯⋯跟妳一樣,我猜。」
她之前告訴我,一塊派的好壞,只要一口就能知道。他道。
「這個我知道,只要一口你就會知道是不是什麼多了——或是少了。」瑪莉接過了話,火光在灰色的眼裡躍動,彷彿是清晨要亮起來的天空。
「對,只需要嘗一口就會知道,這餡餅真的很不得了。一口就讓我想全部吃光,太危險了。」不知名的青年點頭如搗蒜,隨後像是舞台劇般煞有介事地舉起了手上的餡餅,「如果妳做的糕點是書,那肯定是多蘿西·華茲華斯[24]的詩。」
對英倫文學所知甚少、也從不感興趣的瑪莉當時沒聽懂對方說的是什麼,可見他熠熠生輝的神態,她無來由地相信,那定是極好的意思。
青年名作勞埃德,威爾斯人,是皇家郵政某個子公司的約聘員工,被分配到東英格蘭人力不足的分部支援,因此才搬來了這個小鎮。異鄉人的孤獨感讓兩人一拍即合,他倆無話不談,而勞埃德每回品嚐她新作時、臉上從不掩飾的滿足,就像維多利亞海綿蛋糕[25]裡頭那層畫龍點睛的草莓醬,輕易填滿她的心。
勞埃德家境貧困,讓他讀完高中、能找到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已是父母能給他最大的支持,可那無法澆熄他對浪漫主義的熱情,不同於某些半吊子知識份子的傲慢,儘管他在言談中總會引用幾句詩文,卻不教人討厭,好像他是真正用他所知最好的方式、傾盡全力表達。
青春期的少女在暗喜及困惑之間擺盪,因為她知曉那些讓在她心上萌發了什麼,卻無從得知那些是與她相同的東西,抑或是她自我意識過剩的錯覺。
有人說曖昧是一段關係最好的時刻,像是發酵時間恰好的麵包,因為來得太快的成果食之無味,可熟成太久又容易發餿(went sour)。瑪莉不知那用在他倆身上是否合理,可她想像過跟勞埃德的無數未來,而在他終於牽起她的手時,她曾理所當然地想,他會一直牽著自己走過長長的紅毯。
可事實是,他帶她走過田野、山嶺和湖畔,唯獨沒有那條通往家的道路。
不知打何時開始,勞埃德會以一種像是被打擾了的表情婉拒她難得主動的親暱,他不再把她攬入懷裡閱讀濟慈[26]、拜倫[27],或是雪萊[28],言談裡不再有無盡的愛,當他望向她時,眼裡笑裡不再有來自西南方海岸線的明朗;因此,當不諳文學的她在山澗終於讀懂那句「青春的願望都實現了,那些願望因深思熟慮的選擇而成熟,我這個山谷的囚犯,怎能不慶幸呢[29]」,滿膛都是想要向世界傾訴的喜悅,卻在他面前無語凝噎,連帶腳下的溪水都忽地冷得讓人發顫。
當時我們窮困潦倒、前途未卜,但深愛彼此,我以為這就是我們所需的一切了。
直白地說,那是我們僅有的一切,因此後來他並非有意隱瞞,因為它(愛)確實消失了。
We were poor but in love. I thought that's the only thing we needed.
Frankly speaking, that's merely we had. That's why, he ended up not hiding. It was just gone.
有人說,所有愛的開始都是相似的,瑪莉曾拼了命想找出這話的下半句,想知道她們之間「出了什麼錯」,有無任何修補的可能——可壞掉的派就是壞了,作為一個甜點師,她可以面不改色地將那些狼藉盡數丟進垃圾袋,但作為一個人,她花了很多年才把這段壞掉的感情放下。
她們沒有惡言相向,只是漸行漸遠,像是一者加入泡打粉、另一方則加入了杏仁粉,送入烤箱後,自然而然成為兩種不同的甜點,無論他們原始是否用了相同的麵糊[30]。店主夫婦隱約察覺到她們之間有什麼變了,善解人意地沒有多提,徒增感傷。可即便失去了在麵包店工作的最大意義,瑪莉仍在那兒工作多年,青澀的面龐淬煉成比同齡女孩穩重的模樣,而當她挽起袖子揉搓麵糰時,灰眼珠裡的專心致志,是她最迷人的時候。
後來,在三十歲的臨門一腳,勞埃德跟鎮上的女孩步入了禮堂。
兩人依舊是朋友,瑪莉沒有推辭,為他們製作了當地人從未見過的精緻婚禮蛋糕。她不會翻糖,那時代的電冰箱也還不普及,她整夜無眠,用糖霜和奶油擠出一朵朵黃水仙及玫瑰,襯得雪白底色像是花嫁的裙擺,上頭開出一片美不勝收的花田。
勞埃德看見成品時,眼眶立時紅了。他沒有哽咽,著一身俊朗的西服,握住瑪莉的手,說這是他此生見過最美的蛋糕,甚至不用嚐上一口,他就能想像到它吃起來多美味。
這話沒有文人的修飾,質樸誠懇,讓她笑彎了眼睛。
不,她笑道,還是吃一口吧。
「只要一口你就能知道。」他倆相視而笑。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a0aCnVJql
#Side E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MaqARhVta
珊曼莎為亞瑟感到高興,不在於那些房產的價值,而是他比世間任何人都珍視逝者留下的一切,想必瑪莉姑姑也會同意這點。矛盾的是,正因如此,她無法由衷感到高興,到底這種獲得來自於失去,一如以前在醫院當志工時,她從沒完全理解對那些匹配到骨髓的罕病患者說出「恭喜」,是不是一件對的事。
過戶的文件流程繁冗,亞瑟那陣子很少回倫敦,兩人少有碰面的時候,在電話聯繫被視為緊急之中的緊急的時代,文字訊息的傳遞使人有時難能辨識出線路對頭的一方是否真如上頭雲淡風輕,她也怯於確認,怕將自身的惶惑投射在向來冷靜的亞瑟身上。恰逢超市百貨最忙碌的大節日,「正職員工無必要原因不可在平日晚上或週末排假」成了極佳的理由,讓她的惴惴不安隱沒於日常的磨耗中,直到葬禮當天的清晨才搭夜間巴士到諾丁罕,在瑪莉姑姑家倉促沖了個澡後,便在霧濛濛的晨色中隨亞瑟驅車前往墓園。
在安息禮拜時,教堂外就下起了雨。聽唰拉拉的聲響越來越大,讓珊曼莎不由得侷促起來,排隊在棺前獻花時頻頻看向窗子,好似如此就能讓烏雲散去。
天不從人願,例行流程結束後,他們隨抬棺的禮儀人員走到墓地,雨是小了點、始終沒停,天空滿是陰霾,隨時都會落下瓢潑大雨。果不其然,在墓前默哀時,天色一黑,雨點驟然大了起來,拿著傘的人也下意識縮起肩膀,聽牧師宣告今日就此結束,眾人紛紛加快腳步離開。
滂沱大雨將傘面打得砰砰作響,她淺底的瑪莉珍鞋被方才不留意揚起的水花浸得濕透,粘膩的水氣順著鞋襪從前掌逐漸暈染到後跟,像被惡作劇黏在背後甩不掉的便利貼,見其他賓客跑向停車場,她本也想隨之跑回教堂避雨、卻不自主地被亞瑟如故的步調引導,彷彿她也受制於那把傘下的空間。
她說不清這種模糊、窒息卻又綿密交纏的情緒是什麼,只是下意識不欲觸碰,像是吹熄蠟燭前的第三個願望,話說出口便臨夢碎。
將注意力放在半米內路面窟窿,珊曼莎第一時間沒聽清亞瑟說了什麼,只是按慣性抬頭看他,與之同時,將左腳重重踩入半個腳板大小的水坑。
「見鬼!」她低咒,濺起的泥水甚至沾上了長裙裙擺。氣急敗壞地將裙子撩到膝頭,她將多餘的布料沿腰際掐緊打了個結,確保不會輕易鬆開後,對這個緊急應變尚可接受的她復而望向他、語氣和緩幾分:「抱歉,你剛剛說了什麼?」
就見那雙素來冷靜的深灰色眼睛在雨裡毫無波瀾,小心謹慎又滿是鋒芒,彷彿隱於平靜水面之下的漩渦,但無論其下湧動的是什麼、都不比那個提問讓人心旌動盪——
「妳願意嫁給我嗎?」他道,順應珊曼莎的震驚停下了腳步,傘面體貼地朝她這一側傾斜。她可以輕易想見,只消這幾秒他背上的西裝布料大概已經濕透。
然而,亞瑟未因此動搖半分,面色無恙地凝神看她。說不上是因為緊張、或幾刻鐘前才完成的下葬儀式,向來帶笑的他面上沒有日常的溫煦微笑,假這種慎重其事表達出了所言非虛,他的的確確是在求婚。
兩人之中,總自嘲浪漫細胞不足的她儘管未曾期盼燭光晚餐、小提琴獨奏或玫瑰花束,但也從未預想到那個請求會發生於此情此景。
興許這不是最理想的景況,不過她無意也沒有理由拒絕,然而不知怎地,這種順理成章無端讓珊曼莎心慌,他很好、她也是,那能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珊曼莎低聲答應,聲音輕得像要被這場瓢潑大雨掩蓋,但那雙驟然被點亮的灰色眼睛,讓她心存的一絲僥倖瞬時徹底熄滅,像是還未點燃就被毫無聲息掐滅的煙頭。她被亞瑟鮮少顯露熱切情緒的目光灼傷,忍不住別開了眼,低頭偽作整理衣裙。
為何這明明是正確答案,卻讓她感覺是種錯誤呢?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7VRzcWyr9K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FyF3TNC3Q
待冬天一過,他們一道去選了婚戒,為婚禮的瑣碎事宜與花費發愁,周遭親屬都獻上了祝福,為這對愛情長跑恰恰十年的佳人欣喜不已,便是不婚主義的特瑞莎也早早丟了一張禮物清單給亞瑟,告訴他要什麼自己圈起來,省得她在辦公室裡燒腦時還得花心思維護親友關係。
珊曼莎感覺自己為這個等了半輩子,可當選定的婚禮日期節節逼近,她又莫名生出許多壓力——她是個超市店員,縱使還掛著會計的名頭和加給,小有存款,但作為一個妻子或未來的母親,這足夠嗎?
更應該問,她準備好了嗎?
還是應該問,都這麼多年了,如果不是現在、那什麼才是「最好的時機」呢?
有時想著想著,一夜就過了,她無端消瘦,朋友都以為她為要新成人婦興奮壞了,可她知道,興奮之下有著深淵。
枕邊人自然也留意到她的不自然,亞瑟益發寬容,無聲擔起更多的家務,時會安撫她緊張也沒關係,許多婚前憂鬱症的案例證明了那是人之常情,盡己所能用他的方式給予支持,可珊曼莎很難說清,那是否真讓她輕鬆了一些。還是說,這件事根本不可能讓她輕鬆?
有天,他在網路上看到二輪電影院的宣傳,是他倆都很喜歡的導演舊作,因此在一個珊曼莎難得有空的午後,他們一道去市區看了《愛在日落巴黎時》[31]。片裡主角多年後重逢的愛情依舊,璀璨如舊時的光輝,談吐有著時光淘洗後的瀟灑及成熟,有失落,亦有失而復得的暗喜,但在散場之際,他坐在位置上聽著片尾曲、等待演職員播畢時異常安靜,靜得像一片隨時會鳴起響雷的烏雲,讓隨女主角的自彈自唱不禁同男主角一樣笑起來的珊曼莎分外不解。
「那他『恰如其分』的妻子呢?」搭乘地鐵回程的路上,亞瑟總算主動打散了身上凝滯的情緒,話題來得沒頭沒尾,讓她愣了好一會兒,才回想起電影裡的橋段。
「所以你會結婚,是因為崇拜的男人都結婚了?」
「不是,那感覺比較像我心中有個完美的我,而我想變成那個樣子,就算可能需要壓抑真實的自我,我也想嘗試。很好玩,我當時覺得是誰並不重要,沒有人能成為你的一切,重要的是承諾和扛起責任。我的意思是,愛不就是尊重、信任和欣賞嗎?而我當時感覺到的正是這些。」[32]
——這是一種暗示嗎?
這念頭讓珊曼莎如鯁在喉,遲遲說不出一句聰明的回應,見她如此,亞瑟似乎理解成了別的意思——或許是讓他沉默許久的那層意思——沒有多說,視線落上玻璃窗的倒影。
她也望了過去,好像早有預料地,發現視線所及中沒有她。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rPsC77Zws
*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107CUMFgJ
後來發生的事,像一連串睡不安穩又醒不來的夢。
珊曼莎得知久未聯繫的青梅竹馬愛德華到倫敦洽公時,特意撥空跟對方約出來吃了飯。愛德華早先從街坊鄰居口中聽說她年中要結婚了,貼面禮時第一句話就是「恭喜」,見她面上一閃即逝的錯愕,驀然生出幾絲憫然,親暱地摟著她的肩坐了下來,借助酒精放大的感官敏感,傾聽她無從傾訴的徬徨不安。
月色迷人,他人的體溫在情感脆弱時分格外教人眷戀,愛德華細數的過往讓她懷念起年少無憂的自己,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如此,但她知道,她沒那麼醉,只是不想清醒,渴求自短暫的放縱得到那些無解的窒息感中一點喘息。
可當她真正清醒時,發現現實又變得更加窒息,而她已無法置身事外。
率先發現他們的情事的是愛德華的女友,在尖叫與謾罵聲後像一陣突來的雷陣雨消失了,愛德華看起來也沒有特別遺憾的樣子。然後,亞瑟也知道了,在她還來不及反應過來的時候,將好不容易排定的婚禮日程悉數取消,不在乎高額的違約金,也不在乎他人的耳語,將兩人之間的爛帳收拾得乾乾淨淨,像那句他曾告訴她的西班牙俚語「人間消失(desaparecer como fantasma)」。
亞瑟整整一個月沒有回到兩人的居所,對她的訊息與電話不聞不問,連帶特瑞莎也對他的近況三緘其口。在珊曼莎最後一次打給她時,特瑞莎語氣平靜中不掩不耐,盡可能禮貌措辭地說:「我接下來工作會很忙,如果沒有緊急情況,能不能不要再打過來了呢?」
而她們之間唯一的公約數,唯一可稱上緊急的,也只有那個人。珊曼莎百口莫辯,因為她的行為舉止在此之中,看來無疑是最不在乎的人。
最後,她終於找到空檔去了諾丁罕一趟,在那欉重新種下的大花耬斗菜前,找到了在除草的亞瑟。
不同於形容憔悴的她,他看起來變化不大,沒有為情所困的失意,也沒有見她就如被踩著尾巴的貓的劍拔弩張,深灰色的眼睛不悲不喜,好像他不在意,也好像他不再在意了。
那眼神看得珊曼莎心頭一空,鼻頭發酸,滿腹說詞僵在喉頭,像是一口濃痰,最終化成了一股沒有道理的委屈。
「我想知道,除了忠誠、責任心與尊重信賴那些狗屎之外,你當初和我求婚的原因還有什麼?愛呢?你有沒有愛過我?」說到這時,珊曼莎都能感知到自己的無理取鬧,倒映在那雙身灰色的眼珠裡像隔著一個世界,以致後半句聽來更似乞求,乞求對方拉住搖搖欲墜的自己——儘管彼此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有一點也好。」
亞瑟靜靜望她,本應為成年人體面的道別,此時卻像一種拒絕。
半晌,在她就要忍受不了這種靜默的時候,他總算開了口:「或許當時是有的。但是現在,我也不是那麼確定了。」
那句話那麼誠實、那麼冷靜、輕得毫無指向性,卻讓珊曼莎感覺,遠比這段時間遭逢的任何冷嘲熱諷都要令她痛苦。
她哭得不能自己,可這時,亞瑟還是上前給了她一個擁抱。
她知道,這一刻不再是患得患失的臆想,她是真的失去他了。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9XMYi6XiH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DFuMX2tLq
FIN.
[1] 柯林・馬嘉露(Colleen McCullough)《The Thorn Birds 刺鳥》,一九七七年。
[2] 神韻合唱團(The Verve)《Urban Hymns 人文頌歌》〈Bitter Sweet Symphony 悲喜交響曲〉,一九九七年。
[3] 李察·艾希克羅(Richard Paul Ashcroft),英國創作歌手,於一九八九年成立搖滾樂團神韻合唱團(The Verve),並擔任主唱。
[4] 邦妮·派克(Bonnie Elizabeth Parker)和克萊德·巴羅(Clyde Chestnut Barrow)是美國經濟大恐慌時期的「鴛鴦大盜」,於美國中部合夥搶劫銀行、小商店和郊區加油站,其犯罪事蹟吸引媒體和民眾廣泛關注。他們至少殺害九名警察,並被聯邦調查局列為「公敵(Public enemy)」。
[5] 巴瑞·曼尼洛(Barry Alan Pincus)《In the Swing of Christmas 在聖誕節的音樂中搖擺》〈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聖誕就在不遠處〉,二〇〇七年。
[6] 《Peter Pan & Wendy 小飛俠與溫蒂》是迪士尼的經典動畫長片,改編自蘇格蘭作家詹姆斯·馬修·巴利(Sir James Matthew Barrie, 1st Baronet)的小說《Peter Pan 彼得潘》。主角彼得潘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和其他孩子在夢幻島(Never Land)上對抗詹姆斯·巴塞洛繆·鐵鉤船長(Captain Hook)及海盜。
[7] 辛蒂・羅波(Cynthia Ann Stephanie "Cyndi" Lauper)《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只想玩樂》,一九八三年。
[8] 辛蒂・羅波(Cynthia Ann Stephanie "Cyndi" Lauper)《Time After Time 一次又一次》,一九八四年。
[9] 皇后樂團(Queen)《The Works 作品集》〈I Want to Break Free 我想要出逃〉,一九八四年。
[10] 新秩序樂團(New Order)是一九八〇年代的英國代表樂團之一,樂團曲風結合了後龐克與電子舞曲。
[11] 強納斯兄弟(Jonas Brothers)是美國男子演唱團體,由大哥凱文·強納斯(Paul Kevin Jonas, Jr.)、二哥喬·強納斯(Joseph Adam Jonas)以及弟弟尼克·強納斯(Nicholas Jerry "Nick" Jonas)所組成。
[12] 麥莉·希拉(Miley Ray Cyrus)是一名美國歌手、詞曲作家及演員,因主演迪士尼頻道電視連續劇《孟漢娜(Hannah Montana)》而成為了青少年偶像。
[13] 賈斯汀·德魯·比伯(Justin Drew Bieber)是一名加拿大創作歌手及詞曲作家。
[14] 一世代(One Direction)是一個英國-愛爾蘭男子音樂團體。
[15] 麥可・波頓(Michael Bolton)《The One Thing》〈Said I Loved You...But I Lied 說我愛你卻詞不達意〉,一九九三年。
[16] 威廉・華茲渥斯(William Wordsworth)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17] 瑪麗・安・蘭姆(Mary Ann Lamb)及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兄妹皆為英國散文作家,共著《Tales fro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而出名。因瑪麗精神疾病病發時刺殺了母親,姐弟終生相依為命。
[18] 法式鹹派(Quiche)又稱洛林鄉村鹹派、洛林鹹派,是以雞蛋揉合熟煮的碎肉、蔬菜或起司(牛奶或鮮奶油)等食材製成的糕點,為法國傳統爐烤佳餚。
[19] 糖漿餡餅(Treacle tart)是由油酥脆餅和糖漿製成的傳統英格蘭甜品。
[20] 聖誕樹幹蛋糕(Bûche de Noël)是法國聖誕節的甜點,作為聖誕大餐的最後一道食物,用以代替從前過冬至燃燒木柴的習俗。
[21] 蕾絲小脆餅(Brandy Snaps)是大英國協地區流行的傳統小吃或甜點食品,通常是將焦糖的脆餅捲成像雪茄的管狀,中間填入打發的香草(或白蘭地)鮮奶油,類似於義大利奶油甜餡煎餅卷(cannolu)。
[22] 百果餡餅(Mince pie)是英國的節日甜點,通常會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製作和食用,內餡由切丁的果乾、種子和各種香料混合而成。
[23] 法式千層酥(Mille-feuille)又稱拿破崙蛋糕,是一種來自法國起源,在英國、義大利及俄羅斯等地都流傳甚廣的多層次、發酥皮的蛋漿甜品。
[24] 多蘿西・華茲渥斯(Dorothy Mae Ann Wordsworth)是一名英國作家、詩人,也是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渥斯的妹妹。
[25] 維多利亞海綿蛋糕(Victoria sponge cake)又稱維多利亞三明治(Victoria sandwich),是一種將兩片海綿蛋糕中間夾著果醬和鮮奶油,上層灑滿糖霜的英國傳統甜點。
[26] 約翰・濟慈(John Keats),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27] 喬治・戈登・拜倫,第六代拜倫男爵(George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革命家。
[28] 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29] 多蘿西・華茲渥斯(Dorothy Mae Ann Wordsworth)《Grasmere - A Fragment 葛拉斯湖畔-片段》,年代不詳。原文全句:「My youthful wishes all fulfill'd, Wishes matured by thoughtful choice, I stood an Inmate of this vale How could I but rejoice?」
[30] 此指瑪德蓮蛋糕(Madeleine)與費南雪(financier),兩者差異最大的除了模具外,瑪德蓮的麵糊添加了全蛋和泡打粉,口感較蓬鬆;費南雪僅使用蛋白,並加入大量的杏仁粉,吃起來相對紮實、濕潤許多。
[31] 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Stuart Linklater)《Before Sunset 愛在日落巴黎時》,二〇〇四年。此片承接一九九五年電影《Before Sunrise愛在黎明破曉時》,下接二〇一三年電影《Before Midnight愛在午夜希臘時》,是「愛在三部曲(The Before Trilogy)」的第二部。
[32] 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Stuart Linklater)《Before Sunset 愛在日落巴黎時》,二〇〇四年。原文全段:「So you got married because men you admired were married?」「No, no, it...it's more like I have this...this idea of my best self! You know? And I wanted to pursue that...even if it might have been overriding my honest self!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 mean, it's funny like...in the moment I remember thinking that it didn't much matter the "Who?" of it all...I mean that…that nobody is gonna be everything to you...and that ultimately it's just a simple action of committing yourself, you know meeting your responsibilities that...that matters. I mean what is love, right, if it's not respect, trust, admiration…and I...I felt all those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