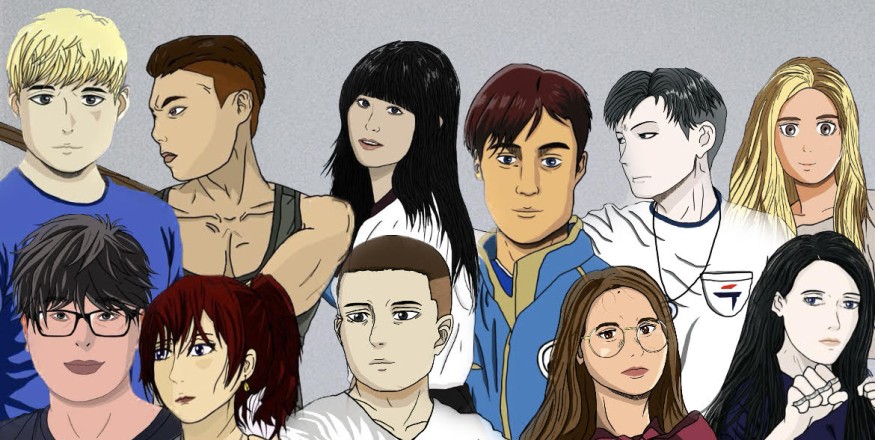x
x
唱詩過後,便是閱讀經文的時間。今天的主題經文篇幅不長,負責誦讀的弟兄輕鬆地唸了一章後,便將講台轉交給牧師,進入講道訓勉的環節。
仰臉一望,發現台上的講員不是誰人,正是堅叔,只見他今天穿了一套整齊的黑色西裝,配上藍色領帶和啡皮鞋,看起來十分大方醒目。
平日的堅叔親切近人,說話雖然充滿智慧,態度卻從來都謙虛平和,不擺架子,是個喜愛與年輕人打成一片、和藹可親的長輩。
然而,當他講道的時候,卻往往會搖身一變,成為一位字字鏗鏘、感染力十足的賢者牧師,說出的話彷彿一輪箭雨,叫你無處可逃,必須面對,每一箭都準確無誤地直入心坎。
此時堅叔正站在講台的中央,稍微調整了一下咪高鋒的角度,便聲如洪鐘地說︰「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佈道會,在座也有很多第一次參與我們崇拜的朋友,在此先歡迎你們的來臨,很高興與大家見面。我是教會的王牧師,大家平時亦會叫我堅叔。」
堅叔微笑著,環視了一下堂內的會眾,便繼續說下去︰「今天的講題叫作『鬼、詭、軌』。那究竟想表達的是什麼鬼呢?其實,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談鬼故,而是要跟你說上帝,講耶穌。在座各位,若是經歷過基督徒向你傳福音,你或會發現,他們老是會對你問及這幾道問題︰『你有沒有信仰?你信不信耶穌呀?你相信人有靈魂、世上有天堂和地獄嗎?』,而你往往會這樣回答他們︰『我信『瞓教』的,你不用跟我講耶穌,我不信這些東西。』。」
「哈哈……」台下傳來幾陣笑聲。
「那麼,什麼是信?怎樣才稱得上是有信心?信心可換作白飯來充飢麼?我告訴你,信心在歷史上成就過的,斷不只有餵飽別人,還有更多驚天動地的事情,但前題是,你所信的,究竟是什麼。」堅叔的話語響徹整個禮堂,如常般慷慨激昂,震撼著在座的每個人︰「所謂的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信心不是看見了才相信,而是未能看見而選擇相信。你或會說,那豈不就是迷信?其實不然。雖看不見,卻還是有跡可尋的。」
身旁的少女全神貫注地聆聽著,看她認真的樣子,似乎是個敬虔的信徒。
堅叔拿著遙控按鍵,身後銀幕中的投影片便跟著跳到下一頁,他托了托眼鏡框,又繼續說︰「因為魔鬼的真實,我們更可以肯定神是真實地存在。魔鬼撒旦並沒有被任何東西引誘犯罪,只因為驕傲,而自甘墮落成魔,而且不願悔改。只要人主動接觸靈界,魔鬼就可以借此機會纏擾他們。在香港,拜神、還神、求籤和燒衣等等的民間傳統,已是一種根深柢固的信仰文化,這或許只是由父母帶給下一代的習俗,但魔鬼最擅長引誘你的方式,正正就是威逼利誘,欺騙和恐嚇。我們在不經意之間,或許已落入了牠們的圈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見證,話說我在加拿大唸書的時候,曾經跟著一位教會牧師驅鬼。當時,有一位同學在寄宿學校裡嘗試與友人玩『碟仙』……」
我開始感到沉悶,聽不了下去,注意力不自覺地逐漸分散,魂遊太虛……
我不相信世上有鬼。
不過,靈界這回事,我的確有過類似的感受。
印象之中,我依稀記起自己每次危在旦夕,或是神智不清的時候,就會去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看見一些截然不同的景象,就像當日在又新街的情形一樣。
感覺不太像是夢境,而是自己的靈魂仿佛被抽了出來,穿越到了一個不同的空間,那時所見的場景極其真實,卻又與現實不太一樣,每每恢復精神後,就會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
那劇烈的痛楚,那突如其來的幻覺,以及那些黑色的嘔吐物……一切一切,都憑藉身體上不同的感官告訴我,所發生的並不只是幻想那麼簡單。
回想起上次來臨教會,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我在聽詩歌時突然嘔吐、情緒激動,繼而動武……
我還注意到,有一句話曾多次不由自主地自我口中吐出︰「沒有,不是我。」
我想要知道箇中的原因。
這時,我又瞧了瞧旁邊的少女,卻見她正忙著按手機,不禁暗忖︰看來不專心聽道的人,不只有我吧……
細看之下,原來她正在用手機中的備忘錄記下講道的內容。
我摸了摸鼻子,頓覺慚愧。
我們教會除了租借幼稚園和小學的場地外,還有一間位於私人屋苑「翠湖居」範圍內的地面店鋪作為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主要作為教會日常行政事務以及團契、小組聚會之用,地方不算很大,大概足夠容納五十多人。
早上的崇拜完結後,堅叔便著我先去吃飯,再邀請我前往教會辦公室與他見見面、聊聊天,想要了解一下我的近況。
我本想回家練功,但想到堅叔或許能把我的過去解釋給我聽,便立即答應了。
「叮叮——」小飾物在玻璃門推開時搖曳作響,我跟著堅叔踏入教會辦公室。
堅叔按下電掣,天花板上的光管遂一閃一閃的陸續亮起來,只見辦公室內空無一人,大廳右方靠牆之處擺放了一枱影印機,旁邊有個排滿靈修書籍的書櫃,書櫃邊緊貼著一枱電子琴,在琴的另一端還有個矮矮的雜物櫃。
轉臉再看大廳中央,分別有兩個工作間,工作間的屏風前座立了幾張方型摺桌;至於大廳的左方,一共有著六個房間,最近入口的那一間門外排列著兩排疊起的膠椅;廳中最末端的位置還有個開放式的廚房,作為茶水間飲食的用途。
「來。」堅叔打開第二個房間的房門,招呼我一同進去。房內佈局簡樸,只有一張書桌、兩座書櫃、一張電腦椅和摺椅。
我在摺椅上就坐,瞥見書桌面的玻璃墊下,全都是堅叔的家庭照,足見家庭的愛,就是他工作的動力。
堅叔啟動冷氣機後,便在桌前的電腦椅上坐下,轉過來面向我,微笑道︰「木框,最近好嗎?」
「不太好,堅叔。」我回應。
「傷口還痛?」堅叔望著我的左手,試著問。
我低頭看了看僅餘三指的左手,吃吃傻笑,心想自己幾乎早就把它忘掉了,遂曲起三指,握成拳頭,回望堅叔回答︰「不是,左手已經好多了,能夠使力,亦活動自如,不再痛了。」
堅叔點頭道︰「康復就好了。說實話,你現在看起來比以前精神多了,身體也似乎強壯了不少,是否已重新開始練功?」
我回應︰「對啊,有一位同門師兄,他每天都會來與我練習太極拳。」
「太極拳?你不是一直在學詠春拳的嗎?那豈不是個很大的新轉變?」堅叔一臉訝異地問道。
「也算是吧。可是遇到難題,只有勇於改變,才能有所突破。」我擺了擺左手,苦笑著說。
堅叔給予我一個肯定的笑容,對我豎起大姆指說︰「你說的沒錯。我很欣賞你這份堅持。這個才是我認識的木框。」
我找到了機會,馬上搶著問道︰「就是了,堅叔,這個就是我近來不太好的原因。」
「什麼原因?」堅叔一臉不解。
我決定向堅叔說出心中的苦惱︰「你認識我,這個沒錯。只是,我不太認識我自己。」
「何出此言?」堅叔翹起二郎腿,全神貫注地凝視著我。
「上次跟你談的那個雷成雨,你猜對了,不,應該說是你該一早便已知道,她是個女生,正確的名字叫作劉星雨,是劉安迪的妹妹。」我向堅叔說。
堅叔尷尬地點頭,似是為上次對我隱瞞而感到不好意思。
我續道︰「他們二人,我都見過面了,也是為了救他們的性命,我才失去了二指,但這些都不打緊。重要的是,我清楚自己喜歡的是劉星雨,也知道自己與她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只是我記不起來。也不知為何,十年前的記憶,我就是記不起來,好像一段空白了的時間。」
堅叔慨嘆一聲,搓揉著頭上的白髮,喃喃地說︰「那已是過去的事了,真想不到,如今你仍是念念不忘。」
聽他的語氣,似是想告訴我更多,我遂住口,不作任何回應,等待他繼續把話說完。
堅叔托了一托他那副已戴了十多年的銀色方框眼鏡,咳嗽幾聲,清清嗓子便說︰「本來我答應過星雨,不再提起此事。只是,這事情對你困擾甚大,更害你失去了二指,我就想,早晚也該與你談談這件事情。此人對你極其深刻,說著說著,你應該很快便會重拾一些印象了。」
我點頭,洗耳恭聽。11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fTeTtGx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