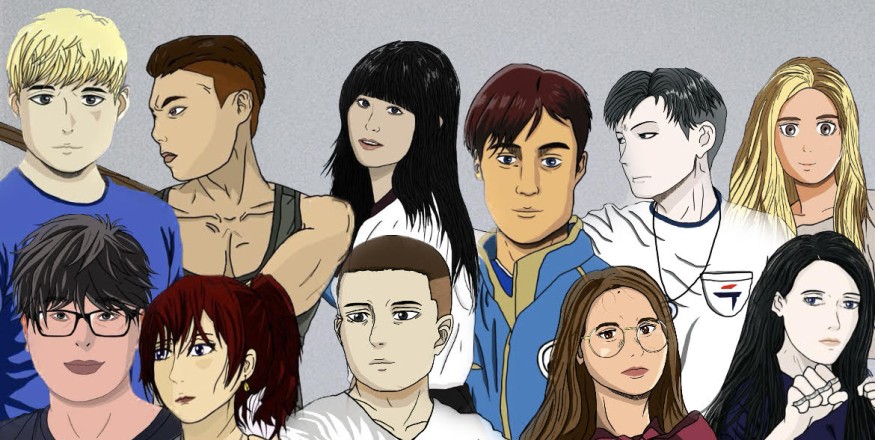x
x
夢醒時,只覺臉上有的是乾掉了的淚痕,我嘆了一口氣,輕輕地把它擦去。
早上十時正。
我從床上起來,快速前去洗手間刷牙、洗臉,然後小心翼翼地剃去下巴的鬍渣。
看著鏡中的自己,雖然頭上只有一堆蓬鬆的短髮,但我還是用髮泥把髮型稍作整理、加以固定,免得看起來像雜草一樣。
梳洗過後,我在廚房匆匆吃了一個麥皮饅頭和兩枚白烚雞蛋,便前往睡房換上一件白色的圓領衫,再披上天藍色的牛仔襯衫,下身則搭配灰黑色的扯布褲。
是時候出門了。
我在玄關處穿好皮靴,臨行之際,又返回睡房,在連身鏡前停了下來,檢視一番,自覺算是整潔,這才安心離開,在客廳中拿取車匙,準備出門起行。
離家時,兆川還在客廳中呼呼大睡,我也就不忘放輕一點地關上木門,一來生怕吵醒兆川,二來更怕兆川起來後苦纏著要跟來,徒添麻煩。
由流浮山駕駛前往荔枝角,大約需要半小時的車程,在早上這個時分,上班的人已經在工作,路上交通暢順。我聽著柔和的曲調,開著汽車,以時速八十公里默默地在公路行駛,背著在後似火的驕陽,朝著九龍方向逆風前進。
此刻一去,便再沒回頭的路。今天的我,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新出發、面對舊事,也就自當義無反顧,只盼能夠為十年前種下的情結,給予自己和別人一個交代。
沿路途經的元朗公路、青朗公路、汀九橋、和葵涌道等等,交通盡都順利無阻,似乎上天也在暗暗為我開出一條康莊大道,助我尋回十年前的故人。
看著擋風玻璃外的前路,知道自己正越來越接近荔枝角,心情便愈是緊張起來,右腳也不經意地踏深了油門少許,加速前行。
終於,全程也不過五首歌的時間,我已到達了荔枝角。
我把車子減速,跟著前車,沿著長沙灣道前駛,「爬格仔」結他店位處的香港工業中心就在眼前,但見一列汽車靠著工業大廈入口外的街道上停泊,我遂跟著大夥兒,把車子駛近停泊在後。
看看時間,十時四十五分,「爬格仔」將要開始營業。我遂熄匙下車,先去門店視察一下環境。
「爬格仔」就在這座工業大廈的十樓,根據他們的網站指引,前往門店可由荔枝角地鐵站C出口往左轉,從而進入B座大樓的入口,進入以後便是一條商店林立的長廊,一直前進,沿途便會遇見可以抵達十樓的升降機。
劉星雨或會駕駛七人車前來,亦不一定會乘坐地下鐵路,只是如今我泊車的地點,位處不但正對著工業中心的入口通道,更是極為接近荔枝角站的地面C出口,待會兒若是遲遲不見劉星雨的出現,想要返回車上歇息,也能繼續觀察一切進出大樓的面孔。
擁有相關工作經驗的我,只要保持集中,絕不會錯過劉星雨的現身。
我沿著工業中心的行車通道,邁進B座的入口,在窄窄的長廊中前行。長廊之中,兩旁盡是衣服時裝的批發商鋪,大多都剛剛開閘營業,尚未有客人來臨光顧。店主們一面把模特兒衣架和展示架擺放店外,一面互相閒聊說笑,看來都是熟悉已久的老朋友。
一路直行,途經不過只有六、七間店舖的距離,我很快便來到了升降機大堂。這座工業大廈有夠古老,至今也是沿用拉閘式的傳統貨用升降機,充滿了懷舊的感覺。
眼見最右側的升降機最先到達地面,我便踏進電梯,先把樓層的鐵閘拉上,再「卡」的一聲拉上升降機的鐵閘,並按下十樓的樓層按鈕。
升降機徐徐地爬升,我透過鐵閘的縫隙,呆呆地看著樓層的閘門一道接一道地往下掠過。
其實,阿祈並沒有說過她是甚麼時候向劉星雨介紹這間結他店的。
劉星雨很有可能早在幾天前已來訪過這裡。
因此,今天多半只是白走一趟而已……
只是,無論如何,今天我都會等到最後的一刻。
反正今天就是大特價的最後一日,換句話來說,這天以內的營業時間,很可能就是我遇上她最大的機會。
所以,我一定會等下去。
那怕是十年,抑或二十年的時間,我也願意等待她。
我凝視著剛剛落在面前的十樓閘門,堅決地點了點頭,伸手把兩道沉甸甸的閘門緩緩地敞開。
十樓跟地面的氣氛截然不同,大堂空空如也,左右兩方各有一條走廊,走廊盡是一間接一間的商戶或辦公室,全都一片死寂,閘門深鎖。
我看了看大堂的指示牌,依照方向踱步至右方的走廊盡頭,在「爬格仔」彩色字樣的醒目招牌下止步,終於順利抵達結他店的玻璃門前。
只見店舖門外已懸著「營業中」的掛牌,透過玻璃看進店內,發現這小店之中,空間雖是不大,但左右兩面的木板牆上卻掛滿了許多木結他,種類非常繁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有手工精細的,也有式樣新穎的,琳瑯滿目,叫人目不暇給。
店內一律以棕色的裝潢為主,胡桃木地板和店舖末端的紅磚牆相映成趣,突顯出一種古典與流行交融的視覺效果,磚牆之下和店鋪中央的位置還一共設有三張小沙發,可供來訪的客人安坐試彈結他。
一首英語的民謠曲調從店內的揚聲器悠然傳出,店中只有一人,似乎就是這裡的店主。
那是個短髮的青年男子,身穿一件印有結他圖樣和本店名號的黑色圓領衫,正於店內為每支結他逐一清潔。目前未有客人光顧,店主獨自一人,臉上掛著從容自在的神色,似是沉醉在音樂之中。
畢竟時間尚早,劉星雨未有現身也是意料中事。我遂於全層的走廊巡視了一周,發現除了此店以外,其他商戶盡都未有開門。靜謐之中,我百無聊賴地又回到了升降機大堂的中央,背靠牆壁,雙手抱胸,決心就此閉目靜候。
樓層走廊寂寥得很,空氣亦流通不足,我站著站著,不禁感覺昏昏欲睡,也不知過了多久,耳邊忽而傳來升降機閘門拉動的聲響……
我猛然睜眼一看,只見一名身材肥胖的女子剛從升降機中步出,正對著我投以懷疑的目光。
「呃……我在等人……」我試著向對方解釋,她聽後只是報以淺淺的微笑,便加快腳步邁進了左方的走廊之中,只聽得一陣急速開啟閘門的噪音,走廊馬上便又回復了寧靜。
若是我一直待在這兒,路過的人看見只會感覺十分奇怪……
當然,我不願將自己與劉星雨碰面的時刻弄得如此尷尬,但霎時又想不出走進結他店裡一直待著的借口,想著想著,轉眼又遲疑了大半小時,我終究還是決定折返地面,再作考慮。
自從今天起床後,我的心跳好像比起平日跳得特別快,腦袋中的思緒更是浮沈不息。
這種緊張的情緒,前所未有,強烈得叫人呼吸困難,感覺就像身處在火箭中的太空人一樣,正在等待發射升空,準備進入另一個世界,探索未知的領域。
十年間積累著的情緒,好像快要決堤。
等待甚是磨人。
「軋。」升降機停止垂降,回到了地面。
我打開閘門,但見人影晃動,原來地面樓層的人流已經增多了不少。
我頃刻全神投入高度的警覺,一眼關七,留意著所有與劉星雨相似的面貌和身影。
偶遇的機會只有一次,不容有失。
將近正午,工業中心開始出現不少前來閒逛的老人和婦人,我一面視察,一面步行重返大樓的入口,繼而在入口旁邊的一面易拉架前停下,嚴密注視每個進出的路人。
今天是星期二,進出的人比起假日自是少了,卻還是絡繹不絕,使我一刻都不敢鬆懈。擦身而過的人,男男女女,同行的不多,普遍是獨自前來,在這熱浪逼人的酷暑盛夏之中,皆是汗流如注。
一個大叔推著手推車「噹啷噹啷」的焦躁地從旁步至,險些輾過我的腳尖,我想要罵他,但此時不是分心的時候。
我繼續觀察著路人。
此時此刻,驀然讓我想到了當日在旺角等待黑火出現的情景。當時要找尋的是罪犯,不是意中人,心情自是跟現在千差萬別,但心裡的緊張卻是跟現在的有點相似。
我真奇怪,對於愛恨的情感,自問竟是不相伯仲的看重……
不知道黑火如今怎麼樣了。自從那天他跟我打了一場架後,一直銷聲匿跡,社會中亦再也沒有流傳關於他們作案的新聞。
莫非他真的成功當上了元朗的「金龍」話事人,作風因此轉至低調?
抑或他早已被捕?
罷了,與我無關。
無論如何,反正如今我已不再對他有恨,他只不過是個腦袋有問題的青年,犯案的人,就留給查案的人吧。
至於蚩尤……
不,不應再想這些事情。
無數條身影在我眼簾下晃動而過,卻沒有半個像是劉星雨。等著等著,不經意的便過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看看手機,現已一時許。
「咕嚕……」肚子開始打起鼓來。
好了,現在是「爬格仔」店主的午膳時間,門店將會暫時閉門休息,相信劉星雨也不會在這時到來,我一於趁這空檔,去附近找點吃的填飽肚皮。
我便起行踱到工業中心對出的街道,在街角處往右拐,來到了通州西街之上。
我在一間麵包店快快地買了一個咸餐包、一盒牛奶,便急步回去自己的車子,拉門在客座位上就坐,一面聽電台,一面啃麵包,一面繼續觀望進出B座入口的人。
就是這樣,時針不經不覺地過了一圈又一圈,麵包早就在胃中消化淨盡,牛奶也喝得半滴不剩,時間很快已將近下午四時,而劉星雨卻仍是不見踪影。
這個時候正值學生下課,入口的人流亦見增多,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張臉逃得過我的眼目。
一則新聞此時正好從車內的電台播出,引起了我的注意︰「昨夜凌晨,香港新晉職業拳手潘梓誠在上環永和街與一名男子發生衝突,二人動武出手,潘梓誠最終被對方打傷頭部,當場失去意識,現正在東華醫院接受治療,其經理人及家人至今一直謝絕傳媒採訪,暫時未有進一步的消息,警方正在追查該名男子的下落……」
我不禁揚起眉頭︰潘梓誠在街頭被人擊倒?
我感到詫異,皆因這姓潘的是位香港近來頗有名氣的職業拳擊手,綽號「港魂」。他曾兩次奪下「世界拳擊理事會」[1]的洲際「輕蠅量級」[2]金腰帶,是個實力超群的年青拳手,我以往在網上直播之中看過他的拳賽,對於他的「勾拳」和「大擺拳」組合技術有著深刻的印象。
真想不到,他會敗在一場街頭毆鬥之中。與他對上的男子,竟然能把他打至重傷,也確是個不容小觑的強手。
忽然,一把尖銳的叫囂聲從後傳來︰「別跑!賊子!」
[1] 「世界拳擊理事會」︰世界性拳擊組織,總部位於墨西哥城,於1963年2月14日創立。
[2] 「輕蠅量級」︰拳擊比賽中的重量級別之一,規定拳手身體重量不得超過108磅(49公斤)。
ns 15.158.61.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