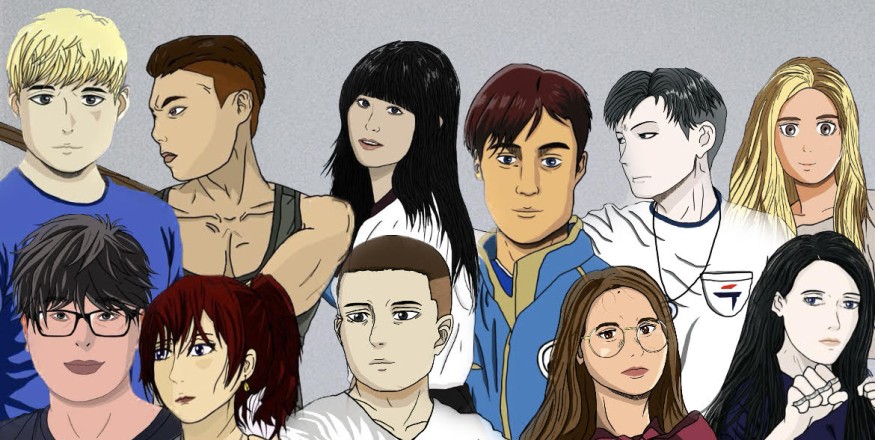x
x
晨光輕輕的灑落在我的臉上,帶著柔和的暖意,十分舒適。
當我睡得正甜,一位美女才剛在夢中出現的時候,耳邊突然聽到「砰」的一聲,把我直接召回現實。
我氣炸了,從沙發起來便大鬧︰「呀我頂你個……木框?」
眼前的是木框,他剛關好了房門,蹣跚地向著客廳前進,經過我身邊時,也沒看過我一眼。
木框看起來很虛弱,整個人消瘦了許多,身上還是穿著當天出院的衣服,披著的仍是那件棕色的皮夾克,然而皮夾克比起昔日破爛得更為嚴重。更讓人擔心的是,他的頭髮和鬍子,甚至連指甲都長了許多,加上身上的一股臭味,實在與街上的丐幫無異。
我忍不住,試著喚他︰「喂,兄弟。」
木框聽到,卻沒有理會我,也沒有停步,繼續前行,緩緩的進入了洗手間。也好,至少這對我的態度如常一樣。
我跟著他,在洗手間門外看他,他正在小便,也沒有關門。
匆匆解決後,他甚至沒有洗手,也沒有沖廁,便轉身返回客廳。
此刻的這個木框,彷彿一具失去靈魂的軀殼,一臉呆滯、雙目無神的他,跟平時那個我行我素、四處暴走、瘋瘋癲癲的木框,判若兩人。
木框步近廚房,用右手拈起廚櫃上的紅酒,遞到嘴邊,先用口咬掉酒瓶的木塞,才大口大口地把紅酒灌進嘴裡去。
我沒好氣地問道︰「你這幾個月以來究竟有沒有喝水、上廁所?」
木框充耳不聞,好像我沒有存在過一樣,他一口氣喝光了整瓶紅酒,便遺下空瓶,逕自前往鞋櫃,穿上鞋,推門,離家外出了。
回顧這段日子以來,今天應該是木框首次出門,看他現在的模樣,我只怕他連回家的路都忘記了,因此想了一想,還是決定跟著他。
木框的步履十分緩慢,好像老人家似的,一路上,我都保持著距離,難得他願意出街外走走,我也不想打擾他。
大概了花了七分鐘的時間,我們才步出了屋苑的正門,更亭外的保安員向我們說了一聲「早安」,但只有我禮貌地回應。
天時暑熱,烈日當空,木框低著頭,默默地望著自己的影子前行,朝著前往下白泥的單程行車路,徒步出發。
這路上盡是一片荒蕪。我一直尾隨著木框,經過了廢棄的倉庫、擱置的建築工地、破舊的教會,沿途都是渺無人煙,連經過的車輛也沒有。近來炎夏已到,天氣熱得很厲害,僅僅上星期三,天文台甚至錄得流浮山的最高氣溫為攝氏三十八度。
四處暑氣蒸騰,我這個大胖子,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實在不宜外出。剛才出門不久,我早已揮汗如雨,真是不明白木框怎能穿著皮革克,走了這麼遠的路。事實上,我猜他也沒料到天氣熱了這麼多,畢竟每天都只是困在房間裡。
一小時過去了,我倆在這條寂寞的深灣路上走著,大概也步行了將近兩公里。他真的行得超慢,我又餓又熱,著實快要暈倒了。現在如果有的士經過,我會毫不猶豫招手截停,然後上車叫司機慢慢尾隨這傢伙。
道路兩旁綠樹環繞,我們來到深圳灣大橋橋底的附近,有兩三隻流浪狗從左面的鐵皮屋旁的草叢那裡跑來,怒氣沖沖地向我們不住吠叫。我欲上前拉住木框,但他已毫無畏懼地繼續前行,在惡犬間直行直過,惡犬也沒有襲擊他,只是沒趣地垂著頭返回草叢去。我於是跟著木框繼續前進。
究竟木框想去那裡?如果是下白泥,不如駕車吧,坐的士也好。
半小時又過去了,放眼到處仍是一片荒涼,連人影也沒有半過。走著走著,我大感無聊,打了個呵欠,木框聽到後,突然停了下來,我馬上捂著嘴巴,跟著止步。
木框呆站原地,片刻後,便又再度起步前行。
他的腦袋裡是不是開始有毛病?
接下來是一條長長的直路,景色漸漸豁然開朗,右方的是一片野草,後方有著一條小村落;左方的是個大池塘,池塘之後是綠油油的山巒;伴隨而來的,左右兩旁的電線桿上還有鳥兒哼唱之聲,使我的心景逐漸回復舒暢平和。
回頭看,都走了這麼長的一段路了,無論如何,做兄弟的,就陪伴到底吧。
就這樣走下去,大約又過了四十五分鐘,我們到達了一個釣魚場。放眼遠處的魚池邊,有四、五個人正在釣魚,總算有人出沒。看見他們,又想起昨天在幸福山莊「吃放題」,饑餓感更是強烈。
我們走過了一條小橋,又經過田野、芭蕉樹叢,良久,前方的路開始漸轉為斜坡。我們沿路走上,雖是吃力,卻無減木框邁步的意欲,他依然低著頭靜靜的前行,只是把腳步放得更慢。
十多分鐘後,我倆終於登上了斜坡的頂點,此時右方的雜草林木已然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遼闊的後海灣。
海闊天空之下,長長的深圳灣大橋橫跨兩岸,風輕吹,天地間的雲霧也在徘徊不定。
走著走著,我和木框不一會兒便又走了兩公里左右,身邊的景物重複又重複,我身心俱疲,開始懷疑人生,想不通為什麼要受這些苦,是我太重,還是路太遠?靈魂的重量又是多少?大概比我的體重更嚴重,不然我的腦袋怎麼比雙腿還要難受。
忽然,木框停下來了。
他就呆站在路邊的石地之上,身旁是個被螥蠅圈轉環繞的垃圾站,傳出陣陣的惡臭。
只見木框凝視著前方不遠處的雜草和水窪,徐徐的仰臉遠眺,我遂循著他的視線望去,發現更遠之處便是下白泥。
他於是又再起步,向著下白泥前進。
ns 15.158.61.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