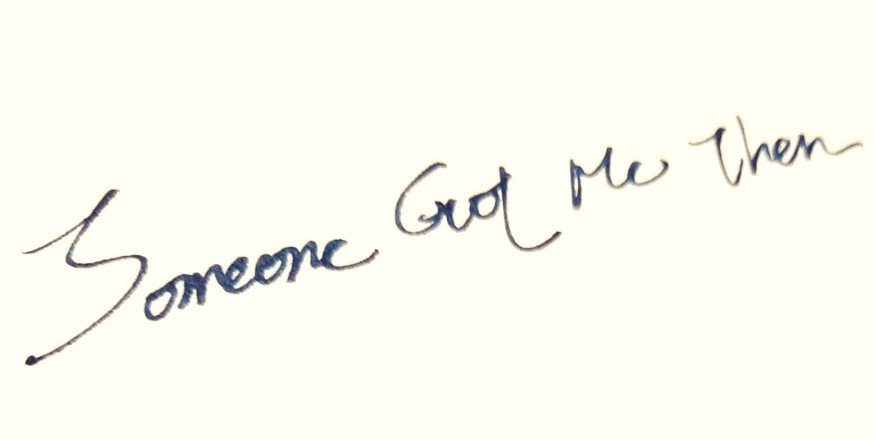|設定2020年8月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lBNSLIrHJ
|伊利安2022年生賀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rStno3lC4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0f8TJBUsx
伊利安很少提起自己的生日,因為聽者往往會戲劇性地驚訝道「哇,是獅子座呢」,又補上一句故作幽默或自作聰明的「和你好像不太像呢」。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對這種反應司空見慣,他總會腆著臉打哈哈揭過。大部分人會順水推舟隨他翻過這事,但也不乏欠缺場合感的人,煞有介事地比較獅子座公認特質與他的實質差異一番後,見他面色不虞才訕訕停下。
而在盛夏誕生,也注定他鮮少有機會與同儕共同慶賀。年輕學子的心與世界很小,恨不得用待辦清單將難得的暑期長假填滿,自然不可能在還未發育完全的大腦裡撥出一個空位,惦記班上某個素來低調的同學的生日。
卡莉娜是少數的例外,但這更可能因為伊利安是她最初的、也是一貫的例外。
聽他因疫情延後碩士學程第三學期的課程,決定要回老家待幾個月,當時在五金行值班的她一錘定音,說生日當天要同他聚一聚,讓他在電話另一頭哭笑不得地說:「行吧,我不迷信生日前不能慶祝那一套,但妳也知道拉耳朵、砸蛋糕有多煩人,別找太多人來。」
而在卡莉娜大笑著回答了「拉倒吧,你在這兒才沒有除了我之外會一起慶生的朋友」後,收銀機歡快地發出了響亮的「叮」聲。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xjrKnlZTa
伊利安如約而至,但在那天之前,他們已經在鎮上打過幾次照面了。
卡莉娜在後期中學後讀了護理專科,不過在實習過程中,她深感自己不適合這種面對大眾——尤其並不友善的那些——的工作,因此畢業後毅然回到老家,在鎮上的大型五金行從兼職做到正職,有時假日跟她開車行的遠房表哥學修車和掛雪鏈,生活步調不快,但恰恰適合這個城鎮。
好悠閒啊。這也是伊利安回到老家時,最直觀的感受。
熟絡於歐洲城市與莫斯科的步調,每次回到故鄉,他總會有種腳背上站著一個五歲大孩子的拖沓感,好似連全身肌肉都得鬆動幾分才能更好地融入其中,否則看來缺乏從容與明智,活脫是躁鬱症患者的初癥。
當然,快與慢是種相對概念,伊利安不知道當自己被問「你知道時間是什麼嗎」能否做出比發愣更直覺的反應,但在霍金的傳記電影中,男主角的搭訕語是少數他能自艱澀的物理理論中察知一點人文情懷的:「時間不是個普世皆同的定量。過去我們以為它是,以為它就是這麼存在的,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時間的流逝速度都是一樣快的,就像無限延伸的併行鐵軌。時間曾被認為是永恆的,但我們現在知道它不是,你得知道這有多重要,時間不能作為參照物,因為它不同於其他有固定參考值的東西,時間不是絕對的,它是動態的。⋯⋯沒錯,想像你向東方移動得非常、非常地快,比遠東還要遠,遠遠超出視野可及的範圍,而我留在原地,這樣你的時間相對於我而言,就變得很慢了。」
「所以當我跑得非常、非常快的時候,其實我的時間過得非常、非常慢。」明知毫無道理、他也對相對論一無所知,北國青年仍為片中女孩的回應感到浪漫得無以復加。
「你對這種事情⋯⋯嗯,怎麼說,一直都很天真呢。」即便卡莉娜不傾心於熱飲,還是熟練地沖了一杯熱茶給伊利安,得他一句「謝了」才轉而為自己倒了杯冰可樂,用玻璃吸管撥弄表面的冰塊。「我指好的那方面。」
「怎麼說?」特意將靠攏於餐桌的椅子提高後才拉出,伊利安隔著廚房的窗戶,忽地瞅見卡莉娜的母親在外頭向他們招手道別——雖然卡莉娜已經多次重申他倆「不是他們想的那種關係」,她母親每回見到他來訪依舊會展現出過度的熱情,朝兩人擠眉弄眼一番就找了個彆扭的理由出門,聲稱要給年輕人一些「私人空間」——而卡莉娜去年剛拿到駕照的弟弟滿臉木然、不耐地在車門旁拋接著車鑰匙,似乎在咕噥著「到底還要等多久」或「怎麼就不給我一點私人空間」,這一幕讓伊利安也不禁笑著擺擺手,直到見兩人吵嚷上了車才坐下。
「你媽真的很有趣。」他笑道,接過了那杯茶。
「是有趣,但有時也蠻煩人的。」見他的動作也能猜到什麼,卡莉娜不置可否地聳肩,橡樹色澤的微捲長髮隨意盤著,留幾縷不聽話的鬢髮散落肩窩。「後期中學畢業前⋯⋯嗯,我們不是發生了那些事嗎?那段時間鬧得很僵,我就連看到你都覺得很尷尬,更不用說要跟你說話。」
沒想到她會提起這段他倆避而不談多年的往事,伊利安一掃先前的閒適自若,如坐針氈地直起身子,像在草原上聽聞風吹草動的狐獴。
「那時候,我花了好久的時間,才慢慢瞭解到你不是為了拒絕我、所以才變成同性戀。當然,那也不是一種『選擇』,就像我們也不是選擇我們是誰,而是我們本來就是誰,而那也是你原本的樣子。而且,在這個國家也沒人想選擇變成同性戀吧?說這是選擇,好像把這當作一種錯誤,還要統統算在你頭上一樣。」卡莉娜做出一個「無意冒犯」的手勢,見他的肢體語言放鬆了點後,接著說:「當時我們都準備離開這裡,開始新的生活,你大可不告訴我真相;但你沒有,你反而做了一個相當危險的決定,那可能會毀掉你——我表哥知道了準會把你打得頭破血流——這決定很天真,也很珍貴。『誠實』才是你真正的選擇,伊留沙。」
她語末三個字的吐字很輕,讓伊利安極為觸動,千言萬語凝聚於湛藍眼珠的注視裡。
「卡莉,謝謝妳。」良久,他百端交集也只能吐出一句平常不過的感謝,自己都覺得貧瘠。「我對那件事⋯⋯不,我對那一切都感到很抱歉,就算是現在。我本來可以更早說清楚的,對不起,我希望妳知道。」
「我知道。但如果你再道歉,我就要扯些性別歧視的笑話讓大家都不痛快了。」卡莉娜撩起眼皮,被雙眼皮圍繞的深邃眼睛看來慵懶隨意,有意緩和逐漸變得凝重的氣氛,「說實話,我很感謝你。因為你讓我知道,喜歡這樣的一個人不是錯誤,因為你是個很好的人;但同樣地,不喜歡一個人也不是錯誤,因為那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例如,沒有能力。這影響了我看待事情的方式,也使我⋯⋯變得溫和很多吧?我覺得這是一件幸運的事。」
雖然這麼說好像很自戀。卡莉娜笑著,側脥的梨渦像是花期正好的毛蕊菊。
「幸運的是我。」這席話讓伊利安一顆懸著的心總算安放下來,也跟著她沒有原因地笑了起來。
卡莉娜是個很棒的交談對象,務實且對生活充滿熱忱,他捧著茶和她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了周遭的瑣事,兩人各自生活向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發生」,在另一方看來都有值得欣賞的部分。
「嘿,對了。」一段對話的間歇後,捧著冰塊與氣泡盡數消散的半杯糖水,卡莉娜似猛地想起什麼,提起了新話題:「我之前看到你IG上的照片了,他是你的理想型?」
她說起這話時沒有試探之意,彷彿早知有這麼一號人物存在,自然不過的態度讓伊利安愣了一愣,反倒產生了疑問。
「剛開始不完全是,但現在我想不到他還應該需要是什麼樣子了。」他猶疑補上了一句,「我們表現得很明顯嗎?呃、像是一對?」
「我認識的人在不同的社群網站上通常有不同面孔,但IG要比VKontakt(ВКонтакте)或臉書要清楚多了,咳,如果現在還有人在用臉書的話。」卡莉娜攤手道,隨後又回到自己最初的問題,「⋯⋯按你的說法,是他真的這麼完美,還是你有顆戀愛腦?」
乍聽這問題就不自覺揚起笑,青年侃侃而談,斂著眉目的神情和緩,狀似分享著一天發生的趣事:「我不會用『完美』形容他,他自己大概也會說『差得遠了』⋯⋯怎麼說?他有時很固執,但在多數時間好像又什麼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像永遠不會生氣或失控;他也很注意細節,時時刻刻關注著其他人的情緒起伏,卻對自己真正的心情一知半解;當你以為他很傲慢的時候,他又會冷不防露出脆弱的一面、說他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
「你說的⋯⋯」聽這敘述,卡莉娜的表情不覺變得僵硬,像是在克制自己不要說得過於直接,「不就像是總對你愛理不理、偶爾卻會在路邊攤出肚皮的野貓嗎?」
這使伊利安放聲大笑,在道別前將這段話轉述為文字訊息發給遠在倫敦的戀人。
坐了一個下午,伊利安巧妙地迴避卡莉娜家人的返家時間,在用餐時間前以一句「作客好,但在家更好(В гостях хорошо, а дома лучше)」的笑語辭別。知道他苦於婉拒難纏的用餐邀約,卡莉娜沒多做挽留,只在臨行前請他如傳統在玄關坐一會兒,然後從冰箱裡拿出比兩個巴掌大的蛋糕盒讓他捎上。
「是黑森林蛋糕,你可以窩在房間自己一個人吃掉。」卡莉娜說著說著就笑了,給他一個擁抱後便送他到門邊。「生日快樂,伊留沙,你值得這與比這更好的。」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pISrCMbGW
*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IlHJ3wnLJ
拎著朋友的心意,縱使不真心想要私自霸佔整個蛋糕——他可不打算為難自己的腸胃——一時想不到更適合分享的對象,因此他還是趨車到了祖父的小屋。
聽到闔上車門的聲響時,祖父就知道他來了,自房子邊上的雜物室出來迎接,小小的獨立建築裡多是用來置放他倆的木製品,質地包括但不限於西伯利亞松、雲杉、樺木和白楊樹等。
若要伊利安形容,那就是個私人的收藏館,也是他少年時期最安適的遊樂場。
這麼說興許將為人詬病「乖僻」、「疏離」、「不自知的孤傲」,但他必須坦承,年少時他不善與同儕相處,而後也成為不喜歡與同儕相處。這歸因於很多元素,他是獨生子,本更擅長與成年人溝通;他生性藴藉,情感要比得以傳達得要來得宏大澎湃,人們理解《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初戀》裡的愛而不得與絕望,卻無法同理他對於純粹愛意的嚮往,指稱那在以冰雪盛名的國度顯得情感用事,是種不諳世事的喪失份際⋯⋯但也或許,什麼都無需歸因,只是在他在家鄉時,很少感受到世界對他的憐憫與善意,在它把他形塑成那個樣子的時候。
因此,不輕易下定義、告訴他必須如何才是一個「被期望的孩子」的祖父,是他的避風港——小鎮位於內陸,直到十歲出頭前往聖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遊覽時,他才理解那究竟為何意,為什麼在那麼多語言與文化裡,都將港口與海灣視為一種安全的象徵。
海洋一望無際的廣袤、滋潤土壤的水氣,與離岸不遠的瞭望塔令他著迷不已,港口城市既寬大又包容,他曾經以為自己很快會再次回到這、重回大海的懷抱,不料大學卻更往南行,朝以強硬手腕聞名國際的克林姆林宮前行。不是抱怨的意思,因為他確實從首都的學府斬獲頗豐,而阿納托利整個人要比整片海天還要自由,也用自身寬厚的靈魂、祝福了伊利安的自由,後見之明,擁有一位摯友無疑是他這一遭最大的寶藏。
「伊留沙,你想把它切一切嗎?我剛煮了一壺紅茶。」見他手上的提盒,祖父善解人意地問,沒徒生「壽星自己帶蛋糕也太寒澹」的無謂寒暄。「或者當飯後茶的甜點?」
「晚餐後吃吧。」伊利安想了想,和祖父齊步走向主屋,提議道,「茶也不用加糖了,剛好。」
「在茶裡加糖是你們這些年輕人的喜好。」
「咬一口糖喝一口茶的舊習也稱不上是健康的美德,爺爺。」
進屋整頓後,爺孫倆看了一下午的國家地理頻道,那是伊利安在這段漫長暑假裡的新消遣。說來寂寞,他發現當祖父開著電視時,時常不是真的在「看」電視,而是藉由音響的人聲消弭空蕩室內的寂寥,而他會一面聽著小螢幕的談話聲、一面彎著腰在矮桌上將撲克牌排成四列,做著看似枯燥乏味的計算遊戲,直到牌面剩下一張象徵結束的「3」。
伊利安不知祖父是何時、向何人學來這單人撲克玩法的,他同樣不知如何涉及這種無聲,僅能在一旁似個衛護者,陪看著主題為狩獵旅行或大地氣候的科普節目。剛開始實在很無聊,被科技時代慣養的他因資訊焦慮折磨得五分鐘便要拿出手機一回,不過兩三天,逐步熟悉旁白的美國口音,他也深陷其中,對一個研究古生物的環節著迷不已,與情人的對話裡不乏新知的影子。
「我這才知道,原來史前時代各時期的地層,絕大多數的命名都來自發現的地方。」四十五分鐘長的節目結束後,聽甜餅廣告的音樂聲,他低頭在一長串道賀的簡訊裡找出了放在心上的那個,斷斷續續地打字,「但這讓我覺得很奇怪,因為在那個時期,可能那個地方根本就不叫那個名字、也說不定根本不在那裡⋯⋯雖然我自然科學學得很爛,但板塊移動這點常識還是有的。」
將文字傳送出去時,祖父在三人沙發的另一側,氣定神閒地專注於手上的牌組,沒有出聲打破靜默;而他定定看著自己在手機螢幕上交疊的指頭,餐桌上的燭台點著幾根乳白色的尖竹蠟,光影隨燭芯棉線的織法、蠟油的流動與看不見但切實存在的氣流閃動,將他平素白潤的肌膚映成橘與灰。為這狀似暗喻、又似毫無意義的一幕怔了怔,他好一會兒才回過神,拿起遙控器把世界的喧嘩阻絕在一個按鍵之下。
後來一如其他普通的日子,他們簡單地用了晚餐,不夠特別,但也正是這種不特別讓伊利安分外心安。
將馬鈴薯泥和在濃湯裡像個挑食的孩子的口味,是在祖父小窩被允許的特權——他們有志一同沒把這件事告訴伊利安的父母——搭配夾著魚子醬、乾酪、酸奶油與火腿的麵包吃著,讓伊利安總算有比較明確「回家了」的實感,簡樸而情摯,好似情感都埋藏在高熱量的食物之下。
在北方駐軍時曾攝取過量的酊劑(настойка),除了無法推辭的宴客與聚會,祖父只會在深冬溫一點伏特加暖暖身子,因此在伊利安切下那個對兩人嫌大的蛋糕時,他也如先前承諾的那般,熱了下午煮的半壺茶。
許是預見那場景的尷尬,他倆沒有點蠟燭、沒有許願,也沒有唱生日快樂歌,僅互道了聲「慢用(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便各自吃掉了自己的那一份大得根本不像在慶祝生日的蛋糕,在寧靜的甜意裡彼此都鬆懈了幾分,沈浸於酒釀櫻桃奶油與茶水在口腔交織的豐富口感裡,鮮紅色的罐頭櫻桃在澄光照耀下,亮眼得就像聖誕樹頂端的五角星,比羅宋湯(суп)的色澤更明豔。
「伊留沙,生日快樂。」半晌,見伊利安準備起身拾起乾淨的盤面,祖父以眼神示意他別著急,厚實帶繭的手心捂上他的手背,在夏季裡暖烘烘的。「我覺得很⋯⋯遺憾,畢竟這疫情讓你無處可去、只能回家,但是這好像也是這幾年,你待在家最久的一次。這一個月多來,讓我感覺,好像又回到你十歲的時候。」
「⋯⋯對不起。」這開場白讓青年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只好先道歉。
「不用道歉,我年輕時最愛的人也不是我的爺爺,而我相信,他最愛的也不會是他的爺爺。」
伊利安沈默,彷彿待審的犯人等著祖父的後話。
「當然,你的孫子——我知道你會說那是不可能的,但假如呢?——最愛的也不會是你,就像他們總會到更大的城市,他們總會找到比你更愛的、最愛的人。」
「如果我說,」伊利安嚥了嚥口水,「我已經遇到了呢?我的最愛、我也想要成為他的摯愛的人。」
祖父兀自陷入無聲,思索片刻後揚起微笑,笑裡具有巨大的寬容,彷彿在車站向十七歲的他招手道別時驕傲又不捨,因時光與距離的侵蝕一點一點失去他。
「那很好。」沒有出言勸退年少缺乏承諾的愛意,祖父也無譏諷其為不知責任輕重的任性,淡淡對此作出個人的註解,「那麼你們可以在一起很久,很好。」
他、那個人也愛著你嗎?祖父問。
短暫躊躇後,伊利安緩緩點頭答道:「我認為是的。雖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好這樣的決心,但是我可以⋯⋯我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心。」
感覺?我在說什麼鬼話?話說出口他便開始懊悔,怕這聽來敷衍莽撞,侷促地、好似要彌補什麼般慌忙地問:「您會覺得我太草率了嗎?什麼都沒有,就想跟另一個人共度一生。」
「伊留沙,如果這樣不足夠,你認為兩個人一起生活、還需要什麼?」
「呃、錢?」
被他的耿直逗笑,祖父顴骨上的曬斑也因鬆弛的面部肌肉消減陽剛面容的侵略性,這段話比起評價,更似直指對他的寵愛:「挺務實的,你一直都是這麼認真地回應生活,神會眷顧你的。你知道,祂會無私地愛著我們。」
就算我讓祂失望了嗎?險些脫口而出,伊利安堪堪嚥下了話頭。基於對他的縱容,祖父已接受了他不為文本與常人眼光所容的性向——遠在他的父母之前——他無意挑戰神的榮光,也不想讓鑽牛角尖的自我審判迫使祖父選邊站,究竟這份愛的重量是如此深厚澄澈,他不願他愛的人承擔無理的內心拉扯。
他愛的人。這個詞以及背後衍生的意涵,讓他的心登時沉靜下來,像是夏季陣雨過後的空氣,先前的負罪感亦如一場忘得精光的夢,他只朦朧地感知它來過、卻無從證明之。
然後他想,神已經惠他良多,不應再向生命討要更多。他慶幸曾經相信的那些不是世界全貌,他不只是他以為會成為的樣子,他有愛與被愛的能力,而擁有他的愛的人們不會輕易揮霍他的真心。就像孩提時代聽成人的慰問之詞,一切都會在合適的時候以它們原始的樣貌回應他,凡事都會雨過天青、苦盡甘來(До свадьбы заживет)。
這樣就好,這已是現階段的最好。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oPwf2x26r
*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8V676597W
掛斷亞歷山德拉確認他在祖父家留宿的電話時,讓伊利安等了一天的人總算傳來音訊——這麼說有失公允,因為亞瑟凌晨時便捎來了一段祝福語,但按兩人長年的通話習慣,他總覺沒同對方說上話,這一天就不算完整。這讓什麼都看不慣的阿納托利聲稱他倆是「用網路線充當同一條臍帶的連體嬰」,得知這形容時,亞瑟先是挑起了眉,隨後看不出喜怒地以一句「親愛的,你的摯友不是個蠢人,但真要多讀點生物學」反唇相譏,讓伊利安對此哭笑不得。
憶起舊事的青年彎起眼角,不作他想地撥了個語音通話過去,對頭也如他想像的很快接起了電話。
「親愛的,下午⋯⋯你那裡已經是晚上了吧?晚上好,你現在在做什麼呢?」想起青年因疫情無法重返歐洲中部時區,亞瑟的話遛了個彎,在腦中迅速做個簡單的運算後接上話。
「躺在床上聽音樂,」聽筒對面背景沒有雜音,年長一方的聲線清晰,伊利安猜他應該在家,便歇下心漫談起來。生來清冷的音色因釋然而變得含糊,略帶黏糊的語調像是撒嬌, 讓話筒另一頭的人無聲勾起嘴角,聽他還沒有自覺地翻著手機的播放紀錄:「這首歌是什麼來著?噢,〈Coming Up Roses一切都會好轉的〉。」
「布萊克的歌?」
「布萊克是哪位(Black who)?」不假思索出口當即發現這話直白得近乎冒犯,心裡為此一緊,伊利安連忙補救性質地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說的是英國歌手嗎?」
亞瑟意義不明地低笑了幾聲,好整以暇答道:「是,他是個利物浦的歌手,但你的反應很正常,畢竟他的活躍時代在八零年代末期。那麽,年輕人,你的〈一切都會好轉的〉又來自於誰呢?」
「唔,是部叫做《Begin Again 曼哈頓練習曲(2014)》音樂電影裡頭的主演,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同時也是插曲的主唱。」
「我知道那部電影。巧合的是,她也是個英國人。」
「噢,原來,這也難怪。我記得她曾出演電影版《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與偏見(2005)》,但不記得男主角的名字了⋯⋯所有版本裡,我只記得柯林・佛斯(Collin Firth)飾演的達西先生(Mr. Darcy)。」
這應是出於偏好吧?亞瑟的聲音因刻意壓低而撩人,調笑之意也讓青年羞澀,頓時支吾起來,最後放棄似地坦白、小小地賭氣道:「對啦,我就是對這類型毫無招架之力,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再說下去就過了分際,得到肯定答案後亞瑟也沒揪著這不放,轉而問起他今天過得如何。
「都是那樣吧?跟家人朋友聚餐吃飯、頂多吃點蛋糕聊聊天,和平時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差不多。」只是這裡沒有你。有意識地收住話頭,伊利安無意將氣氛營造得煽情或凝重,兩者他都不善於應對,儘管距離他們邂逅已經整整四年。
然而,縱使沒有直言,與他聯想到了一塊的亞瑟也陷入短暫的沉默,似一個渺無聲息的嘆息,才接續說:「我記得聽音樂是你在就寢前的『小儀式』,你這是打算要睡了嗎?」
「嗯,爺爺說明天要早起去山裡的教堂望彌撒,天沒亮就得醒來準備了。但我現在好清醒⋯⋯」伊利安嚥了嚥口水,耳根隨後來說的話發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聽到你的聲音。」
這話成功取悅了遠洋電話另一頭的對象,聲調依舊沉穩,但從細微之處能聽出其中的愉悅之情,英倫男子如隨口一提地提議道,用詞不失調侃與寵溺之情:「那就是鄙人的責任了。既然是睡前時間,何不讀個短篇故事,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聽他一個同意的鼻音,亞瑟儼然像個深夜公路廣播的DJ,粗略介紹自己接下來要讀姜峯楠《Exhalation: Stories 呼吸》一書裡收錄的短篇小說——「真的很短,不到十頁。」他補述,似乎將青年的輕笑聲視為一種不以為然——〈What's Expected of Us 天註定〉。
「我最早是在《Nature 自然》上讀到這篇短文的。那時大概是金融海嘯發生前後,網路普及率在大多數國家都逐步提高⋯⋯喔,這麼說應該能引起共鳴:差不多是臉書開始在青少年之間變得流行的時候。」
伊利安覺得很神奇,在這個蘋果手機每年出新機就讓人等得心焦的時代,聽他這描述卻久得彷彿是上個世紀的事。不過仔細思量,那其實是自己不到一半人生之前發生的變故,明明在還需要在固定時間、坐在課室裡固定座位的年紀,他也曾聽說全球性的經濟崩盤,以及冰島後來藉火山爆發自嘲的那句「灰金如土(cash turned ash)」。
「說得多了。總之,我加入的一個科幻小說同好的論壇談到這故事,分享感想的網友讚不絕口,聲稱那故事的精采度不亞於讓羅伯特・海萊恩(Robert A. Heinlein)聲名大噪的〈Life-Line 生命線〉。因此,我請特瑞莎幫忙留意了那些二手實體書的門路,幸而她在那個圈子的同事靠著手腕弄來了一本——那時離初出版已經超過五年了,又是在學術期刊這種冷僻書目上刊載,若沒有特殊門路也只能向隅,等出版商重新輯錄成冊了。閱讀過後,我深深迷上了這作家,直到今日,他在其他著作裡提及的議題依舊會在我腦中浮現,我也希望你會喜歡這個故事。」
那我們就從這開始吧。有意為之,亞瑟放緩了讀速,盡可能將朗誦的內容唸得字字清晰,而伊利安則在他唸第一句「這是一篇警告訊息,請大家仔細閱讀」時,就發現這是個糟糕的睡前故事選擇,因為他的好奇心已經全被挑起、了無睡意。
後續也如亞瑟敘述得那般精彩,第二人稱的口吻使他置入其中,好似他也身在那個剛發行數百萬計的「預知器(Predictor)」的時空,一切充滿無限可能,但當你摁下那個預示幾秒後的自己的按鍵,又會發現未來只有一種可能。
「既然如此(未來無法改變),為什麼我還要傳(這篇警告訊息)?」許是因為斷句,讀到這裡的亞瑟頓了頓,隨後以詠嘆調道出結尾——
「因為我沒得選擇(Because I had no choice.)。」
被這句話的餘韻激起一身雞皮疙瘩,直到亞瑟停下閱讀喝了一口水後,伊利安都還未能從短故事營造出的、好似在幽谷裡吶喊的深遠與浩瀚感裡回神,就聽對頭的英倫腔喃喃自語:「⋯⋯睡著了嗎?」
「沒有。」背道而馳地因此整個人被喚醒,青年反射性回應後,忽然覺得這有點喜感,無法自持地笑了起來,連帶話音都因笑意而斷斷續續。「怎麼辦⋯⋯你說這、噗哧,你說這故事,不就讓人更清醒了嗎?」
你好爛,我整個晚上大概都睡不著了。伊利安動靜越來越大,在床上笑得渾身發抖,幾乎要用被褥把自己捲成一個新物種。
被年輕人毫無來由也毫無保留的大笑感染,話筒另一方的亞瑟也揚高了嘴角,自然地接過話荏,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那就達到我的目的了,繼續陪我到睡著吧,親愛的。」
「你還在工作吧,這樣好嗎?」
默認了他的猜測,亞瑟饒富興味地反問:「我以為,比起擔心打擾我的工作,你會先忿忿不平為什麼這時間我還在工作?」
伊利安遲疑一會兒後,不太確定地答道:「因為這是你自己安排的工作時間,如果我這麼問了,不就好像在否定你⋯⋯的判斷能力嗎?」
「我喜歡這個答案,非常。」
「原來是試探嗎?」
「不完全是,只是特瑞莎總會對我的生活步調提出『應該更有效率的規劃』的主張。」
「你是想變個法子說她有控制慾吧。」
亞瑟也笑了出聲,狡猾地以問題回應對方的問題:「難道她沒有嗎?」
「跟你談話太危險了,這是什麼MI6的審問技巧嗎?」感覺自己這個晚上笑點特別低,伊利安自顧自地笑起來,一邊又不好意思地將臉半埋入被窩,避免笑聲太大傳過去,不知悉悉簌簌的布料摩擦聲無異於欲蓋彌彰。
「只是利用一個普世價值——來自墜入愛河的戀人的盲目偏愛罷了。」亞瑟笑著說,「親愛的,我不否認我十分享受這種為我而生的不公義。」
或者說,特權?他沈吟道。
「說特權也沒有什麼不對?喜歡與被喜歡,本來就是種特別待遇吧。」伊利安模糊不清地說,隔著一層薄被的嗓音軟綿綿的,連帶那些話語聽來都藕斷絲連得旖旎,「就像木工,我可以在太陽下劈柴(batoning),用一個月的時間慢慢把木頭切成、刻成、鏤成、組成我希望它成為的樣子,因為我覺得那是有趣的,是我想要嘗試的,是我喜歡的⋯⋯同樣的道理,如果我覺得那東西沒意思,那它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也是嗎?」這話來得唐突,笑到還有點暈的伊利安好一會兒才意會過來,面色微熱,也敏感地察覺到了什麼。
「你是,你是我喜歡的一部分。」猶豫間,青年繼續道:「嘿,我感覺、你今天好像有點⋯⋯想要證明些什麼?呃,可能是我的錯覺吧,但你是不是想要我說什麼?」
亞瑟立時噤聲,經短暫的寂靜後,用一個吁嘆起頭,「可能是太久沒見到你,又想到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比較急躁了,就忍不住想要證明我是被你需要的。親愛的,聽來很愚蠢吧?」
「我覺得⋯⋯滿可愛的,雖然是有點蠢,但我說的不是手段——為什麼要證明你是被需要的?『我愛你』這件事,不就是一種自證嗎?」伊利安為自己的話口乾舌燥,靈光一閃:「等等,你是想聽到這句話,是嗎?」
本該為得逞感到心滿意足,但不榮譽的小心思被直白攤在陽光下,仍讓男人無法一如往常故作從容。
「是,而且我也想告訴你,我愛你。」亞瑟自我解嘲,「我也知道很傻,但我今天想說這句話的渴望遠遠要比『生日快樂』來得多。」
被這話的坦率梗住,伊利安只能暗道幸好不是面對面,否則他定是要為這無法遮掩的面熱被對方戲弄一番,悻悻然道:「我沒想到,你直接起來讓人這麼難以招架。」
「虛長這些歲數,也就是多了點厚臉皮的程度吧。」
「可能也沒那麼厚臉皮吧,」青年吞嚥口水的聲響意外地大,「你很膽小呢,就算被識破也沒有要求我再說一次。」
被反將一軍的亞瑟自嘲似地笑了幾聲,難得外放的情緒卻像是自喉頭一個字一個字摳出的乾澀,「是呢,我是個膽小的人,只能藉旁敲側擊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是也因為你的膽小,你才是你。我愛你,亞瑟・安斯提。」一如既往,年輕人的聲線彷彿冬林中醞釀的生機,在寒意裡有著從未蒙塵的真情,「我不喜歡過生日,而這也絕對不會是我度過最好的生日,但有一件事我和你有類似的看法:我想聽見這句話的渴望、遠遠要比『生日快樂』來得多。」
亞瑟怔愣片刻,在青年看不見的對頭,不可控地鬆開了深鎖的眉頭,報以笑容:「還請給我一個更正式嚴謹的表現機會。伊利安,我愛你,深深地愛著你。我不是個有儀式感的人,也從不明白為何人們要在這種讓母親受盡磨難的日子大張旗鼓⋯⋯但是現在,我開始覺得,你存在的每一天都值得慶賀,親愛的——我最親愛的。如你所言,因為喜歡,所以產生意義;而我想,這個世界、我的生活、我看這世界的方式,此時也因你產生某些意義。我喜歡那些,就算目前我尚未得知它們具體是『什麼』。」
「你這麽說,會讓我產生自己給你的生活帶來什麼『良好影響』的錯覺。」
「不需要。」意識到這話的斷裂感容易讓人心生怯意,亞瑟解釋道:「你不需要帶來『什麼』,因為你光是存在,就已經是『什麼』。我不是因為需要你而愛你,而是愛你,讓我需要你,也想要你需要我。」
所以,愛真是人最自私的產物啊。他感歎道。
「所以才是特權吧。」不如以往碰上負面意涵的字眼就易陷入不安,伊利安思忖後道:「我感覺你有點變了⋯⋯不是壞的那種意思,但你會使用『什麼』這樣模稜兩可的詞,讓我挺驚訝。」
「我是不喜歡含糊其辭,」亞瑟沉聲道,「但我更不想以那些不精確的辭藻籠統命名它。記得你提起的那些古地層命名方式嗎?老實說,以人類視角的命名方式是傲慢了點,那些『什麼』或許本就存在,只是在人類有限且混亂的語境裡,未能找出它們最真實的名諱。」
「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伊利安試圖用舉例跟上為這跳躍性的話題。
「我認同,或許印地安人多有同樣的感覺,明明他們就跟印度沒有半點關係。」順著他的話,亞瑟提起另一個地理大發現時期(Age of Discovery)的誤解,得來他深以為然的悶哼,不帶指向性地笑了一笑。「或許是因為『她』,我在年輕一點的時候,對定義與正名近乎偏執——現在可能你還能時不時見到這種執拗的小尾巴,若你見到,也請毫不憐惜地將它揪出來,我會感謝你的——認為事物都有它應該在的『位置』上,渾然不覺這種想法何等僵化,畢竟就連數學語言裡,都有無法在數軸上呈現的無理數,不是嗎?我被這種自以為是誤導多年,後來才慢慢發現,可能很多事情就是沒有原因、就是不需要為什麼,它們有好有壞,例如我和珊曼莎在一起的那幾年、例如她最後選擇離開我、例如我還是不想跟羅德有更多生活上的接觸⋯⋯這些難能定義的東西構成了這樣的我,當時遇見你的我,與現在因你而每天都有微小的改變的我。」
「親愛的,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有種強烈的預感,我們會一起找到答案。」對作風保守的他倆而言,這句話缺乏根據,相較於篤定、更像一種倔強與逆反心。
然而,亞瑟的語氣如此溫柔敦厚,像是黎明前夕的清晨薄霧,靜美得讓伊利安不忍推開。
一霎時,青年福至心靈地摸索到年少記憶的餘溫,那些本無關聯的事物在這一刻、似乎都連結了起來。
他嘴開了又闔,終將那些吉光片羽薈萃於一句欣然接受的「嗯」。
一切都會好的,連同他們還不知道名字是什麼的那些。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VWxGn7wGp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EACgSPHMv
FIN.
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q8ZzXFf1j
【註解/引用】
《Hawking 霍金傳(2004)》
“Time is not universal quantity. We used to think that it was, we used to think that it was just there, marching on at the same pace for everyone everywhere, like a railway track that stretches to infinity. Time was eternal. Now we know it isn't. You have to know this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Time is not background thing, it is not absolute, against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measured. It's dynamic.”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M9WxD53ph
“Dynamic?”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7abtd8lDQe
“Active.”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GRqgrGj14
“Active?”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2IwwZVR74
“Wonderful. If you were to travel east very very quickly...”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Bz01sFL7y
“Out of sight? The far east?”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wSl3mZMit
“The far far east.”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Y8ISvWf1i
“Completely out of sight?”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qBfnkSpTx
“Yes, completely out of sight. And I stay right here, your time will slow down relative to mine.”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Fz37i2K85
“Like I get really really slow?”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Iexwmcy8G
“If you went very very fast.”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IPWmzvCXG
“If I went very very fast? I get really really slow!”33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6hRTBM4xS
“Your time would, relative to mine.”